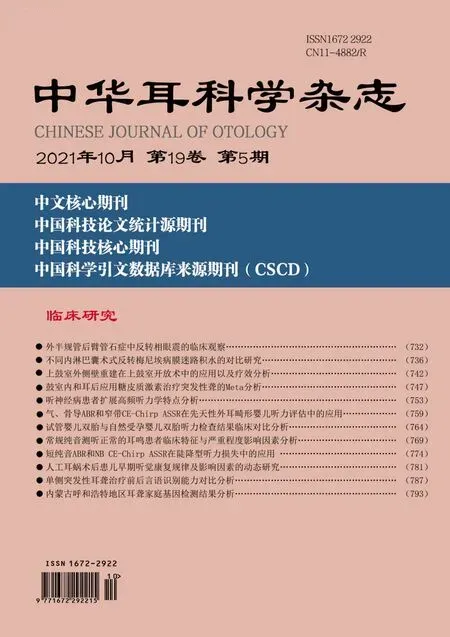單側突發性耳聾治療前后言語識別能力對比分析
陳琪鄭海峰諶國會夏紅艷王大勇張麗娜王秋菊趙立東*
1浙江中醫藥大學(杭州310053)
2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醫學部;國家耳鼻咽喉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解放軍耳鼻咽喉研究所;聾病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聾病防治北京市重點實驗室(北京100853)
3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耳鼻喉科(浙江溫州325015)
突發性耳聾(突聾)是指72h內突然發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至少在相鄰的兩個頻率聽力下降≥20dB HL[1]。美國和德國報道突聾發病率分別為5-27/10萬[2]至160-400/10萬[3]不等,多為單側發病。臨床表現主要為突發聽力下降,耳鳴、耳悶及眩暈等。目前,臨床上對突聾療效判定主要集中于純音聽閾的改善情況,對言語識別能力改善關注較少。然而,言語識別能力直接影響患者日常交流能力,其改善情況對突聾療效評估具有重要意義[4]。美國2019年指南提出:突聾者患病后初始聽力水平仍在可用范圍內,PTA提高>10dB或WRS提高≥10%為部分恢復[2,5],而國內對于治療后言語識別能力的改善關注較少,同時缺少該方面的文獻報道。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以WRSmax改善情況作為言語識別能力改善指標,分析ISSNHL患者治療后WRS改善情況及其影響因素,為進一步的療效評估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自2016年3月至2019年3月,于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治療的患者220例。納入標準:①72h內突然發生的聽力下降≥20dB HL,至少影響2個連續頻率的單側突發性耳聾;②感音神經性耳聾;③有治療前后完整純音測聽和言語識別率測試結果。排除標準:①其他形式的突然聽力下降,如分泌性中耳炎,Hunt綜合征等;②治療前言語識別率正常者;③無法良好配合言語識別率檢查的患者;④對側耳存在聽力異常者。
1.2 病例收集
收集滿足上述標準患者的信息,包括性別、年齡、病程(從發病到住院的時間)、合并癥(具有高血壓或糖尿病或高血脂癥)、發病誘因、伴隨癥狀(耳鳴、耳悶、眩暈以人數統計)、純音測聽和最大言語識別率。依據兒童型(0~18歲)、成年型(19~59歲)、老年型(≥60歲)對各年齡段進行劃分[6,7];依據病程≤1周,>1~≤2周,>2~≤4周,>4周對病程進行劃分[8]。
1.3 聽力學檢測方法
所有患者在治療前后于符合國家標準的隔聲室內,使用校準后的頭戴式氣導耳機TDH-39和B71骨導振子,由專業聽力技師使用校準后丹麥耳聽美Conera聽力計Otosuite進行PTA和WRSmax測試。WRS測試材料采用解放軍總醫院郗昕編制的《普通話言語測聽—單音節識別測試》詞表[9],測試詞表內置于Otosuite軟件中。根據WHO 1997聽力損失分級法計算純音平均聽閾,言語輸出聲強為患者測試耳純音平均聽閾閾上30dB SL,若患者反饋不舒適,則調整為閾上20dB SL,以獲得最大WRS,對無法達到純音平均聽閾閾上20dB SL者,以聽力計可達到的最大給聲強度為言語輸出聲強。計算正確字數占總字數百分比,即為WRSmax,本研究以WRSmax≥90%作為WRS正常的標準。
1.4 聽力損失程度和分型
PTA以氣導閾值計算,如未引出反應,以聽力計產生的最大聲強增加5dB計算[10]。根據《突發性聾診斷和治療指南(2015)》(指南)進行分型,考慮到平坦型和全聾型突發性聾分型里面存在相對更嚴重的低頻或者高頻聽力下降,故本研究采用250Hz、500Hz、1000Hz純 音 氣 導 平 均 聽 閾 與2000Hz、4000Hz、8000Hz純音氣導平均聽閾的差值是否大于15dB HL作為標準對聽力曲線進行劃分,當差值大于15dB HL且前者平均閾值大于后者時為上升型,當差值大于15dB HL且前者平均閾值小于后者時為下降型,當差值小于等于15dB HL時為平坦型[11]。低頻下降型和高頻下降型經計算分別都滿足上升型和下降型曲線的分型。對于低頻下降型及高頻下降型聽力損失按受損頻率平均值分級,對于全頻下降型聽力損失按WHO 1997標準進行聽力損失分級:26-40dB HL(輕度);41-60dB HL(中度);61-80dB HL(重度);>80dB HL(極重度)。
1.5 療效判定
初始聽力為此次發病于本院檢查的第一次聽力結果,終末聽力為療程結束后1月左右的聽力測試結果,包括PTA和WRS結果。以受損頻率聽閾改善情況判定PTA療效,以WRS改善情況判定WRS的療效。依據指南[1]療效分級,計算有效率。由于目前國內還未有評估ISSNHL療效的WRS具體指標,且國際上評估標準不一致,分別有將WRS提升20%[12]、25%[13]等作為改善指標的。鑒于中文測試詞表每張25詞,分制為百分制,即每個字代表4%,20%代表5個詞,易于計算。故采用WRS提升≥20%或WRS≥90%為治療有效標準。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資料采用±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資料采用中位數(25四分位數,75四分位數)表示,組內比較采用Willcoxon檢驗。非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資料采用Spearman秩相關分析。等級資料相關性分析采用Mantel-Haenszel卡方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P<0.05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情況統計
納入患者共220例,男性119例,女性101例,兒童型19例,成年型187例,老年型14例;左耳106例,右耳114例。病程≤1周48例,>1~≤2周42例,>2~≤4周53例,>4周77例;有合并癥28例,無合并癥192例;有誘因68例,無誘因152例。耳鳴181例,耳悶88例,眩暈90例。上升型23例,平坦型123例,下降型74例;輕中度43例,重度60例,極重度117例。詳見表2。
2.2 治療后純音聽閾、言語識別率的療效及兩者相關性
依據指南,本研究總有效率為43.2%。WRS療效為WRS提升≥20%或WRS≥90%,共79例,其中37例WRS恢復正常,總有效率為35.9%。治療前后PTA和WRS比較結果見表1。結果表明經治療PTA有顯著提升,WRS有顯著改善。相關性分析發現兩者存在顯著負相關r=-0.797,P<0.001,即治療后PTA越低,WRS越高。

表1 治療前后純音聽閾和言語識別率療效Table 1 Comparison of pure tone average and word recognition sco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2.3 言語識別率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對WRS各個影響因素,包括性別、耳別、年齡、病程、合并癥、發病誘因、伴隨癥狀(耳鳴、耳悶、眩暈)、聽力曲線、聽力損失程度,進行單因素分析,具體結果詳見表2。性別(χ2=2.207,P=0.137)、耳別(χ2=1.928,P=0.165)、年齡(χ2=0.645,P=0.724)、合并癥(χ2=0.001,P=0.982)、發病誘因(χ2=2.887,P=0.089),耳鳴(χ2=0.544,P=0.461)、耳悶(χ2=0.474,P=0.491)和眩暈(χ2=2.311,P=0.128)均非ISSNHL治療后WRS的影響因素,主要影響因素為病程(χ2=28.045,P<0.001)、聽力曲線類型(χ2=14.688,P=0.001)、聽力損失程度(χ2=10.289,P=0.006)。

表2 言語識別率療效影響因素單因素分析Table 2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rative effect of word recognition score
2.4 言語識別率療效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因變量為WRS療效,將病程、聽力曲線、聽力損失程度納入回歸模型(采用逐步進入法)。各變量均采用啞變量,對比方式為指示符,參考類別為第一個。Hosmer and Lemeshow 檢驗χ2=10.384,P=0.239(P>0.05,認為當前數據中的信息已被充分提取),說明模型擬合度較高。與病程≤1周相比,病程>1~≤2周療效與其無差異(P>0.05),病程>2~≤4周和病程>4周療效更差(P<0.05);與平坦型相比,上升型療效更佳(P<0.05),下降型療效與其無差異(P>0.05);與輕中度相比,重度療效與其無差異(P>0.05),極重度療效更差(P<0.05)。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相較治療前,治療后PTA和WRS均顯著改善(P<0.001),且兩者間存在顯著負相關r=-0.797,P<0.001,即治療后PTA恢復情況越好,WRS恢復也越好。純音測聽是測試聽敏度的、標準化的主觀行為測聽反應,具有良好頻率特異性。WRS測試可反應患者的聽力水平、聽覺傳導通路和聽覺中樞的功能狀態[14]。研究發現言語識別能力測試較純音測試更具敏感性,當聽力未發生顯著下降時,言語識別能力的下降可與內毛細胞或聽神經纖維損失相一致,只有當內毛細胞或聽神經纖維損失>80%才開始影響PTA,此時對言語識別已經產生嚴重的影響[15]。因此言語識別能力對反應聽覺通路的受損狀態具有重要意義,言語識別能力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應了聽覺通路功能的改善。
病程≤1周患者與病程>1~≤2周患者WRS療效無統計學差異,而病程>2~≤4周和病程>4周患者療效顯著差于病程≤1周患者,即WRS的恢復情況與發病到首次接受治療的時間間隔相關,時間越短療效越好。多項研究均表明,突聾患者治療時間越早,聽力改善情況效果越好[14,16]。聽力改善使得患者可接受更多聲音信號,有助于WRS改善。同時,發病后2周是療效出現顯著變化的時間點[14,17]。
本研究中聽力曲線為上升型、平坦型、下降型患者WRS有效率分別為69.57%、35.77%、25.68%,該結果與突聾多中心研究發現的低頻下降型(即上升型)預后最好一致[6]。回歸分析發現,聽力曲線為平坦型患者WRS療效與下降型患者無統計學差異,上升型患者療效顯著優于前兩者,這種療效差異可能與各曲線不同致病機制相關。上升型聽力曲線可能為膜迷路積水和螺旋韌帶局部供血障礙,造成組織缺氧損傷以及電解質內環境紊亂所致,大部分積水及堵塞為可逆病變,故預后良好;平坦型聽力曲線可能為內耳血管紋功能障礙和(或)耳蝸供血障礙以及組織缺氧所致,受影響面積更大,故預后較差;下降型聽力曲線可能為耳蝸基底轉受病毒感染導致基底轉Corti’s器和血管紋萎縮,聽神經纖維損失所致,主要影響毛細胞為不可逆病變,故預后更差[11,18]。
分析發現聽力損失輕中度者與重度者的WRS療效無統計學差異,但極重度者療效顯著差于輕中度者,風險是輕中度者2.908倍。言語信號處理需要頻域、時域、強度等信息,聽力損失程度直接影響聽覺中樞對信號的可聽度[19],即言語信號在傳遞過程中隨聽力損失增加而信息丟失增加,直接影響信號處理。因此,聽力損失程度重者的聽覺系統受損更嚴重,言語信息丟失更多,即使在治療后WRS恢復情況也較差。聽力損失輕中度者和重度者間療效無統計學差異,原因可能是聽力受損對重度者生活影響更大,故治療時間更早,而治療時間對WRS的療效有影響[20]。
言語識別測試對真實環境下個體交流情況的反應有重要意義,將PTA與WRS結合來評估ISSNHL療效能更全面反應患者恢復情況。本研究發現ISSNHL患者治療前病程、聽力曲線類型和聽力損失程度是治療后WRS療效的影響因素,為預估ISSNHL患者治療后WRS恢復情況提供參考。

表3 言語識別率療效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acy of speech recognition word recognition sc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