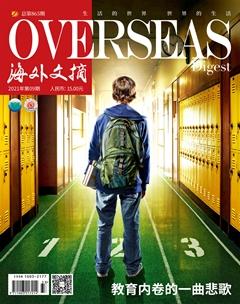走出去的印度
Kyle

| 投資亮點 |
一架嶄新的天橋立于贊比亞首都盧薩卡中部,橋上飄揚著印度的橙、白、綠三色國旗。遍布這座城市的,是由鋼鐵技術帝國塔塔集團旗下塔塔汽車生產的卡車,無論建造高樓還是收集垃圾,它們都能派上用場。車內引導司機的標識有英語和印地語,車上的人通過印度巴蒂電信公司運營的移動網絡相互撥打電話。
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公民,許多贊比亞人對印度公司的存在并不感到訝異。塔塔汽車在很多國家都設有大型裝配廠,比如南非和馬來西亞。巴蒂公司則是非洲最大的電信運營商之一。炭黑是汽車輪胎的一種原料,而埃迪亞貝拉集團正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炭黑生產商,也是印度最大的工業投資者和出口商之一。
即使在政府眼中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比如基礎設施建設和通訊,印度對外直接投資(FDI)也不會被認為懷有地緣政治陰謀或霸權野心。“這是印度的賣點之一。”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的加雷斯·普萊斯說。
過去,人們常常將印度這一擁有大量資本的新興市場力量比作中國。但今時不同往日,中國對外投資過去十年的激增讓這種比較不再經得起推敲。相比之下,印度FDI約占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總量的7%,有些乏善可陳,但對于不想承擔政治風險的外國投資者來說,它的做法值得借鑒。
| 投資全貌 |
長期以來,來自不同新興市場的企業一直投資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內行政拖延、市場混亂和融資約束等問題讓印度企業積攢了不少經驗,這對它們打入國際市場助益良多。1955年,印度還幫忙組織了商討“南南合作”的萬隆會議。
印度對發達國家的投資更有可能吸引眼球。塔塔集團收購泰特萊茶葉公司和捷豹路虎的一筆筆交易,不僅涉及家喻戶曉的品牌和數億美元的資金,還頗有些反帝國主義的意味。印度對貧窮國家的對外投資存量與它對富裕國家的大致相等,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直在穩步增長。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數據顯示,印度2019年的FDI達到約460億美元,高于2010年的約400億美元。其中,300億美元在亞洲,130億美元在非洲。
總部設在印度的跨國公司通常會在投資地設立子公司,并通過毛里求斯等避稅天堂運營資金。在印度出生或擁有印度國籍的1800萬海外印度人中,不乏更換了護照、在當地注冊公司的企業家。“如同一幅拼圖。”劍橋大學的賈伊·巴蒂亞如此形容。
| 每塊拼圖 |
印度大部分FDI源自私營企業,這些公司出于商業目的在海外開展業務。其中,肯尼亞的印度企業被當地人戲稱為“火箭”,因為它們只想火速撈完錢,然后回家。此外,還有總部設在印度的跨國投資者,以及世代在國外做生意,尤其是在非洲經商的印度移民家庭。
幾個世紀以前,印度商人就開始定居在印度洋邊緣地帶。19世紀,數千人被派往大英帝國的邊遠角落,在毛里求斯種植園工作,在肯尼亞修鐵路。許多人留了下來,開始自己做生意。其他身在印度的人則勇敢地乘坐單桅帆船,長途跋涉來到非洲加入他們。“我們習慣從歷史和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所以,印度做什么都繞不開中國這個話題。”國際問題專家帕拉戈·康納說。他的父親在非洲為塔塔集團工作。在他們眼中,19世紀90年代印度勞工在肯尼亞修建的鐵路被“馬達拉卡快線”取代,是中國在非洲崛起的標志。這條由中國承建的新鐵路以肯尼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紀念日“馬達拉卡節”命名。
散居在海外的印度人也曾遭到憤恨。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總統伊迪·阿明就曾將亞洲人趕出烏干達,還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但總體而言,共同經歷培養出了感情。肯尼亞政府甚至承認,亞洲人是其第44個官方部族。維姆·沙阿的祖父從印度移民而來,約35年前,沙阿和父親、兄弟共同創立了生產果汁和牛飼料的Bidco Africa。他知道內羅畢最地道的印度菜在哪里,還在耆那教徒社區當志愿者,但他自認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肯尼亞人,手里拿的也是肯尼亞護照。
印度獨立以后,國內的實業家們開始將目光投向國界以外。貝拉集團1959年在埃塞俄比亞設立的紡織廠是第一批境外印資企業之一。隨后,東南亞地區經濟體逐漸開放,貝拉集團在該地區擴張。第二次規模更大的對外投資潮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彼時印度政府放松了資本管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普雷瑪–錢德拉·阿圖科拉拉的數據顯示,2020年,印度企業在海外有4590個立項,遠超20年前的395個。
印度企業傾向于在投資地雇傭當地勞動力和購買當地設備。2006年,世界銀行調查了非洲近450家企業。世行發現,印資企業從印度引進的工人不到總人數的10%,從印度本土購入的設備,占比僅為22%。主持這項研究的經濟學家哈里·布羅德曼說,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現在。
這種情況可能與許多印度公司仍然是家族企業有關。外派高管們既要憂心創始人的聲譽,也會擔心自己的行為讓印度的形象受損。魯德拉普·邁特拉負責塔塔汽車的國際商用車業務。他談到了公司為海外市場發展作出的貢獻,包括想方設法將救護車與垃圾車分別送往斯里蘭卡和尼日利亞。“毋庸置疑,我們有責任為印度打廣告。”邁特拉說。
是生意所到之處方能插上三色旗,還是三色旗所在之處有生意可做?
一些人認為,印度FDI沒有充分發揮其海外移民的作用。首位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拒絕利用海外企業為外交政策服務,歷屆政府都在追隨他的腳步,對印度企業的海外發展充其量不過是提供有限的支持。外交官抱怨說,除了向所駐國政府獻殷勤、為來訪的印度企業家鋪設紅地毯外,其他的就愛莫能助了。馬努·坎達利亞90年前出生于肯尼亞,他的父母是古吉拉特人。如今,坎達利亞是非洲最知名的實業家,他非常惋惜印度政府沒有把海外印度人當成“工具”或“資源”。
| 生意與三色旗 |
印度前外交大使葛基特·辛格暗示,印度政府如果加大支持力度,削減本土企業在海外投資的成本,這些企業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根據美國進出口銀行的數據,2019年,印度官方提供了70億美元的中長期出口信貸。
獨立于政府為印資企業帶來了另一個優勢。自2010年收購科威特電信公司Zain在非洲的移動通信業務以來,巴蒂公司的戰略力量得以凸顯。但公司高層阿希爾·古普塔說,巴蒂“毫無疑問”會做非洲政府所要求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斷開通信網絡。古普塔還補充說,巴蒂的海外運營絕不會聽從印度政府的命令。
并非所有帶有印度血統的商人都堪稱祖國的代言人。莫罕達斯·甘地曾在南非做海事律師,給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古普塔三兄弟則不然,他們于上世紀90年代從印度北方邦遷居至南非,是2018年導致雅各布·祖馬下臺的腐敗丑聞的核心人物。在其他地方,韋丹塔資源公司與贊比亞政府就銅礦開采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印度政治中心新德里與商業中心孟買之間保持獨立,在太平盛世效果良好。然而,當印資企業海外業務一塌糊涂時,祖國印度的日子也不太好過;反之亦然,當印度的對外關系變得錯綜復雜時,投資者們會發現,海外的生意并無起色。“是生意所到之處方能插上三色旗,還是三色旗所在之處有生意可做?”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坦維·馬登說,“到最后你會發現,它們是相互交織的。”
[編譯自英國《經濟學人》]
編輯: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