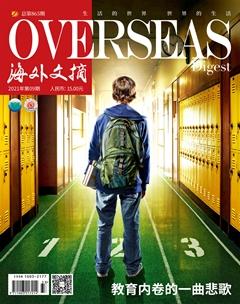“雞娃”之殤
約書亞·科爾曼 喬·平斯克 Kyle編譯

不計其數的課外活動、事無巨細的生活管理、充實卻受監督的休閑時間……這樣的育兒方式普遍存在于美國至少整整一代中產階級家庭中。研究人員用“精細”一詞來形容這種育兒方式。很難說它從什么時候開始成為了美國父母要求自己遵循的標準,但至少可以說,它的誕生正是因為貧富懸殊在這個時代愈演愈烈,經濟落后給孩子帶去的負面影響是幾代人以來最大的。
| 代價高昂的賭博 |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家長們迫于壓力,下了一個代價高昂的賭注:如果他們犧牲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友誼,把盡可能多的時間和資源投入在教養子女上,就有可能讓孩子成年之后擁有穩定的生活。這種賭博游戲有時會獲得回報,不過更多的情況是,孩子長大后不再那么需要父母了,這些全身心為孩子付出的家長們繼而發現自己陷入迷茫,不知所措。
前幾代人不需要為孩子的幸福和未來操心。上世紀60年代,我和我的兄弟們在俄亥俄州代頓市長大,父母從不記掛我們,我們也從不惦念他們,那是自由童年的黃金時代。我們每天盯著電視幾小時,吃的早餐含糖量驚人。每個夏天,我們總是在清晨就沒了蹤影,在午飯點騎車回家,之后又消失,直至薄暮時分才趕回去。我父母也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母親每周和牌友打一次麻將,每周末都和父親一起出去玩,但從不告訴我們那是“約會之夜”。父親每周末在市中心的基督教青年會打壁球。我們幾個是否會有被忽視的感覺?關于這點,他似乎并沒有心理負擔。
花費大量時間參加各項活動或與非家庭成員共度,對那個年代的家長來說不是一件稀罕事。社會學家保羅·阿馬托發現,相較于60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人而言,我父母那輩的夫婦,“朋友數量多出51%,與配偶共享社交圈的概率高出39%,所持各類休閑機構的會員身份多出168%,與配偶分享會員資格的可能性高出133%”。
| 家庭負擔日趨加重 |
我父母比他們之后的幾代人都輕松,因為他們是抱著孩子以后肯定會比自己過得好的心態來養兒育女的,正如他們上一輩人所做的那樣。“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等收入群體的年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而那些處于收入分配底層的人,收入增長得更多。”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瑪麗安·庫珀在其著作《漂泊無依:不穩定時代的家庭》中寫道。此外,“1965—1971年,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上大學的人數翻了一番”。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貧困問題,種族歧視依舊剝奪了許多人的發展機遇,但種族隔離現象在慢慢減少,收入分配也變得更加公平。在農業和靈活用工行業,雇主通常都會提供醫療保險,許多工作也有養老金保障。
然而到了70年代,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常態化,反共主義開始盛行,調整經濟結構的觀念占了上風,其中包括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場。在80年代,企業和政府都朝著終結社會契約的方向行進,而這些契約造福了嬰兒潮一代的父母輩。耶魯大學政治學者雅各布·哈克形容這種轉變是“巨大的風險轉移”,即經濟和健康風險“被政府和公司卸到勞工及其家人身上”。
舉例來說,1980—2004年,“常規養老福利覆蓋的勞工比例從60%跌至11%”,庫珀在書中寫道。企業提供的醫療保險對職工及其家屬的保護力度遠不如從前。相較于1975年,當下有孩子的美國中產階級夫婦平均每年多工作15周。
“每個家庭的經濟和情感負擔迅速增加,其增速在半個世紀以前還令人無法想象。”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家弗蘭克·弗斯滕伯格寫道。對經濟保障和社會競爭的焦慮,將美國父母推入了工作和育兒的狂潮,這迫使許多人為擠出更多時間監督和鞭策孩子,拋棄了友誼和休閑活動。
| 不平等時代的產物 |
“精細育兒”最初被視為一種中產階級現象。21世紀初,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里奧把這種育兒方式稱為“協作培養”,并將之與不需要父母過多參與的“放養”理念相比較。她發現,“放養”在工薪階層和貧窮家庭中更常見。貧窮不僅令父母無力支付孩子的興趣班費用,同時也是消耗他們精力、注意力和耐心的主要壓力來源,而這三者正是陪伴孩子所需的。

精細育兒。父母犧牲個人生活,把更多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在教養子女上。

巨嬰式育兒。孩子已經長大,但父母的育兒方式還停留在事無巨細、百依百順的嬰幼兒階段。
比較可信的是,擁有足夠財力的美國家庭最早施行“精細育兒”,接著所有人開始仿效。與其他文化變遷相仿,精英文化逐漸演變為大眾文化。
許多孩子受益于這種養育方式,它教會孩子如何做好時間管理、保持個性。然而,父母過多參與會剝奪孩子自力更生的意識,超負荷的課外安排也讓他們身心疲憊。同時,有證據顯示,父母過度“雞娃”將增加其孩子長大后罹患抑郁癥的風險,也更易讓他們對生活不滿。對父母而言,這樣的育兒理念可能會讓父母——尤其是母親——時時惶恐自己沒有盡力為孩子提供最好的未來。
“精細育兒”適用于不平等時代。經濟學家馬賽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齊奧·齊利博蒂解釋說,社會整體轉向這種養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不平等現象加劇的反應。在合著《愛、金錢和孩子》中,他們論證說,在社會高度不平等的國家比如美國,由于企業和政府做得太少,父母不得不竭盡全力去幫助和支持他們的孩子。這與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比如德國和瑞典,它們出臺了更多的家庭友好政策。
越多的課外補習和業余活動,意味著進入一所知名院校的幾率越大,從而可以保障孩子在未來獲得一份最優人才方能勝任的高薪工作,這是“精細育兒”的內在邏輯。然而,換個角度來說,如果我不用為優質幼兒園、初高中、大學的費用發愁;如果我確信我的孩子即使沒有大學學位也可以過得很好,因為他們獨立后,市面上有大量像樣的工作等著他們;如果我深知我不會因為孩子生病——更遑論我自己生病——而囊中羞澀,那我將更容易放松心情,和朋友外出游玩。
| 父母與子女漸行漸遠 |
根據一項研究,從1985到2004年,每個成年人與朋友、同事、鄰居維持的親密關系數量平均減少了1/3。與此同時,他們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迅速攀升。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1965到2011年間,已婚爸爸陪伴孩子的時間從每周2.6小時增至7.2小時,幾乎增加了兩倍;已婚媽媽的親子時光則從每周10.6小時增至14.3小時,增加了近1/3。在此期間,單身媽媽陪伴孩子的時間從1985年的每周5.8小時增至2011年的11.3小時,幾乎增加了一倍;而單身爸爸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則從每周不足1小時增加到約8小時。

掃雪機父母。他們像掃雪機一樣披荊斬棘,為孩子清除人生路上的一切障礙。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增加親子時光成為了一種趨勢,不僅流行于美國,也發生在其他富裕的西方國家。不過,許多國家出臺的社會政策,并不會迫使父母為了陪伴孩子而放棄自己的社交生活。根據布魯金斯學會2020年的一份報告,北歐國家和很多西歐國家通過立法或勞資談判縮短了工時標準。
盡管不計其數的研究證實了友誼對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然而美國家長在瀕臨崩潰時,往往最先犧牲友誼。前幾代父母從朋友、愛好和各類組織處收獲的生活意義與情感支持,到了當代父母這里,就指望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文化高級研究院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近3/4的學齡兒童家長希望自己能成為孩子成年之后最好的朋友。某種程度上,這一愿望正在變成現實。研究表明,與短短40年前相比,現在的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的接觸要頻繁、親密得多。
成為孩子好朋友的美好愿景蘊含著當代父母的內心訴求:父母在孩子身上傾注的所有愛和資源,孩子要以同樣親密無間的關系來回報。然而,這會帶來很多問題,在孩子遠離膝下時尤甚。我常常從成年子女口中聽到,他們希望自己的父母有界限感。
當孩子退縮、想要更多空間或者排斥父母時,那些為孩子犧牲友誼的父母可能會感到孤獨無依。在現實生活中,這有時會帶來嚴重的后果,早逝、癡呆、自殺、心臟病、抑郁癥往往都與孤獨感和社會孤立狀態脫不了干系。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說法,如今,近1/4的65歲及以上老年人處于社會孤立狀態,超過1/3的45歲及以上成年人感到孤獨。《我們從未如此:美國家庭與懷舊陷阱》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斯蒂芬妮·孔茨解釋道:“父母忽視自己的社交圈和其他成年人關系,將致使他們過度依賴孩子的支持和鼓勵,當孩子搬出去住,或者沒有照父母的意思對他們體貼入微時,他們很容易就會對外界失去興趣。”
| 幸福的鑰匙 |
美國父母與朋友疏遠有諸多原因,“精細育兒”只是其中一個。女性經濟角色轉變的同時,與工作、家庭生活相關的政策卻未能及時匹配。越來越多的家庭依賴于雙職工的收入,而工作以外的休閑活動,時間上不允許。當下美國父母的工作時間堪稱史上最長,工作強度也前所未有的大,但收獲的回報卻日益減少。鑒于以上殘酷事實,無怪乎現代家庭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發現,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其中22個成員國中,美國父母的幸福指數墊底。

直升機父母。他們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孩子上空,監督孩子的一舉一動,時刻準備挺身而出,解決孩子遇到的困難。
“童年已成為善良的最后堡壘,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可能收獲更多愛的最后一方凈土。”精神分析學家亞當·菲利普斯和歷史學家芭芭拉·泰勒在合著《論善良》中寫道,“事實上,這個社會愈發讓人難以相信善良的存在,而現代人對養兒育女如此癡迷,可能不外乎是執迷于社會中僅存的、來自天真孩童的那一點善良。”然而,過度依賴親子關系以滿足我們的情感和社會需求,對孩子不公,對父母有害。
許多國家通過社會政策維護公民的幸福感,讓他們放松心情,與孩子,也與自己的愛好、朋友共度歡樂時光。這是明智之舉,我們理應如此。
[編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編輯: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