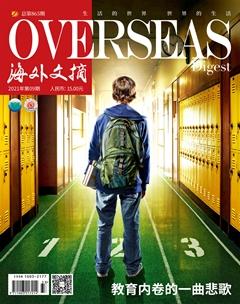教育內卷的一曲悲歌
凱特琳·弗拉納根 熊文苑編譯

| 天之驕子 |
道爾頓學校是曼哈頓最難進的私立學校之一,部分原因在于,這所學校知道一個重要問題的答案:對沖基金經理想要的是什么?
他們想要別人沒有的東西。在道爾頓,這意味著一名駐校考古學家、一間教學廚房、一處屋頂溫室,以及一座劇場。“接下來就是直升機機場了。”當地土地管理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說。這所學校最近剛進行了一次改造,將四座教學樓中的一座加高了兩層,為的是讓學生更好地提前適應“他們即將繼承的精彩世界”。
因此,當道爾頓年薪70萬美元的新校長吉姆·貝斯特告訴家長他們居然有一個得不到的東西時,他失策了。他說,學校今年秋季不會開設線下課堂。如果曼哈頓其他精英學校也不開課,道爾頓家長的反應可能還沒那么強烈,但三一學校、布里爾利女子中學、南丁格爾·班福德學校、查賓學校和斯賓塞學校都將繼續開課。
交著5.4萬美元學費的道爾頓家長,能眼睜睜看著自家孩子落后于同齡人嗎?更重要的是,他們會打開《紐約時報》,關注新冠疫情一個最殘酷的不平等之處嗎?——私立學校得以繼續開課,而公立學校被迫停課,那里的學生在電腦屏幕前百無聊賴地上著網課,無人關心。
私立學校家長有時會抱怨,他們納稅供養公立學校,卻得不到一點回報。但事實恰恰相反。公立學校家長有什么理由供養私立學校?埃克塞特私立中學在校學生只有1100人,卻坐擁13億美元資金;安多佛私立學校只有1150名學生,卻通過一項籌款活動獲得了4億美元。而這些巨款都是百分百免稅的。
在美國,上私立學校的學生不足2%,但耶魯大學2020年的新生中,有24%畢業于私立學校,普林斯頓大學的這一比例為25%,布朗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是29%。更夸張的是,這些名額并非平均分布在全國1600多所私立學校,而是集中在幾所精英學校:近五年來,道爾頓約1/3的畢業生進入了常春藤高校,斯賓塞學校也是一樣;哈佛西湖高中和格里諾貴族學校進入哈佛的學生則分別有45和50人。
在成為私立學校家長之前,我也曾經嘲笑過他們。但在當了七年私立學校老師后,我見識到了中學能夠達到的水平,并且下定決心,無論學費多高,都要讓我的孩子也接受這樣的教育。而從老師轉變為家長的身份后,我才真正意識到私立學校的“內卷”有多么夸張。
| 精英陷阱 |
心理學家邁克爾·湯普森2005年的著作《理解私立學校家長》讓我更清楚地了解到了私立學校的方方面面。湯普森到訪過800多所私立學校,在他看來,位高權重的家長們在氣勢洶洶地找五年級老師談話時,并沒有意識到這正是他們與手下員工溝通的方式。

湯普森在書中寫道:“私立學校家長與老師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學校行政人員和老師花費在應對家長的訴求和擔憂上的時間越來越多。”
16年過去,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了。為此,湯普森與另一位心理學家羅伯特·埃文斯共同撰寫了一本新書。埃文斯說:“過去幾年中的一大變化是,家長們再也不愿善罷甘休。多數時候,他們也不是無理取鬧,而只是不愿放棄努力。許多家長總是擔心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別人。”他們需要不斷得到安慰。
等到孩子上了高年級,家長們又希望老師、教練和升學顧問幫助自家孩子打造一份令哈佛無法拒絕的簡歷。埃文斯說:“這種家長已經想好了預期結果。在工作中,他們的確能取得這樣的成果,因為他們可以把任務安排給手下的員工。”在這些家長眼中,老師就是員工,但問題是,老師并不為他們工作。
為什么這些家長一直需要安慰?因為他們“發現讓自己的孩子過獨木橋——從幼兒園到大學一直上最好的學校——的難度越來越高”。更重要的是,家長們感覺到,與自己年輕時相比,孩子們將面對更加慘淡的世界。他們生活富足、養尊處優,不需要在贏者通吃的殘酷經濟環境中打拼,但他們害怕自己的孩子必須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即便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也未必能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
埃文斯說:“半數律師都認為自己的收入對不起當年的學費。”如今,進入頂級醫學院的難度令人咋舌:2018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稱,118所知名醫學院的平均錄取率是6.8%,而頂尖醫學院的錄取率僅有2.4%。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尼爾·馬克維茨提出“精英主義陷阱”的概念,意指這樣一種體系:社會上的富人越來越多,但贏家名額越來越少。馬克維茨寫道:“如今的精英依然聲稱他們的成就源于才能和努力,他們的方法適用于任何人。但實際上,現在的精英主義排斥所有小圈子以外的人。”這種體系踐踏窮人,抽干中產階級,讓富人家的孩子疲憊、焦慮、不堪重壓,堅信自己的前途取決于能否考上一所申請拒絕率高達90%的大學。
接診過許多這類孩子的一名兒科醫生告訴我,孩子們開始崩潰,家長則向醫生尋求促進學習的藥物和安眠藥。在意識到孩子成績不夠好后,許多家長咨詢朋友,拜訪教育心理學家,為孩子進行一系列檢測,而且總能查出一些問題來。如此,在醫生出示證明后,孩子就可以不限時地參加SAT和ACT考試。
然而,家長們從來不會覺得充滿高壓氣氛的學校本身才是癥結所在。他們認為,孩子必須行駛在正軌上:吃藥,通知老師記載自己患有疾病,然后把目標對準斯坦福。
| 瘋狂時刻 |
一所出類拔萃的私立學校往往擁有知名的學生家長,西德威爾友誼中學便是如此。這所坐落于華盛頓特區的貴格會學校擁有四位知名家長:克林頓夫婦和奧巴馬夫婦。
與其他貴格會學校一樣,西德威爾旨在幫助學生聆聽并回應上帝的圣音。但如今的西德威爾家長對大學招生的關注甚于貴格會本身。
“怎樣讓孩子上西德威爾?”這已經成為一個無解的問題。最佳策略可能是家長去競選美國總統,然后——如果競選成功的話——遞交入學申請表吧。
貴格會就像一道堤壩,保護其信徒免受金錢與權力的誘惑,但所有堤壩都有破防的時候。兩年前,西德威爾的家長們終于爆發了。在沉重的升學壓力之下,2019屆的部分學生家長發起了一場恐嚇、監視、跟蹤和破壞行動,并被媒體曝光。
時任西德威爾升學顧問辦公室主任的帕特里克·加拉格爾給家長寫郵件說:“請控制住自己。”根據加拉格爾制定的新政策,你大致可以猜出這些家長們都做過什么。新政策包括:不得使用匿名號碼打電話或寄匿名信,不得向升學顧問傳播關于其他學生的謠言,不得在與升學顧問交談期間私自錄音。

加拉格爾的郵件內容表明,為了提高自家孩子的升學幾率,家長們不惜阻撓其他學生的升學之路。這封郵件寫在寒假之前,意在讓家長周知,有人圖謀不軌,但學校已經采取對策,這些人不會得逞。但所有高年級學生的家長都驚恐萬分,擔心自己的孩子受到影響。
寒假結束后,西德威爾校長布萊恩·嘉曼向家長們寫了一封后續郵件,重申加拉格爾的政策。他還提醒家長,升學顧問“不會回復對別人家孩子分數的打探”。嘉曼說,家長們的行為“愈發囂張越界”,甚至包括“辱罵學校工作人員”。但學校會寬容以待,因為嘉曼承認,升學“會極大地考驗家長的耐心和情緒”。在該學年結束時,西德威爾的三名升學顧問中已有兩人辭職。
大學招生是富人少有的需要與他人爭奪資源的時刻。在收到大學拒信的恐懼面前,他們喪失了一切理智。
| 資本游戲 |
私立學校經常作出一些讓人無法理解的決策,家長們像原始人一樣試圖破解其中的奧秘。他們想,私立學校最看重的應該是大學錄取率?不對。或許是考試分數?體育成績?學校名譽?都不對。
答案是金錢。
私立學校沒有稅款、市政債券或額外撥款,學校的一切支出——綠植、電子白板、教學樓、足球、心理醫生、校內教堂——都來自自籌捐款。
學費可以涵蓋學校運行的部分經費,但依然不夠——反正學校對家長是這樣說的,而且總能用一張圓餅圖加以證明。無論位于何處的哪所學校,家長們有多么富裕,校方總在彌補“資金缺口”。我個人對此存疑,但這顯然是學校“年度贈予”籌款活動的最佳理由。新家長還沒從5萬美元的學費中回過神來,就發現原來還要出更多錢。私立學校的生計依賴于這些雙職工家長,他們特別在意孩子的教育,也有能力為此買單。
資金大頭往往來自學校大型項目的募款活動,這些活動的名稱往往都很可笑,比如“想象未來”和“等價交換”,而且一般會持續數年。在私立學校,所有學生家庭在學生讀書期間都會參與至少一項此類活動。
私立學校都接受哪些形式的捐款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它們不接受的。無論你的資產是什么,學校總有辦法將它們兌換成現金。斯賓塞學校明確表示,該校接受的捐款形式包括信用卡、支票甚至證券。你可以在遺囑中把錢留給學校,取出部分退休金捐給學校,把學校列為人身保險受益方,或者為學校設立慈善基金。
必須承認,在私立學校,金錢就是一切決策的出發點。湯普森說,私立學校在家長與學校的關系上投入越來越大,從籌款的角度來說,這對學校有利,但對教育而言,這未必是件好事。
多年來,許多學生都對我說,他們覺得,家長捐款多的孩子在學校受到的待遇與其他同學不一樣。他們說得沒錯。私立學校的捐款來自學校高層管理人員苦心經營的人際關系,因此,捐款者的孩子在學校得到優待合情合理,這也正是事實。

| 贏者通吃 |
去年秋天,我與普林斯頓大學2020屆的學生連姆·奧康納進行了交談。他從特拉華州的一個小鎮考入普林斯頓。他之所以選擇這所大學,是因為在他申請的所有學校中,普林斯頓學費最低,甚至比特拉華州立大學還低。
奧康納在中學時花了兩個暑假完成必修的體育課,這樣才能在學年中排進更多科學課。即便如此,他在進入普林斯頓后才發現,自己比來自私立學校和精英公立學校的學生差得多。
奧康納在《普林斯頓人日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討論這些學生在大學里的優勢。他寫道,美國大多數中學難度最高的數學課程是微積分,但“有錢的中學普遍開設多元微積分和線性代數,而這些通常是大二或者大三的課程”。安多佛中學等一些頂尖私立學校還開設有機化學。
私立學校的這些優勢不僅能幫助學生進入頂尖大學,更能讓他們在大學里如魚得水。近十年來,普林斯頓大學2/3的羅德學者是私立學校畢業生(國際學生除外)。著名的Sachs獎學金獲得者也有2/3來自私立學校,該獎學金為兩名即將畢業的學生提供出國工作、學習或旅行的機會。47%的“班級榮譽獎”(每個班級的學術獎項)獲得者來自私立學校。這就是富裕的家長將孩子進入正確的預科學校視為頭等大事的緣故——他們知道,贏家會一直贏下去。
家長急于知道哪些是頂尖高校的對口學校。升學顧問告訴家長,時代變了,現在沒有直升頂尖大學的中學了。但這句話其實有所保留。
善拓·揚在讀高三時,身邊考進頂尖大學的學長并不多,但他決定樹立高遠的目標,并最終上了哈佛。他認為應該揭開招生的神秘面紗,因此搜集了哈佛、普林斯頓和麻省理工這三所高校的生源信息。
揚將搜尋結果發布在了PolarisList網站上。在普林斯頓2015年至2018年畢業的學生中,絕大多數來自精英學校、富裕地區的公立學校以及著名的預科學校,它們是勞倫斯威爾學校、埃克塞特中學、德巴頓中學、安多佛學校、迪爾菲爾德學院等。在向普林斯頓輸送生源最多的25所中學里,只有3所是公立中學。
勞倫斯威爾學校是離普林斯頓不遠的一所寄宿制學校,也是向普林斯頓輸送生源最多的中學。如果你就讀于勞倫斯威爾,那么你考入普林斯頓的幾率比在史岱文森高中高出七倍,雖然后者是紐約市的頂級公立中學。普通的美國中學就更無法與之匹敵了。
| 教育困境 |
私立學校的上述問題源于其商業模式。私立學校的存在依附于富裕的家長與有權勢的管理人員之間的勾連。這個體系追求的是更大、更好、更多。學校在課程和校園建設等方面彼此競爭,許多學校都擁有奢侈的設施。
在一個公平的社會里,教育不是奢侈品。
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限制家長的捐款額,還需要認識到學校不是攀比之地。只有在不那么富裕的情況下——或許少接收幾個有錢家庭的學生——學校才會變得更平等。
一個公平的社會不需要這種昂貴的學校,私人財富也不需要資助教育事業。在一個公平的社會里,我們不會讓富裕人家的孩子和極少數幸運兒接受精英教育,而讓窮人家的孩子上沒有希望的學校。在一個公平的社會里,教育不是奢侈品。
而在我們當下的國家里,擺脫貧困以及走出工薪階層的路徑越來越少。大多數公立學校走向破敗,而昂貴的私立學校愈發成為勝利者的入場券。在美國,富人的孩子所在的很多學校都設有大門和保安,意為“你們很珍貴”,而窮人家孩子集中的學校則安裝了金屬探測器和警察,意為“你們是個威脅”。
公立教育曾幫助好幾代美國人跨越出生的階層,而今卻已無可挽回地沒落了。我所在的加州,公立學校里只有一半學生的閱讀能力達到了平均水平,數學能力甚至低于平均水平。如果一場危機持續的時間足夠長,它就不再是一場危機,而只是一個事實。
為窮人家孩子提供教育的學校難道不應是我們最好的學校嗎?
1988年,26歲的我開始在哈佛西湖高中教書,當時這所名為哈佛中學的學校經費充裕,但還沒有名震全球。校園有些簡陋,有幾棟樓還建在山里,一座教學樓每逢大雨就漏水,我們走過濕漉漉的地毯,教室地板上全是腳印。但我毫不在乎。在那些單純的日子里,學校就是改寫人生的地方。那就是我們能給予學生的一切。
[編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編輯: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