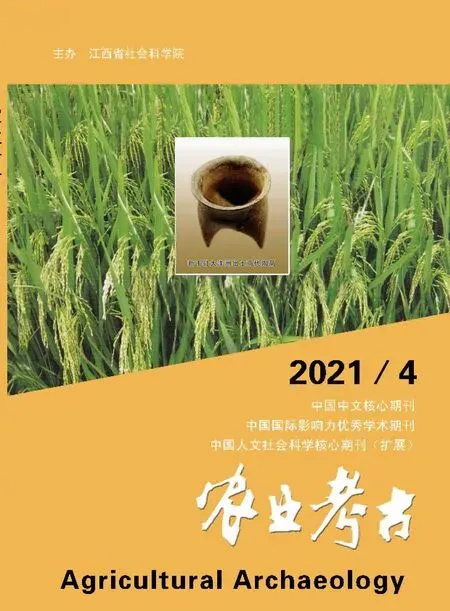先秦至漢晉時期云貴高原烏蒙山區原始農業的變遷*
張 勇
烏蒙山區位于我國西南云、貴、川三省交界處,主要包括滇東北、貴州西部及川南等地。先秦至漢晉時期,這一帶生活著眾多部族或族群。很多學者對該地區古代族群的生計和經濟活動做了研究①,大多數人認為當地古代居民以農業為主要生產部門,兼有漁獵、畜牧、制陶等生產活動。目前研究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研究者大多以現今的行政區域劃定研究范圍,忽略了相鄰的不同行政區之間古代族群生計活動的聯系;二是研究者往往從面上概括形成籠統認識,對一些關鍵問題未做深入探討,如農業耕作方式、生產工具演變、作物品種、農業發展的遲滯和不均衡現象等。有鑒于此,本文從種植業入手,結合考古材料、民族志和歷史文獻,梳理先秦至漢晉時期烏蒙山區各地族群的原始農業發展過程,并對相關問題展開討論,以期獲得對南方早期山地文明發展的進一步認識。
一、從原始農業到傳統農業的演變
烏蒙山區產生原始農業的時間很早,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貴州西部地區就有了原始農業[1]。早期居民從原始時代的采集、狩獵等生計活動中發展出了原始種植業,特別是糧食作物的種植,它成為農業中最主要的生產部門。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研究原始種植業,對其他生產活動暫不討論。根據耕作方式、工具及技術的不同,可將先秦至漢晉時期烏蒙山區的原始農業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
由于歷史文獻中有關先秦時期烏蒙山區農業生產的記載極其稀少,目前只有通過考古材料和民族志來復原原始種植業的生產面貌。現已發掘且公布材料的這一時期的考古遺址有貴州畢節瓦窯[2]、威寧中水雞公山、營盤山、吳家大坪②以及云南昭通魯甸野石山[3]等地。另外,像云南昭陽區的閘心場、黑泥地、雙龍井、過山洞,魯甸的馬廠[4](P30)以及曲靖的八塔臺(第一期和第二期墓葬)[5](P185)等遺址和墓地也大體屬于這一時段,只是材料比較零散。下文主要以瓦窯、雞公山、營盤山、吳家大坪、野石山等遺址為典型,展開介紹和分析。
1.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
瓦窯、雞公山、營盤山、吳家大坪、野石山等遺址均出土大量磨制石器,種類有斧、錛、穿孔石刀等(圖1),雞公山遺址還出土了一件石鐮(圖1-6)。學界一般認為石斧、石錛等石器是原始社會先民使用的砍伐農具③。先民用斧錛砍倒山林,然后將樹木曬干燒成灰燼,以增加土壤肥力,之后才開始播種,這就是刀耕火種的原始耕作方式。近代南方一些少數民族仍在使用類似方式,如20世紀50年代之前云南的獨龍、基諾、傈僳族等少數民族群眾在每年春天到來時,都會先用鐵刀將山林砍倒,曬干,放火燒成灰,然后用竹棍或木棍點種包谷、小米。種完就不再管理,待農作物成熟時再來收割。由于土地地力容易耗光,這種燒荒耕作的土地種1-2年后就要丟荒,村民要另外選擇林地燒山播種[6](P90)。其耕作方式除使用鐵刀而不是石斧、錛外,其余過程與原始的刀耕火種是一樣的。
在上述云南少數民族的耕作方式里,砍刀和點種用的竹木棍是最主要的生產工具,除此之外,基本不需要其他工具。我國邊疆很多少數民族經營原始農業時也只有這兩類工具[7](P7)。播種之前首先要砍伐林木,這是一項艱苦繁重的任務,沒有專門的工具,只靠雙手無法完成。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先民在金屬工具發明之前只能使用石斧、石錛等砍伐器,這種生產習慣長期延續,根深蒂固。即使進入青銅時代后,人們也仍然習慣使用斧錛類工具。如雞公山、野石山兩個遺址分別出土一件銅錛(圖1-11),曲靖八塔臺墓地部分春秋時期墓葬里出土多件銅斧(圖1-12)。它們可以視為過去的砍伐工具石斧和石錛的延續。
根據上述民族志材料,烏蒙山區先民耕作時應當還使用竹木材質的工具。只是這類工具不容易保存下來,所以考古發掘中難以見到相應的實物。從瓦窯等遺址只出土斧、錛等砍伐石器來看,結合近代南方山地民族的生產實際,可以推斷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烏蒙山區的原始農業處于初級階段,使用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
2.作物品種
這一時期烏蒙山區種植的糧食及其他作物品種,可以從雞公山、吳家大坪等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略窺一斑。兩地均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經鑒定,屬于人工栽培的粳稻。另外,雞公山遺址還出土粟、黍和大量蕓薹屬植物種子,后者包括白菜、青菜、甘藍等蔬果栽培品種的種子[8](P73)。由于全部的發掘報告沒有正式公布,關于稻種和其他作物種子的鑒定結果只是一種初步推測,還不能作為明確的判定依據,僅為參考。
不過,從烏蒙山區南部出土情況來看,稻類作物很可能早已出現了。例如曲靖八塔臺墓地附近出土的稻谷遺存,提供了當地早期稻作農業存在的線索。曲靖珠街鄉扁窟坑洞穴遺址出土炭化的人工栽培粳稻,經測定,其年代約在商末[5](P2)。這一地區至今仍普遍種植水稻。
從上述遺址來看,烏蒙山區早期居民種植稻谷是可以確定的。至于具體是什么稻種、是否有其他農作物,還有待于更多考古資料的公布。
3.收獲工具和方式
瓦窯、雞公山、營盤山、野石山等遺址都出土各種類型的穿孔石刀(圖1-2、3、10),出土的石鐮只有一件,暫不討論。這一時期居民主要使用石刀,并且以“摘穗”的方式收割谷物。有學者指出這與其農業技術水平有關[9]。因為早期農業選擇品種的技術不發達,作物成熟期不一致,摘穗方式可以保證最大可能收割所有的作物;另外,人們為了減輕天災對作物造成的損失,也會將不同的作物混種,以保證至少部分收成。“摘穗”可以盡量收獲不同時期成熟的作物。民族學資料也表明原始農業最初的收獲方式就是用手拔或摘穗,如云南苦聰人、佤族、怒族,臺灣高山族等,都是這樣做的[7](P45)。
(二)戰國至西漢
戰國秦漢是西南夷活動的重要時期。西漢司馬遷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10](P2991)滇人和邛都人分別活躍在滇池周邊和邛海至安寧河谷一帶,夜郎分布地一般認為在滇東和貴州西部,大體上處于烏蒙山區范圍。司馬遷對夜郎等部族的農業和社會狀況簡單概括為“耕田,有邑聚”。考古出土的材料、歷史文獻和民族志等資料揭示了較詳細的當地原始農業的面貌。
這一時期的典型遺址和墓地分布在普安青山銅鼓山④、貴州赫章可樂⑤、威寧中水銀子壇(梨園)⑥、云南曲靖八塔臺及會澤水城村[11](P117)等地。它們的主體年代在戰國至西漢時期。大部分墓地的墓主族屬包括地方土著民族和漢人移民及其后裔。
1.從刀耕火種到鋤耕方式
貴州赫章可樂的柳家溝和普安青山的銅鼓山兩處遺址都出土了斧、錛、穿孔石刀等石器(見次頁圖2)。曲靖八塔臺墓地戰國以來的土著墓葬里出土了若干銅斧(圖2-11),在西漢中晚期的土著墓葬里則出土若干鐵斧、鐵刀(見次頁圖3-1、2、9、10)。無論是石斧、石錛,還是銅斧、鐵斧、鐵刀,都可用作砍伐農具。在上述遺址和墓地出土的翻土農具如鋤、犁之類,數量很少,這表明烏蒙山區在戰國至西漢時期,大部分土著族群仍然使用刀耕火種的耕作方式。只不過砍伐工具有所改進,生產效率也應有所提高。
這一時期已有了少量銅質翻土農具。赫章可樂墓地西漢前期的土著墓M189出土1件銅鋤(圖2-7),普安銅鼓山遺址出土1件銅钁(圖2-6)。近些年來,人們還在烏蒙山區南部及邊緣地帶的盤縣、普安、興義等地征集或采集到一批青銅鋤、钁(圖2-8、9),它們的形制與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文化的同類器物相似[12](P93)。銅質翻土農具數量雖不多,卻能說明新的耕作方式已經出現。
西漢中晚期,隨著漢王朝開發西南夷,漢人移民進入烏蒙山區后,帶來先進鐵農具和生產方式。地方土著民眾受漢人影響學會使用了新式鐵農具,這在考古方面有很多證據,如赫章可樂土著民族墓葬里出土了鐵鍤、鏟、钁等翻土農具(圖3-5、8),M153甚至還出土了一件鐵鏵(圖3-7),漢人墓葬里則出土有鐵鍤、鏟、铚等農具(圖3-4、6)。會澤水城村墓地出土了鐵鍤和鐵鋤(圖3-4,原報告為鍤,根據孫機先生的研究[13](P10),從其外形看,應定名為鋤)。
鋤、鍤、鏟、钁這一類農具,在生產中主要用于起土和翻土。它們的出現表明烏蒙山區各族人民對土地的利用方式和耕作方式有了巨大變化。原先的刀耕火種土地每種完一季莊稼后就要拋荒,原本是不用翻土的,只有預備種下一輪作物時才有必要對其他土地進行翻土。隨著人口增加,當人們需要相對安定的定居生活時,就要增加單塊土地的利用年限,而在重復使用前,土地必須翻土。因此,烏蒙山區出土的各類翻土農具表明戰國至西漢時期原始種植業的耕作方式正在從刀耕火種演化到鋤耕方式。這一時期雖然有犁鏵出現,但屬于個例,不能確定是否已出現犁耕,故還是統稱為鋤耕。從刀耕到鋤耕,這是原始農業依次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
類似的發展路徑在云南一些少數民族的生產中也可見到。如傈僳族的土地耕作制度經歷了從刀耕走向鋤挖,最后發展為牛耕的過程。其中刀耕方式屬于不固定的游歇地,鋤挖地是半固定耕地,牛犁地是固定的耕地[6](P92)。西盟佤族的農業耕地也經歷了從刀耕火種的砍燒地,逐步過渡到鋤挖地為主,再往后出現牛犁地的變化[7](P3)。從出土的翻土農具再結合上述少數民族的耕作方式演變過程來看,烏蒙山區的原始種植業也經歷了上述變化,大約在西漢時期,鋤耕農業已經出現并且發展起來。
鋤耕農業反映出土著居民社會生活狀態的變化。戰國至西漢時夜郎等部族處于“耕田,有邑聚”的社會階段。這種定居的農業聚落生活不是突然出現的,從原始農業經歷的變遷來看,烏蒙山區土著族群顯然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才逐漸形成農業聚落,特別是在受到周邊相對發達的滇人青銅文化和外來先進漢文化影響后,當地族群才開始從刀耕火種的游耕狀態進入半定居或定居的農業生活。特別是到西漢中晚期,文獻中反映出這一時期包括夜郎等部族在內的土著族群邑聚數量眾多。如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牂柯、談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萬余人皆反”[14](P3843)。漢成帝河平年間(前28—25),牂柯太守陳立誅殺夜郎王興之時,“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余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14](P3845)。眾多邑聚說明土著族群過著相對穩定的定居生活,結合前述出土農具和民族志資料看,夜郎等部族的土地耕作制度已發展到有半固定或固定耕地的階段,其原始農業進入鋤耕農業階段。
2.糧食作物品種
這一時期烏蒙山區種植的作物有哪些?目前出土的植物遺存數量較少,已公布的有兩例。一例是普安銅鼓山遺址出土陶支子,上面有較多稻草痕跡。另一例是赫章可樂土著墓葬M153出土的銅鼓里裝有稻谷和大豆遺存。上文提到周邊地區如曲靖盆地和威寧中水盆地,在商周時期都有種植稻谷的歷史。銅鼓山和可樂都與這兩地有大體相似的地理環境、氣候和水土的山間盆地,也應當適合種植稻類作物,所以戰國至西漢時期稻谷應是烏蒙山區的主要糧食作物,或許還有豆類和粟類作物。史書記載西漢晚期牂牁太守陳立殺夜郎王興之后,“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14](P3845)。
從山地環境和民族志資料看,早期山地族群種植的可能是旱稻和粟類等旱作農作物。如南方地區的獨龍族、怒族、景頗族、門巴族、僜人、苗族、瑤族、黎族、高山族等少數民族的原始種植業都是從山地開始,主要經營山地旱作。水田出現時間很短,像獨龍族的水田是新中國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才開墾的。西盟佤族最早栽培的是旱稻,直到近代才在外界影響下開始種水田[7](P142—145)。這從一個側面可以印證前文所說商周時期威寧中水雞公山、吳家大坪等遺址出土的稻谷可能為旱稻品種。
3.收獲工具
柳家溝遺址和銅鼓山遺址都出土各種類型的穿孔石刀,這說明當地居民仍然延續了“摘穗”的收割谷物方式。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收割工具的材質有了變化,如曲靖八塔臺墓地采集到了一件銅爪鐮(圖2-10),在赫章可樂漢人墓葬里出土了一件鐵铚(圖3-3)。這說明從新石器時代經過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烏蒙山區居民一直在使用“摘穗”方式收獲谷物。
(三)西漢末至兩晉時期
漢晉王朝都在烏蒙山區各地設置郡縣。一些遺址和墓地分布地往往也是漢晉郡縣治所或統治中心區。如赫章可樂是漢代漢陽縣治⑦,昭通的昭陽區為漢代朱提縣治、犍為屬國郡治及晉朱提郡郡治,曲靖為漢代味縣及晉代建寧郡郡治。烏蒙山區東部邊緣地帶的清鎮、平壩、安順等地為漢晉時期牂牁郡中心區。南部邊緣地帶的興義、興仁為漢晉宛溫縣縣治所在[15](P29—30)。
隨著郡縣設置,大批漢人移民遷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工具隨之傳入。原有土著族群受到先進漢文化的影響,吸收了傳統農業的先進因素。烏蒙山區的原始農業開始向傳統農業轉化,農業生產總體上有顯著進步。這主要反映在技術、工具和作物品種等方面。
1.技術和工具
技術包括牛耕和水利兩方面。首先看牛耕,雖然前述歷史時期部分遺址和墓地中曾出土牛骨,文獻中也有這一地區養牛的記載(“牛羊勞吏士”),但是在東漢以前云貴高原上真已出現牛耕技術?還沒有充分肯定的證據。西漢中晚期漢人移民可能帶來牛耕技術,前述西漢晚期赫章可樂土著文化墓葬M153出土1件鐵鏵,說明當時或許有犁耕方式。但它不能作為牛耕出現的證據,因為用人力也可以挽犁耕地。從民族志資料看,在原始農業的早期階段,牲畜主要用于食用和利用皮張等,只是在鋤耕和犁耕農業發展起來后,牲畜才逐漸用于農業生產。盡管如此,利用畜力馱運和犁耕,都是比較晚的事[7](P175),因此西漢中晚期烏蒙山區是否有牛耕技術尚不明確。
東漢時耕牛出現了,這方面有考古和文獻的證據。云南昭陽區曾采集一塊東漢畫像磚,上面刻有人牽牛圖像,牛鼻子上有系繩(圖4-1)。李昆聲先生認為它顯示的是耕牛形象并提出云南部分地區東漢初中期已出現牛耕技術[16]。這里補充一則材料,貴州赫章可樂墓地的一塊東漢畫像磚上刻有人牽引牛車的圖案[17],從圖上看,人手與牛鼻之間有系繩(圖4-2),那么這拉車的牛也可能是耕牛,另外,牛既然能拉車馱運,那么人們也應當利用牛的畜力來耕地。
蜀漢時期有了關于耕牛的明確記載。《華陽國志·南中志》提到諸葛亮平定南中地區后,“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18](P185)。另外,史載蜀漢李恢平定南中后,“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19](P1046)。從出土畫像磚和文獻記載看,東漢時期包括烏蒙山區在內的云貴高原已經出現了牛耕技術。
另一項技術是農田水利設施的修造和相應的灌溉技術,它在西漢末被引進烏蒙山區的農業生產中,隨后傳播到滇池區域。史載,漢平帝時梓潼文齊在朱提地區帶領民眾“穿龍池,溉稻田,為民興利”[18](P216)。王莽時期,他轉任益州太守后,“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余頃”[20](P2846)。這些水利設施和相應的灌溉技術被內地官員引進后無疑推動了云貴高原原始農業的飛躍和進步。
東漢時期烏蒙山區有了發達的農業水利技術。這在當地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器中得以反映(圖5)。如貴州赫章可樂東漢墓出土1件[21],烏蒙山南部邊緣地帶的興義、興仁的東漢中晚期墓葬共出土3件⑧。這些模型器的平面形制分為長方形和圓形兩種,均呈淺盤狀。模型結構都是由象征陂池和稻田的兩部分組成,兩者之間有過水涵洞、水渠、水閘或溢灌口相連通。象征稻田的部分有規劃整齊的小田塊,有的底部還刻畫出一行行的秧苗形象。陂池內則捏塑出魚、蛙、螺、蓮、菱角等水生動植物模型。
墓葬隨葬品往往是現實中物質生活和生產情形的曲折反映。通過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可以看到東漢時期烏蒙山區多地居民已學會修造農田水利設施,掌握了先進的灌溉和生產技術。技術的進步不止于此,模型器中稻田被分成小田塊,是因為山區稻田內為保證水面高度一致,田塊不宜過大,只能分成小塊。秧苗成行排列,顯示其播種時采用了育秧移栽、行播等技術,而不是原始的散播方式。至于陂池中養殖的水產與稻田組成稻魚共生系統,這在今天的南方很多稻作區都可見到。這些技術進步都是在原始種植業發展到精耕細作的稻作農業階段后才會出現的。
這一時期出現的工具除了刀、斧、斤等砍伐農具外,還有鋤、鍤、鏟、犁等翻土農具,基本上延續了上一階段的農具種類,只是數量較少。不過,從上述牛耕技術運用情況看,烏蒙山區的居民在東漢時應該已經學會使用犁、鏵等農具翻土。另外,精耕細作的稻作農業也要求有更多類型的工具,以適應多個環節的精細化生產。
上述技術和工具的發展意味著烏蒙山區農業耕作制度和農業階段的躍遷。在條件優越的農耕區和山間盆地,刀耕火種的流動耕作方式可能漸漸轉變為固定在一地耕作。土地耕作方式從鋤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農業經營方式從粗放式演變為精耕細作的田園化管理。至此,烏蒙山區的原始農業開始邁向精細化的傳統農業階段。
這一變遷過程是漫長的。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并沒有在烏蒙山區各地立刻得到普及推廣。云貴高原地貌環境復雜多樣,各地生產條件不一致,農業發展水平不均衡。很多山區族群可能還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階段。到東晉時牂牁郡仍有“畬山為田,無蠶桑”[18](P196)的現象。前述這一階段出土的鐵農具數量較少,砍伐工具多,也暗合這一事實。
2.糧食作物種類
這一時期種植的糧食作物品種變得豐富起來。前述文齊在朱提地區“溉稻田”以及出土的東漢陂池稻田模型,都說明烏蒙山的壩區和山間盆地已經栽種水稻。另外,晉代郭義恭所撰《廣志》記錄朱提、建寧兩地種植的豆類,“重小豆,一歲三熟。槧甘白豆,粗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花,可為面”[22](P370),可見豆類糧食品種之多。粟類作物也有種植,前述西漢晚期已有粟類。至唐代,“牱咩牱蠻……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土氣郁熱,多霖雨。稻粟再熟”[23](P5276)。在烏蒙山區南部的曲靖盆地以南及滇池西部,“土俗惟業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后,還種粳稻。小麥即于岡陵種之,十二月下旬已抽節如三月,小麥與大麥同時收刈”[24](P256)。從這幾段記載可知,稻、粟、麻、豆、黍、稷、麥等糧食品種于唐代在云貴高原上已普遍種植。唐代與漢晉時期相去不遠,據此推斷烏蒙山區居民彼時種植的糧食也包括上述種類。
二、相關問題討論
烏蒙山區的原始農業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現象,下面分別討論這些現象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躍遷式發展
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周時期,在漫長的歷史中,烏蒙山區原始農業始終停留在刀耕火種階段。進入戰國至西漢時期,在周邊先進文化影響下,烏蒙山部分地區逐步發展到鋤耕農業階段。又在西漢末至東漢時期迅速躍遷到傳統農業階段。
最開始的影響來自發達的滇人青銅文化。戰國晚期至西漢早中期滇文化發展到鼎盛時期,并且向四面擴散。其影響往東部和北部到達了烏蒙山區的腹地。烏蒙山區的北部和南部邊緣地帶出土的少量滇式青銅鋤、钁等農具就是滇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它表明烏蒙山區一些部落和族群在滇人生產方式的影響下,從原始的刀耕火種開始進步到鋤耕農業,但是這種影響還是局部和片面的。
西漢中晚期,烏蒙山區迎來一波快速的發展。漢王朝在西南夷地區普遍設立郡縣。為了供給軍政人員的開支,政府還下令招募農民到邊疆墾荒,“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25](P1421)。漢人移民帶來先進的鐵農具和技術。進入東漢后,烏蒙山區的原始種植業有了巨大改觀。大部分地區的居民開始使用鐵農具,牛耕和水利技術出現,表明當地不僅有了犁耕農業,還出現了精耕細作的稻作農業生產體系。糧食作物品種也有所增加。
綜上可見,兩漢時期是烏蒙山區原始農業的加速發展期。其實質性變化的根源主要是先進漢文化的影響,且隨著時間推移,進入當地的外來人口不斷增加,東漢以后的蜀漢、兩晉官府在這一地區不斷增設新的郡縣機構,加大了開發力度。正是由于官府的開發活動以及外來漢移民輸入的先進工具和技術,烏蒙山區原始農業的生產面貌才得以逐漸改變,并且在幾百年內出現了飛躍式的發展。
(二)滯后性發展
烏蒙山區原始農業的發展過程包含矛盾,既有躍遷式的發展,又表現出滯后性的一面。具體來說,土著族群對外來先進生產方式經歷了一個從排斥到逐漸接納的過程。這里以西漢中晚期到東漢早期各地遺址和墓地出土的鐵農具為例,略作分析說明。
烏蒙山區的赫章可樂、威寧中水、會澤水城村、曲靖八塔臺、普安銅鼓山等墓地和遺址都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鐵器。主要包括兵器、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三類,有刀、劍、矛、鏃、削、斧、斤、鋤、鍤、鏟、钁、铚、鑿、釜、三腳架等。出土鐵器中有一個現象:刀、削、斧等砍伐農具數量多于鋤、鍤、鏟、钁、犁等翻土農具,其簡要情況如下。
赫章可樂墓地共出土約258件鐵器(部分鐵器銹蝕嚴重,無法分辨器形),其中,刀和削共約134件、鐵斧7件、斤1件。鐵農具有鍤、钁、鏵、铚等共19件,斧、斤之類鐵器為砍伐用具。刀可作兵器,也可用于砍伐林木。削是加工竹木的工具,故可將刀、削視為砍伐類農具。鍤、鏵等是翻土農具。
觀察胎兒正中矢狀切面多為觀察胼胝體及小腦蚓部等重要結構,胼胝體與小腦蚓部均要到16~18周之后才能發育完成,而孕周較大的胎兒由于胎頭較低,顱骨衰減明顯等原因極難獲得正中矢狀切面,故選擇孕周19~34周的胎兒,對其分別進行二維及三維的掃查方法獲得正中矢狀切面。
威寧中水銀子壇墓地3次發掘共出土21件鐵器。其中鐵刀有11件(可能也包括鐵削,報告中未做區分)。未見鐵制翻土農具出土。
會澤水城村墓地共出土38件鐵器,其中有刀(削)18件、鍤2件(其中1件應為鋤)。
曲靖八塔臺墓地的西漢中晚期墓葬共出土61件鐵器,有刀11件、削20件、斧9件,沒有鐵制翻土農具出土。
普安銅鼓山遺址共出土17件鐵器。其中砍刀有5件。未見其他鐵農具。
上述各墓地和遺址的主人大多數是土著族群,只有赫章可樂和威寧中水有部分漢文化人群墓葬。即便漢人墓葬出土的鐵器中,刀、斧、削等砍伐用的工具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赫章可樂的墓地雖然出土了較多翻土農具,但其數量仍然不及砍伐類的鐵器多。從總體統計數量看,烏蒙山區的土著族群在西漢中晚期至東漢早期這一時段內偏向于選擇使用砍伐類工具。即使在東漢及兩晉時期這一地區出土的鐵制翻土工具的數量也沒有刀和削多。
雖然西漢中期以來漢人移民為西南夷地區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但是從當地出土的工具構成比例和變化趨勢看,不可高估先進漢文化帶來的影響,烏蒙山區大部分土著族群沒有馬上接受先進的鐵農具和生產方式,而是延續了過去砍林燒荒的原始耕作方式。對先進的鐵制翻土工具以及相應的土地耕作技術,他們有一個從排斥、觀望到接納的轉變過程。
這種轉變,在近現代云南偏遠山區的少數民族中可以觀察到。如獨龍族最早從周邊地區引入的鐵農具是鐵刀,在鐵刀傳入幾十年后才開始傳入和使用鐵尖小木鋤。漢式鐵鋤、鐵犁在獨龍江地區的推廣使用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事。像西盟佤族、拉祜族、苦聰人等也都長期使用鐵刀等原始農具,晚近才使用鐵鋤、犁等先進農具。比較典型的是勐海布朗族,他們在解放前使用的農業工具只有大刀、鐮刀和小手鋤。1954年,解放軍送給當地群眾一批鐵鋤頭,但他們不愿意使用這些翻土農具,將其大部分閑置或作其他用途[7](P14-15)。上述各少數民族,長期習慣于砍倒燒光的刀耕火種耕作模式。面對外界輸入的先進農具,他們更愿意使用鐵刀做為砍伐工具。再者,從經濟的角度看,鐵刀除了砍林開荒外,還可用于狩獵、防身以及在生活中用于砍柴、破木、開路等多種用途,是一件萬能工具。先進鐵農具要等到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才逐漸被接納。
先秦以來,烏蒙山區各地民眾經歷了漫長的刀耕火種原始農業階段,已經習慣于使用斧、錛等砍伐工具。當先進鐵器傳入時,他們優先選用了鐵刀、斧、削等砍伐和加工竹木的工具,這是過去工具使用習慣的延續。這導致他們接納鋤耕農業和犁耕農業的生產方式比較緩慢。另外,早期鐵器輸入時數量稀少,比較珍貴,兵器是優先輸入的鐵器。鋤、犁只能用于翻土,而鐵刀作為萬能工具,可以一器多用。所以漢晉以來烏蒙山區出土的鐵農具數量遠遠少于砍伐農具。上述原因也提示研究者在觀察西南山地族群的生業經濟時,不可從漢人地區傳統農業的角度去看待山地原始農業。
(三)不均衡發展
從西漢中晚期以來,烏蒙山區原始農業出現了飛躍式的發展,但同時也存在滯后性的一面,這是從歷時性角度來說。從共時性地域分布來看,烏蒙山區的原始農業存在不均衡發展的現象。
原始農業發生躍遷式發展,演變為傳統農業的地方,一般分布在兩漢時期從巴蜀地區通往云貴高原腹地的交通線上或附近。如從四川宜賓,溯橫江河谷而上,經昭通到達曲靖的路線是秦漢時期的五尺道。這條道上的昭通(今日的昭陽區)是漢代朱提縣治及犍為屬國郡治所在地。西漢中葉唐蒙出使夜郎后,開辟了南夷道。赫章可樂位于此道上,這里是兩漢時期漢陽縣的縣治。烏蒙山區東部的黔西、清鎮、平壩、安順西秀以及南部邊緣地帶的興義、興仁等地均處于漢代從巴蜀地區逆赤水河谷南下,經黔中地區到達黔西南地區的交通要道上[26]。上述地方分布有大量漢晉墓葬,它們往往是大型漢人聚落和官府機構所在地。那些反映傳統農業生產的鐵制農具和陂池稻田模型器往往都出土在這些地方。
然而,在遠離上述交通要道和漢王朝統治據點的偏遠山區,原始農業的發展比較滯后,如威寧中水銀子壇墓地出土鐵器中未見翻土農具,只有大量砍伐工具。墓地還出土了牛、馬、豬等家畜及野豬、獾等野獸的骨骼,還有蚌殼,這表明當地原始農業還停留在刀耕階段,除了種植業,居民還依賴養畜、狩獵、捕撈等活動維持生計。又如普安銅鼓山遺址出土鐵器中不見鋤、犁等翻土農具,雖然有銅钁出土,但數量太少,只有1件。在該遺址的地層中出土大量動物骨骼、牙齒、角枝等,種類有牛、羊、豬、狗等家畜,獼猴、竹鼠、豪豬、鼠、熊、水鹿、麂等野生動物。此外還有箭鏃、魚叉、魚鉤、石網墜等漁獵工具出土。這可以看出銅鼓山的古代居民生業方式多樣化,原始農業不是唯一和主要的生產部門。
另外,史書記載烏蒙山區南部邊緣的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面,百姓資之”[20](P2845),這或許說明烏蒙山區古代居民至漢晉時期仍以采集植物資源為主要生業方式之一,原始農業只是一種生計輔助方式。
原始農業在烏蒙山區不同地域發展不均衡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生產習慣外,主要與漢晉時期朝廷對該地區的統治方式有關。中原王朝在廣大西南山區設置的郡縣據點往往沿交通路線分布,其有效統治的區域也分布在交通線上的節點及附近地區。這些地方有大量的漢人移民及其后裔聚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比較容易擴散傳播。而在遠離交通節點和要道的偏遠山區,土著族群很難在短期內接觸并吸收先進的文化因子,所以其社會生產水平總體落后于交通線上的大型漢人聚居區。
三、結語
先秦以來,烏蒙山區早期居民從原始采集、狩獵等生計活動中逐漸發展出原始的種植業。在漫長時間里,種植業進步緩慢,長期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初級階段。這可以從各地出土的大量砍伐類工具看出。
戰國至西漢時期,烏蒙山區土著族群先后受到周邊滇人青銅文化和先進中原文化的影響,其原始農業迅速從刀耕火種的階段躍遷到鋤耕農業階段;個別地方可能已出現犁耕農業。不過,盡管自西漢中期后中原的鐵農具已傳入,烏蒙山區大部分土著族群沒有立刻接納漢人的先進工具和技術,而是繼續沿用傳統的刀耕模式。至東漢兩晉時期犁耕農業才發展起來,并且農業生產中運用了先進的水利灌溉技術。隨著漢晉中原王朝對此區域的持續開發,外來人口漸增。在先進漢文化的影響下,烏蒙山區的原始農業開始向傳統農業過渡。
烏蒙山區地形復雜,地表崎嶇不平,多高山河谷,少平原丘陵。傳統農業生產條件不足。在少數山間盆地產生了早期文明,受到自然條件限制,他們的原始農業生產水平落后,通過采集、狩獵、捕撈等生計活動獲得的食物資源有限,不足以維持大量人口生存。所以烏蒙山區在漢人進入前,大多數山地文明發展程度不高,規模不大,往往呈散點狀分布,無法形成大型聚落中心。只有部分山間盆地的地理環境、水土資源等條件比較優越,其早期文明達到一定的規模,西漢中葉后,這些地方往往成為朝廷開發本地區的據點和交通線上的節點。由于大批漢人移民及后裔聚居在此地,當地土著族群受到漢文化影響,其原始農業逐漸演化為傳統農業。至于那遠離漢人聚落和交通線的邊遠山區,原始農業發展緩慢。
人類社會的各種發展總是要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烏蒙山區自先秦到西漢,原始農業生產水平落后,早期文明的發展也受到了限制。只有到西漢中葉后,當地原始農業出現躍遷式發展,才向傳統農業過渡。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青銅文明在這一時期也逐漸走向了衰落,終至瓦解消失;原有的各土著族群大多也隨之消失或融入到漢文化人群中。對云貴高原烏蒙山區原始農業的研究,為探索南方早期山地文明和族群的發展演變提供了一個角度。
注釋:
①相關論述和研究參見以下論著:侯紹莊,史繼忠,翁家烈《貴州古代民族關系史》,貴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張合榮《貴州古代民族農業發展略論》,載《貴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貴州通史編委會《貴州通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版;楊勇《戰國秦漢時期云貴高原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周志清《滇東黔西青銅時代的居民》,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顏全己,楊軍昌《論漢代古夜郎區域的農耕稻作發展》,載《農業考古》2020年第3期58-65頁。
②相關資料參見: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威寧縣文管所《貴州威寧縣雞公山遺址2004年發掘簡報》,載《考古》2006年第8期;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威寧縣文管所《貴州威寧縣吳家大坪商周遺址》,載《考古》2006年第8期;張合榮,羅二虎《試論雞公山文化》,載《考古》2006年第8期。
③參見以下論著:宋兆麟《我國的原始農具》,載《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陳文華《農業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④相關資料參見:程學忠《普安銅鼓山遺址首次試掘》,載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研究所編《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劉恩元,熊水富《普安銅鼓山遺址發掘報告》,載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研究所編《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普安銅鼓山遺址》,載國家文物局編《2002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⑤相關資料參見:貴州省博物館編《貴州赫章縣漢墓發掘簡報》,載《考古》1966年第1期;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赫章縣文化館編《赫章可樂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赫章可樂2000年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⑥相關資料參見: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威寧縣文化局《威寧中水漢墓》,載《考古學報》1981年第2期;李衍垣等《貴州威寧中水漢墓第二次發掘》,載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第十輯)》,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李飛《貴州威寧銀子壇墓地分析》,四川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專業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
⑦學界對漢陽縣治所在地的認識較一致,代表性論述參見:宋世坤《試論夜郎與巴蜀的關系》,載《貴州文史叢刊》1982年第1期;張合榮《貴州出土漢代燈具與郡縣地理考察》,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5期;楊勇《戰國秦漢時期云貴高原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⑧相關出土資料參見: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組《貴州興義興仁漢墓》,載《文物》1979年第5期;貴州省考古研究所《貴州興仁交樂漢墓發掘報告》,載貴州省博物館考古研究所《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