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
沙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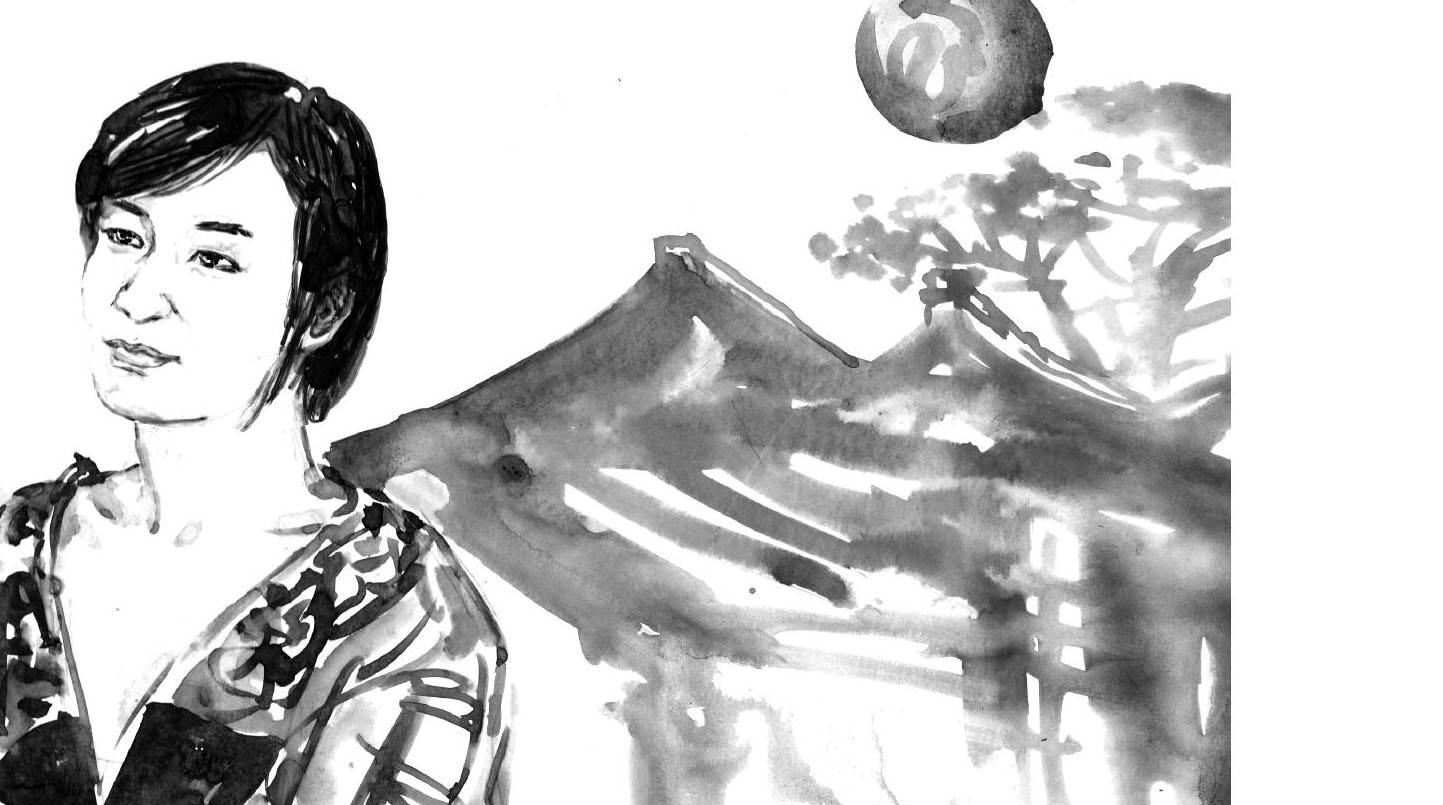
徹底醒過來的時(shí)候,我為自己的悲傷感到驚異。這悲傷如此真切,以至我疑心,制造夢(mèng)境的潛意識(shí)其實(shí)是一位虛構(gòu)大師。
我不知道為什么會(huì)夢(mèng)見Z的死。或許在夢(mèng)中,我所哀悼的并不是Z,而是我們之間曾經(jīng)存在過的友誼。如果年輕時(shí)有人宣稱他來自未來,說前路上正徘徊著一場(chǎng)超級(jí)瘟疫,我肯定不會(huì)相信。我也不會(huì)相信我和Z終有一天會(huì)分道揚(yáng)鑣,形同陌路。
是否人們?cè)谀贻p時(shí)更容易保持一致?那時(shí)候我們愛詩(shī),一個(gè)松散的小圈子,偶爾聚會(huì),喝酒,聊天,時(shí)光就這樣過去許多年。但在許多年里,我都不曾想過,如果將詩(shī)歌視為一條道路,每個(gè)人為這條路設(shè)定的方向和目的地其實(shí)大有不同。
如今想來,早在十年之前,我和Z之間的裂隙就已經(jīng)初現(xiàn)端倪。那時(shí)候我還在Y城,像國(guó)內(nèi)所有的四線城市一樣,在這個(gè)東北小城的日常生活中,穿插著大量的人情支出。那一年,Z的兒子考上了大學(xué),他為此大宴賓客。而在半年之前,一位曾經(jīng)與Z在同一個(gè)機(jī)關(guān)工作過的熟人告訴我,因?yàn)槭Щ穑琙妻子經(jīng)營(yíng)的干洗店損失了數(shù)萬元,Z上報(bào)給單位領(lǐng)導(dǎo),整個(gè)Y城公安系統(tǒng)為他的家庭搞了一次募捐。見我滿臉愕然,熟人撇嘴一笑:“怎么?你一點(diǎn)兒也不知道嗎?”
我沒有應(yīng)邀參加Z兒子的升學(xué)宴,只托熟悉的文友捎去了二百元錢。即使彼此已有十幾年的交情,Z的兩番行事還是讓我大感意外。
將近兩千年前,一個(gè)叫管寧的人只通過兩樁小事,便確認(rèn)自己與某人絕非同類,于是毅然割席斷交。而我既無管氏的敏銳,更沒有他的決斷,雖然意識(shí)到彼此志趣殊異,仍試圖維持表面上的禮貌和圓滿。
直到有一天收到Z的一條私信,回復(fù)的時(shí)候,我才發(fā)現(xiàn)消息已無法發(fā)送。
但只有在夢(mèng)中,我才有勇氣與Z鄭重道別——死亡,這是永遠(yuǎn)的、真正的離別,因?yàn)楸舜碎g再也無法回頭。
后來我就離開了Y城。在離開Y城之前的數(shù)年里,時(shí)常有朋友與我聊著聊著,突然就沒頭沒腦地冒出來一句:“你真不像是Y城的人呢!”我知道他們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怎樣才能像一個(gè)真正的Y城人:在該謙恭的時(shí)候謙恭,在該致敬的時(shí)候致敬,在該合唱的時(shí)候張開嘴巴——盡可能將自己混淆于大眾。然而道路和腳印終會(huì)泄露內(nèi)心的想法,在致密而堅(jiān)硬的資源壁壘之下,就連沉默,也往往是不合時(shí)宜的。而另外的事實(shí)則是,我們都曾期待經(jīng)年的老友可以彼此心照,相攜成長(zhǎng),直到對(duì)此再也不抱任何奢望。
人到中年,我終于確信,時(shí)間并不會(huì)彌合人與人間的隔閡,相反,它的筆觸只會(huì)一再加重自我的輪廓,從而使深淵更深,使這周身的鎧甲更厚、更沉。
是不是神奇的DNA,讓我們自覺遠(yuǎn)離那些一再帶來失望的人們?
在離開Y城三年之后,我無意中看到一個(gè)官方公布的統(tǒng)計(jì)數(shù)字:三年之間,Y城總共流失了十六萬人。我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這十六萬人中的一個(gè)小小分子,一顆裹挾于洪流之下的渺小沙粒。而每當(dāng)我坐在返鄉(xiāng)的列車上,總會(huì)清楚地辨認(rèn)出同一車廂里的Y城人——不,不是口音,是那種在同一片土地上出生和長(zhǎng)大的人才可能共同擁有的隱秘標(biāo)記。我會(huì)從他們的衣著、表情以及舉手投足間的微弱余音中,突然撞見我自己和故人們的影子。西方人往往難以區(qū)分中國(guó)人、日本人和韓國(guó)人,但在東方人自己眼里,這三個(gè)國(guó)家的人其實(shí)氣質(zhì)迥異。據(jù)說黃種人的膚色來自文明發(fā)軔的黃土高坡,而Y城人的血液里則奔涌著一條泥沙俱下的大河。那是一條寬廣的、混濁的、一言難盡的河流,它于Y城城北蜿蜒而過,并于市區(qū)以西將自己隱匿于遼東灣的蔚藍(lán)海域。在水運(yùn)昌隆的年代,這條著名的河流一度風(fēng)光無限,河面上林立的帆影和河岸上一字排開的南北商號(hào)互為映像,共同寫就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繁華宣言。然而,當(dāng)我七歲那年進(jìn)入小城,這條緊鄰渡口的小街早已破敗不堪,街兩旁殖民時(shí)期的小洋樓一個(gè)個(gè)茍延殘喘,樓頂上的枯草搖曳出徹骨的荒寒。我在媽祖廟前的小攤上買了三分錢的糖稀,用手指長(zhǎng)短的兩根小木棍把它拉成一條線段,再纏繞在一起。如果有足夠的耐心,紅褐色的糖稀會(huì)在這拉伸和攪拌中慢慢轉(zhuǎn)變成神奇的金黃色——這是小街留給我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甜蜜記憶。
后來那條街道被修繕重建,成了商業(yè)步行街。規(guī)劃者原本豪情萬丈,要一舉拿下國(guó)家級(jí)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名頭。省內(nèi)的幾位歷史學(xué)者應(yīng)邀趕來,他們圍著那些煥然一新的建筑物轉(zhuǎn)了一圈,相顧無言。最終,市政府出面召集專家組開會(huì),要求學(xué)者們顧全大局,無論如何也要通過市級(jí)歷史文化遺產(chǎn)的評(píng)定。
那條風(fēng)格復(fù)雜的步行街建成后,我去過幾次。有兩次,我在渡口周圍轉(zhuǎn)來轉(zhuǎn)去,試圖找到我家老房子原來的位置。那兩間平房本是我父親單位的公產(chǎn),房改時(shí)我家出資買了下來。我祖父母在那棟房子里住了多年,我出嫁前也隨他們住在那兒。到了動(dòng)遷的時(shí)候,這一帶斷了水電,我祖父母便搬了出來。一天早上,我祖母又趕回去看她的房子,卻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變成了廢墟。我祖母頓時(shí)傻在那里。兩天后她見到我,臉上仍涌動(dòng)著驚駭交加的余波,她翻來覆去地控訴:“他們?cè)趺茨苓@樣?要是我沒搬出來,是不是要把我埋在里頭?”我母親也心有余悸,說算了,咱去把字簽了吧。
或許,我一直不喜歡這條被修整一新的街,是因?yàn)樵趦?nèi)心的某個(gè)角落里,掩埋著它曾經(jīng)帶給我祖母的驚悸?
而隨著祖父和祖母的相繼逝去,這片土地,明確地刪減了它與我之間的必要聯(lián)系。
這一天,有人對(duì)我提起了這條街,他說他從來沒有去過。
這位馮同學(xué)是我的初中同窗。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考入一家“全球五百?gòu)?qiáng)”企業(yè),后來調(diào)入日本分公司,現(xiàn)居?xùn)|京。下個(gè)月,他將前往加拿大定居。
馮說,這座他出生和長(zhǎng)大的城市,如今煥然一新,他已經(jīng)找不到任何過往時(shí)光的印記,這讓他深感茫然。
我說,也許,將來留在小城里的,多數(shù)是些在機(jī)關(guān)事業(yè)單位工作的人吧。
馮說,完全有可能。其他行業(yè)會(huì)日漸沒落。
我說,若是那樣,這城市會(huì)荒蕪。
馮說,如果變成一座小鎮(zhèn),或許更為美好。
我一時(shí)呆住。這座城市,真的會(huì)變成一座小鎮(zhèn)嗎?真是一個(gè)瘋狂的想法。
我想起前一年初冬,我回到小城,下了從高鐵站開往市區(qū)的公交車,拖著行李箱走在家門前那條熟悉的小街上。人行道坑洼不平,行李箱在路磚上東倒西歪地蹦來跳去,類似我小時(shí)候玩過的跳房子游戲。街上行人不多,迎面走過來的人向我投來驚訝的一瞥——是行李箱讓我看起來像是天外來客?毫無預(yù)兆地,仿佛時(shí)光斷流,我眼前這一段小街上的行人離奇地消失了,街兩旁所有商鋪的門扉凝止不動(dòng),只有午后的風(fēng)聲穿過街兩邊蒼老的槐樹……駭異之下,我屏住呼吸,甚至不敢回頭——如果身后街角處那幾位曬太陽(yáng)的老人也突然消失了,是否意味著我已身陷異境?電光石火之間,透過祖母的眼睛,我見識(shí)了這人間巨大的驚駭:廢墟降臨,所有屬于你的現(xiàn)世安穩(wěn),頃刻間煙消云散……謝天謝地,一個(gè)女人終于在我的視野中現(xiàn)身,接下來是小轎車和慢吞吞的行人。商鋪的鋁合金玻璃門開合間發(fā)出輕響,斷掉的時(shí)間之繩索無聲接合,小街恢復(fù)了它的流淌。
仿佛劫后余生,我吁出一口長(zhǎng)氣,心里暗自慶幸。
或者,就在那一刻,這座城市向我預(yù)演了它的未來?
我想起從前,走在Y城的大街上,總會(huì)有攬客的司機(jī)和乘務(wù)員關(guān)切地向我招呼:“哎!你要去哪兒?”不,我哪兒也不去,我只是一個(gè)下班回家的人。
那時(shí)候我并不知道,有一天我真的會(huì)離開這兒。
而在離開Y城之后,我才慢慢明白,所謂故鄉(xiāng),并非一個(gè)地理意義上的概念,它是心靈與心靈之間的契合與滋養(yǎng)。年輕的時(shí)候,我也曾有過所謂的“鄉(xiāng)愁”——每當(dāng)想起我度過整個(gè)童年的那個(gè)叫鄭屯的山村,我的鼻翼就會(huì)發(fā)酸,內(nèi)心充盈著一種柔軟的、莫名的暖意。后來我明白了,這暖意來自童年,來自對(duì)給了我無限寵愛的祖父母的懷想和追憶,它與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其他人,并沒有直接關(guān)系。在離開鄭屯之后的許多年里,我沒有再見到那些鄉(xiāng)鄰。直到成年之后,隨著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相繼歸葬于鄭屯村的西山墓園,我才再次見到了那些老去的鄉(xiāng)人。我遠(yuǎn)遠(yuǎn)注視著他們的臉,試圖從中辨認(rèn)出往日時(shí)光的輪廓。離開村莊的時(shí)候,我只是一個(gè)七八歲的孩子,而今,我這張中年的臉,業(yè)已完全無法鍥入他們的記憶。換言之,在我和他們之間,真正意義上的交集并不存在,而且無論往昔、現(xiàn)在和將來,盡皆如此。
一個(gè)沒有故鄉(xiāng)的人,于他而言,所謂異域,也不復(fù)存在。
(插圖:珈 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