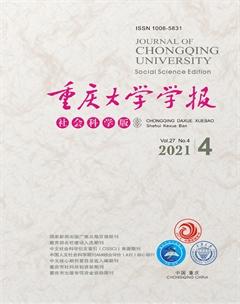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影響









摘要:如何保證就業穩定、促進城市化的可持續性發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已有文獻普遍只是單獨地研究了人力資本或產業結構升級對城市化的影響,而忽視二者之間的協同作用。文章基于1999—2016年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創新性地測算了不同類型城市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之間的匹配度,并運用兩步系統GMM模型就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與城市化之間呈顯著的正向線性關系,但會因城市規模和地區差異而有顯著不同;從不同城市規模看,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正向影響不如特大型城市突出;從地區差異看,相對于中西部地區城市,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正向影響更強,但對于特大型城市而言,上述情況則正好相反。因此,我們要注重城市化的可持續性,作好不同規模和不同區域的城市產業發展和就業方向定位,以提高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促進城市化進程。
關鍵詞: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城市化;城市規模;地區差異
中圖分類號:F249.2;F121.3;F29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1)04-0199-17
引言
城市化是一國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和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發展迅速,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中國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為58.5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已高達42.35%,而人力資本
如無特殊說明,本文的人力資本是指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普通高等教育的從業人員。和產業結構升級是影響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中國統計年鑒》和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高校畢業生人數從1999年的84.76萬猛增到2017年的735.80萬,這些高校畢業生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城市的第二尤其是第三產業部門工作,促進了城市化發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趨勢分析:2003—2017年》[1]的數據表明,約4成高校畢業生的第一份工作與其專業知識不太對口或者毫不相關。而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的數據,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人力資本在1999—2016年期間每年在第三產業就業的比例均超過第二產業,但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的城市只有137個。顯然,人力資本就業的產業分布與產業結構的發展并不匹配,這是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不佳或工作更換現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勢必會影響城市化進程的可持續性。為此,本文試圖探究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影響,及其在不同規模城市和不同地區城市之間的差異。
有關人力資本與城市化之間關系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非常廣泛。Black和Henderson認為人力資本能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城市收益以及經濟增長,因而可促進城市化[2]。Diamond構建了一個關于人力資本、工資、房價和公共服務的完整理論框架進行分析,結果表明人力資本在規模上的擴大對城市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3]。Simon和Nardinelli發現人力資本積累對英國各大城市規模擴張有著決定性的推進作用[4]。眾多學者的實證分析結果也均表明人力資本對城市化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5-8]。而國內外學者對產業結構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則觀點不一。一種觀點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可以加速城市化。如庫茲涅茨[9]認為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現,因而工業化過程等產業結構變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10-12];向俊波和陳雯認為產業結構主要通過作用于要素市場等影響城市化[13]。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去工業化”等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的過程,會引發大量員工下崗失業和結構性失業而不利于城市化[14-17]。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普遍只是單獨地研究了人力資本或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的影響。事實上,不同規模和不同地區城市的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具有不同的特點,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之間需要一定的匹配度,才能保證就業的穩定性、促進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18]。因此,把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作為兩個獨立因素,來考察它們對城市化的影響,就會忽略二者之間的協同作用。本文的創新之處就在于運用了時間跨度較長的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運用動態面板模型重點考察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之間的匹配度對城市化的影響,并探索其在不同規模和不同地區城市的差異性,以提出不同的高等教育發展、產業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戰略,合理推進城市化。
一、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的測算
(一)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分布的基本情況
1.不分城市規模條件下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分布的情況
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0—2017年)的原始數據,我們測算了1999—2016年期間不分城市規模條件下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分布的情況,所有城市總體上第一、二、三次產業所占GDP比重和各產業人力資本分布的均值分別為8.147%、49.843%、42.225%和1.956%、46.897%、50.066%,說明所有城市總體上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其次為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但人力資本就業方向卻以第三產業為主導,其次是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因而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之間總體上存在明顯的錯配問題。從不同區域看,東部地區城市第一、二、三次產業所占GDP比重和各產業人力資本分布的均值分別為5.444%、51.591%、42.957%和1.114%、51.251%、47.603%,中西部地區城市上述指標則分別為9.654%、48.854%、41.827%和2.431%、44.494%、51.421%,可見,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之間錯配的現象在中西部地區城市表現得更為突出。
2.劃分城市規模條件下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分布的情況
本文根據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區(不包括市轄縣)每年的實際非農業人口數和實證分析所需樣本量,以及1989—2014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把287個樣本城市劃分為小型城市(50萬人口以下)、中型城市(50萬~100萬人口)、大型城市(100萬~200萬人口)和特大型城市(200萬人口以上)4種規模。同樣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0—2017年)的原始數據,我們測算的上述4種不同規模城市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分布的情況如下。
從不分地區不同城市規模的角度看,1999—2016年期間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當中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第一、二、三次產業所占GDP比重的均值分別為7.981%、49.733%、42.286%,8.817%、50.273%、41.585%,9.690%、50.267%、40.044%,3.704%、47.670%、48.624%;而三次產業人力資本分布的均值依次分別為2.612%、42.195%、53.266%,2.360%、47.168%、49.491%,1.541%、47.974%、49.144%,0.748%、49.631%、49.842%。說明除了特大型城市三次產業產值占比高低依次為第三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以外,其他規模的城市仍以第二產業為主導,其次為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產值占比優勢并不十分明顯,并且第三產業占比隨著城市規模擴大而呈先下降后上升趨勢,并非部分學者所認為的“城市規模和第三產業發展呈現正相關”。可是無論城市規模如何,人力資本主要集中就業于第三產業,明顯超過該產業產值占比;而在第一產業就業的人力資本占比居然不到3%。除了特大型城市第二產業就業的人力資本占比超過第二產業產值占比以外,其他規模城市第二產業就業的人力資本占比均低于第二產業產值占比。
從分地區不同城市規模的角度看,同期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第一、二、三次產業所占GDP比重的均值分別為8.040%、50.401%、41.558%,5.667%、51.938%、42.377%,5.289%、53.187%、41.516%,3.687%、49.638%、46.673%;而三次產業人力資本分布的均值依次分別為1.437%、44.678%、53.863%,1.220%、50.995%、47.837%,1.030%、53.070%、45.780%,0.659%、51.739%、47.606%。中西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第一、二、三次產業所占GDP比重的均值分別為7.921%、49.627%、42.452%,10.203%、49.477%、41.255%,12.462%、48.355%、39.189%,3.704%、44.638%、51.658;而三次產業人力資本分布的均值依次分別為2.916%、41.638%、52.999%,2.888%、45.446%、50.221%,1.861%、44.848%、51.269%,0.890%、46.215%、53.395%。可見,分地區不同規模城市的人力資本—產業結構之間匹配的特征與不分地區不同規模城市的人力資本—產業結構之間匹配的特征非常相似。
綜上所述,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明顯的錯配問題,并且在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表現得更為突出。
(二)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的測算指標與結果
1.測算指標
本文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的測算指標主要有“結構偏差系數”[19]和“結構協同適配度”[20]。
(1)結構偏差系數。
結構偏差系數用于測度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之間在數據總量方面的靜態差異,其計算公式為:
DSj=Gj/Ej-1""" (j=1,2,3)(1)
式(1)中,DS為結構偏差系數,Gj為j產業所占GDP的比重,Ej為j產業從業人力資本占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當DS>0時,表示人力資本不能滿足該產業發展;當DS=0(越接近于0)時,表示該產業的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在數量總量層面完全匹配(越匹配);當DS<0時,表示該產業中已存在的人力資本過多,并將被迫流入其他產業部門。
(2)結構協同適配度。
結構協同適配度反映人力資本適應產業結構變動而自動調整的動態適配能力,其計算公式為:
Md=3j=1Gj*Ej3j=1G2j*3j=1E2j(2)
式(2)中,Md為結構協同適配度,其取值范圍為[0,1]。Md的值越大,表示該城市的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之間的協同性越好,即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變動越具有靈敏的適配性。
2.測算結果
根據《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0—2017年)的原始數據,我們測算了1999—2016年期間不分城市規模和分城市規模條件下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結構偏差系數DS和結構協同適配度Md,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
(1)不分城市規模條件下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的測算結果。
表1顯示,總體上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結構協同適配度Md的均值分別為0.988(接近于1),說明總體上人力資本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偏離度不大,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變動較為靈敏。但進一步分析則會發現,第一、二、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系數均值分別為3.531、0.067和-0.153,說明第三產業逆向偏離結構均衡狀態為15.3 %,亦即第三產業中約有15.3%的人力資本亟待轉向其他產業部門;第二產業對于地方經濟的貢獻水平高出均衡狀態為6.7%,亦即表明在第二產業從業的人力資本還不能滿足當前該行業的發展所需;在第一產業從業的人力資本根本無法滿足該產業的發展,缺額為當前該行業從業人力資本數量的3.5倍多。可見,總體上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的匹配問題是,人力資本從業主要集中于第三產業而很少從業于第一產業,而第三產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水平尚需很大幅度的提升才能吸納當前該行業的從業人力資本數量;第二產業的人力資本卻不能滿足當前該行業的發展所需。
從分地區情況看,東部地區城市和西部地區城市結構協同適配度Md的均值分別為0.994和0.981,說明總體上東部地區城市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變動的靈敏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區城市。具體地說,東部地區城市和西部地區城市第一、二、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系數均值分別為5.306、0.007、-0.097和3.215、0.111、-0.178,盡管東部地區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城市的人力資本均主要從業于第三產業而很少從業于第一產業,但中西部地區城市第三產業吸納當前該行業的從業人力資本所需提升生產效率和創新水平的幅度要遠大于東部地區;雖然在東部地區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城市第二產業從業的人力資本都不足,但東部地區城市第二產業吸納人力資本的能力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城市。
(2)劃分城市規模條件下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的測算結果。
表2顯示,從不分地區不同城市規模的角度看,1999—2016年期間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總體上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的結構協同適配度Md的均值分別為0.975、0.986、0.983和0.997,說明總體上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變動的靈敏度不如特大型城市高。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系數的變化表明上述現象的形成原因在于,人力資本主要集中從業于第三產業而很少從業于第一產業,但第三產業尤其是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第三產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水平尚需很大幅度的提升才能吸納當前該行業的從業人力資本數量。
從分地區不同城市規模情況的角度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特大型城市的結構協同適配度Md的均值分別為0.976、0.995、0.993、0.995和0.974、0.980、0.969、0.998。一方面仍然說明總體上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變動的靈敏度不如特大型城市高;另一方面則說明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人力資本結構的變動對產業結構的變動的靈敏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區同類城市,但對于特大型城市而言,上述情況正好相反。東部地區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城市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系數的變化表明上述現象的形成原因在于:一方面無論東部地區城市還是中西部地區城市,也無論城市規模如何,第三產業尤其是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第三產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水平尚需很大幅度的提升才能吸納當前該行業的從業人力資本數量。另一方面盡管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力資本都不能滿足該產業發展,但東部地區城市第二產業吸納人力資本的能力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城市;對于特大型城市而言,上述情況正好相反,即雖然第二產業從業的人力資本都相對過剩,但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第二產業吸納人力資本的能力要低于中西部地區城市。
二、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影響分析
將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Md)作為一個外生變量引入生產函數,即:
posm為人口密度,表示人口聚集程度。蘇紅鍵和魏后凱認為人口聚集對城市化有著雙重影響,一定程度的人口聚集有利于產業發展升級以及人才的吸引和留存,從而促進城市化;但過度的人口聚集會帶來交通擁堵、房價高漲、環境污染等一系列擁擠效應,不利于城市化[22]。因而人口聚集對城市化影響應該是其正負效應的綜合。我們參照范紅忠等[23]、王珍珍和穆懷中[24]的做法,人口聚集程度用人口密度,即各城市單位土地面積的人口數量來表示(單位:萬人/平方公里)。
open為FDI總額占GDP比值,表示對外開放水平。一個城市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能促進其經濟發展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進而推動城市化的發展[25]。本文采用FDI/以2002年為基期的實際GDP來衡量對外開放水平。其中FDI先以當年匯率折算為人民幣,然后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折算成以2002年為基期的實際值。
road為道路密度的自然對數,代表基礎設施水平。通常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能降低生產和生活成本、提高城市對勞動力和企業的吸引力,從而促進城市化。我們參照王家庭和臧家新[26]的思路,基礎設施水平以道路密度,即年末實有鋪裝道路面積/建城區面積來表示(單位:萬平方米/平方公里)。
houk為房地產開發投資額的自然對數,代表房地產規模。諸多研究表明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創造了大量新城,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化。我們借鑒王家庭和臧家新[26]的做法,用房地產開發投資額來衡量房地產規模,并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指數把其名義值折算成以2002年為基期的實際值(單位:萬元)。
gov為政府財政支出與GDP的比值,代表政府干預程度。在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會積極通過行政力量來提高公共品供給和公共服務水平,以吸引更多優質資源促使當地經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城市化。我們參照袁航和朱承亮[27]的做法,用政府財政支出與GDP的比值來表示政府干預程度。
dh、ds分別是經濟特區或沿海開放城市,直轄市、省會或副省會城市的虛擬變量。這是為了體現沿海地理位置、行政級別對城市化的影響。
此外,δi表示一個城市地理位置、歷史文化等不隨時間變化的固定因素。本文將北京、天津、上海3個直轄市,和隸屬于遼寧、河北、山東、浙江、江蘇、廣東、福建、海南等8個省的地級及以上城市的虛擬變量均設為DD,并取值為1,表示東部地區的城市;把重慶1個直轄市和隸屬于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新疆、寧夏、青海、甘肅、陜西、山西、四川、貴州、西藏、湖北、廣西、江西、云南、湖南、河南、安徽等19個省份的地級及以上城市的虛擬變量均設為DZX,并取值為1,表示中西部地區的城市。DD、DZX主要用于控制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區劃對城市化的影響差異。θt表示一個城市的時間效應,本文將2001、2008和2009年設為1,其他年份均設為0,用于控制中國入世和全球金融危機等宏觀經濟形勢對城市化所產生的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dh、ds以外的其他控制變量、核心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均采取對數形式進行回歸,目的是減少異方差性。
(二)數據來源
我們采集了1999—2016年期間中國東部地區101個、中西部地區186個,總共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作為實證分析的樣本。其中人力資本的數據來自于2000—2017年各城市的統計年鑒,由于各城市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普通高等教育的從業人員數據和畢業生進出城市數據的缺乏,本文以相應的畢業生人數來代替該城市的人力資本;各種價格指數均來自2000—2017年《中國統計年鑒》;其余變量的原始數據均來自2000—2017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表3是不同規模城市條件下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所有城市樣本的回歸結果與分析
本文使用兩步系統GMM方法對所有城市樣本進行回歸,結果列于表4。表4中所有模型的Wald檢驗結果均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表明各模型整體上顯著有效;Sargan檢驗和AR(2)檢驗的統計量所伴隨的P值均大于0.05,分別表明所列模型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是外生的和隨機誤差項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可見,各模型的設定是有效的。
1.總體樣本回歸結果及其分析
表4中的模型(1),是以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的城市作為總體樣本進行回歸的結果。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lnMd的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總體上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與城市化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每提高1%,將帶來28.60%的城市化效應。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就業與產業結構越匹配,即人力資本在產業間流動和工作變動頻繁的現象越少,將越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留存和城市化的穩步發展。
2.分組樣本回歸結果及其分析
表4中模型(2)—模型(5)分別是按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4種不同規模城市進行分組回歸的結果。其中,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lnMd的系數分別為0.280、0.098、0.482和0.533,并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這說明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4種規模城市的城市化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但是這種正向影響在特大型城市最為突出。原因在于: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仍以第二產業占為主導,其次為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但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則更傾向于第三產業就業,而由于受過早地“去工業化”的思想影響,這些城市在規模仍然較小無法支撐過多產業集聚、尚未充分挖掘第二產業潛能的情況下過早過快地發展第三產業,也只能是發展人力資本不愿意進入的低附加值的傳統服務業,因而上述類型城市的第三產業無法全部吸納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就業,這樣造成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相對偏低,人力資本的就業并不穩定、流動性增大。對于特大型城市,繼續增加第二產業比重反而會抑制城市經濟的發展,因而更側重于發展第三產業,形成“三、二、一”的產業發展格局,這迎合了人力資本從業于第三產業為主導的意愿,因而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人力資本對城市化的正向影響會小于特大型城市。
表4中人力資本投資率lnSh的系數在小型城市和中型城市中顯著為負,在大型城市中雖然顯著為正但不如特大型城市突出,這表明人力資本投資率的上升并不一定會促進城市化,原因在于一個城市的人力資本被培養出來還要能被該城市的產業部門所吸收,否則人力資本會流出該城市,不利于城市化。物質資本投資率lnSk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固定資產投資有利于企業的興辦和城市化進程。未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普通高等教育的勞動力lnL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當前中國大多數城市仍以勞動密集型的第二產業為主導,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很大,而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促進了城市化。人口密度lnposm、對外開放度lnopen、道路密度lnroad、政府干預程度lngov、經濟特區或沿海開放城市虛擬變量dh和直轄市、省會或副省會城市虛擬變量ds的系數均為正值,說明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基礎設施的改進、政府干預、沿海區位優勢與城市行政級別的提高均有利于城市化。房地產開發投資額lnhouk的系數在模型(4)和模型(5)中顯著為負,說明在大型城市和特大城市房地產投資額的增加并不會有利于城市化,這主要是因為城市房子數量多但房價過高,是不利于人口向城市聚集和城市化進程的。
(二)不同地區城市樣本回歸的結果與分析
為了考察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影響的地區差異性,我們設置了東部地區城市虛擬變量DD和中西部地區城市的虛擬變量DZX分別與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的交互項DD×lnMd和DZX×lnMd。我們仍舊運用兩步系統GMM方法對式(15)進行估計,結果分別列于表5和表6。其中Wald、Sargan和AR(2)檢驗的結果表明各模型的設計是合理的。
表5中的模型(7)—模型(10)和表6中的模型(12)—模型(15)分別是按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4種城市規模進行分組回歸的結果。在這些模型中,東部地區城市和中西部地區城市的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lnMd的系數大小及其顯著性水平的變化,同樣表明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和特大型城市4種規模城市的城市化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但是這種正向影響在特大型城市最為突出,其原因和所代表的經濟含義類似于表4。另外,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lnMd的系數要大于中西部地區城市;而對于特大型城市情況正好相反。原因在于雖然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力資本均不能滿足該產業發展,但東部地區城市第二產業更發達、其吸納人力資本的能力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城市,因而更有利于城市化進程;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第二產業轉型第三產業的現象比中西部地區城市更為普遍,因而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第二產業吸納人力資本的能力要相對較低,同時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金融、信息等以高新技術為特征的第三產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水平又不能吸納涌入該產業就業的全部人力資本[28],因而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于城市化的正向影響要低于中西部地區特大型城市。
另外,表5和表6中的控制變量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和經濟含義均類似于表4中的回歸結果,不再贅述。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1999—2016年中國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重點考察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影響,結論如下:(1)總體來看,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的提升能促進城市化,但這種促進作用會因城市規模和地區差異而有顯著不同。(2)就不同城市規模來而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的促進作用不如特大型城市突出。原因是除了特大型城市的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占居主導地位以外,其他規模城市仍以第二產業為主,而受“城市規模和第三產業發展呈現正相關”以及“去工業化”思路的影響,人力資本的就業更偏向于第三產業就業,因此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及其對城市化的促進作用要低于特大型城市。(3)就地區差異而言,相對于中西部地區城市,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更有利于城市化進程,但特大型城市則相反。原因在于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第二產業發達程度及其吸納人力資本的能力要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城市;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第二產業轉型第三產業的現象更為普遍,但第三產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水平又無法吸納大量從中西部地區城市涌入東部地區城市并于第三產業就業的人力資本。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的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要注重城市化的可持續性。政府部門和城市發展部門不要盲目城市化,應該充分結合城市自身的產業結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吸引人才的政策,以提升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使城市化發展具有可持續性。
第二,要根據城市規模作好產業發展定位和就業方向定位。除特大型城市以外尤其是小型城市和中型城市,要防止陷入“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陷阱,不應過早過快地“去工業化”而盲目發展第三產業,這類城市應該著力發展、健全第二產業,形成完善的制造業等第二產業集聚效應,一方面形成各產業部門之間和內部、各行業甚至各企業之間的勞動力構成的合理化,另一方面為城市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作鋪墊。教育部門應該引導高校畢業生盡量向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第二產業部門就業,在專業設置和招生方面不應過分地向第三產業專業傾斜,以免對該類城市的第三產業部門形成巨大的就業吸納壓力。而特大型城市要盡量做大做實第三產業,以吸納第三產業當中剩余的人力資本,提高人力資本—產業結構的匹配度。
此外,考慮到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對城市化影響的地區差異,首先,我們要積極鼓勵并引導高校畢業生進入中西部地區城市第二產業就業,甚或進入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的第二產業部門就業,盡量少進入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就業,以更好地提高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匹配度,促進城市化的可持續性。其次,東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在將標準化的、無法產生更多集聚效益的成熟第二產業向中西部城市合理轉移的同時,應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二產業,保證其一定的就業吸納能力;東部地區特大型城市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實現向現代高級服務型第三產業的轉型,以增強其就業吸納能力。中西部地區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應合理布局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積極承接東部地區城市向外轉移的成熟制造業,充分挖掘第二產業發展的潛力,努力形成強大的制造業產業集群和就業吸納能力;中西部地區特大型城市要以強大的制造業等第二產業發展為依托,重點培育能夠吸納大量人力資本的第三產業,改善城市就業狀況。
參考文獻:
[1]岳昌君,周麗萍.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趨勢分析:2003—2017年[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7(4):87-106.
[2]BLACK D,HENDERSON V.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07(2):252-284.
[3]DIAMOND R.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3):479-524.
[4]SIMON C J,NARDINELLI C.The talk of the town: human capital, information,and the growth of English cities,1861 to 1961[J].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1996,33(3):384-413.
[5]陳輝民,徐運保.高等教育、城市化與經濟水平相關性研究[J].現代教育管理,2016(3):32-36.
[6]陳翔,易定紅.人力資本提升對我國城鎮化影響的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7(9):101-112.
[7]CHOY L H T,LI V J.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s inclusive urbanization[J].Cities,2017,60:504-510.
[8]蔡興.教育發展對新型城鎮化水平影響的實證研究[J].教育與經濟,2019(1):35-45.
[9]KUZNETS 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 and spread[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252.
[10]CHENERY H B.Interactions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xports[J].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80,70(2):281-287.
[11]安虎森,陳明.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與我國城市化推進的路徑選擇[J].南開經濟研究,2005(1):48-54.
[12]李春生.城鎮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制與實證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18(1):47-54.
[13]向俊波,陳雯.區域產業結構演變與城市化進程:以江蘇省蘇州市為例的分析[J].中國經濟問題,2001(4):44-48.
[14]馬春輝.中國城鎮居民貧困化問題研究[J].經濟學家,2005(3):75-82.
[15]DOUSSARD M,PECK J,THEODORE N.After deindustrialization:Uneven growth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Postindustrial” Chicago[J].Economic Geography,2009,85(2):183-207.
[16]楊冬民,黨興華.中國城市貧困問題研究綜述與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0(7):81-84.
[17]ANDERSON G,FARCOMENI A,PITTAU M G,et al.A new approach to measuring and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 membership:Examining poverty,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in urban China[J].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16,191(2):348-359.
[18]王春暉. 區域異質性、產業集聚與人力資本積累:中國區域面板數據的實證[J].經濟經緯,2019(1):87-94.
[19]CHENERY H B,ELKINGTON H,SIMS C.A uniform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pattern[R].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Economic Development Report,1970.
[20]霍影,姜穎,籍丹寧,等.人才結構調整與產業結構升級協同適配評價方法研究:高等教育智力支撐視角下以東北三省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4(9):59-63.
[21]陳彥光.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三種模型及其動力學分析[J].地理科學,2011(1):1-6.
[22]蘇紅鍵,魏后凱.密度效應、最優城市人口密度與集約型城鎮化[J].中國工業經濟,2013(10):5-17.
[23]范紅忠,周啟良,陳青山. FDI區域分布差異的市場機制研究:來自中國287個地級以上城市的經驗證據[J].國際貿易問題,2015(4):116-125.
[24]王珍珍,穆懷中.高等教育人力資本與城鎮化發展[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76-85.
[25]陸銘.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M].北京:格致出版社,2013.
[26]王家庭,臧家新.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與城市蔓延:基于我國35個大中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教育與經濟,2017(4):3-8,25.
[27]袁航,朱承亮.西部大開發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了嗎:基于PSM-DID方法的檢驗[J].中國軟科學,2018(6):67-81.
[28]張文武,左飛.產業結構和城市規模對城市減貧的影響:基于中國100個城市的面板數據的分析[J].城市問題,2018(8):12-21.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industrial structure
matching degree on urban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87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ZHOU Qiliang1, FAN Hongzhong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iangxi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Nanchang 330099, P. R.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P. R. China)
Abstract:
How to ensure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s an issue worthy of attention. Generally,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r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 urbanization, but ignores the synergy between them.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7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16, this paper creatively calculates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and then uses two-step system GMM model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industrial structure matching degree on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industrial structure matching degree and urbanization, but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due to the size of citi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sizes’ differen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industrial structure matching degree of small, medium-sized and large cities on urbanization is not as prominent as that of super-large cities.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human capital-industrial structure matching degree of the small, medium and large cities in eastern cities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ization, but for the super-large cities, the situation is just the opposite. The paper urges policy initiativ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ization,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of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direction according to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reg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human capital-industrial structure; matching degree; urbanization; city scale; regional differences
(責任編輯 傅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