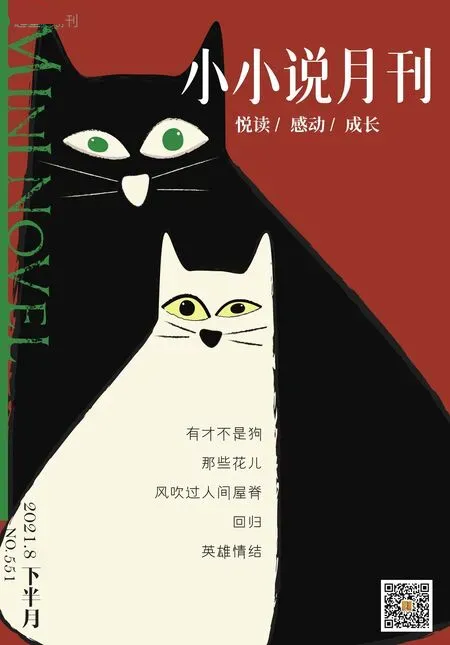說真話的鳥(外一篇)
◇王 溱

小區里有樹。小區里的樹都是圈養的。圈養的樹可招不來好鳥,鳥婆婆決定離家出走。
鳥婆婆當然往西走。唐僧取經就是往西走。西邊既有經書,自然也有講經的人,鳥婆婆想聽他們講一講,兒子到底去哪兒了。
鳥婆婆問過鳥兒,但每只鳥說的都不一樣。
過路的燕子說,你兒子在一個洞穴里呢,那個洞穴黑漆漆的,常年滴著水,可冷了。聽得鳥婆婆狠狠打了個寒顫。
在低空盤旋的魚鷹說,你兒子在海上一艘小船里呢,浪很大,不定什么時候就翻了。鳥婆婆就急了,暈船似的怎么都站不穩。
還是常年在小區最大的鳳凰木上搭窩的小麻雀靠譜些,鳥婆婆問了好幾次,都說你兒子在一個很溫暖的沙灘上躺著曬太陽呢,沙灘上的沙子都是金子做的,太陽一照金燦燦。鳥婆婆追問那可有天使陪著他?那小麻雀就說不來了,撲騰來撲騰去顧著喂巢里的幼崽。
鳥婆婆只好嘆氣,這些鳥兒嘰嘰喳喳能把人說蒙了,真假難辨。
我問奶奶,鳥婆婆干嗎總跟鳥兒說話呀?
奶奶說,要不怎么叫鳥婆婆呢?
她從小就懂鳥語嗎?
奶奶高深莫測地搖頭。她以前可不跟鳥說話,倒是她兒子養著幾只小八哥,整天逗著它們說話。
后來呢?
后來鳥婆婆就悄悄把鳥籠打開了,她可不喜歡兒子整天只對著鳥說話。
那是什么時候?
她兒子還在的時候。
其實我們整個小區的人都知道,鳥婆婆的兒子在幾年前就死了,在河涌里淹死的。小區旁邊那河涌多深呀,常年掛著“水深勿近”的牌子,她兒子怎么還敢下水?他是不識字么?當然我們誰也不敢問,一問鳥婆婆,鳥婆婆就變成童話書里邪惡的巫婆,她干樹枝一樣的手會伸過來捉我們。捉住了可不得了,幸好我們總能從她手里逃脫。每次她都在我們背后尖著嗓子喊,你們這些小泥鰍,萬不能溜去河涌里游泳啊。
言歸正傳。鳥婆婆這次是穿著一件白色底的花衣裳出走的,外頭還套了件透明雨衣。都沒下雨,套什么雨衣?鳥婆婆認真地說,我往西走,很快就會下雨了。我問,你怎么知道?她說是一只鷓鴣鳥說的,那鳥剛從西邊飛來。我很想知道那鷓鴣說的是不是真的,就一路悄悄跟在鳥婆婆身后。
往西走不遠處就是那條河涌。河涌上有橋,鳥婆婆在橋上站了好久才捶捶腿繼續往前走。走過一條街,走過一個小公園,再過去就是郊區了,那里種滿了龍眼樹,滿樹都是白花花的龍眼花,鳥婆婆走得很慢,像個移動鳥窩緩緩地在花間穿梭。
鳥婆婆的頭發很久沒打理過了,亂糟糟確實像個鳥窩。鳥婆婆把頭發在頭頂繞了又繞,這窩就更舒適了。我猜想她是在等一只鳥,一只講真話的鳥。
豆大的雨點從天而降,打在龍眼花上,又打在我身上。果然下雨了呢!我不敢再往前走了,龍眼樹再往前還是龍眼樹,仿佛沒有盡頭。
我狠狠地撞到了樹杈上,捂住額頭蹲在地上。一只手伸過來拉我,是鳥婆婆。她焦急的聲音變了調,你怎么跟來了喲?小孩子哪能自己亂跑喲。
鳥婆婆身上的雨衣套到了我身上,她頭上的鳥窩被雨打歪了,漏下的水沿著她臉上的溝壑一路流到嘴邊,再從她缺了一顆門牙的嘴兩邊往下滴。她說過那門牙是小時候咬甘蔗咬掉的,我當然不信,我也咬甘蔗吃,怎么沒掉?鳥婆婆說不信你問鳥兒,那甘蔗可甜。我嘟嘴,到哪去找一只那么多年前的鳥兒?就算找到了,它也不一定說真話。
鳥婆婆拉著我往前走,地太滑了,我們跌了一跤,我摸了摸門牙,沒掉。前方有一個簡易板搭建的棚子,是看林子的人搭的,我們鉆進棚子底下躲雨。看林子的人急急給我們打來熱乎乎的洗臉水,遞來了干毛巾,又絮絮叨叨說自己的女兒今年要上初中了,歌唱得也賊好……鳥婆婆并沒有過多地寒暄,她的注意力在棚角一只進來躲雨的白色小鳥身上。
我問鳥婆婆這是什么鳥,她不回答我,只顧靜靜地呆呆地看著鳥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這鳥不怕生,慢條斯理地梳,不時發出幾聲低沉的叫聲,像個話家常的老人悠閑地打著毛線。我從鳥婆婆眼睛里看到了從沒見過的光,一種羊脂白瓷器那樣的光澤。
走吧,放晴了。鳥婆婆拍了拍我的后腦勺。
去哪兒?
回家。
你不去找講經的人了?
鳥婆婆說,不去了,那只鳥已經告訴我兒子在哪里了。
我興奮起來,在哪兒?
在一朵柔軟舒適的云上。鳥婆婆說著嘴角微微翹了起來,他的周圍全都是善良的人,勇敢的人。
本文再補充一點說明:概念既然是語言系統任意地切分出來的,不同的語言系統切分出來的概念就沒有完全對等的可能性;但對于“牛”這類有實體指稱的詞而言,不同的系統切分出來的概念剛好就是相同的[15]。陳嘉映指出了其中的原因,“語言系統對概念的區分不是完全任意的。例如自然品類,楊樹、柳樹、松樹等等,它們的分界線差不多是由現實強加給語言的”[9]77。總之,任意性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9]77,索緒爾最終未能將事物從符號中排除出去。
我懷疑這是鳥婆婆糊弄我的,就像糊弄我門牙的事一樣。倒是看林子的人激動地拉著鳥婆婆的手一個勁兒地點頭,對的,對的,好人都是會上天堂的……他還沒說完,鳥婆婆就把我拉走了。我們離開的時候,那只鳥也飛走了。
我問鳥婆婆,你怎么確定這只鳥說的是真話呀?
真話假話有什么所謂呢?鳥婆婆說,其實答案我早就知道了。
捉迷藏
阿云怎么還不來找我?那個啃瓜比誰都麻利的小子哪去了?
我躡手躡腳從衣柜里出來,輕輕拉上柜門。把手上有只蜘蛛對我張牙舞爪,顯然很不滿意我弄破了它的網。
客廳里坐著一個男的,跟我長得蠻像,看見我先是驚愕繼而憤怒:“你終于舍得出來了?!”
他的憤怒讓我心虛,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對我有這么大意見。我捂著鼻子繞過他腳邊一堆垃圾往外溜,尤其是那些發了霉的泡面盒。我要去找阿云,一出門卻看見了阿乖。
阿乖這小子怪得很,每次捉迷藏他都像沒事人一樣在街上閑逛,大搖大擺。他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看,所有的車都躲著我!”的確,車子都長了眼睛,誰也不敢往這個沒長眼睛的人身上撞。
我當然不認同他的邏輯。
阿乖目前掌管著一整間的豬肉檔,他手里的刀正在磨刀棒上揮舞得嚯嚯響。“怎么可能?誰敢捉我。”
旁邊一個買肉的卻壓低聲跟我說:“別聽他吹,他被阿云捉住幾次了,又放了。”
“為什么放?”我也壓低聲音問。
那人反問我:“捉一個根本沒藏起來的人有什么意思?”
我驚訝地看向他,才發現跟我說話的居然是阿民。
這個阿民很能藏的,每次捉迷藏都會藏到一個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一個人形雕塑的后面,或者別人的影子里,總之就是不容易被人發現的,他享受那種在找的人垂頭喪氣時突然從他身后跳出來的快樂,而且每次都能得逞。阿民讀的書比我多,比我聰明那是一定的。

“你被阿云捉住了嗎?”我問他。
阿民有些不高興,他糾正我說:“我怎么可能被捉到,是我自己跳出來嚇他的。”
我表示很羨慕,“我也想跳出來嚇他,可他還沒有來找我。”
“所以你還躲著?”
“對。”
他豎起大拇指,“你真能躲,這都三十年了。”
我有些得意,“小意思,我還可以再躲三十年。”
“阿云會不會已經忘記要找你了?”
“不可能,”我認真地說,“我們拉過勾的。他只是還沒有找到我而已。”
阿民大笑,“但愿吧。”
我向他打聽阿云在哪里,阿民抬頭看天,有些為難的樣子。“這不好說,”他踢著那雙亮得反光的皮鞋說,“有時他在股市里,有時他在超市里,有時在這個市里,有時又在隔壁市里……你知道,他做什么都很快的。”
我想起阿云用一分鐘啃完半個瓜滿嘴滴紅汁的樣子,點點頭表示贊同。
“所以你還是等吧,找他可不好找。再說了,按照游戲規則,也應該是他找你的。”
這點我認同,我一向最遵守規則的。但我在衣柜里也確實待煩了,我問阿乖和阿民愿不愿意撇開阿云重新玩一次捉迷藏,他們還沒開口呢,倒是有兩個女人急匆匆跑過來了。
“誰也不許跟那個躲在衣柜里的男人玩捉迷藏!”她們嚴厲地警告她們的丈夫。
我很生氣,她們這樣說讓我很沒面子。我狠狠地瞪著她們表示抗議,但她們已經不再理會我了,只顧著相互炫耀她們新買的首飾。瞧,阿乖老婆脖子上掛著的珍珠有鵪鶉蛋那么大。
我很想聲明點什么,可又拿她們沒辦法。阿乖和阿民看起來十分聽她們的話。
我只好氣鼓鼓回家,那個跟我長得很像的男人依舊在客廳坐著,手里依舊捧著手機。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回到柜子里去的。”那男人輕蔑地看了我一眼。
我嘟囔道:“游戲還沒有結束!”
“算了吧,”他冷笑了一下,“那破衣柜不過就是一個消磨時間的無底洞。”
對于他這樣的評價我很難過。我憤憤地躲進衣柜里,衣柜雖然破,但隔音很好,世界終于清靜了,聽不到任何傷人的話。倒是他玩手機的聲音一直在響,好像可以穿透衣柜,好像怎么玩都不會沒電似的。
我在衣柜里又待了些日子,或許一天,或許一年,阿云還是沒找到我。我怕他不好找,故意弄出了點聲響,但阿云還是沒找到我。我突然有點害怕,他會不會一輩子都找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