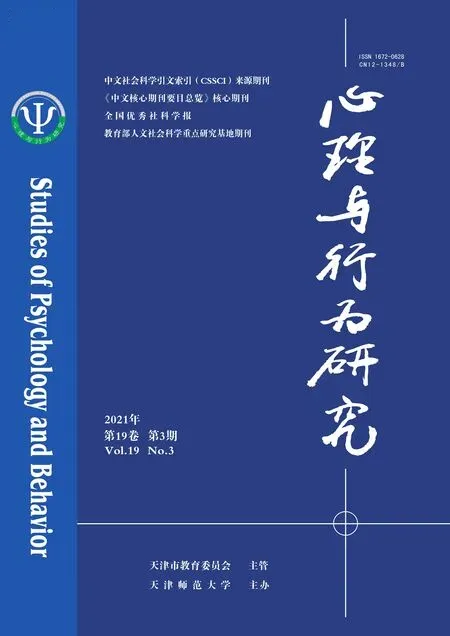父母教養方式與隨遷兒童問題行為關系的交叉滯后分析*
馬玲玲 余鴻燕 范為橋 孟 小
(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上海 200234)
1 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大量農村居民遷移到一、二線城市工作和生活,其子女也遷移到相應的城市,形成了隨遷兒童這一特殊群體。在城市兒童中,隨遷兒童所占比例不斷增加,甚至超過城市原住兒童(上海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 2017)。以往研究顯示,隨遷經歷對兒童心理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生活環境的巨變往往會導致家庭功能障礙和不良的兒童心理結果(Stevens & Vollebergh, 2008)。鑒于隨遷兒童人口比例的增加,他們的心理發展與社會適應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社會發展的和諧與健康。
然而,由于隨遷兒童面臨的處境相對不利,他們可能需要面對教育政策的不公、城市原住兒童的歧視性目光和侵害行為(方曉義, 范興華, 劉楊, 2008)以及各種社會適應問題。由此導致這一兒童人群往往表現出較為嚴重的內化(如抑郁、焦慮等)與外化(如攻擊、違紀等)行為問題(李夢婷, 范為橋, 陳欣銀, 2018; Hu, Lu, & Huang,2014)。此外,由于家庭經濟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隨遷兒童很可能由父親或母親單獨撫養,居住條件相對較差,使其家庭系統功能受到不良影響(金燦燦, 劉艷, 陳麗, 2012)。
Lerner(2007)的發展情境理論強調個體與其所處情境的動態相互作用,并加入時間維度,提出了個體發展的循環作用模式。Chen和Schmidt(2015)的情境交互發展模型則具體強調了兒童和其生態環境(文化、父母、同伴等)的互動過程,認為兒童可能會因為得到重要他人的認可而強化自己的行為,同時兒童行為的變化也會導致重要他人對其評價的變化。本研究基于以上論述,從微觀生態環境視角探討父母教養方式等家庭因素與隨遷兒童行為的相互關系,這對于深入理解并有效地促進隨遷兒童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Baumrind(1971)的教養方式理論,溫暖和控制是最為典型的教養方式。父母溫暖是指通過對兒童需要的敏感、支持和關愛來表現父母的接受(Landry, Smith, & Swank, 2006),它被認為是影響兒童問題行為的有力預測因素(Rothenberg et al., 2020)。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溫暖屬于積極的教養方式,與問題行為之間存在負相關(Yeung &Leadbeater, 2010)。Park和Dotterer(2018)也發現父親溫暖會負向預測其子女一年后外化問題行為水平。
控制是指父母試圖通過監督、限制和建立家規等方式來管理兒童的行為(Barber, Olsen, & Shagle,1994)。隨遷兒童父母的教養方式中,過分干涉、懲罰壓力的頻率相較于城市兒童更多。武萌、陳欣銀、張瑩、盧珊和王爭艷(2018)發現母親的強制性控制策略能夠顯著負向預測男孩的不順從行為;Bayer,Sansonb和Hemphill(2006)則發現父母控制會正向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行為。但是這些研究僅考慮了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問題行為的影響,而忽略了兒童行為對父母教養方式的反作用。
少數縱向研究采用交叉滯后設計探究了父母教養方式和兒童問題行為間的相互關系(呂勤, 陳會昌, 王莉, 陳欣銀, 2002; Barbot, Crossman, Hunter,Grigorenko, & Luthar, 2014),發現兒童行為一定程度上也能影響甚至塑造父母的教養方式(Hoeve et al., 2009)。Barbot等對361位美國低收入家庭母親進行間隔5年的2次追蹤研究中發現,母親教養方式(行為控制、卷入、拒絕)和母親所感知的兒童問題行為之間存在交叉滯后關系。一項間隔2年的2次追蹤研究也證實了父母教養方式(父親懲罰、母親懲罰)與兒童在2~4歲時的外化問題行為之間的交叉滯后關系(呂勤等, 2002)。
然而,以往在研究父母教養方式與子女行為時,往往將父親與母親教養方式合并為父母教養方式。有研究發現父親和母親即便采用同樣的教養方式,也可能會對兒童的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最終導致兒童不同的發展結果;事實上,父母親所采取的教養方式相似度很低(Winsler, Madigan, &Aquilino, 2005)。有研究發現母親過度保護能夠顯著預測子女的內外化問題行為,而父親過度保護對子女內外化問題行為的預測作用卻不顯著(Berkien,Louwerse, Verhulst, & van der Ende, 2012)。有鑒于此,本研究采取追蹤設計方法,以6年級的隨遷兒童為被試,以Baumrind(1971)經典的教養方式模型為參照,分別探究父親、母親的教養方式與兒童問題行為的動態作用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1)父母溫暖和行為控制與隨遷兒童問題行為之間存在交叉滯后作用;(2)上述交叉滯后效應在父親和母親教養方式之間差異顯著。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來自上海市4所公立中學的477名六年級學生(隨遷兒童)參與了本研究。其中,男生占比57.10%,平均年齡為11.54歲(SD=0.64歲)。2014年12月進行第一次施測。隨遷兒童平均流動時長為8.60年(SD=3.27年)。兒童被試的家庭中,有87.50%的父親和79.96%的母親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高中或中專及以上的父母人數占比分別為42.95%和31.21%;收入在3000~10000元之間的父母人數占比分別為64.37%和53.19%。
第二次施測(2015年11月)和第三次施測(2016年10月)人數分別為303名、208名。被試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兒童由于戶籍限制轉學回到戶籍所在地。MANOVA分析結果表明,完整參加3次施測與未完整參加3次施測的隨遷兒童在T1的父母教養方式和問題行為上無顯著差異。此外,流失被試與完成研究被試在性別、隨遷時長、父親收入上無顯著差異;流失被試相比完成研究被試在父母教育水平、母親教育水平和母親收入上更低。
2.2 研究程序
問卷調查以班級形式進行團體施測。施測均征得學校領導及老師的同意,參與調查的學生填寫知情同意書。主試在自習課上發放問卷,測試時間約為30分鐘,所有問卷當場回收。每名參與調查的兒童均在第一次施測時收到了一本兒童文學讀本作為答謝。
2.3 研究工具
2.3.1 隨遷兒童問題行為
采用Achenbach和Rescorla(2001)編制的青少年自評量表評估問題行為;其中,外化問題15題,內化問題16題。采用3級評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計0~2分。分數越高,表示兒童的問題行為越多。本研究中三次施測的外化問題行為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0.85,0.85;內化問題行為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0.90,0.92。
2.3.2 父母教養方式
采用Schaefer(1965)編制,Chen,Liu和Li(2000)修訂的教養行為問卷中文版評估教養方式。其溫暖維度包括5個項目,如“我父親/母親和我在一起度過了很多愉快而又親密的時光”。控制維度分為行為控制和心理控制,以往研究發現父母對青少年的行為控制水平高于心理控制水平(Manzeske & Stright, 2009)。考慮到被試完成測驗的時間限制,本研究僅考察了行為控制。行為控制維度包括5個項目,如“當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父親/母親總想知道我在干什么”。該問卷采用5級評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計1~5分。分數越高,表示父母親使用該種教養方式的程度越高。母親教養方式三次施測的Cronbach’s α系數在0.63到0.89之間,父親教養方式三次施測的Cronbach’s α系數在0.72到0.85之間。
2.4 數據分析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考察共同方法偏差。結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22個,首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14.79%,遠小于40%,說明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SPSS22.0進行描述統計以及使用Mplus7.4進行交叉滯后分析。采用全息極大似然估計法來處理缺失值。
以往研究發現,性別和家庭經濟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父母教養方式和個體問題行為(張茜洋等, 2017)。隨遷時長會影響兒童對遷入城市的社會認同水平,從而影響其社會適應狀況。本研究將性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及隨遷時長作為控制變量。
3 結果
3.1 父母教養方式、隨遷兒童問題行為的描述性統計
表1 報告了研究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以時間(T1、T2、T3)和父母(父親、母親)為被試內變量,性別(男、女)為被試間變量,父母教養方式為因變量,多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時間0.11]、父母[Wilks’ Λ=0.93,F(3, 171)=4.33,p<0.01,主效應顯著,性別[Wilks’ Λ=0.99,F(3,的主效應不顯著,未發現各因素間有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表明,母親行為控制顯著高于父親行為控制T1的父母溫暖顯著高于和

表1 父母教養方式和隨遷兒童外化、內化問題行為的描述性統計(M±SD)
將性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隨遷時長作為控制變量,對三次收集的父母教養方式和隨遷兒童問題行為進行偏相關分析(見表2)。其中T1、T2、T3的父親溫暖、母親溫暖與兒童內外化問題行為均顯著負相關,除T3的父母控制與兒童內外化問題行為相關不顯著外,T1、T2的父母控制與兒童的內外化問題行為均顯著正相關。

表2 父母教養方式和隨遷兒童外化、內化問題行為的偏相關分析
3.2 父母教養方式與隨遷兒童問題行為的交叉滯后分析
由于父親、母親的教養方式差異顯著,因此后續分析將分為父親和母親兩個模型進行。為檢驗變量之間的跨時間一致性,本研究比較允許路徑跨時間不一致模型(非限制模型)和限制路徑跨時間一致模型(限制模型)差異是否顯著。相關文獻指出,非限制模型與限制模型之間差異顯著的標準是:Δχ2(p<0.05),ΔCFI≥?0.01,ΔRMSEA≥0.015(Negru-Subtirica, Pop, & Crocetti, 2015)。本研究中父親非限制模型與限制模型的比較結果為:Δχ2(14)=12.75,p>0.05,ΔCFI=0.00,ΔRMSEA=0.004。母親非限制模型與限制模型比較結果為:Δχ2(40)=37.45,p>0.05,ΔCFI=0.00,ΔRMSEA=?0.004。因此,本研究選擇更簡潔的路徑跨時間一致模型(限制模型)。
為探究父親、母親教養方式與子女問題行為的相互作用是否存在差異,限制父親、母親教養方式與子女問題行為相互作用的路徑系數一致,比較限制模型與非限制模型擬合指數的差異。結果表明,父親、母親教養方式與子女問題行為的相互作用存在顯著差異,Δχ2(24)=37.24,p<0.05,ΔCFI=0.01,ΔRMSEA=?0.002。此外,為探究父母教養方式與問題行為之間是否存在性別差異,進行了多組比較。結果表明,父親、母親的模型性別差異均不顯著,即父親、母親的教養方式與兒童問題行為的關系不存在性別差異。其中,父親的非限制模型(允許男生、女生路徑不一致)和限制模型(限制男生、女生的路徑一致)的比較結果為:Δχ2(8)=15.98,p>0.05,ΔCFI=0.01,ΔRMSEA=?0.003,母親的非限制模型和限制模型的比較結果為:Δχ2(8)=15.99,p>0.05,ΔCFI=0.00,ΔRMSEA=0.004。
最終,父親的模型擬合結果:χ2/df=1.22,CFI=0.96,RMSEA=0.031,SRMR=0.063。母親的模型擬合結果:χ2/df=1.25,CFI=0.98,RMSEA=0.041,SRMR=0.063。如圖1所示,T1、T2的母親溫暖分別負向預測T2、T3的外化問題行為。T1、T2的外化問題行為分別負向預測T2、T3的母親溫暖。如圖2所示,T1、T2的父親溫暖分別負向預測T2、T3的外化問題行為。T1、T2的外化問題負向預測T2、T3的父親溫暖,T1、T2的父親行為控制分別正向預測T2、T3的內化和外化問題行為。

圖1 母親的溫暖、行為控制與兒童內外化問題行為的交叉滯后分析結果

圖2 父親的溫暖、行為控制與兒童內外化問題行為的交叉滯后分析結果
4 討論
4.1 父母溫暖、行為控制及隨遷兒童問題行為隨時間的變化趨勢
研究表明隨遷兒童感知到的父母溫暖隨著時間的變化呈下降趨勢,具體為父母溫暖在T2得分顯著低于T1,T2與T3無明顯差異。感知到的父母行為控制在T2時間點上也有下降的趨勢但差異不顯著。這與以往研究一致,父母教養方式會隨兒童的年齡發生變化(陳鐘奇, 劉國雄, 王鳶清, 2019;Barber, Stolz, Olsen, Collins, & Burchinal, 2005)。一方面,在父母看來,這一時期隨遷兒童面臨從小學到初中的轉變,需要學習獨立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父母可能適當減少強制性的要求;另一方面,隨遷兒童進入初中階段,自我意識增強,同伴關系的重要性在初中階段不斷發展,可以在同伴處獲得溫暖與支持,減少對父母的依賴。
父母教養方式和隨遷兒童問題行為三次測量得分均各自相關顯著,父母溫暖和隨遷兒童內化問題分別具有較高的相關,說明父母溫暖與內外化問題隨時間變化具有一定的穩定性;而父母行為控制三次測量得分的相關相對較低,可能與隨遷兒童家庭的“流動”特點有關,管教和監督在一定意義上需要家長花費一定的時間與精力,而隨遷兒童父母多半為進城務工人員,工作變動頻繁加上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從而導致父母的行為控制穩定性相對較低。
4.2 父親、母親溫暖與隨遷兒童問題行為的交叉滯后作用
本研究結果表明父母雙方溫暖的教養方式與隨遷兒童外化問題行為之間存在負向的交叉滯后效應。一方面,隨遷兒童父母越多采用溫暖的教養方式,其子女的外化問題行為越少,這與以往一般兒童的研究一致(Berkien et al., 2012; Park &Dotterer, 2018)。這說明無論兒童來自什么樣的家庭背景,父母雙方溫暖型的教養方式都具有保護和促進兒童健康成長的作用。
另一方面,隨遷兒童外化問題行為對父母溫暖具有反向塑造作用,即子女外化問題行為較多時,父母表現出較低的溫暖教養水平。可能由于隨遷家庭的父母相對一般家庭的家長面臨更多的生活與工作壓力,因此在面對子女較高水平的外化問題行為時,他們很難用溫暖和關心的態度來處理。換言之,隨遷兒童較高水平的問題行為很可能會引起父母不滿和失控感,甚至敵意(Carrasco,Holgado, Rodríguez, & del Barrio, 2009),進而減少父母溫暖教養方式的使用。盡管隨遷兒童的父母面臨著異于一般父母的壓力,但是,作為成年人,也應顧及和體諒子女同樣面臨著異于城市兒童的學習與社會適應壓力,使用更為積極的教養方式促進子女的健康成長。
關于溫暖型教養方式與內化問題行為的關系,以往針對一般兒童的研究都發現父母溫暖可以減少兒童內化問題行為(劉廣增, 張大均, 羅世蘭, 房立艷, 2018)。例如,劉朔、劉艷芳、王思欽和劉紅升(2015)發現母親溫暖有助于減少隨遷兒童內化問題行為。但是本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這或許提示了隨遷兒童群體及其父母的特殊性。一種可能是,父母相對弱勢的社會經濟地位導致其對子女的關心也停留在相對外在的行為,而不能深入了解和關心子女的內化問題。
4.3 父親、母親行為控制與隨遷兒童問題行為的關系
本研究發現父親行為控制導致兒童出現更多內外化問題行為,而母親行為控制對兒童問題行為的作用卻不顯著。這印證了父親和母親的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影響是不一樣的(Berkien et al.,2012)。從家庭系統理論的角度來解釋,行為控制可能會通過影響親子關系質量從而影響兒童的問題行為(Cowan, Cohn, Cowan, & Pearson, 1996)。由于行為控制涉及到限制、監督等策略,因此父母行為控制可能會影響親子關系質量,導致親子間的沖突。與本研究的結果一致,有研究發現父親與子女間的沖突能夠正向預測內外化問題行為,而母親與子女間的沖突對子女的問題行為沒有預測作用(Hakvoort, Bos, van Balen, & Hermanns,2010)。對于隨遷兒童家庭而言,可能因為母親在家庭中作為主要的照顧者,而父親作為家庭的領導角色所展現的控制行為對兒童的影響更為明顯。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父親控制對兒童問題行為具有顯著預測作用,也進一步說明有必要分別考察父親和母親教養方式對兒童行為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未發現內外化問題行為對父親行為控制的預測作用,即在行為控制與問題行為關系中只存在父母效應,而子女效應不顯著。這與Rothenberg等(2020)通過元分析得出教養方式與問題行為關系中子女效應高于父母效應的結論不一致。一方面可能與本研究的被試群體有關。以往研究表明,由于生存壓力大,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及自身教育理念的限制,隨遷兒童父母表現出“單行原則”的教養方式。另一方面可能與文化有關。在中國,無論經濟地位高低,家長都對孩子的教育抱有較高期待、過分關注學業成績。因此學業成績可能在其中作為額外變量影響兒童行為與父母的監督和控制的關系。
4.4 不足與展望
由于研究條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本研究僅僅關注了隨遷兒童。事實上,他們在城市生活適應中最直接的關聯對象是城市原住兒童。已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城市兒童,隨遷兒童父母的教養方式更為消極(張茜洋等,2017)。但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隨遷兒童父母的教養方式中得分較高的是溫暖型。此外,隨遷兒童和城市兒童的發展與父母教養方式之間關系的差異也存在一定爭議(武萌等, 2018; 張茜洋等,2017)。因此若能將隨遷兒童和城市兒童父母教養方式與問題行為間的關系模型進行對比,或許更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
其次,本研究僅考察了父母的行為控制與兒童問題行為之間的關系。Barber等(1994)認為父母心理控制、行為控制分別預測子女內化和外化問題行為。Lansford,Laird,Pettit,Bates和Dodge(2014)也發現父母心理控制、行為控制均能顯著預測子女內外化問題行為的變化。未來研究可以深入比較父母的行為控制與心理控制對子女內外化問題行為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
5 結論
本研究支持了父母溫暖型教養方式與隨遷兒童的外化問題行為之間的交叉滯后作用,并且相較于父母行為控制,隨遷兒童更多感受到的是父母溫暖。此外,研究也發現父親行為控制能夠正向預測隨遷兒童內、外化問題行為,而母親行為控制的作用則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