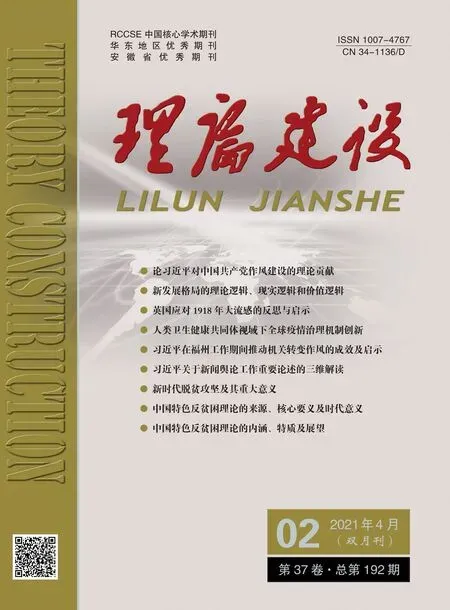長三角區(qū)域文化資源整合及軟實(shí)力提升研究
尹維杰,項(xiàng)曉艷
(中共長興縣委黨校,浙江 湖州313100)
隨著長三角經(jīng)濟(jì)活力的持續(xù)釋放以及區(qū)域內(nèi)工業(yè)化、城市化進(jìn)程的強(qiáng)勢推進(jìn),“長三角一體化”再度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guān)注。2018年11月,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jìn)口博覽會上宣布,“支持長江三角洲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并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著力落實(shí)新發(fā)展理念,構(gòu)建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jì)體系,推進(jìn)更高起點(diǎn)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1]。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長江三角洲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標(biāo)志著“長三角一體化”開始從一個(gè)地區(qū)性構(gòu)想正式升級為國家戰(zhàn)略,長三角地區(qū)承載的歷史使命、責(zé)任必將更為重大。從地緣結(jié)構(gòu)來看,長三角地處環(huán)太湖沿岸,地跨長江經(jīng)濟(jì)帶,涵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也即通常意義上的“三省一市”。近年來,長三角地區(qū)以占全國1/26 的土地、占全國1/6 的人口,產(chǎn)出了全國1/4 的GDP、1/4 的財(cái)政稅收、1/3 的進(jìn)出口貿(mào)易和58%的外資利用額,長三角已成為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chuàng)新能力最強(qiáng)的區(qū)域之一,在國家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大局和全方位開放格局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gè)國家、一個(gè)民族的靈魂。”在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之時(shí),長三角地區(qū)便肩負(fù)起了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重大使命。長三角一體化建設(shè)不單單是各個(gè)城市的堆砌、經(jīng)濟(jì)資源的集聚以及產(chǎn)業(yè)集群在城市地域空間的密布,更是涉及歷史、文化、制度、服務(wù)等領(lǐng)域的復(fù)雜性工程。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并非要抹殺文化的自我認(rèn)同感,如果地域“人格”過于強(qiáng)烈、張揚(yáng),將對一體化發(fā)展產(chǎn)生沖突和碰撞,從而削弱城市發(fā)展的內(nèi)在功能。長三角文化精神是長三角地區(qū)在區(qū)域競爭乃至全球角逐中制勝爭優(yōu)的“軟實(shí)力”,集中反映了“長三角人”的精神風(fēng)貌、觀念心態(tài)、人格風(fēng)范,著力點(diǎn)在于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推動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又好又快發(fā)展,其落腳點(diǎn)在于社會秩序和諧穩(wěn)定。區(qū)域一體化建設(shè)最終目的、歸宿并不僅僅是追求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卓越,而是要在這一動態(tài)化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實(shí)現(xiàn)區(qū)域經(jīng)濟(jì)社會的協(xié)同發(fā)展,從而為實(shí)現(xiàn)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現(xiàn)實(shí)保障、物質(zhì)供給[2]。
一、緣起:長三角一體化興起的歷史文化底蘊(yùn)
馬克思認(rèn)為:“人創(chuàng)造了環(huán)境,同時(shí)環(huán)境也在創(chuàng)造人。”區(qū)域文化是由不同人群在不同時(shí)期創(chuàng)造的,帶有鮮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時(shí)代性烙印。長三角地區(qū)文化底蘊(yùn)深厚、遺產(chǎn)資源豐富、歷史跨度長。據(jù)馬家浜文化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一萬年前,江南地區(qū)便已擁有較高的文明程度,人們在長期生活實(shí)踐中逐漸養(yǎng)成了勤勉、機(jī)敏、堅(jiān)韌、崇文、重商等文化個(gè)性,塑造了特有的文化心理、人格風(fēng)范、價(jià)值理念。
(一)開放包容、外柔內(nèi)剛
梁啟超曾言:“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依美學(xué)來看,長三角文化主要是水文化,充滿詩性、藝術(shù)和審美情趣,主動融合、浸潤、和諧是水的基本特質(zhì),千年中華文明史主要是水文化發(fā)展史。從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中,都可以發(fā)現(xiàn)水文化帶來的恩賜,水文化折射的柔性品質(zhì),印證了長三角文化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主要體現(xiàn)為兩點(diǎn):一是對城市移民的依附,二是對外來文化的容納。明清之際的蘇州,其府城的“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寧、太平、寧國人氏……總計(jì)約有二萬余人”[3]。開埠以來的上海,更是圈粉無數(shù)海內(nèi)外移民,世人皆以“遠(yuǎn)東第一大都市”代稱之。同時(shí),這種文化的發(fā)展與異域文化的學(xué)習(xí)、交流以及融合不可分割。史料記載,吳立國之始乃因太伯奔吳,吳越文化交流,乃至吳越文化的融合足以說明這一問題。六朝時(shí)期,佛教在江南的迅速發(fā)展以及唐代禪宗在江南的廣泛傳播也印證了江南文化的開放性。特別是以魏晉為主導(dǎo)的中原移民攜其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上的優(yōu)勢,與長三角原有的文化發(fā)生激烈沖突、碰撞和趨同、整合[4],令長三角文化既“柔情似水,又“無堅(jiān)不摧”。依托這種強(qiáng)大的文化力,長三角地區(qū)以自我文化為核心,理性接納各種外來文化,使得長三角地區(qū)不僅成為經(jīng)濟(jì)增長極,更成為“文化核心圈”。
(二)經(jīng)世務(wù)實(shí)、義利并重
從唐代的“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宋代的“蘇湖熟,天下足”、明末清初的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萌芽到近代實(shí)業(yè)家的蓬勃發(fā)展,再到今天長三角城市群的不斷壯大,足以印證長三角地區(qū)重商主義的人文傳統(tǒng)。吳文化中的重商主義特質(zhì)和商品意識,使得蘇南民眾具有超強(qiáng)的對商品經(jīng)濟(jì)的天然適應(yīng)情節(jié),并逐漸養(yǎng)成了聰慧勤勞、儒雅細(xì)致、心靈手巧、包容開放的競爭意識,“蘇南模式”應(yīng)運(yùn)而生[5]。同傳統(tǒng)儒學(xué)文化中講究“義在利先、舍生取義”相區(qū)別的浙東學(xué)派推崇“工商皆本、義利并重”,講究事功主義、務(wù)實(shí)進(jìn)取。明末清初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客,工商皆本”的觀念主張,亦表明江浙一帶已經(jīng)開始向理性主義的商品意識轉(zhuǎn)變,從事商業(yè)活動成了市民生活的常態(tài)。這種重商主義的精神傳統(tǒng)直接促成了“雞毛換糖”的義烏模式、“走南闖北”的溫州模式,并為改革開放后鄉(xiāng)鎮(zhèn)民營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壯大積淀了豐富的文化財(cái)富,也對浙江經(jīng)濟(jì)體制變遷的轉(zhuǎn)軌產(chǎn)生了深刻的作用[6]。徽學(xué)文化在受程朱理學(xué)、桐城學(xué)派在受“嚴(yán)謹(jǐn)治學(xué)、格物致知、崇文重教”思想影響的同時(shí),在與江南文化的長期浸潤、碰撞轉(zhuǎn)型過程中,還逐漸養(yǎng)成“敢為人先、大膽探索”的首創(chuàng)精神。上海“海派文化”作為長三角文化中的地標(biāo)性文化,在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移民文化的浪潮影響下,秉承吳越文化優(yōu)點(diǎn),在張揚(yáng)時(shí)尚、開放多元的城市建設(shè)過程中不斷孕育出創(chuàng)意無限的文化個(gè)性和魅力。
(三)敢想敢試、大膽創(chuàng)新
長三角的文化精神是長三角在區(qū)域綜合競爭中具有優(yōu)勢的“軟實(shí)力”,集中反映了長三角人的精神風(fēng)貌、人格風(fēng)范、心理態(tài)勢。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diǎn),每個(gè)時(shí)代的“精神”都與其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存在著某種內(nèi)在的淵源關(guān)系[7]。同自然經(jīng)濟(jì)條件下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習(xí)俗相比,長三角文化格外注重人欲,重視家庭和家族的血緣親情關(guān)系,批判傳統(tǒng)理學(xué)家的禁欲思想。例如泰州學(xué)派的李贄堅(jiān)決反對傳統(tǒng)“男尊女卑”等級秩序,強(qiáng)烈抨擊理學(xué)家鼓吹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倡導(dǎo)正常的人倫物理。由于中原地區(qū)的商周文化、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東南沿海的越文化、山東半島的齊魯文化影響,歷經(jīng)南北文明的多次交流、碰撞、融合,長三角地區(qū)產(chǎn)生了許多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文化基因。“在傳統(tǒng)浙學(xué)文化中,創(chuàng)新冒險(xiǎn)精神是浙江文化最顯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機(jī)和創(chuàng)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力量。”[8]習(xí)近平主政浙江期間在談及浙江現(xiàn)象時(shí)說:“浙江人的這種‘文化基因’,一旦遇到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必然‘一有雨露就發(fā)芽,一有陽光就燦爛’,迸發(fā)出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極大地推動著生產(chǎn)力的解放和發(fā)展。”習(xí)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如此強(qiáng)調(diào)創(chuàng)新,是因?yàn)樗羁桃庾R到創(chuàng)新是一個(gè)地區(qū)持續(xù)發(fā)展的不竭動力,也說明創(chuàng)新更是一個(gè)地方引人入勝的“女神”[9]。長三角文化并不是一種原封不動的文化傳統(tǒng),而是既傳承過去又與時(shí)俱進(jìn)、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新傳統(tǒng)”,是一種“當(dāng)今時(shí)代精神”的有機(jī)集合。
二、困境:長三角區(qū)域文化資源整合及軟實(shí)力提升面臨的挑戰(zhàn)及機(jī)遇
(一)區(qū)域協(xié)同與行政壁壘的對立
文化認(rèn)同程度影響著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文化凝聚力,決定著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基本動力。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的行政壁壘主要在于中央劃定的“一體化”發(fā)展邊界與滬蘇浙皖之間的主體職責(zé)邊界發(fā)生了沖突。具體而言,造成壁壘的原因,從主觀上看是各行政主體的價(jià)值取向不同,就客觀來說,各主體有不同的職責(zé)邊界,這些職責(zé)邊界和一體化的共同目標(biāo)難免產(chǎn)生沖突、對抗[10]。基于相似的資源稟賦、人文地理,長三角各城市間文化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布局雷同、同質(zhì)化現(xiàn)象較為明顯。
當(dāng)前,長三角主導(dǎo)產(chǎn)業(yè)布局往往與主體發(fā)展期待相呼應(yīng),主要是為提高經(jīng)濟(jì)效益、品牌效益,裝備制造、電子信息、汽車等項(xiàng)目集聚效應(yīng)最為突出,而沒有考慮一體化進(jìn)程中的文化產(chǎn)業(yè)協(xié)同。另外,一些政策領(lǐng)域又存在跨區(qū)界溢出效應(yīng)與行政轄區(qū)的邊界沖突,影響了資源的合理分配。在文化市場開放、生產(chǎn)要素整合、文化遺產(chǎn)資源配置等方面還存在各種地方保護(hù)主義,易把他方發(fā)展訴求“拒之門外”。比如2002年,浙江寧波與江蘇宜興關(guān)于“梁祝文化爭奪戰(zhàn)”就暴露了長三角區(qū)域內(nèi)部文化資源整合的無序、雜亂,凸顯了區(qū)域行政壁壘在一體化中的制度瓶頸。
(二)資本評價(jià)與文化價(jià)值的對立
資本對于文化的評判價(jià)值與文化自身的客觀價(jià)值會有很大不同,資本強(qiáng)調(diào)的是能夠帶來增值的文化形態(tài)和文化項(xiàng)目,要求能夠帶來短期效益的產(chǎn)業(yè)形態(tài)。按照這種內(nèi)在邏輯,它就會更為推崇、提倡關(guān)于時(shí)尚文化、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渲染,而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就會逐漸減弱。若沒有超越短期利益的長遠(yuǎn)追求,以江南文化為內(nèi)在支撐的長三角城市群就可能失去獨(dú)特的文化標(biāo)識和民眾賴以生存的文化精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和排頭兵,長三角文化市場也不可避免帶有了“文化功利主義”“文化商品主義”等資本誘導(dǎo),打亂了文化事業(yè)投入與產(chǎn)出的因果鏈條。比如青年群體對流行歌曲的追捧,對黃梅戲等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漠視,以及安徽皖南地區(qū)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對傳統(tǒng)徽派民居的破壞等就是生動例證。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qiáng)調(diào):“人類文藝發(fā)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粗制濫造,不僅是對文藝的一種傷害,也是對社會精神生活的一種傷害。”[11]面對城市現(xiàn)代化的圍攻、堵截,南京珍貴的古城墻屢屢被毀,以致江蘇省人大不得不通過《南京城墻保護(hù)條例》等法規(guī)來應(yīng)對。任由資本主導(dǎo)文化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不僅會侵犯人們的生活世界,更容易剝奪老祖宗建立已久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導(dǎo)致文化內(nèi)涵的喪失。
(三)功能阻滯與區(qū)域創(chuàng)新的對立
由于行政壁壘、部門分割、本位主義等主體約束,長三角文化創(chuàng)新要素市場流動性不足。“盡管長三角地區(qū)很早便啟動了關(guān)于區(qū)域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文化實(shí)踐,但區(qū)域創(chuàng)新機(jī)制與創(chuàng)新制度、規(guī)則等領(lǐng)域存在文化斷層,致使各自創(chuàng)新資源與特色優(yōu)勢難以實(shí)現(xiàn)優(yōu)勢互補(bǔ)、功能互動。”[12]在新產(chǎn)品科技“研發(fā)、生產(chǎn)、加工、制造”新興產(chǎn)業(yè)鏈條上,“三省一市”未能就此構(gòu)建和而不同的區(qū)域協(xié)同創(chuàng)新體系,這主要還歸咎于各地之間忽視了文化上的同根同脈,進(jìn)而誘發(fā)各地出現(xiàn)地方創(chuàng)新中的排他性。
根據(jù)表1數(shù)據(jù)可知,“三省一市”在科技創(chuàng)新層面勢頭迅猛,創(chuàng)新文化在地域科技研發(fā)中作為一種基礎(chǔ)性、先天性的元素,具有不可或缺的顯性功能。但“各自為政、單打獨(dú)斗”的現(xiàn)象又同時(shí)存在。實(shí)際上,與產(chǎn)業(yè)特色、生態(tài)特色、功能特色相比,文化特色是最基礎(chǔ)、最深厚、最穩(wěn)定的特色,受傳統(tǒng)行政管理體制的影響,長三角創(chuàng)新驅(qū)動的文化元素與一體化發(fā)展形勢訴求未能有充分銜接。習(xí)近平總書記寄語長三角:“創(chuàng)新主動權(quán)、發(fā)展主動權(quán)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3]江南文化在新時(shí)代的弘揚(yáng)、傳承,若不能引領(lǐng)創(chuàng)新發(fā)展理念一體化進(jìn)程,恐怕就要在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的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斷層,導(dǎo)致文化品味滑坡。

表1 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科技研發(fā)創(chuàng)新程度對比[14]
三、出路:長三角區(qū)域文化資源整合及軟實(shí)力提升對策
文化軟實(shí)力越來越成為區(qū)域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長三角文化建設(shè)應(yīng)該是鮮活的、具體的,是外在現(xiàn)象與內(nèi)在精神的高度契合,文化軟實(shí)力提升并不等同于各個(gè)文化子系統(tǒng)文化特色的簡單疊加,而是在各個(gè)系統(tǒng)協(xié)同作用基礎(chǔ)上形成的新特質(zhì)。長三角區(qū)域文化資源整合主要應(yīng)規(guī)避文化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雜亂無序,堅(jiān)持因地制宜,既立足本地實(shí)際,又要與時(shí)俱進(jìn)地豐富現(xiàn)代文化特色和優(yōu)勢,讓文化軟實(shí)力提升與精神培育相統(tǒng)一。
(一)強(qiáng)化區(qū)域互動、內(nèi)外聯(lián)通,構(gòu)建行政推動與市場主導(dǎo)緊密協(xié)作的共生文化體魄
長三角一體化需要處理不同行政主體、經(jīng)濟(jì)主體、社會主體的利益關(guān)系,解決各主體的職責(zé)邊界和一體化共同目標(biāo)之間的沖突。城市規(guī)劃學(xué)家芒福德認(rèn)為,“確定城市的因素是藝術(shù)、文化和政治目的”,“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體……不單是權(quán)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極”。這就需要構(gòu)建一個(gè)符合各方心理認(rèn)同的區(qū)域文化共同體。一方面,需要讓共同體文化對個(gè)體統(tǒng)攝、引導(dǎo)、吸引和關(guān)懷,另一方面?zhèn)€體更要對共同體文化自覺皈依、奉行和遵守。在文化軟實(shí)力建設(shè)上,應(yīng)著眼宏觀文化統(tǒng)籌整合布局,梳理各地文化軟實(shí)力與區(qū)域整體文化風(fēng)貌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把各地生活習(xí)俗、價(jià)值觀念、道德風(fēng)尚等納入?yún)^(qū)域共同體,提升群體生產(chǎn)力,促進(jìn)各成員對共同體文化的遵守,促進(jìn)城市群信任溝通。比如舉辦長三角文化節(jié)、組建長三角文化企業(yè)、共享長三角文化資源等,特別是有效利用長三角國際文化產(chǎn)業(yè)博覽會、上海進(jìn)博會等國際性文化宣介平臺,跳出長三角文化產(chǎn)業(yè)本土化的狹隘空間,刺激形成“更新迭代、功能融合、優(yōu)勢互補(bǔ)”的發(fā)展勁頭。同時(shí),要提升對長三角民間文化互動交流的關(guān)注度,發(fā)揮政府對民間文化的投入、支持力度,守護(hù)鄉(xiāng)村宗祠、傳統(tǒng)村落、民間戲曲、非遺傳承等文化資源,增強(qiáng)文化自覺,強(qiáng)化文化凝聚力。
(二)尊重文化差異、錯(cuò)位發(fā)展,打造個(gè)性特色與時(shí)代精神相得益彰的區(qū)域文化品牌
長三角文化軟實(shí)力提升不貪大求全,而是要以品質(zhì)論高低、以特色論輸贏,以特色集聚發(fā)展要素、以特色鑄造品牌效應(yīng)、以特色形成核心競爭力。盡管長三角城市群有著相似的資源稟賦、文化基礎(chǔ),但在文化秉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北面南米”“北辣南甜”等個(gè)性差異。這就務(wù)必要梳理好自身家底,尊重差異、錯(cuò)位發(fā)展,避免“千城一面、萬樓一貌”。在現(xiàn)有文化資源基礎(chǔ)上,主攻最具特色、最具優(yōu)勢、最具潛力的文化資源,培育各個(gè)文化領(lǐng)域的“單打冠軍”,走差異化、獨(dú)特化文化發(fā)展道路。上海“海派文化”作為引領(lǐng)長三角一體化的地標(biāo)性文化,在立足傳統(tǒng)、主動發(fā)揮文化包容性、開放性方面要有所作為,把“外灘文化”“金融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潛力倒逼出來,以特色產(chǎn)業(yè)文化為基礎(chǔ),培育“產(chǎn)城融合”發(fā)展的新載體;江蘇有著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革命文化等寶貴資源,在用足用活“古都文化”“紅色文化”諸多方面應(yīng)有所突破,讓明十三陵、中山陵、雨花臺等特色品牌靚起來,撬動長三角文化的歷史厚重感、力量感;浙江的“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數(shù)字文化”等最為突出,應(yīng)靈活運(yùn)用“城市大腦”“云計(jì)算”“大數(shù)據(jù)”“區(qū)塊鏈”等數(shù)字科技,努力打造長三角智能文化新高地;安徽承擔(dān)長三角民間文化傳承的重任,要在文旅融合、儒學(xué)復(fù)興等領(lǐng)域多下苦功,保護(hù)徽學(xué)遺產(chǎn)、村落資源、戲曲工藝,傳承江南文脈。要立足現(xiàn)有文化發(fā)展基礎(chǔ),始終做到在規(guī)劃中體現(xiàn)文化特色、在建設(shè)中彰顯文化魅力、在發(fā)展中再造文化精神,推動形成“群雄崛起、錯(cuò)落有致”的差異化發(fā)展格局,著力打造富有地方特色和時(shí)代風(fēng)貌的長三角區(qū)域文化品牌。
(三)創(chuàng)新體制機(jī)制、集智聚力,培育開放創(chuàng)新與高端引領(lǐng)共融共生的先進(jìn)文化生態(tài)
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動機(jī)、熱情和意志總是在一定的文化環(huán)境中得以激發(fā)、孕育和強(qiáng)化的。文化是一種系統(tǒng)性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為人們提供了對與錯(cuò)、善與惡、美與丑、正與反的行為規(guī)則。“長三角區(qū)域應(yīng)以長遠(yuǎn)發(fā)展的戰(zhàn)略眼光,加快開展具有長三角特色的文化產(chǎn)業(yè)人才發(fā)展機(jī)制,創(chuàng)造自由寬松人才發(fā)展環(huán)境,吸引全球各類領(lǐng)軍人才和創(chuàng)新團(tuán)隊(duì)落戶長三角。”[15]注重發(fā)揮長三角雙一流高校的人才優(yōu)勢,增加高校科研經(jīng)費(fèi)投入,以“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攻克一批“卡脖子”關(guān)鍵技術(shù),讓關(guān)乎國家前途命運(yùn)的尖端領(lǐng)域不再被“卡脖子”。實(shí)際上,在一個(gè)鼓勵(lì)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勇于冒險(xiǎn)、推崇競爭、容忍失敗,以成就、公平正義論英雄的文化市場環(huán)境中,人們就會樂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彰顯自身價(jià)值;而在一個(gè)不思進(jìn)取、懼怕失敗、委曲求全、恥笑失敗的文化環(huán)境下,人們便害怕各種風(fēng)險(xiǎn)挑戰(zhàn),往往一遇挫折便知難而退了。戈比認(rèn)為:“對于許多企業(yè)來說,是否將企業(yè)向某一地區(qū)擴(kuò)展或遷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yè)所親賴的雇員群體是否滿意那里的社區(qū)生活服務(wù)水平,這就是人們經(jīng)常提到的生活質(zhì)量。”這種生活質(zhì)量不僅僅止步于公園綠地、體育場館、設(shè)施設(shè)備等物質(zhì)文化空間,更加需要構(gòu)建一種鼓勵(lì)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文化環(huán)境。比如“鼓勵(lì)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能屈能伸、容忍失敗”的家庭環(huán)境,“公平正義、和衷共濟(jì)、開放包容”的企業(yè)文化,“簡化程序、效率優(yōu)先、唯實(shí)惟先”的政府理念,“守信篤實(shí)、實(shí)干爭先”的社會環(huán)境等都在區(qū)域文化一體化建設(shè)中發(fā)揮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教化作用。
四、結(jié)束語
2020年8月20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合肥主持召開扎實(shí)推進(jìn)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座談會時(shí)強(qiáng)調(diào):“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不是一日之功,我們既要有歷史耐心,又要有只爭朝夕的緊迫感,既謀劃長遠(yuǎn),又干在當(dāng)下。”[13]推進(jìn)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是繼京津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qū)、長江經(jīng)濟(jì)帶之后的又一大世紀(jì)性工程,要從中華民族永續(xù)發(fā)展的大局來考慮、看待問題。實(shí)現(xiàn)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只是一體化發(fā)展的過渡手段,長三角一體化發(fā)展水平的研判標(biāo)準(zhǔn),最終還要看是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是否符合“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是否造福于子孫后代的美好未來。
在實(shí)現(xiàn)長三角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上“大而強(qiáng)”的同時(shí),更要格外關(guān)注文化上“精而美”的景觀布局,既要集聚“人才、技術(shù)、資本”等現(xiàn)實(shí)要素,也要注重文化軟實(shí)力提升的精神支撐。對于以江南文化為內(nèi)在精神支撐的長三角城市群文化軟實(shí)力提升,不可僅僅局限于儒學(xué)史書典籍的考據(jù)與闡釋,要放眼“三省一市”文化本體樣態(tài),有序整合各地文化資源,發(fā)揮文化在長三角一體化建設(shè)中的引領(lǐng)和示范性作用。通過文化的力量克服長三角一體化建設(shè)過程中由于傳統(tǒng)社會紐帶的斷裂、社會團(tuán)體整合基礎(chǔ)弱化可能出現(xiàn)的“原子化、無序化、工具化”社會現(xiàn)象,以“小橋流水人家”等多種文化場景消弭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中產(chǎn)生的文化自卑感、精神虛無感、心理失落感。“在現(xiàn)有文化資源整合基礎(chǔ)上,傳承優(yōu)秀區(qū)域文化,保護(hù)區(qū)域文化遺產(chǎn),守護(hù)長三角區(qū)域共同的精神家園,推進(jìn)區(qū)域文化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化。”[16]從而,讓共同的歷史記憶、價(jià)值觀念、人文習(xí)俗等有序重構(gòu),發(fā)揮文化在長三角一體化建設(shè)過程中的引領(lǐng)、滲透、感召及輻射作用,把長三角地區(qū)打造成一個(gè)“大度開放、和而不同、引領(lǐng)時(shí)代”的現(xiàn)代性文化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