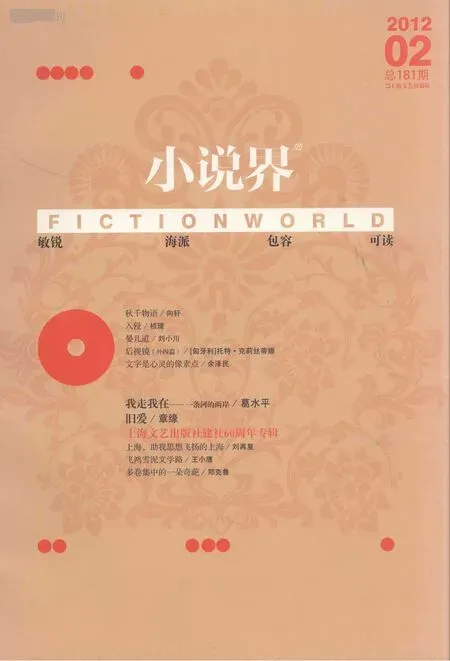船在海上
于一爽
在甲板上,一直有人和郭一并排附在欄桿上,也許是中國人,或者說中國人是大概率事件,因為如今最喜歡去世界各地搞旅游的都是中國人。而有一點讓郭一十分驚訝,從側面看他,好像鼻子掉了一塊。郭一不確定,也許只是角度問題。這個人很高,一直沒有轉過身來,雕塑一般。甲板上還有躺椅和鋼絲床,落了一些鳥糞枯葉灰塵沒有人坐上去,而且顯然已經很久沒有人坐上去了。郭一抬頭看見只信天翁,翼展三四米,翅膀又窄又長。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一些追逐船只的小海鳥,也許這些海鳥并不小,但因為飛得很高,看上去都是微縮版本,在一起發出刺耳的聲音。因為船只還行駛在海峽中,并未靠近半島和大陸,速度很快,海鳥追著船只的速度也很快。唯一的信天翁很快就飛走了。郭一知道,這類海鳥大多會死于捕魚鉤。每年有數十萬只。真是一群傻鳥。她替它們可憐。偶爾會射來一股刺眼的陽光,抬頭看這些海鳥的時候就像在皺眉頭。
郭一在一艘開往極地的船上。
人并不多,大概150人,有三分之一是工作人員,這是她估算的。此前她還在介紹上看見了這艘船的更多信息,載客量:174人,長度:107.6米,寬度:17.6米,吃水:5.3米,冰級:A-SUPER,航速:15節,載重:5590噸。船像一張紙片一樣浸透在冰涼的海洋中。還有船長的照片。留著胡子,看上去正像一個船長應該有的胡子。他駕駛這艘船在極地往返了25年,看樣貌很不喜歡和人說話。事實上也毫無必要。兩片很薄的嘴唇閉合在一起,就像希望嘴唇消失一樣。
這是一艘蘇聯時期建造的船,蘇聯解體之后作過賭博船。因為是冷戰時期的間諜船,安裝了許多大功率電源輸送的粗電纜和頎長的無線電天線,以及核心設備——用于探測核潛艇的放射性探測器,船身包裹著一層厚厚的鋁板,以防止敏感的通訊系統被岸上的敵方竊聽。官方文件中宣稱,其曾被派遣至北大西洋為國際電信聯盟工作。但是,人們更愿意相信,此舉是以竊聽英美之間的通訊為主要目的……
這僅僅是一些數字故事,和郭一毫無關系。她更好奇旁邊的高個子,高個子的鼻子。她已經在船上呆了兩天,還沒有穿越德雷克海峽,只有穿越這片海峽,才可能抵達極地半島。作為游客,她沒法深入極地大陸,僅是搞一些觀光,發一些朋友圈。
這是她能到達的邊界。海峽風大浪大,她在船上吐了兩天,此時此刻平靜一些,她來到甲板上,胃里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吐了,鼻孔里灼熱的氣息瞬間凍成冰粒,風向著她的身體呼嘯而來呼嘯而去,但依然感覺神清氣爽。郭一拼命呼吸空氣。她的目光向遠處望去,遠處和近處一樣,全是水,船開過的地方是一層雪白的浪,也許不應該用雪白來形容,因為真的比雪還白。她想起一位朋友寫的詩: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極其白賊白簡直白死了啊。這首詩寫得好極了,因為只是說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但是并沒有說怎么白,她想,不能理解這首詩的人就是因為真的不能理解這首詩。比如何多,就不能理解這首詩,甚至因為郭一理解了這首詩,而覺得兩個人終歸不能一起生活。在地球的另外一邊,此時此刻,她想起兩個人曾經的關于這首詩的爭論,最后以何多的一句話收場。何多用手指肚敲擊著桌面說:看我們兩個人誰能笑到最后!
郭一希望笑到最后的人是他而不是自己。是不是笑到最后都會死。笑到最后的人也不會笑著死。人都怕死。
如果從地圖上看,會覺得海峽的形狀非常奇怪,很難讓人相信僅是洋流沖刷的結果,更像是一顆行星生生把兩個大陸撞開,因此被人類形容為魔鬼才走的海峽。海峽長300千米,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明天的這個時候她將到達半島。天上的云絮像塑料泡沫似的。她知道還有更強烈的寒冷等待著她。
在郭一所知道的不一定準確的資料里,她所能了解的極地是這樣的——
大概在2億年前,雖然同樣位于高緯度地區,但當時的極地遠沒有今天這般寒冷,蕨類、蘇鐵等植物生長茂盛,森林綿延、郁蔥,各種古獸繁衍其間。物種昌盛,萬象更新。代表性動物水龍獸因其生存環境復雜,身長從0.6米到2.5米不等,上下頜前端可能有喙狀嘴,用來切碎植物,兩顆長牙是其顯著標志。一億多年前關鍵性的轉折出現了,大陸開始分裂,只有極地陸塊孤零零地留在極地。3400萬年前,南美洲與極地陸塊的最后連接,也被板塊運動無情切斷,海水噴涌而入,形成了寬達900千米的德雷克海峽。大陸四周沒有其他陸地、山岳的阻隔,海面上無遮無攔,風率先降臨,它自西向東環繞極地,風力時常高達7級以上,人稱咆哮西風帶。強風吹動海面,形成海浪,海浪又帶動深層海水形成更強大的洋流,洋流環繞極地,同樣無遮無攔,流速越來越快,規模也越來越大,最終形成了一個寬600千米-2000千米,深達2-4千米的超級洋流,極地繞極流。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洋流系統,流量超過全球所有河流總徑流量的幾百倍,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兩大屏障,將整個極地包裹起來,來自北方的暖流難以進入,內部的寒流亦難外散,內外熱量交換受阻,極地大陸幾乎被“封印”其中。至冷之中,冰雪紛紛飄落,高山上發育出巨大的冰川,將極地的山峰切割得尖削凌厲。當冰雪堆積超過千萬年,極地98%的陸地都被巨大的冰川所籠罩,稱為冰蓋,原本高聳的山峰,只能露出尖尖的山頂,有如白色海洋上的小島,名為冰原島峰。大體上,我們如今看到的極地面貌就是這么形成的。
最冷的地方,地表溫度在冬夜可降至零下90度左右。但是作為游客,這些都見不到,比如在極地大陸東部有一條無人涉及的1000公里的冰脊,因為所處的高緯度,一年中都是漫長的極夜,陽光射入的角度很大,單位面積所吸收的太陽熱能就非常少了。白色冰雪對陽光的反射率達到80%,可以說大部分熱量在接觸極地大陸之后又被反射回了太空。
甲板上有人往海里扔面包,但看不見魚。一定有魚,海里怎么會沒有魚呢?面包撕得很碎很小,看上去撕面包的人有很多心事或者僅僅是因為無聊。郭一喝著手里的蜂蜜姜茶,也是為了緩解嘔吐。姜的味道很濃,她只放了一丁點蜂蜜,蜂蜜沒有完全融化在茶里,沉在了底部,她沒有湯匙也懶得攪拌。杯底的琥珀色讓她覺得賞心悅目。天上落著雨。極地的雨很冷,落在手背上,像小型電擊,她想,應該爭取這分分秒秒的時間,再看看這片海峽。如果不能看出這一片景色和那一片景色有什么區別,那簡直可以說這趟旅行無聊至極。海峽最深的地方是5248米。
就在這個時候,高個子轉過身,郭一看清了,他的鼻子缺了一塊,缺了很大的一塊,可以說整個鼻子就只剩下一個凹小的輪廓。他的個子白長那么高了,郭一想,并且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會在極地看見一個沒有鼻子的人。高個子對著郭一點頭微笑,然后離開。郭一從未見過沒有鼻子的人。吃驚。她感覺非常恐怖。她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還有不少人在欄桿邊等待鯨魚。也許會來也許不會來。她想起自己在海洋館見過海豚,潔白的海豚,眼睛看上去總是彎成一條線,微笑大使,但是她更想看見鯨魚。巨大的物體,都讓她感覺神圣,仿佛它們正是從數億年前存活到今天,因為巨大、笨拙而顯得十分確定和永恒。
也有幾個阿姨支著桌子在甲板上打麻將。她瞥見一個胖阿姨吃了一個瘦阿姨五萬,糊了一把捉五魁,外加一個幺雞暗杠。瘦阿姨說:我帶出來的錢都要被你吞掉喲,我還不如灑進海里。
郭一把身體大幅度探向欄桿外面,一小部分海水拍打在甲板上,濕滑,她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掉到水深5000米的地方,那樣估計也要掉一會兒。她也想過人是不是可以不出生,那樣的話往子宮也要縮一陣。但也僅限于一種聯想。郭一使勁攥住自己的小書包,她害怕手機一類的東西被刮跑,雖然她已經兩天沒有信號了,但她知道,之所以沒有信號是因為自己決定讓它沒有信號,而手機無論如何是不能丟的。5000米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兩座衡山和一座華山統統扔進去看不見山頭。兩大洋在此交匯,因此形成了著名的風暴,全年的風力都在八級以上。郭一想,八級?沒概念。她不知道臺風幾級,她沒有見過臺風,她生活在北方一座干旱的城市,有一年謠傳臺風會來,她趴在陽臺上等了一天,后來又說不來了。她也曾經計劃在最恐怖的季節去沿海等臺風來,事到如今,她都沒有看到過臺風。
已經兩天了。
船上的生活很規律,每天7點鐘船艙的喇叭開始廣播,因為喇叭是最萬無一失的,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所有人都可以快速聽到信息逃生。郭一的船艙所在位置的最近逃生路線在前甲板,她已經在上船的時候做過三次演習了。8點到9點是早餐時間,因為此次船員多是印度人,所以印度餐居多,午餐是12點,晚餐是6點,分別一個小時,如果趕不上就沒有了。郭一自己沒有帶任何食品,她討厭把方便面火腿腸帶到世界各地。因為她不怕餓,如果餓了她就睡覺。船上沒有信號,如果需要信號,就要自己買,一分鐘10美元,她不想花這10美元,10美元在她生活的城市可以買很多東西,比如吃一頓肯德基或者麥當勞。當然,她想,這艘船上的多數人都不會在乎10美元,就算10萬美元他們也不在乎。郭一因為提前訂票,所以住到了優惠的船艙。她的隨身行李很少,有一身軍綠色的棉衣棉褲,是在網上買的,網上的圖片是一個穿著軍綠色棉衣棉褲的人在看冰柜,可以說是冰柜管理員的職業裝。價錢并不貴,很像小時候穿的那種棉衣棉褲,如今在城市中已經沒有人這么穿了。郭一買了最小號,穿上之后,褲子一直往下掉,但她決定拿到極地來,如果不拿過來就更沒機會穿了,褲子一直往下掉可以當被子蓋在身上。這一身軍綠色讓郭一很像一個要被流放到遙遠地方的政治犯。
又在甲板上站了一會兒,她聽見喇叭,是午餐時間。早餐都吐了,肚子很空,她第一個往餐廳走,她不想等大家都來的時候排隊,她不喜歡為吃飯排隊,這會讓她恨上食物。餐廳是自助餐,郭一裝好了自己的盤子之后坐到了窗邊,窗邊可以看到延綿起伏的海浪。她裝了很多因為她不想再起來去裝一次,她怕回來的時候位子都沒了,如果吃不掉她就打算用餐布蓋上。盤子里的蛋糕緊緊貼著咖喱牛肉,牛肉旁邊是一些滾圓的炸湯圓,特意為中國人準備的。她剛落座,就看見高個子拿著盤子走過去,她很想問問,鼻子是不是被什么人咬下來的。高個子實在太高了,要做一些類似鞠躬的姿勢才能從旋轉餐盤上夾到自己要吃的菜,讓人替他難為情。
她坐在位子上一顆一顆仔細剝著滿滿的磷蝦,可以不用剝,但她又不是沒時間。她看著窗外,天上的云散了,一絲縫隙都沒有了。
磷蝦非常非常小,它們能夠忍受超過200天的饑餓,甚至會出現負生長,所以通常2-3年也不過長到5厘米左右,但保守估計總量在5億噸以上,相比之下,人類的總體重也才4億多噸。她又感覺自己在吞噬很巨大的事物。
高個子坐在了隔桌,并沒有挨著窗戶。他低頭吃東西,看上去只想盡快把東西吃完。如果不是因為鼻子,他可以說長得非常帥,郭一想,他會不會因為帥被別人打,打壞了鼻子。
很快,餐廳的人多了起來,胖阿姨瘦阿姨還有更多阿姨坐了過來。沒錯,她想,人老了就有錢了。在吃午餐的時候廣播里說,因為風浪大,也許登島的時間又要延后了。失望不言而喻,如果沒有登島就是虧了,但沒有人敢抱怨天氣。郭一當時正在喝咖啡,一部分咖啡傾灑了出來,她聽見旁邊的瘦阿姨說——一年之中聽說也就只有小半年可以,其他大半年都不可以。郭一想,她說的可以就是不虧,不可以就是虧。胖阿姨點頭。大家感受到了同樣的安慰。大意就是——反正都虧了。
郭一想,她們還是抓麻將的時候更可愛。她快速喝掉剩下的咖啡以免更多液體傾灑出來。
飯后,郭一照例要在船上逛逛,否則她實在無事可做,她又不會去打麻將。船上有一間理發室,她走進去問價錢。理發師也是一個高個子,她忽然覺得有必要將這個消息告訴另外一個高個子。在自己的城市,她一年,十年,也碰不上一個高個子。大概兩個人都有兩米。理發師正在扭動脖子,做一些運動。于是她問理發師:你是哪里人。理發師說:蒙古人。然后又問郭一:你是哪里人。郭一說中國人。理發師說:內蒙古。
郭一打量這間小小的理發室,也許這只是必要的設施,而整個行程都不會有人光臨。只有一把椅子,墻上貼著三款發型,男士的板寸,男士的中長發,中間還有一個大波浪女士。圖片上三個人的牙齒都很白,但其實她最想說——你知道這個船上還有一個高個子嗎?或者不止一個,如果有足夠的耐心,會發現,兩個,沒錯,現在不就是兩個嗎?或者三個四個成百上千個也不一定。但是因為她的英語不好,所以她就什么也沒說。
理發室旁邊是一家小小的超市,里面賣一些方便食品、極地紀念品,還有一些在玻璃鎖柜里,聽說是一些極地藝術家的限量版,價格不菲。郭一覺得藝術家一定要貴,不貴就不值錢了。
之后無事可做,只能重新回到船艙了。她的船艙被刷成藍色,就像在海底波光粼粼。之后她在一張白紙上寫——今天看見了兩個高個子。白紙是船艙免費提供的便簽。昨天她也寫了,她寫:何多在分手后第一次沒有聯系我,我也沒有聯系他。
船艙的四周都是鏡子,郭一想——如果有鏡子,人怎么會孤獨呢?她把昨天喝過紅酒的杯子扔在水池里,她想此時此刻最孤獨的莫過于水池里的杯子了,已經從紅色變成了淡紅色。她感覺不到探險船一絲一毫的行駛。
船艙的床頭掛著一幅企鵝,沒有比掛著一幅企鵝更天經地義的了。而讓郭一不明白的是,企鵝穿了西裝打了領帶,目光朝下,郭一躺在床上正好目光朝上,和企鵝對視。她絕對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和一只漫畫企鵝對視,大概是正常的企鵝在極地見得太多了,所以船艙里特意準備了西裝領帶企鵝。她不知道其他船艙是不是也一樣,比如更貴的船艙,是不是會有一兩只正常的企鵝,當夜里暈船醒來的時候,不必覺得不可思議。她想這幅畫一定是來自中國,中國某個小小的城市,那個城市的一部分人就以制作這種畫糊口度日,因為企鵝很矮,所以只穿了西裝沒有西褲。西裝一直拖到畫面的邊緣。
她知道如果這只企鵝忽然說話也一定不要太驚訝。
畢竟,此地,最多的就是企鵝,可以說,沒有看見就已經聞見了。據說,企鵝最早會飛,后來它們不再需要飛,因為游泳可以讓它們捕獲更多的磷蝦。它們光滑的羽毛內保留了一層空氣層,既可以增加浮力,也有助于隔絕極地冰冷的海水。仔細觀察會發現,它們的腳和耳朵都變得非常非常小,這是為了減少熱量的流失。
另外一件事便是衛生間里還有一只西裝領帶企鵝。衛生間的門很沉,下面還開了一個洞,類似讓小貓小狗爬進爬出那樣的裝置,衛生間的玻璃有一條裂紋,閃電一樣四散。但并沒有碎。
她忽然明白一件事,自己是不是在極地都無所謂了。在不在地球上都無關緊要。她把兩只企鵝調換了位置。衛生間的擺在了床頭,床頭的擺在了衛生間。
吃過飯之后,她的指甲上全是咖喱味道。她喜歡咖喱,但是不喜歡咖喱味,就像自己喜歡抽煙但是不喜歡煙味。所以郭一每次都對著空氣凈化器抽煙,看上去就像空氣凈化器抽了不少煙一樣。
狹小的空間中她身體發麻,她覺得自己已經很小了,簡直可以從下面的貓洞狗洞爬進爬出。
她打開網絡,這意味著她要破費十美元了。何多的微信就在這個時候過來了,微信里說:不要在你的詩歌里寫我是不是手淫,我從來不手淫!
郭一感覺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只可憐的貓或者狗,只想往下面的洞里爬。何多看上去很憤怒,竟然用了嘆號。
離開城市之前,她在一個公號發了一組詩歌,里面多是一些愛恨情仇,可是她發誓:沒有一首是寫給何多的,更沒有一首是寫他的。有人規定不可以寫手淫嗎?
這太可笑了,男人手淫可恥嗎?一個不手淫的男人比沒有鼻子還可恥嗎?
她還沒有回,何多又在信息里說:我真想咬你。
郭一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這是什么意思,是真的要咬自己嗎?咬哪兒呢?不會也咬鼻子吧?可又像一種曖昧。他們分開一個月了,還在恨對方。郭一和同事一起工作,工作著工作著就工作到了床上,就沖這一點,難道還不應該被何多把鼻子咬下來嗎?她用手摁了摁自己的鼻子,實在想象不出如果沒有了會怎么樣,也許應該問問高個子,但顯然她不會這樣做。而人也不能自己咬到自己的鼻子。想到與何多戀愛的時候,兩個人經常互相咬住對方的鼻子,或者聞一聞,就像小動物在辨識彼此。
鼻子被咬掉了是不是還能接回去?
她記得以前在晚報上看過一篇報道,一個男的不小心切掉了手指頭,慌忙去醫院,因為太慌忙,把手指頭(也許是最重要的大拇指)忘在了家里的菜板上,回去拿,因為太慌忙,又忘在了出租車上。但她不知道這篇報道有什么意義。
接著又是一條信息。在郭一看來,何多就是這么精神錯亂。信息里說:我夢見你了。每天打開門又是一扇門。
在地球的另外一邊,現在是夜里,也許他真的夢到自己了。郭一想,但也許自己才是精神錯亂的那個人。還在渴望什么?
她關掉網絡。需要重新拼貼理解這一切。
在船上,每天的生活都一樣,她連每天穿的衣服都一樣,內衣內褲秋衣秋褲外褲外衣,毛背心,大衣,手套圍脖帽子。就像是一種人形動物的包裝套。還有兩層襪子。船艙的天花板很低,因為狹小,四周裝了鏡子,仔細聽還有管道的聲音。她摸了摸鏡子里面的自己,冰涼傳入指尖。
她大部分時間都在自己的船艙,除了吃飯的時候,或者下船的時候,有時候吃飯前后會去周圍走一走,極少,她總怕碰見什么人,擔心有人和自己打招呼,問長問短甚至交一個朋友。
郭一喜歡在自己的船艙喝酒,酒是餐廳買的,她喝得很節約,因為怕喝多。沒有冰塊,她感覺十分滑稽,極地到處都是冰,但她此時此刻連一塊冰都沒有。
就在這個時候廣播又響了,里面說他們可以駛入一個類似海灣的地方,坐上橡皮艇看鯨魚,這個地方經常有鯨魚出沒。郭一開始穿衣服。她有點后悔喝了酒。穿了很多層,還有橡皮鞋救生衣要去更衣室穿。救生衣是一次性的,如果打開就不能收回了,打開的方式是吹一下前胸的哨子。還有墨鏡,這里的紫外線很強。之后統一做好生物消毒就可以下船了,十個人一個小艇。
上艇的時候,高個子正好坐她對面,沒有隊形,這多半是一種巧合。要刷卡上艇,便于統計人數,她也有機會近距離看一張沒有鼻子的臉,超過了看鯨魚的樂趣。另外,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看見他們的探險船,船頭在呼呼冒著白色蒸汽。她想起一首詩中的一句:船在海上。
但四周并不是雪白一片,山脊上長出一叢叢綠色,成百上千年才長一毫米一厘米,僅僅貼著地衣。也有點像何多之前的板寸,她想一定是非常柔軟地微微地探出。這個時候導游說:這里最多的是座頭鯨,它們都是成群出現,用鰭拍打水面,跳躍出水面。所有人都在期待,只是你不能確定它們在小艇的哪個位置,會不會在下面。觀看的時候很安靜,不能發出聲音,有一些來自鯨魚的聲音像從遙遠太空傳來的聲吶。高個子真的很高,坐下去的時候郭一都要仰著頭。她不能一直看,有時候她也看看鯨魚。因為穿了很多,臉都被圍巾蓋了起來,可以說缺了一塊的鼻子更明顯了。郭一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這讓她感覺恍惚。她的襯衫一直扣到喉嚨上,她摘下手套,松開了一點。大概一年前,她與何多在東南亞的一個海灘,碧海藍天椰風樹影,一切都像明信片一樣,和這里的無比寒冷正好相反,那里是無比燥熱。不知道從哪里,走過來一只耕牛,慢悠悠的,那種只有在水田才可以看見的耕牛,四周的人包括何多都無動于衷,好像只有她看見了,正像此時此刻,她就是這樣的感覺。
鯨魚,耕牛,四周被包圍的藍冰,一個人殘缺的臉上,古老的巨大的永久的,甚至也許是邪惡的,死亡的,一無所有的,不知道為什么讓她著迷,她有一刻感動了,于是干脆一直盯著對面的人看。艇上的其他人在拍照,只有快門的聲音,郭一連手機都沒有拿出來,高個子早就察覺了這一切,他偶爾拍照也是用手機,更多時候就讓郭一看。世界上多數問題都是因為不夠直接。此時此刻多好。身體就是靈魂。這樣的鼻子比成千上萬完美的鼻子都更吸引郭一。當她這樣想的時候,橡皮艇劇烈地搖晃了一下,就像是被一條座頭鯨托了起來。橡皮艇兩側的人離得很近,郭一下意識抓住高個子的大衣角,往下看是清澈的云,上方是水,沒有形狀,混合著灰色黑色白色。藍色是底色,其他的顏色在藍色中蔓延。郭一知道自己即將消失在這一切之中。終于和所有一切的關聯都沒有了,她向四周望去,當人從環境中分離出來的時候,四周都變成了藍色。深淺,海天,火焰冰塊都是藍色。就像碎了的瓷器片,褪色的吸墨紙,冰山上的一塊胎記……
往回開都坐好!
導游的一句話將郭一拉回來。她不再看高個子,倒是高個子一直盯著她。她攏了攏被風吹亂的頭發。也許在別人看來根本沒有攏的必要。下艇的時候她踩到一個毛茸茸的東西,低頭發現是一只死鳥。毛已經被踩沒了。她想,并不只是她一個人踩的結果。只有自己半個腳掌大小,她低頭把鳥扔進了水里。一點水花都沒有激起來。很難想象它也曾經有過生命。
因為今天天氣很好,所以才可以出海看到鯨魚,或者說太好了,光線很刺眼,就像古往今來的熱量,鉆石被灼燒成灰燼。
這里真美,但有什么用呢?郭一不得不這么想。就像她不得不暫時來到這里一樣,離開眼下的生活,然后再像傳送帶一樣被帶回去。
聽說你是一個作家,回到公共區域之后正準備喝蜂蜜姜茶的郭一被導游攔住問。
誰說的?
那我們肯定有我們的渠道。導游吹了一口茶,茶上面起了一層波紋。郭一把茶杯抱在手里,很溫暖。看著四周來來往往的人。有人下船了,有人要上船。1959年美蘇英法等國經過反復磋商簽訂了《南極條約》,在這里沒有領土要求沒有軍事活動當然更沒有人。其中規定了上島人數,所以船上的人要分批上島。我們肯定有我們的渠道,她反復咀嚼導游這句話,覺得很邪惡。
沒名的作家。郭一說。
那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真沒名。
那你寫過什么我拜讀一下。
等我寫了更好的再告訴你。
我看你不和別人說話,是不是作家都這么有個性?
我真的不是作家。
反正我覺得你挺有個性的。
我就是不愛說話。
你寫什么的?
我真不是作家。
謙虛!
我不是謙虛。
那怎么能當一個作家呢?
等我當了再告訴你。
你要是需要拍照可以喊我。
哦。
我看你不拍照。
嗯。
你太有個性了,果然是一個作家,是不是作家可以描寫這種景色?
也不一定吧。
我就沒讀過什么作家的書,你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作家。
等我真成作家你再叫我作家吧。
那你都寫什么呢?
沒寫過什么。
愛情小說?
也不是吧。
那你回去好好描寫描寫極地,爭取讓更多人來。
啊。
是不是作家自己寫作就不用和別人聊天了,昨天晚上喝酒你也不在。
我不會喝酒。
那多沒靈感啊!反正現在和作家說話是不是有點打擾作家?
沒有。
能不能晚上和你一起在餐廳吃飯,我向你請教一些寫東西的事情,我真的沒見過作家真人。
請教?
你們作家都不愿意承認自己是作家,我看你就像。
你說是就是吧。
你覺得我能當作家嗎?
都能當。
又謙虛了。我就一直想寫我身上的事,特別傳奇。
我就沒什么傳奇的事。
那你把我的傳奇的事寫了吧。
哈。
你要寫了我請你喝酒!哦對了你不會喝酒。那當作家能養活自己嗎?
我真不是作家。應該不能。可能有人能,我不能,因為我不是。
那我晚上吃飯給你講講我的事。
呃。
別嫌我說的沒意思。
不會,郭一說。但她其實在想,我一定覺得你沒意思,因為多數人都沒意思,我也沒意思,怎么會有意思呢?而你已經表現得很沒意思了。
說到這里的時候,導游的茶都喝光了,他起身說:我不能再陪你喝了。
郭一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茶,已經涼了,還沒動,茶水里能映出自己的臉,她覺得這笑容很陌生。
導游走了兩步又轉身回來說:那我加你個微信吧。又補充了一句:我還沒加過作家的微信呢!
郭一忽然感覺有點無恥這個人,就說:可我不怎么發也不怎么看。
你掃我還是我掃你?導游說著找出了自己手機的二維碼命令到:你掃我吧。
通過后他快步離開,還說了一句:晚上餐廳見。看上去你心事重重,可能你們作家都這樣。
可能你們作家都這樣,這句話聽上去很刺耳。
郭一打開他的朋友圈,簽名是:收集地圖上每一次的風和日麗,昵稱是開心果。
寒冷讓人對一切失去熱情。外面的霧氣忽然濃重,讓人不知道濃重的霧氣中有什么,好像從這個門走出去就會撞到。導游看上去很年輕,和年輕人稱兄道弟讓郭一感覺吃虧,于是她將對方的朋友圈設置成了彼此都看不見的那種。
郭一絕對不會和任何人承認自己是一個作家。在來極地之前,她看過一本小說就叫《極地》,她以為多少會和這里發生一點關系,事實上并沒有,講的是一個女人想出軌,最后被出軌對象用手銬綁在床上,她發瘋一樣試圖打開,想把床頭板拉下來卻發現辦不到,想發出巨大的聲響喊叫但是嘴里被塞了棉布,使勁踩地板但是樓下并沒有回應。房間越來越冷,她一絲不掛,持續的麻木在身體里擴散,寒冷從頭上到身上(大致)。小說最后寫:因此,她想到了極地,(也許這里是點題的),她還想到了冰雪和尸體,想到地獄,想到永恒。
這些同行的爛小說讓她根本不想承認自己是什么作家,也許她寫得更爛也不一定。但她確定一點,沒有人想來這里出軌。
當這一切結束之后,她發現高個子也在旁邊喝茶,大概所有上船的人都在這里喝茶,不然還能去哪兒呢?郭一起身又去倒了一杯,把冷的倒掉,然后坐到高個子對面。這是她第一次想主動和別人說話,她感覺自己的身體變得很輕盈。
她不相信這幾個字是從自己嘴里發出來的。她問高個子:你覺得極地有意思嗎?
她知道這么問是因為自己覺得沒意思,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意思透了。她甚至不知道這樣受罪的日子什么時候結束。她又覺得自己是不是很低級,要去和一個沒有鼻子的人說話。
高個子說自己來過很多次,這里是他的摯愛。
很少有人用到“摯愛”這個詞。郭一反反復復咀嚼這個詞。她都快忘記摯字怎么寫了。
摯愛?她說了出來。
你別笑。高個子說。
如果你不說我感覺這些詞就再也沒有人說了。郭一又念了一遍:摯愛。這兩個字讓她的心一緊,就像一張塑料紙被揉成一團。人應該在這個地球上摯愛一些什么,哪怕是一只企鵝。如今來到了極地,她打算找一只讓自己摯愛的企鵝。但在沒有找到企鵝之前,真的沒意思透了。她也很快忘記了剛才看過的鯨魚。
看上去高個子不喜歡說話。也許是因為不喜歡自己的鼻子。
她把頭抵在冰涼的窗玻璃上,從玻璃傳過來引擎的震動。玻璃中看到的自己,比鏡子中看到的自己美一些,但依然說不上是那類美的女人,盡管她早就習慣了,但多少有些遺憾。想到遺憾的事情她就習慣性地把手背放在鼻子下面聞一聞。
我的鼻子就什么都聞不到,高個子說。
郭一想換個話題,因為這個話題她想保留住。
你個子真高,于是郭一說。
但她知道自己問錯了,她應該問:你的鼻子怎么了?
很奇怪,每個人最終都回到正確的路上。
好像關心一個人的鼻子就是在關心一個錯誤的問題。真希望他的鼻子不存在。最好這個人都不存在,連同他的鼻子一起消失在5000米的海溝里。
高個子只穿了一件短袖,也許喝了茶之后很熱。看上去根本不是在極地而是在東南亞的某個沙灘上,一樣的椰風樹影一樣的碧海藍天一樣的耕牛。有什么不可以呢?
郭一很想碰碰他的鼻子,或者應該是鼻子的那個部分。但她又害怕這好像是某種不祥之兆。
高個子把剩下的一口喝完說:我都習慣了。
郭一不知道他說的我都習慣了是什么意思。她就這樣盯著高個子看,他看上去就像馬戲團的演員,那些因為身高原因而被招進馬戲團和侏儒搭檔的演員。一直抵在窗玻璃上的頭很涼,鼻息處有水霧。
高個子起身,和她揮了一下手,好像是去放回茶杯,也可能沒有揮手只是動了一下手。兩個人離得很近,中間是一個茶幾,可是郭一感覺他很遙遠。陽光照在茶幾上,沒有陽光的地方和有陽光的地方天壤之別。陽光透過玻璃留下一片片條紋,還有一部分照在臉上手上,人就像漂浮在水面上。大概所有人都應該感到心滿意足吧。海上的水汽像一只毛毛熊一樣籠罩著這一切。這遙遠的感覺讓郭一想到自己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在游樂園,也許不是游樂園,就是馬戲團,或者是那種有馬戲團的游樂園,臨時的馬戲團,一個叔叔請她吃冰激凌,她沒有吃,叔叔自己吃了,后來又吃了一根,一共吃了三根一模一樣的冰激凌,之后給了郭一50元錢,在1991年。叔叔說:你真像我死去的女兒。不知道為什么,從那句話之后,郭一就感覺自己已經死了。而且自己值50元錢。但為什么一個死了的人又活了很多年?
很快高個子又重新坐回來。
郭一很感激他沒有問那些傻問題,比如像導游一樣說:一個人出來多沒勁。
郭一想,就這樣,真好,可以說,也可以不說,最好不說,企鵝就從來什么都不說。
她也從來不會覺得一個人沒勁,要是沒勁,兩個人才是真的沒勁,而一旦沒勁這兩個字從另外一個人嘴里說出來,就真的發生了。一個人不會感覺什么是有勁的什么是沒勁的,那多半是一個有意思的人。不知道為什么她覺得高個子正是這樣的人。人可以生活在這里,也可以生活在那里,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天上的鳥水里的魚,可以完整可以殘缺。一切都可以就不會再有沒勁的事情出現了。高個子就是接受了這樣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是先從自己殘缺的鼻子接受了這一切。郭一想,要是自己有一個這樣的鼻子呢?自己還會來極地看企鵝嗎,還是會干脆變成一個非常放肆的人?
兩個人就這么坐著,郭一發現這里還有蒼蠅。
極地會有蒼蠅嗎?于是她問。
除非是從北京和我們一起飛過來的。高個子說。
郭一看見這只蒼蠅翅膀的四周輪廓若隱若現,小腿在跳動著,很辛苦。
你是第一次來嗎?高個子問。
郭一點頭,她可沒有十萬塊錢再買一次船票,她更不知道什么人會再來一次,光一次就夠了,美是真美,無聊也是真無聊。這就像形容某一類女人,但絕對不是她這類女人,因為她不夠美。何多有一次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看上你什么了。但因為當時兩個人還在熱戀,郭一很容易將這句話理解成一種撒嬌。她現在才恍然大悟,也許何多說的是真的。想到這一點,讓郭一后背發熱。
整個下午都被延長了,兩個人一共也沒有說上十句話,沒有鼻子會影響說話嗎?郭一忽然提議說:我的船艙還有酒,你喝嗎?這句話說出口之后,她又擔心會不會有什么誤會。高個子說行。
到船艙之后,郭一給餐廳打電話說自己暈船,讓服務生送一點切片面包來。
十分鐘之后,服務生送來了切片面包,小圓面包,還有黃油果醬。用一塊餐布蓋住。可以說,這一切,真像那么回事兒。但要是有涪陵榨菜就更好不是嗎。
人沒了鼻子能活嗎?兩個人大概喝了半個小時之后郭一忽然問,也許是一個小時,狹小的船艙內沒人能感知時間的流失。郭一坐在沙發上,高個子坐在地上。
沒有回答,因為這顯然很愚蠢,高個子不就是活的嗎?正坐在自己的對面。她想到何多給自己講過的一個故事,何多在法院系統工作,他故事的主人公正是他的同事,一個女法官。女法官的兩個孩子被謀殺了,在法庭上,女法官忽然沖向謀殺犯,開始咬所有她能咬到的地方。
人到最后一步能做的就是這些。
兩個人自始至終沒有碰杯,碰杯的時候酒會灑出來,不舍得浪費。
這個船艙不舒服,每天夜里睡覺都晃。郭一說。
我睡哪兒都行。高個子說,我年輕的時候經常睡防空洞,因為離家出走。
為什么離家出走?
不知道,可能是因為年輕,現在也是離家出走。
但是還得回去。郭一說,我就沒離家出走過,一次,哪怕一次,都沒有。小時候不敢,偶爾想過,后來又想,真這么做我爸我媽準會哭瞎眼。后來大了也就更不想了,不知道想有什么必要。真走了也沒什么必要。
接下來又是很長一段時間的沉默。郭一用手摳黃油果醬。她沒有碰小圓面包,否則會讓她有一種坐飛機的感覺。
我給你講一個考察站的故事吧。高個子說,很突兀,而且他顯然不會講故事。故事是這樣的:我忘記是哪個國家的考察站,一個駐站人員,在這里工作了一年,第二年終于可以換回國了,但之后沒有人接替他,他只能繼續留一年,于是在一天夜里,他就將考察站燒了。大概是五十年前的事情。我想起來了,可能是英國,因為后來他就回到了英國,蹲了監獄,妻離子散,大概這樣。
后面的就沒意思了,郭一說。但前面的很有意思,就是瘋了的那個部分。并且郭一感覺,高個子大概一直想找一個人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后面的讓這個故事變得很合理。高個子說。
我覺得前面的更合理。我受不了在這里一年,我從上船的第一天就有一種預感,我要下船,盡快下船,但是一旦開出去就哪兒都下不去了,除非跳下去,可我也不會跳下去,我怕冷。
郭一說出這個“冷”字的時候,真的有一股冷意,她縮縮肩膀。
你為什么給我講這個故事呢?郭一很懷疑,有點恐懼,她想:他要干什么?進而她又想到,這個故事和你的鼻子有什么關系嗎?
酒很快喝完了,因為無話可說,之后兩個人分別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機,但是郭一的手機沒有信號,除非她打開信號。她感覺此時此刻,兩個人應該分別看一眼手機然后心滿意足地說:我的老婆(老公)沒有給我打電話。也許高個子有老婆,但,郭一真的沒有老公。因為只有這樣心滿意足地說上一句之后,他們才會意識到真的應該各回各屋了。
高個子臨走的時候說:要不要我幫你把空瓶子拿出去?
高個子走后,郭一再次打開網絡。她忍不住撥了何多的語音通話,并非借著酒意,她覺得有意思的事情也變得沒意思了。電話里的聲音,一絲一絲遙遠空濛,她感覺一只不存在的野獸的舌頭在舔舐自己。響了幾下之后沒有人接聽,郭一沒有再等,掛斷。她想得非常荒誕,她覺得何多一定不敢接,掛斷之后何多的微信就過來了,三個字:有事嗎?郭一回了一句:你沒有資格再騷擾我,你又不是我的摯愛,然后就直接拉黑了。大概說出了摯愛兩個字讓她感覺大好。分手之后為了保持體面一直沒有互相拉黑對方,她想,自己拉黑了一個從不手淫的人,這多么珍貴。
何多不能告訴郭一什么是真的,郭一也不能告訴何多什么是可笑的。她反復咀嚼“摯愛”這個詞,覺得終于將它說出口了,她知道也許艙外最后一絲天光已經消失了,但她看不到。
之后,郭一在沙發上睡著了還做了一個夢,夢里自己一邊想事情一邊數地上的瓷磚,忘了夢里想的是什么事情,什么地方的瓷磚,她就感覺自己在想事情,也不是重大的事情,但是若有所思。夢里很清晰,瓷磚是正方形的,非常非常正,很多正方形又拼成一個更大的正方形。
第二天一早,外面的太陽渾圓臃腫,看上去更像一個太陽。太陽很狂又很確定。在餐廳,她又碰見了導游。
郭一說:昨天暈船。
導游說:怪不得沒看見你。
郭一說:我一會兒回去還要躺著,對不起啊。
說著郭一站起來,她沒有回船艙,她去了餐廳的洗手間。她一個人把馬桶蓋掀起來,褲子沒脫就在上面坐著,馬桶和門的距離合適,正好可以睡一會兒。她想:如果一切順利,今天她就可以看見企鵝了,雖然不少人警告她企鵝非常臭。她想和一只企鵝拍照,她覺得自己更像一只綠色的企鵝,因為衣服的緣故。但是她也有一絲絲緊張,她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只企鵝配合自己拍照,不要等一切都準備好了,企鵝自己走掉了或者被更多的企鵝擠跑了。當她這樣想的時候,有人敲門,她不敢回答,她擔心是導游。又過了一會兒敲門聲更猛烈,她起身按了沖水按鈕,出來的時候發現是一個準備打掃的黑人,她說了幾句sorry。很謙卑,她幾乎感覺到了自己無恥的樣子。
之后她來到頂層,頂層更貴,她還沒有來過。船艙下面有一個大吧臺,頂層有一個小吧臺,更小,但是有幾個巨大的真皮沙發,和一架鋼琴。郭一發現小吧臺的地板都是正方形的瓷磚,這很難不讓她想到昨天的夢。唯一的不同是夢里一點聲音都沒有,她是默片里的主人公。胖阿姨和瘦阿姨也在這里,她們真的是非常有錢的老年人,住在了海景房,不知道她們是不是能接受頂層的劇烈搖晃。她們分別做了發型,一定是那個內蒙古人干的。她們正在聊船票的價錢,因為不同的渠道于是不同的價錢。阿姨們旁邊還有一個小女孩,大概沒上小學的樣子,郭一想:她真幸運,小小年紀就看遍世界各地。小女孩撥弄琴鍵,郭一聽出鋼琴很久沒有調過了,大概從這艘船建造好之后就沒有調過了,像冷戰時期的聲音。她已經沒有那么期待見到高個子了,因為就算是共度的時光,她也沒有把想說的話說出口,那些好奇的問題已經消失不見了。小女孩見人并不害羞,大概是郭一也長了一張娃娃臉的原因。小女孩走過來說:姐姐,你可以用紅被子燈塔列車大戒指給我講一個故事嗎?
郭一摸了摸她的頭,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她為什么在這里。想問她是怎么想到這幾個詞,而不是那幾個詞的。而這一切又和此時此刻有什么關系呢?
郭一低頭說:紅被子,燈塔,列車,大戒指……但是她毫無思路。小女孩仿佛并不在意她的答案,只是想調戲她。調戲,沒錯,就是調戲。她閉上眼睛,感覺鋼琴里傳來了一首溫柔的樂曲,這讓她獲得了片刻的寧靜。她坐在一艘船上,這艘船正在駛向地球最寒冷的地帶。她想,很快自己就會適應船上單調重復熟練的生活。人應該好自為之。
片刻之后她感到一種解脫,因為無處發泄的憤怒而帶來的一種解脫,于是她干脆給導游回了一句微信——我不是作家,我是詩人,給你看看我寫的詩,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于是她把讓何多惡心的那首詩貼了過去:
所以最后
你背井離鄉
對著一只企鵝手淫
當然,郭一原來的詩并不是這樣的,她因地制宜做了調整,僅僅保留了手淫兩個字,她非常想激怒誰。點了發送之后她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她一直覺得自己的鼻子不是很漂亮,很塌,戴上眼鏡多半會掉下來,當然,也沒必要很漂亮。她可以做整形手術,但是這一切又有什么區別呢?
自問自答
說說這篇小說?
2020年年初一個人去南極,因為結婚了想一個人去遠一點的地方。在剛踏上南極大陸的一瞬間有被打動,但是這種打動很快就消失了,只想快點回到北京,這篇小說寫的就是在南極無聊的日子,也是我理解的自深深處,空無一物。
2020年最大的體會……
下半年懷孕了。此前一個月,姥爺去世。懷孕就是一個人的身體里包含著另外一個人。漫無邊際想了很多,比如我可以接受自己變老,但是不能接受寶寶變老,但這不也是另外一種矯情嗎?一本書上寫,未來世界的第一個永生人已經誕生,這讓我想起朋友寫過的一篇文章叫《活去吧》,但聽上去就像是一個倒霉蛋。
不再害怕什么?
今年不再害怕去醫院了,甚至有點愛上了去醫院,還陪老公去過次急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