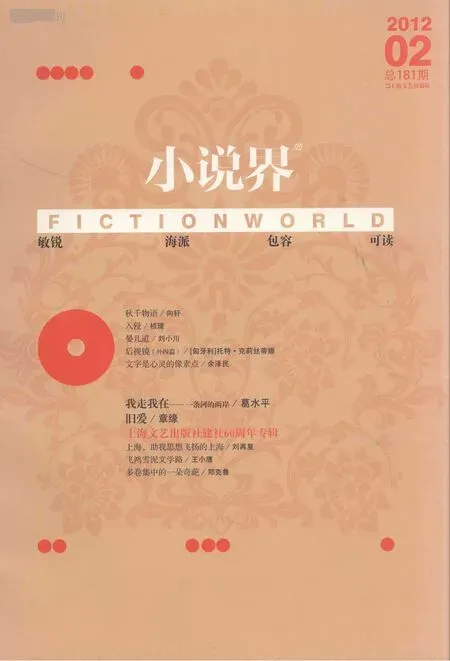小老虎:奇妙的大腦奇妙的嘴
項斯微



但凡聽過獨立音樂人小老虎的說唱,感受過他即興的能力,都很難不去好奇他的大腦里究竟裝著些什么,才能使那些奇妙的文字組合,源源不斷地通過他的嘴說出來唱出來。
對此,小老虎自己其實也想知道。
在美國,小老虎遇見過一個腦科學家,見識了他的即興表演之后,腦科學家走過來拍拍他說:“你這(即興)都怎么來的?”小老虎答:“就跟說話差不多。咱們倆在交談的時候,你也沒過多去想,但你不也說了出來嗎?”
事后回想起來,他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一個腦科學家他(居然)問我這個問題。其實仔細想想,我那個回答不算很像樣。現在大家已經這么電腦化了,對人腦的認識還是極少。”
近些年,他迫切地想了解“大腦的運作”這類關乎事實的事,看了大量非虛構方面的書籍。
想不到吧!
浪漫的,天馬行空的
在說唱藝術越來越被關注的當下,做了多年說唱的獨立音樂人小老虎也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在沒有參加任何一檔當紅說唱綜藝battle的情況下,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當然,比起其他音樂形式,說唱在中國大眾眼中依然算新鮮事物,只能說環境比過去要好。也有不了解說唱的人,以為說唱的主題大多都是金錢、女人,或者是“得不到的金錢和女人”。說唱歌手不被尊重不被看重的事,也時有發生。
小老虎用作品說話。
他的創作里,當然有金錢,但那可以是“有時候不想上班”的社畜在對抗著“糟糕的物價飛漲”,也可以是“華爾街的禮花彈”;他的創作里,當然也有異性,但異性可以是“一千顆流星落在我們嘴里”的抒情對象,也可以是被“命運拔掉頭發”的Juliana,更有可能是北京胡同里的老大媽。
他把詩人食指朗誦《六十甲子》的原音放進作品里,取名《一個詩人的晚年》。他在歌里寫故事,描繪站在河岸邊打水漂的人、變成熊的音樂家。
他也在歌里回應“如何評價說唱歌手小老虎”:“有人稱贊,說他是個詩人,有人說他是個鄉村配樂詩朗誦,有人說他是個藝術家,有人說他連韻都不會押……我只知道,谷歌沒我懂你的寂寞。”
多戲謔,多詩意,多浪漫,多天馬行空,現實生活中的一點一滴,都被他寫進歌里,闡釋,解構,再創造。
但走進小老虎位于上海市區的家中,細細打量他堆滿書籍的餐桌、書架、唱片架,會發現,浪漫和天馬行空并不多見,反而是非虛構類書籍占領了大部分山頭。書架上,北京80后文藝青年繞不過去的《王朔文集》已是屬于過去的回憶,并不會再被他拿起。
小老虎的閱讀趣味,那是相當嚴肅的。
羞赧的,遲疑的
小老虎手邊在看的書有好幾本。
目前在看的書是購于深圳舊天堂書店的《何以為我》、出版社朋友寄來的賈森·雷諾茲的詩體小說《最長的一分鐘》、基思·約翰斯通的《即興》……唯一一本“正正經經”的小說,是跟著朋友一起看的雷蒙德·錢德勒的《漫長的告別》,他把主角馬洛聽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圖良(蘇聯作曲家)感到不耐煩的段落摘出來,發上微博,夸贊馬洛是個迷人的偵探。
詩體小說《最長的一分鐘》的主角則是個15歲的黑人男孩,“故事簡單地說,就是一個黑人男孩的哥哥被槍殺了,他就拿著槍要去報仇,一層一層下電梯,最后下到一樓,這書完了。其實是首敘事詩。賈森·雷諾茲的語言很有意思,有很多的文字游戲,還有很多符合口語甚至說唱押韻這種音律的東西,含有音樂性,我覺得就很好,當時想著是不是能做些音樂方面的嘗試。”
在小老虎看來,能有出版社給他寄書,是件好事,當然“不是為了省錢”,而是因為可以收到一些平時他“看不見”的書,就像《最長的一分鐘》,他看了會有收獲,“這兩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覺得我好像有點文學氣、人文氣質,所以這種跟音樂、跟黑人文化相關的這些書,可能都會寄給我。”
話題一旦觸及“文學氣質”這種事,個頭很高的小老虎顯出了一些羞赧,一些遲疑。說到創作中的文學性和詩意,他會說自己在歌里寫的頂多算是“小故事”,不能被稱之為“小說”,“我沒寫過小說,想,但是有點畏懼。我說唱里很多故事性的東西是來源于滋養我的故事書,很多很多,像田中康弘的《山怪》,還有一些典故。我小時候就喜歡看希臘神話、伊索寓言這類的。”書架上,《西游記》《一千零一夜》《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被他整齊地擺在一起。
小老虎承認自己喜歡詩歌,“我喜歡詩歌的一些抽象性,詩歌的畫面感也好,速度感也很好,語句之間給人聯想和回味的余地。”但如果定義他是個“說唱詩人”,他會跳起來立馬撕掉這個標簽,并且覺得“惡心”。
可能在他的自我定義中,自己頂多算是個詩歌愛好者。他提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鮑勃·迪倫:“誰的勤奮程度能趕得上他!他太厲害了,因為他是第一個在音樂領域里——就跟傻不拉幾的陳凱歌拍的《梅蘭芳》里說的,別讓人家瞧不起咱、提拔咱們行業的那種,鮑勃·迪倫就是這樣的人。在他之前,所謂的流行音樂里面,歌詞從來沒有上升到一個有所謂的文學價值的層次,無論美感還是表達,是他憑一己之力,把這個東西弄到這了,后來才有可能出現更多的優秀的詞人。所以現在讓我真說我比較喜歡的詩,我倒真寧愿說很多就在音樂里,而不是舉一些特朗斯特羅姆之類的。我覺得特別好的一些,真的影響比較深的,其實反而是這些音樂里的歌詞。”
偉大的,深層的
故事與詩歌之外,小老虎目前的閱讀興趣,集中在非虛構這塊。他隨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本書,翻得有些舊了,是《腦袋里裝了2000出歌劇的人》,由美國神經病學專家奧利弗·薩克斯所著,一本關于音樂與大腦的神奇之書,“里面講了他的很多病例,有很多音樂跟你的健康、你的想象、你的聽覺和很多的神經之間有關聯。里面有很多神奇的案例,比方說一個能記住2000出歌劇的人,一個得了阿茲海默癥的人。你可能說不出完整的話,你也記不清楚很多事,但是你對一些音樂的記憶極其清晰,放一首歌你就跟著唱,甚至歌詞也記得很清楚。”
由小說閱讀轉向非虛構閱讀,在小老虎看來,也許是因為他希望借此解答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疑問,“小說當然也能帶來思考,但是社科類、非虛構的寫作,可能就會更直接。非虛構類的書籍也讓我更好判斷,基本在書的封皮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它是研究什么的。如果是虛構類的話,可能就需要去關注很多文學評論和靠朋友推薦”。
至于買書,小老虎還是習慣去書店買。回北京,他必去三聯書店,這兩年搬來上海,路過不錯的書店他都會進去逛逛,他還在上海的神獸之間書店辦了三個月的會員卡,“那里不是可以借書嘛,我借了兩本書,一本是語言學的,一本講腦科學的。”
不難發現,身為說唱歌手,小老虎真的是對語言和大腦非常感興趣,有種端正的學習態度。
“我依然覺得語言可能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整個文明全都建立在語言之上,所以我是非常尊重而且重視語言這東西的……至于大腦,我覺得誰都應該感興趣,大腦是人類最后的價值了,但我們又對人腦的認識很少。在這個領域,我更感興趣的是,比如即興說唱是怎么來的。”他明確知道自己有語言天賦,也隱隱知道一些大腦的運作原理,就像即興,“我知道一點點方法和規律的東西”,但更深層的東西呢?他希望能通過閱讀,了解得更多一點。
小老虎還干過一件事,就是讓搞電腦科技的朋友分析自己所有的歌詞,看看哪個詞用了多少遍、出現最多的詞是什么之類的事,他把分析報告保存在電腦里,借此了解自己創作中的語言習慣。
叛逆的,抓不住的
虛構小說就這樣悄然退出了小老虎的閱讀世界嗎?這么說也不盡然。小老虎也有過瘋狂看小說的時期,那時,他還在北京讀中學。憶當初,那個不好好學習的中學生叫做趙宏,距離他被“小老虎”這個名字套牢,還有好幾年的光陰。
趙宏只有語文成績拿得出手,但他不在乎。
少年趙宏和兩個好朋友組成了秘密團體,“他們倆也熱愛音樂和電影。班里的人都在積極地上晚自習備考,我們就聽著音樂,聊藝術電影。那是我最早確立自我價值的時期。當時也挺偏激的,就知道這是一種自我確立,看其他人都跟傻×似的,而我們感興趣的,是牛的東西。”
那時,小老虎對學習基本是放棄狀態,“家里人也覺得你不靈了,在學校也得不到什么肯定。我們就躲進小說里。我們學校當時有個很大的圖書館,二層是封起來的,我們就專門翻到二層去偷書。當時也是有點傲氣,覺得其他人都是只知道學習根本不看書的,圖書館給他們沒有用,我們才是真正關心和懂這個的人。”偷到后來,他們仨都偷成精了,還按版本偷,按出版社偷,“比如說商務印書館的,或者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甚至同一本小說我們還會看譯者是誰。”
在圖書館,趙宏“偷”到了一套四本的《王朔文集》,一下子就著迷了,“當時我就沉浸在王朔的小說里。之前可能喜歡的還是《圍城》這種。”王朔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一是他寫作的背景就是北京;第二是他的那種語言比較好讀,總體有一種頹廢和叛逆的感覺。我覺得叛逆可能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這跟我喜歡說唱音樂,包括前期接觸搖滾音樂,有點一脈相承。叛逆我覺得特別重要,包括現在的這些說唱音樂跟脫口秀,種種,我覺得精神內核都是這個。王朔的叛逆也是比較多樣的。我大學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王朔。”
對,盡管頭幾年沒好好學習,但選了文科的趙宏還是順利地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他現在已經不會再讀《王朔文集》了,但那種叛逆的精神內核還一直跟隨著他,在他身上“起著作用”,也被他放進說唱里。
他的那兩位好友,當時還偷了一本赫爾曼·麥爾維爾的《白鯨》送給他,希望他“像白鯨一樣(保持)抓不住的那種感覺”。那本《白鯨》,到現在小老虎也沒看完,但是這份發自好友內心的祝福,小老虎一直沒忘記過。
小老虎×他的書單
“很多作家,都是一說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其實作品并沒有認真讀過。你還老覺得自己對他們有種想象,這想象慢慢還變成了真的。”比如說愛倫坡,比如說張愛玲,真正讀過之后,小老虎才理解了他們的奧義。
所以說,讀書真不能自以為是,這可以算是來自小老虎的閱讀忠告。
在小老虎的書架上,其實還有很多漫畫書,他和很多中國獨立漫畫家都是好朋友,中外漫畫都看得很深入。他的書架上還擺著異常漫畫所出的漫畫家逆柱的怪獸撲克牌,一看就是老漫畫人——“漫畫里的文學性其實也是非常強的。”
他本來想著要推薦一兩本漫畫書,我們一看,都不好買。罷了,還是來點非虛構吧。
《何以為我》(阿列克斯·提臧)
“就像女人絕不是低人一等的性別,男人也不是。”
《山怪》(田中康弘)
“盡管我是一個越來越傾向于非虛構類閱讀的人,但我還沒有無趣到無法相信這些傳說。”
《斜目而視》(斯拉沃熱·齊澤克)
“挺難懂的一本書,但里邊舉的通俗文化里的那些例子都非常的偏門,而且有趣。”
《土摩托看世界》(袁越)
“這是一個我真實見到的,把理性、嚴謹、科學和浪漫結合在一起的人。在我們都因病毒無法去看世界的時候,借著這本書帶你出去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