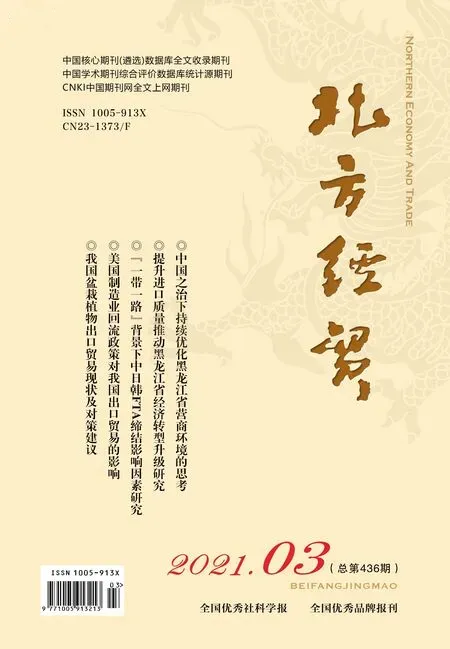“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三維探析
王雪慧,殷昭魯
(魯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煙臺264025)
自古以來,海洋就是聯通世界各國人民相互交流與溝通的紐帶與橋梁,同時也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重要資源寶庫。因此,“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一個明顯的軌跡,就是由內陸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強盛”。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依托于海洋,人類社會的交流聯通依靠著海洋。當前以海洋為載體的市場、技術、信息、文化等全球化合作正在日益緊密。因此,共同構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提出既順應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新趨勢,加快海洋領域全球化的進程,同時通過構建海洋領域的開放平臺還能夠推動“海絲”沿線國家間在海洋領域的交流、合作與發展,深度契合“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
一、歷史之維:延續中國古代絲路精神
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于秦漢,發展于魏晉,繁榮于隋唐,鼎盛于宋元,停滯于明清,是一條始于絲綢、茶葉、香料、陶瓷衍生為經貿文化交流的世界性海上貿易黃金通道。因為我國歷史的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與波浪式前進的相互交錯的過程,因而我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不斷在曲折中得以向前接續發展。
(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秦漢時期,我國進入第一個大一統階段,國家的相對安定以及國力的較為強盛都為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在這一時期,伴隨著木帆船的產生發展以及近海航行技術的極大進步,加之當時的人們已經能夠準確摸索到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季風規律并將其準確應用在航海上。因此,在秦代我國就已經有徐福船隊東渡至朝鮮、日本,在漢代更是出現西漢海船遠航至印度洋,這條航線也成為我國最早開辟的“海上絲綢之路”。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繁榮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我國再度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社會的動蕩不安也延緩了我國海上貿易活動的持續發展。但是由于當時我國的東南沿海形勢相對穩定繁榮,因此在這一時期我國航海中心開始自北向南轉移,東南沿岸出現了東吳船隊巡航臺灣與南洋,同時隨著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航運技術的不斷發展,在當時通商的絲路船隊最遠已經能夠到達波斯灣海域。
結束魏晉南北朝的動蕩時期后,我國也迎來第二個大一統階段———隋唐時期。在隋唐時代,我國經濟社會得到空前發展,引領著世界經濟貿易潮流。特別是在以開放和包容為氣度的唐朝,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藝術、思想等領域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國的航海技術也因此得以日趨成熟完善,那時的人們不僅能熟練掌握季風航行、利用北極星的高度進行天文定位導航、運用觀測計算的“重差法”測量航海陸標,還能夠準確解釋潮汐現象以及利用赤云和暈虹預測臺風。因此這一時期,大陸與臺灣恢復了通航,鑒真東渡直至日本,海絲商船直航遠至紅海與東非之濱。在東海、南海和印度洋上,滿載著我國各類貨物的船只隨著季風航行而去到亞歐各國,又帶著絲路沿線各國的物產、科技、宗教回歸國內。各國的文化、思想、科技在海上絲綢之路得以交匯、融通。唐朝國都長安也因絲路興盛,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國際性都市,各國使臣、商人、僧侶紛來沓至。但即便當時唐朝處于世界中心,我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也一直都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建立在平等自愿、互學互鑒的原則上。此外,隨著“海上絲綢之路”在唐朝的全面繁榮,在我國東南沿海還出現一批像廣州、泉州的大型海港,同時唐代為了大力發展對外航海貿易事業還專門設置了總管海路邦交外貿的市舶使。但隨著唐朝的由盛轉衰,我國又一次經歷分裂局面。五代十國時期,東南沿海航海貿易的昌盛繁榮使我國海上絲綢之路保持著接續發展,而這些都為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三)“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與衰退
宋元時期,以羅盤導航為標志的航海技術取得重大突破,我國也率先進入“定量航海”的新階段,再加之水密隔艙技術在造船業的廣泛應用以及前人廣泛積累的天文、季風、臺風等一系列航海知識得以熟練掌握,宋代開辟出了第一條橫越太平洋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靖康之變”后,宋朝皇室開始南遷,在這一過程中大批具有先進造船經驗與航海技術的工匠和農民也隨之南遷,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最終完成。因此,南宋時期就更為注重對“海上絲綢之路”線路的開拓,建立通航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也達到了五十多個。而到元代,無論是遠洋航行規模還是造船、航海技術更是遠超唐宋,“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甚至已經能夠延伸至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沿岸,與一百二十多個亞非歐國家建立了“海上絲綢之路”航線。
自1405 年起,明成祖朱棣派遣鄭和七次下西洋,遍訪亞非各國,深度開拓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較為系統完善的海上交通網絡。然而,在鄭和下西洋不久明朝政府就開始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隨著明清封建主義逐漸保守與僵化,我國繁盛一時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從此進入由盛轉衰的停滯時期。
縱觀近千年來,我國的“海上絲綢之路”跨越茫茫大海聯通著世界,為促進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以及東西方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碰撞作出了巨大貢獻,開放性也由此成為我國古代絲綢之路最鮮明的精神特質。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這也就是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國際間普遍廣泛的交往使世界各國不斷對外開放從而成為一個整體,各民族、各國家也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信賴中形成普遍、完備的生產方式,歷史也真正轉向“世界歷史”。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正是在準確把握歷史與理論辯證關系的基礎上融通古今,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重新解讀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并賦予“海上絲綢之路”新的時代內涵。因此,“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提出既延續了我國古代的絲路精神,同時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在新時代的中國化運用。
二、實踐之維:開創國際海上合作新范式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將我國“對外開放”與“經略海洋”這兩大戰略思想相聯系,以國際重要港口為節點,旨在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通融、民心相通,推動生產要素依托海洋在國際間自由流動,開創合作模式多樣、涉及產業多元、覆蓋范圍廣泛的國際海洋經濟合作新范式。
(一)“政策溝通”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提供首要保障
我國通過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構建藍色伙伴關系、簽署海上合作備忘錄或合作規劃、參與多邊合作組織等多種合作機制共同制定新政策、達成新共識。2014 年,我國與馬爾代夫共和國簽署共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諒解備忘錄并與斯里蘭卡簽署“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馬欣達愿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2015 年,我國同匈牙利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關于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這也是我國首次同歐洲國家簽署關于“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文件。2017 年,我國與葡萄牙正式建立了藍色伙伴關系,并與歐盟共同舉辦了“中國- 歐盟藍色年”。2018 年7 月,中歐又簽署《關于為促進海洋治理、漁業可持續發展和海洋經濟繁榮在海洋領域建立藍色伙伴關系的宣言》。在此基礎上,2019 年9 月,首屆中國- 歐盟海洋“藍色伙伴關系”論壇在布魯塞爾順利舉行。由此可見,“政策溝通”不僅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與沿線各國政府之間的政治互信,更為投資、技術、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在國際海洋領域間的自由快速流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設施聯通”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基礎領域
港口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和樞紐,打通了中外交往的海路,書寫著國際海洋貿易新篇章。因此,我國一直都是在尊重沿線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在吸收高質量、高效率的海洋生產要素進入我國國內市場的同時,將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海上基礎設施產業推向全球化市場,從而推動我國一批優勢涉海企業“走出去”,主動承攬國際海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將優勢涉海“產業整體輸出到不同的國家去,同時幫助這些國家建立更加完整的涉海工業體系”。“設施互聯”既能最大程度實現國內資源有效配置又能夠助力國際港口基礎設施優化升級,推動國際社會共同建設安全高效的海上運輸大通道。至2019 年4 月我國已經在全球20 個國家參與了56 個國際港口的建設或投資,并建成多條安全通暢的海上通道。目前,我國仍在建設的國際港口有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希臘比雷埃夫斯港、阿聯酋哈利法港。
(三)“貿易暢通”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核心內容
“經濟要發展,國家要強大,交通特別是海運首先要強起來。”我國憑借經濟實力強、輻射帶動作用大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區域優勢,自2009 年開始推進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大連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建設;2011 年推動建設天津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廈門東南國際航運中心;2015 年又提出打造廣州南方國際航運中心。當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以上海為中心南北分布均勻的國際航運中心體系。至2019 年11月,我國已經相繼建立上海、廣東、天津等十八個自貿區和海南自貿港,并與47 個絲路沿線國家簽署了38 個海運協定。其中,以“絲路海運”命名的有“50 條航線,開行1024 個航次,完成集裝箱吞吐量86.12 萬標箱,同比增長超過10%。‘絲路海運’的規模和國際海運品牌影響力不斷擴大,推動了國內港口與沿線國家港口之間的貿易往來”。
(四)“資金通融”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提供有力支持
構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構建世界范圍內廣泛的利益共同體,拓寬海洋產業國際合作的投融資渠道,打造以我國為中心的國際政經網絡。因此,除了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專項資金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我國各級政府、境內外金融機構、民營企業等主體也為“一帶一路”倡議設立多種專項基金與貸款。至2017 年底,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國際性專項投資基金有20只,地方性絲路基金有52 只,而這其中專門涉海的專項基金就有4 只(如表1 所示)。

表1 2011-2017 年涉海的“一帶一路”專項基金
(五)“民心相通”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凝聚社會力量
近年來我國舉辦了中國海洋經濟博覽會、廣東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博覽會、中國(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品牌博覽會、“海上絲綢之路與跨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一系列國際海洋交流會議、設立了“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項目、打造了以“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特色的專屬旅游線路、還舉行了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題的國際藝術活動等一系列與海絲相關的活動。同時我國還積極舉辦了2016 年瀾湄國家旅游城市(三亞)合作論壇、2020 第十二屆青島國際帆船周·青島國際海洋節等一系列涉海的國際性會議與賽事。通過這些活動,筑起了我國與沿線各國相互交往的橋梁與紐帶,更加深了各國民眾之間的認知與了解,增進了世界海洋文明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三、目標之維:彰顯“海洋命運共同體”最高指向
當今世界處于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范圍內百年未有之變局加速變化,新的挑戰風險也層出不窮,例如當前隨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而在海洋領域,當今世界各國間海洋權益的博弈也進入到了“白熱化”階段,沿海各國都想在海洋開發中占據更多海洋資源優勢,因此想要解決當前各海洋國家日趨激烈的爭端,就需要用共同體思想去化解這些爭端。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將“世界歷史”理論同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相融合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下重新審視我國乃至世界因海洋問題產生的諸多矛盾,對未來世界海洋發展提出了“海洋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
(一)“海洋命運共同體”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在海洋安全領域的進一步深化
一方面,“海洋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在海洋安全領域的進一步深化。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基本出發點就在于我國在處理國際海洋利益爭端時始終秉持的是平等協商的基本立場,并始終提倡世界海上武裝力量以共同體這一形式進行有效的交流與合作,以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共同保障海洋領域的和平與安全,以此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展營建一個和諧穩定的外部海洋環境。
(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實現“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平臺
另一方面,“海洋命運共同體”既是一個理念,更是一項長期實踐。“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則是實現“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平臺。在海洋經濟發展過程中,世界各國在海洋國際貿易、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環境保護等諸多問題上都是緊密相連的。特別是自2008 年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上升,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而在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導的國際治理體系之中,“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嚴重缺乏話語權,導致一個不平衡、不對等的全球化。……基于這種大形勢,東盟國家出口受阻、投資資金不足。而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國內市場,可以吸收其商品,也可以為其提供資金,滿足其外部市場與資金需求。”因此,我國所提出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在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則的基礎上,希望世界各國都能以“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為紐帶擱置海洋權益爭端,增進國際合作的共識,共同應對海洋領域的安全威脅,共同開發、利用、保護海洋資源,構建一條依托海洋走向世界,推動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海上經貿之路,并以此帶動國際間藍色經濟的協調發展、藍色文化的相互交融,讓沿線各國人民過上“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海洋福祉,最終彰顯了“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最高指向。
經略海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和平崛起過程中的陸海復合型國家而言,其重要性日益凸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他對新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勢的把脈,是他對中國海洋事業發展的頂層設計,也是他治國理政、推動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抓手之一。該倡議不僅是推進中國“海洋強國”建設中的重要一環,同時因與“海洋命運共同體”結合而更具世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