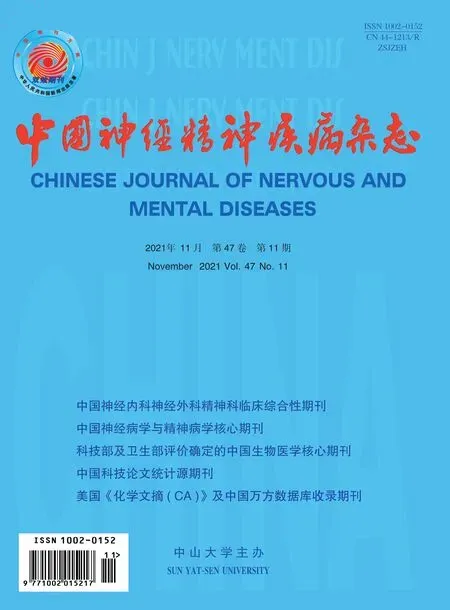自殺與非自殺性自傷青少年額邊緣系統腦區神經影像學研究進展☆
黃倩況利
自殺自傷行為因其發生率及相關風險嚴重性的不斷攀升而逐步引起學術和臨床領域的共同關注[1]。常見的自殺自傷行為包括自殺未遂(suicide attempt,SA)與非自殺性自傷(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二者在青少年時期常共同發生,是自殺死亡的顯著預測因素[2-3]。兒童青少年時期是一個獨特的發展階段,從神經發育的角度來看,這是前額葉系統和邊緣系統發育不同步的時期[4]。額邊緣系統由多個腦區組成,包括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PFC)、扣帶回皮質(cingulate cortex,CC)、杏仁核(amygdala,Amyg)、島葉(insular,INS)、海馬(hippocampus,Hipp)等,與情緒處理和調節、獎賞處理及認知控制緊密相關[5-7]。考慮到額邊緣系統在自殺自傷行為發生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且自殺自傷行為的早期有效識別、預防及干預有助于降低自殺風險,本文對近年來青少年自殺和NSSI的額邊緣系統腦區神經影像學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探尋有效識別二者的客觀神經生物學指標。
1 自殺與NSSI的特征及易感因素
自殺個體具有顯著的絕望、痛苦、社會孤立及沖動等心理特征[8-9],其患抑郁障礙、焦慮障礙等精神疾病的概率較高[10]。研究顯示,13~19歲青少年的自殺風險在性別、城鄉及家庭結構方面存在顯著差異[11]。兒童期受虐待或忽視、精神疾病家族史也與自殺風險較高有關[12-13]。NSSI行為是個體經歷了高度的情緒失調[14]、負性情感[15]和自我批評[16]后用于調節負性情緒或直接傷害自己的行為,其發生也常與抑郁癥等多種精神障礙緊密相關,兒童期不良經歷(如被遺棄、虐待或忽視)對其具有重要影響[8]。
青少年自殺與NSSI的易感因素值得高度關注。“素質-應激模型”認為自殺與NSSI是個體的生物學素質和環境應激源交互作用的結果。神經改變是生物學素質,這可能是導致自殺自傷行為的必要不充分條件。再加上特定的環境暴露,尤其是急性應激(如同伴傷害、人際關系缺失等),使得產生自殺和NSSI行為的可能性增加[17]。在兒童青少年時期,額邊緣系統中的前額葉系統和邊緣系統發育不同步,這一過程對動機性行為有直接影響,靠近、回避和調節系統的神經環路尤其起到重要作用。在動機性行為的三元模型中,靠近系統、回避系統分別受腹側紋狀體和Amyg控制,而用于平衡靠近和回避行為的調節系統主要受PFC控制[18]。因此,雖然CASEY等[4]提出青少年的危險行為源于皮質下邊緣系統發育相對于前額葉系統腦區更成熟的觀點,但自殺和NSSI行為也可能源于靠近、回避和調節系統各個水平上的缺陷。但神經改變不能單獨起作用,而是與應激源產生動態交互作用,進而產生青少年期的自殺和NSSI行為。
2 額邊緣系統腦區神經改變研究
2.1 神經結構影像學研究
2.1.1 自殺行為相關神經結構改變 腹側前額葉皮質(ventral prefrontal cortex,VPFC)和眶額葉皮質(orbital frontal cortex,OFC)的結構改變對情緒抑制、決策和自我控制至關重要[19-20]。在重性抑郁障礙(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和雙相障礙(bipolar disorder,BD)青少年患者中,有SA者VPFC和OFC腦區灰質體積(gray matter volume,GMV)較無SA者顯著減小[21-22]。另外,一項前瞻性研究也發現,基線態VPFC和喙側PFC腦區GMV減小可能增加了心境障礙青少年將來SA的風險[23]。上述研究結果表明,額葉GMV減小可能通過改變情緒調節、決策及自我控制過程參與自殺行為的發生。除額葉外,也有MRI研究報告SA者扣帶回皮質改變[24-25]。在BD青少年中,SA患者還顯示出Hipp、雙側小腦GMV減小[21]。以上研究提示邊緣系統腦區在SA中也可能起到調控作用。然而,目前大部分關于SA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精神疾病診斷背景,且額邊緣系統腦區的研究結果顯示出改變腦區的廣泛性及側性效應(左側和右側),表明其特異性較差,因此,尚不清楚這些差異源于SA還是精神障礙嚴重程度,未來可進一步探討單純SA青少年神經結構的影像學改變。
2.1.2 NSSI行為相關神經結構改變 總的來說,關于NSSI青少年神經結構改變的MRI研究相對較少。目前關于NSSI青少年PFC結構改變的研究僅有1項。該研究發現,NSSI青少年女性右側額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的GMV減小[26]。島葉(insula,INS)作為額邊緣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優先參與內部情緒的產生,并作為信號中繼站來維持體內情緒的平衡[27]。多項研究發現,與健康對照相比,NSSI青少年呈現出INS的GMV減小[26-2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傷的邊緣性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青少年中卻未發現此變化[29],提示INS的GMV改變,除受NSSI影響外,還可能與精神障礙診斷有關,例如BPD。另外,多項研究證實,前扣帶回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的GMV存在顯著改變。在BPD青少年中,過去6個月的自傷次數與左側ACC體積呈顯著負相關[30],關于過去1年有自傷行為的青少年和健康對照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結果[28]。后來的研究還發現,大多數NSSI青少年(55.2%)報告其終生有過SA,再結合前面提到的ACC腦區GMV改變與自殺行為之間的相關性[25],可以推測ACC腦區GMV改變可能參與自殺和NSSI行為的神經生物學過程,這可能有助于自殺和NSSI行為的客觀鑒別。然而,這仍需做進一步的縱向隨訪研究。
2.2 神經功能影像學研究
2.2.1 自殺行為相關神經功能改變 研究顯示,SA個體情緒障礙特別突出,每年高達50%的自殺發生在抑郁發作期,MDD患者自殺的可能性是健康對照的20倍[31]。情緒性面孔識別能力是能夠正確識別他人情緒性面部表情的社會認知能力,是尋求人際間社會交往的最基本技能之一。研究顯示SA個體存在一定的情緒性面孔識別能力障礙[10]。一項基于情緒性面孔識別任務的fMRI研究顯示,與基線態相比,伴BD的SA患者顯示出雙側Amyg與左側VPFC(快樂和中性面孔下)、右側PFC(中性面孔下)的功能連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減少,其中,自殺意念與Amyg-右側PFC的FC呈顯著負相關,自殺方式的致死性程度與Amyg-左側VPFC的FC也呈負相關關系[21]。另有研究表明,伴自殺意念青少年在主動觀看負性圖片的情緒調節過程中,右側背外側前額葉皮質(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活性顯著增高;而在被動觀看負性刺激時,右側丘腦、右側DLPFC交界處神經活動下降[32]。除基于任務態的fMRI研究外,靜息態fMRI研究也發現,伴SA的MDD患者較無SA的MDD患者在額上回、額中回腦區局部神經活動顯著降低[33]。以上研究表明,情緒調節相關腦區神經功能改變可能參與自殺行為的神經調控過程。但由于自殺與情緒障礙常伴隨發生,橫向研究結果仍不足以論證情緒調節腦區功能改變與情緒障礙和自殺之間的相關性。因此,在前期橫斷面研究探討自殺意念、自殺未遂神經功能改變的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開展縱向研究以明確自殺意念向自殺行為轉化、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強弱轉化的特異性神經生物學特征,這可能為未來實現對自殺的早期預警、早期干預提供了客觀影像學證據。
2.2.2 NSSI行為相關神經功能改變 NSSI是減少強烈負性情緒的常見方式,個體通常在實施NSSI行為后表達一種釋放情緒壓力后的冷靜感[34]。探討NSSI神經功能改變的fMRI研究中使用到多種情緒處理任務。在觀看國際情緒圖片系統(IAPS)和自傷圖片以刺激情緒反應的實驗中,NSSI青少年較健康青少年表現出OFC、頂下葉皮質和額中回/IFC活性增強[35]。在情緒面孔匹配任務中,NSSI患者較健康青少年在Amyg-額葉的任務態FC中表現顯著減弱,盡管這與預期相反,但在NSSI組中,每周自傷行為(切割)次數與Amyg-額葉的任務態FC呈正相關關系,提示這一神經環路可能與自傷行為的調節情緒功能有關,進一步地,在NSSI青少年抑郁癥狀得以控制后,這些發現消失,表明這一神經環路異常可能與NSSI青少年經歷的抑郁癥狀高度相關[36]。此外,DEMERS等[37]還報告在觀看面具性恐怖面孔(相比于開心面孔)時,NSSI患者情緒覺察和緣上回、右側IFC之間存在聯系。另有基于靜息態fMRI的研究發現,與不伴NSSI的MDD青少年相比,伴NSSI的MDD青少年顯示出額上回與多個腦區的FC顯著增強[38]。綜上,由于上述研究實驗范式及樣本等因素的差異,研究結果存在嚴重的不一致性,但以OFC、額中回、IFC及Amyg為代表的額邊緣環路腦區神經功能改變可能是未來進一步探討NSSI情緒調節反應的基礎。
沖動控制困難是NSSI個體重要的情緒調節缺陷形式,追求獎賞是沖動行為的維度之一[39]。在NSSI的fMRI研究中,Cyberball范式用于探討個體對社會排斥的神經反應。既往研究發現,與單純抑郁及健康青少年相比,伴NSSI的抑郁青少年的內側PFC和VLPFC神經活性增強,提示其嘗試做出監管調節的程度可能增加,但并未成功,因為在Cyberball任務后,與健康被試相比,伴NSSI的抑郁青少年表現更無助[40]。此外,在解讀他人的評價性社會反饋時,NSSI青少年也表現出負性偏見,這種偏見可能與對社會評價的不同神經反應模式有關[41]。少有的縱向研究發現,經8周N-乙酰半胱氨酸治療后,NSSI頻率減少與左側Amyg-右側補充運動區、右側伏隔核-左內側額上回的FC降低及右側Amyg-右側IFC的FC升高相關[42],提示這些腦區FC的改變可能是NSSI治療的有效靶點。另外研究還發現,在基線態時,NSSI青少年額邊緣系統腦區FC較健康被試顯著降低,經心理干預后,50%青少年報告NSSI次數減少,其中Amyg-PFC連接增強與NSSI改善程度顯著相關,表明額邊緣系統功能改變可能作為NSSI青少年心理治療后NSSI行為改善程度的預測指標[7]。上述研究結果提示,NSSI青少年沖動控制困難可能與情緒調節相關腦區的神經功能改變有關,對情緒調節腦區的關注可能激發將來對NSSI發生機制、治療及臨床預后的進一步探討,這些腦區可能是NSSI的特異性治療靶點。基于目前研究證據,未來可進一步以大樣本、多中心、多檢測手段及數據分析方法的方式來補充探討NSSI青少年額邊緣系統腦區的功能,此外,縱向研究仍具有重要作用。
3 小結與展望
目前研究初步探索了青少年自殺和NSSI行為的額邊緣系統腦區神經生物學改變,發現了以PFC、OFC、INS、ACC、Amyg等腦區為主的多個可能的自殺自傷行為標志性腦區及治療靶向腦區。但研究仍存在許多不足:第一,在自殺和NSSI行為的研究中,鑒于自殺和自傷行為常與精神障礙伴隨發生,研究樣本難以純化,故與健康被試的比較很難將這些神經改變歸因于自殺自傷行為本身還是精神障礙,進而差異腦區的特異性較差;第二,研究樣本量較小,不足以探討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等因素的影響;第三,大多數研究為橫斷面研究,縱向研究較為缺乏;第四,檢測技術和分析方法相對單一。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豐富神經檢測技術和數據分析方法,為探討神經改變的研究提供補充信息。另外,更大、更具多樣性的樣本在考慮內在異質性(如行為的頻率或方式、潛在疾病、藥物使用情況等)的影響方面也更具有優勢。最后,考慮到大多數有自殺和NSSI意念者會在一段時間內實施自殺或自傷行為[43],故縱向研究將有機會發現自殺和NSSI意念向行為轉變的神經標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