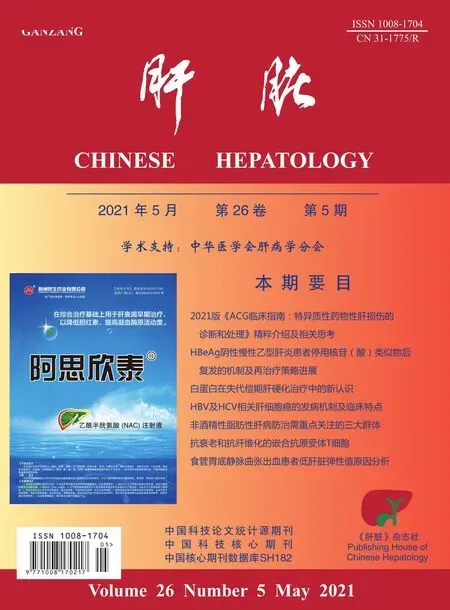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需重點關注的三大群體
宋葉雨 范建高
全球大約24%的成人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2030年美國將有約1億的NAFLD患者,由此導致的失代償性肝硬化、肝細胞癌(HCC)及其相關死亡發生率更高[1]。NAFLD與代謝綜合征密切相關[2]。該病流行范圍如此之廣,卻很少有公共衛生資金用于預防肥胖和NAFLD。若要采取干預措施預防NAFLD或延緩NAFLD進展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和肝硬化,應選擇能長期獲益、有影響后代潛力并具有更高纖維化進展風險的群體作為目標干預人群。基于這些原則,兒童和青少年、準父母以及絕經后婦女是合適的目標人群,需要采取干預措施以減少NAFLD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一、兒童和青少年
兒童和青少年NAFLD患者的病程可能會持續多年,在此期間他們可能會出現慢性肝病的并發癥。即使在控制酒精濫用之后,兒童時期體質指數(BMI)升高仍與成年期肝硬化、HCC和肝臟相關死亡有關。NAFLD患病率在5~6歲兒童約為3%,在青少年中約為8% ~11%,在肥胖青少年中約38%。與成年人一樣,兒童NAFLD患病率也存在種族差異。在一項包含582例2~19歲兒童和青少年的尸體解剖研究中,只有1%的非洲裔美國兒童患有NAFLD,而 8.3% 的白人兒童患有NAFLD[3]。值得關注的是,高達70%的兒童在診斷為NAFLD時已有肝纖維化[4]。包括對肝移植(LT)的需求的并發癥可能在成年早期就會發生,在1987—2012年美國聯合器官共享網絡(UNOS)數據研究中,330例40歲以下患者因NASH肝硬化接受了肝移植,其中14例年齡小于18歲,13例因NASH復發而再次肝移植。成人消化科醫生應抓住機會教育家長預防兒童NAFLD,家長指導下的干預在降低BMI方面有效。
飲食結構西化是兒童NAFLD發病的關鍵。富含精制碳水化合物的飲食與肥胖兒童NAFLD獨立相關[5]。在已確診NAFLD的兒童中,果糖攝入與血液γ-谷氨酰轉肽酶和腫瘤壞死因子的水平升高有關。攝入果糖會改變腸道微生物群和腸道屏障的通透性,導致肝臟脂肪合成、活性氧產生和尿酸水平增高,這些均會促進NAFLD的發生。不幸的是,含有高果糖玉米糖漿的產品是專門向兒童銷售的,這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背道而馳。
減少兒童飲食中的果糖含量將是一項具有挑戰性但值得努力的工作。為時9 d的兒童低果糖等熱量飲食與血壓、血清谷丙轉氨酶(ALT)水平、肝臟脂肪變性和新生脂肪生成降低相關。最近,一項針對11~16歲男孩的研究發現,8周的低果糖飲食(<3%)可以使磁共振成像質子密度脂肪分數(MRI-PDFF)定量的肝臟脂肪變程度減輕[6]。一項系統綜述和薈萃分析發現,應用果糖等熱量交換其他碳水化合物并不會促進健康個體肝臟脂肪變性,這些研究的數據質量總體較差。因此,盡管果糖的代謝作用表明它是唯一有害的,但總的能量攝入也是重要的。
運動是防治兒童NAFLD的重要措施之一。在肥胖兒童中,缺乏日常體育活動與肥胖兒童發生NAFLD以及肝脂肪變和纖維化程度嚴重獨立相關[7]。對NAFLD兒童進行運動治療,僅12周就可降低血液ALT水平和肝脂肪變程度,并可改善胰島素抵抗。不幸的是,尤其對低收入家庭兒童而言,參與體育鍛煉會有一些阻礙,例如缺乏負擔得起的、可到達的、安全的運動場所。
二、準父母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女性懷孕時子宮內環境對后代新陳代謝會產生持久的影響。女性孕前肥胖、糖尿病,孕期體質量增加以及妊娠期糖尿病,與游離脂肪酸向胎兒轉移增加、嬰兒肝臟脂肪儲備增加以及兒童NAFLD有關。孕婦NAFLD與早產和產后出血等不良妊娠結局有關[8]。父親肥胖僅與男性后代發生NAFLD有關,而與女性后代NAFLD無關[9]。令人驚奇的是,高出生體質量和低出生體質量都與兒童NAFLD和肝脂肪變的嚴重程度有關。提示生命早期代謝重編程通過改變DNA甲基化、組蛋白和染色質修飾以及微小RNA等表觀遺傳,選擇性地導致關鍵的穩態基因失調[10]。鑒于代謝綜合征與NAFLD關系密切,解決使兒童肥胖風險增加的因素對于控制NAFLD進展非常重要。
父母肥胖與新生兒臍帶血DNA甲基化改變有關,但在非肥胖父母的新生兒臍帶血中則沒有這種變化。至少有一項縱向研究發現,DNA甲基化改變可延續至童年時期,突顯了它們作為將來代謝綜合征易感性介質的潛力。這些表觀遺傳變化可以通過孕前減肥、鍛煉和調整飲食來抵消。在母親接受減肥手術前后出生的25組兄弟姐妹中,有5 698個基因在兄弟姐妹中存在甲基化差異,包括那些與糖尿病、癌癥和肝臟膽汁淤積有關的基因。對男性進行為期3個月的運動干預可使其精子全基因組低甲基化,包括印跡基因(在后代中保留父系甲基化),比如IGF2(其在NAFLD動物模型中過表達與肝脂肪變嚴重程度及纖維化進展有關)。孕早期對地中海飲食的低依從性與MEG3(一種長鏈非編碼RNA,可在體外模型中減少肝細胞脂質積聚)特定區域的低甲基化有關[11-12]。
嬰兒分娩的方式似乎也可影響兒童NAFLD的發病風險,機制可能涉及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而嬰兒腸道微生物群是通過接觸母親的陰道菌群而形成的。剖宮產出生的嬰兒存在腸道菌群失調,表現為雙歧桿菌減少、腸球菌和克雷伯桿菌增多,這可能導致他們易患NAFLD[13-14]。大型隊列研究表明剖宮產與兒童肥胖有關。在美國波士頓出生隊列中,與母親肥胖相比,分娩方式與兒童肥胖有更強關聯。
母乳喂養與兒童NAFLD、NASH和肝纖維化發生率較低獨立相關,并呈劑量依賴關系[15]。一項包含182例肝活檢證實為NAFLD的超重或肥胖兒童的研究表明,母乳喂養狀態與肝纖維化的關聯比patatin樣磷脂酶結構域3(PNPLA3)基因型更強(OR值:3.1比2.1);其他與NAFLD兒童肝纖維化相關的因素包括父母肥胖(OR2.9)、果糖攝入(OR1.6,增加1 g/d)、維生素D缺乏(OR1.24)以及母親社會經濟地位高(OR0.30)[16]。母乳喂養時間與瘦素(一種有助于產生飽腹感和調節代謝的基因)的甲基化有關,因此表觀遺傳學改變可能起到一定作用。
三、更年期婦女
絕經前后的婦女也是NAFLD防治需要重點干預的群體。更年期與NAFLD的高發病率和疾病進展有關。絕經前,女性NAFLD的發生率和晚期纖維化風險低于男性。絕經后,女性NAFLD發病率較高,晚期纖維化風險與男性相似[17]。一項針對488例絕經后女性NAFLD患者的研究發現,絕經時間越長,肝纖維化程度越重,絕經后每5年肝纖維化風險比增加1.2倍。可能的發病機制包括機體脂肪重新分布和糖脂代謝改變(如雌激素缺乏引起的胰島素抵抗),維生素D代謝改變可能也參與發病。卵巢切除術和多囊卵巢綜合征(PCOS)與NAFLD的發生、發展有關,支持雌激素在NAFLD發生和發展中的重要性[18]。雌激素是一種天然抗氧化劑,可減少脂質的合成和過氧化,并可能通過抑制肝星狀細胞的激活而防治肝纖維化。
鑒于雌激素的保護作用,有學者曾建議用雌激素替代療法(HRT)預防或治療絕經后婦女NAFLD。美國國家健康與營養狀況調查(NHANES)的大數據顯示,接受HRT的絕經后婦女NAFLD患病率比未接受HRT的絕經后婦女顯著減少(OR:0.69;95%CI:0.48~0.99;P=0.05)。然而,最近一項針對489例絕經后女性NASH患者的橫斷面研究顯示,HRT與NAFLD患者肝臟小葉內炎癥程度強相關。
飲食因素也可能會影響更年期NAFLD的進展。為期6個月的低碳水化合物和高纖維素飲食可使NAFLD患者血液糖化血紅蛋白和肝臟脂肪含量降低。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膽堿對于肝臟合成磷脂和膽鹽非常重要,它存在于雞蛋和動物蛋白質中。膽堿缺乏飲食可使模式動物發生肝脂肪變性,膽堿代謝途徑中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肝脂肪變性獨立相關。人體對膽堿的需求是由雌激素調節的,雌激素水平越高,對膽堿的需求越低。在一項對來自美國NASH臨床研究網絡的664例絕經后女性的研究中,膳食膽堿攝入量減少(少于推薦量一半)獨立于年齡和BMI與肝纖維化程度嚴重密切相關。然而,模式動物膳食膽堿和磷脂酰膽堿的其他代謝產物與動脈粥樣硬化有關。在一項地中海飲食預防試驗的巢式病例對照研究中,在調整已知的危險因素后,較高的血漿膽堿水平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相關(HR:1.72;95%CI:1.05~2.81)[19]。為此,膳食中的膽堿與其血液代謝產物水平之間的確切關系尚不清楚。膳食補充膽堿就像雌激素替代療法一樣,有必要進一步研究探討膽堿治療NAFLD的利弊,并警惕這些潛在的相互沖突的風險。據推測,體育鍛煉可以逆轉更年期相關人體成分變化。有限的研究顯示,24周的運動治療可改善絕經后婦女的心肺功能,但對肝酶和肝臟脂肪含量并無明顯影響。考慮到絕經后晚期纖維化風險增高,建議每年或隔年通過NAFLD纖維化評分(NFS)等無創方法密切評估更年期及絕經期婦女肝纖維化程度。然而,在65歲及以上老年患者中,NFS預測肝纖維化的敏感性可能低至20%,需要采用修正的臨界值[20]。
總之,針對易發生NAFLD不良結局的最高危人群的公共衛生干預對于減輕該病的巨大負擔至關重要,預計該病在未來10年將顯著增加。一些干預措施可以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對于病程最長的兒童和青少年,建議他們參與運動和低果糖飲食。對于準父母來說,在懷孕之前的鍛煉和減肥是很重要的。最后,對于更年期婦女,適當的膽堿攝入和重新評估肝纖維化分期將有助于減輕肝纖維化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