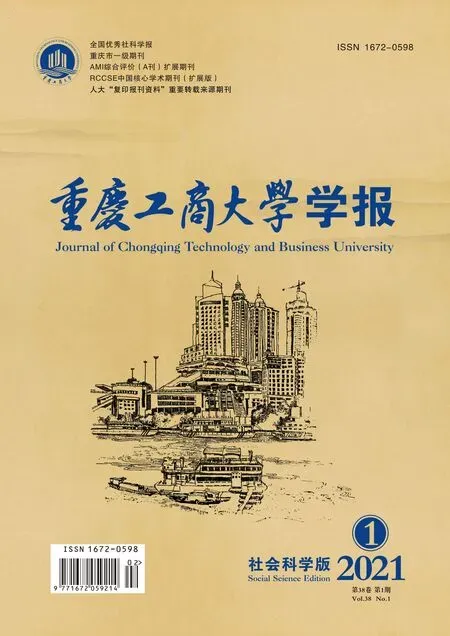我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起源再探討*
王春霞
(浙江財經大學 社會工作系,杭州 310018)
1934年北平精神病療養院社會服務部成立,標志著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在我國出現。筆者曾初步探索了民國時期北平、成都、南京精神病院的“生理—心理—社會”治療模式,展現了我國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早期發展狀況(1)參見《民國時期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研究——以北平、成都、南京三地的實踐為中心》載于《社會工作與管理》2016年第1期和《民國時期醫院社會工作研究》(第八章).人民出版社,2018.,然而這些研究只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淺層次挖掘,對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本身的理論技術分析不夠,從研究視角來看,學科史研究色彩有待加強。例如,社會工作究竟是如何嵌入精神病治療體系中的?精神科醫生為什么愿意與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合作?本文嘗試通過解釋“生理—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的形成過程、擴展和繼承延續,以回答上述問題。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學科視角單一的做法,進行精神病學、心理學和社會工作學科的交叉研究。
一、“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的形成過程
(一)精神病的兩種病因說
1934年,北平精神病院制定《精神病療養院組織規則》并報市政府核準施行,醫院先后設立了護理部、工業治療部、社會服務部、心理治療部、神經病理學實驗室和數據統計部,逐步建立起包括藥物治療、工業治療、社會服務、心理治療及溫水治療在內的精神病專業治療體系。[1]表面上看,北平精神病院社會服務部的建立只是延續了北平協和醫院的做法,其服務人員也全部由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選派并承擔薪資。實際上,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產生作為社會工作的一個重要分支,它的出現標志著“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的形成,這與精神病學的特殊性質密切相關。
19世紀中期,精神病學專業作為醫學分支的地位得以確立。然而從誕生之日起,“精神病學一直在兩種有關精神疾病的見解之間做著痛苦的抉擇。一種見解強調神經科學,對大腦化學、大腦解剖和藥物治療感興趣,在大腦皮質的生物學中發現精神性痛苦的根源。另一種見解強調患者生活的心理社會方面,將他們的癥狀歸因于人們可能不完全適應的社會問題或往昔個人的壓力。神經科學的見解通常被稱為‘生物精神病學’;社會—壓力見解具有疾病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重大優點。……這些觀點自身實際上截然對立,因為兩者不能同時為真。……這樣一來,最重要的是在任何給定的時間里哪種見解在精神病學里占上風”[2]。
(二)阿道夫·梅耶(Adolf·Meyer)(2)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1866—1950,有譯為麥爾、邁爾、邁耶)原籍為瑞士,畢業于瑞士蘇黎世醫科大學,后分赴英、法、德、比等國繼續學習。1894年梅耶轉赴美國,先在芝加哥市開業,1897年到馬薩諸塞省伍斯特精神病院(Worcester State Hospital)任醫務主任,1904年被聘為紐約市布落明德(Bloomingdale)精神病醫院院長,不久被任命為康奈爾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教授。1908年,梅耶又被聘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科教授,并擔任亨利·菲利浦精神病診所首任主任,一直工作到1941年退休。1913年,他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理想的精神保健門診的設想,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美國盛行起來的社區精神衛生工作就是以此為藍圖的。1928年,邁耶當選美國精神病協會主席,他的學生中有三人后來擔任美國精神病協會主席。 提出“心理生物學”理論
“生理—心理—社會”模式的思想雛形最早是在精神病學領域興起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梅耶。[3]梅耶是公認的20世紀上半葉美國最杰出、最有影響力的精神病學家,特別是在他被任命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第一位精神病學教授之后,他的思想在美國一直占據著精神病學的主導地位。[5]
梅耶早期曾研究神經學,他進行了大量尸檢,試圖將大腦損傷與精神病診斷聯系起來。然而,他很快意識到醫院病人癥狀記錄的混亂使所有這些努力毫無意義,這使他對研究活體病人的精神疾病的臨床過程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他決定訓練醫院工作人員進行系統的病史記錄,雇用速記員在檢查病人時做筆記,強調全面記錄患者的心理、生理和發展歷史的各個方面的必要性,這些后來成為“梅耶精神病學”的重要特征[5]。對于精神疾病的起源,梅耶持不可知論。20世紀初,梅耶開始發展他的“心理生物學”,實際上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提法。面對一系列疾病令人困惑的復雜性,這些疾病的病因和治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猜測和即興發揮的問題,梅耶的心理生物學概念提供了一個彈性的總體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可以容納一系列假設和干預措施。
梅耶學說的兩大觀點對“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有直接的影響:一是綜合說。即一個人的身體包含消化系統、呼吸系統、血液循環系統、泌尿生殖系統、內分泌系統、皮膚系統、骨骼系統和神經系統等各種系統,這些系統都各有其功能和特性,但是在一個完整的人身上,這些系統往往不按照生理學上的規律進行工作,而是互相作用和影響,從而呈現出不同的病狀。如果只重視生理學,而不重視心理生物學的研究,是不能了解其意義功能(meaning function)的。二是獨特性。即由于人們各自有特性,各自成為一個“個體”(unit,entity),在類似的情況下,人們產生的反應也往往不同。研究人們的行為時,必須從每個人的實際情況出發,廣泛收集材料,尊重所有事實,經過仔細分析,才能做出決定。在梅耶看來,在收集資料方面,除了病人的生理、心理資料之外,還必須同時收集個人歷史方面的材料。有關這方面的材料,有的是屬于家屬和親屬的,有的是屬于自己的。屬于家屬的材料,通常包括父母、兄弟、姊妹、妻兒、子女的年齡、健康、職業、嗜好、個性、信仰、對自己的影響和家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屬于自己方面的,從出生的時候起,包括個人的發育、生長、健康、學習、工作、婚姻、信仰、嗜好、愛好、個性等。同時,因為個人行為發生的原因、機制以及發生后所包含的意義,又會隨著所處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因此要重視收集不同時期的具體材料。[6]梅耶主張,欲解釋患者的病癥,必先理解其生活史,并發展出了一套基于常識的精神病學研究方法,也因此被精神病學專業長久銘記。[7]
梅耶的精神健康概念是整體式的,包括心、身和環境。人們贊譽梅耶的研究方法整合了從社會科學到神經病學等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8]相應地,梅耶要求醫生收集患者的生活史、家庭、經濟狀況和鄰居等數據——這個過程需要探訪患者的家庭、工作和社區。毋庸置疑,他的觀點吸引了最初的精神健康社會工作者。實際上,阿道夫·梅耶的妻子瑪麗·波特·梅耶就是首位從事精神病社會工作的人。作為丈夫的助手和志愿者,她探訪住在曼哈頓州立醫院宿舍和住在家里的精神病患者,并向梅耶匯報了患者和家庭的情況,直到1904年。[9]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精神病學始于1908年聘請阿道夫·梅耶為第一任主任時,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幾乎是同時開始的。1913年亨利·菲普斯精神病診所創立,梅耶任主任,霍普金斯醫院社會服務部分配了三名社會工作者到該診所工作,使病人的護理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這些早期的社會工作者得到了梅耶的大力支持,因為他認為社會因素可能在精神問題的產生中起著重要作用,社會力量可以被用來提高病人康復和保持健康的機會。[10]
(三)理查德·雷曼(R.S.Lyman)將梅耶的理論帶到中國
中國早期的精神病學主要受到阿道夫·梅耶的“心理生物學”(Psychobiology)理論影響,不僅因為其弟子理查德·雷曼擔任北平協和醫院神經精神科主任,還因為我國第一代精神病醫生大多與梅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系。
理查德·雷曼(Richard S. Lyman)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和梅耶的關系延續多年。1915年雷曼耶魯大學畢業后,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學習,1921年又到亨利·菲普斯精神病診所實習,一直師從心理生物學說的創立者梅耶。雷曼曾被任命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講師,與老師梅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但考慮到自己過于個人主義,他不希望接替梅耶成為亨利·菲普斯的精神病學教授”[11],而是接受了杜克大學醫學院的職位。
雷曼于1931年來到中國,先是在上海醫學院授課,一年后轉到北平協和醫學院神經精神科接替主任職位。雷曼的目標不限于神經精神科的建設,而在推動中國精神病學的建設,除了人才訓練還應“為當地提供富有價值的精神病學工作的示范”[12]。在接下來的五年里,他推動北平協和醫院與北平瘋人院的合作建立起現代精神病醫院。在治療中,雷曼和他的團隊實踐了梅耶所倡導的“生理—心理—社會”精神醫學模式。[13]不過,“雷曼與其說是理論的建設者,不如說是組織者”。雷曼曾向他的導師梅耶解釋說,梅耶的心理生物學思想體系與他自己的經驗非常和諧,以至于他沒有設計出自己的“哲學”。[14]如果說缺乏獨創性,雷曼則擁有活力和熱情。雷曼作為一個優秀的組織者,旨在“組建一支團隊”,實現“神經病學、精神病學和社會服務的統一,與生理學和心理學緊密聯系”。雷曼在寫信招募精神分析師戴秉衡時說,他有一個計劃“發展醫學、精神分析學和社會學相結合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社區的[精神疾病]問題”[15]。
雷曼對梅耶非常忠誠,曾向其索要霍普金斯醫院亨利·菲利普精神病診所的藍圖以指導在北平的建設。梅耶則對雷曼在中國的做法表示贊賞。1937年,雷曼向梅耶解釋說:“我在這方面的未完成的興趣,包括心臟電流和電解質對心室功能的影響、心理測量技術在各種臨床問題上的應用、試圖從人格的社會—心理—生理綜合調查中找出主要因素的方法,以及進一步研究roetgen[sic](注:原文如此)對神經組織的影響、影響行為的種族差異,特別是漢語失語癥等。”[16]由此可知,雷曼非常理性地遵循了梅耶對病人采取的整體研究方法,從各個角度對人的精神癥狀進行分析。1939年,雷曼組織編纂了由北平協和醫院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根據臨床研究數據所著的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論文集[16],可以說是這一思想的成果體現。
二、“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的擴展
我國著名精神病專家粟宗華認為,雷曼“所培養的人員分布全國各地,這是麥爾(即梅耶)的學說之所以在我國精神病學的領域里產生較大影響的一個主要原因”[6]234。雷曼在北平協和醫院神經精神科擔任主任期間,培養了許英魁(北京)、程玉麐(成都、南京)、粟宗華(上海)、凌敏猷(湖南)、張沅昌(上海)、黃友岐(湖南)等醫生,還將他們推薦到美、英、德等國深造。這些人回國后均成為知名的神經精神科專家,分別在所在地創建并發展了神經精神專業,取得了顯著成績。[17]正是由于梅耶學說的影響,我國各地精神病院才紛紛建立了“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
1939年許英魁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林學院回到北京協和醫院任副教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協和醫學院停辦,1942年許英魁應聘到北京大學醫學院創建神經精神科,并擔任主任、教授。他從北平協和醫院帶來了1位護士長、4位護士、1位病理技術員和1位社會工作者。許英魁在課堂上教授學生要“全面關心病人,不僅注意軀體癥狀和體征,還要注意心理狀態。……對精神病人更要尊重。要絕對為病人保密,不要辜負病人的信任。”[18]9、111951年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病院成立,除了采用胰島素休克治療和電休克治療外,還開展了心理治療和工娛治療,“彼此互相學習,受益匪淺”[18]14。
1934年程玉麐由德、美留學后返回北平協和醫院任神經精神科副教授,并時常幫助魏毓麟院長協助指導北平市精神病院的醫療、教學等業務工作。1936年程玉麐應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邀請擔任神經精神科教授及主任,抗戰爆發后隨中央大學西遷到成都。他看到很多精神病人流落街頭,便向成都市政府衛生處要求建立一所精神病院,并推薦他的學生劉昌永擔任院長。1943年底成都市立精神病療養院建成,不僅是華西協和大學醫學學生的實習基地,也是成都各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的實習場所。如華西協和大學“社會系學生林儀初,以她所學的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知識和精神科劉昌永醫師合作,對于治療精神病人起了良好作用”[19]。燕京大學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社會系學生也在該院作個案工作實習,有新病人入院即由實習學生負責與其家屬談話,調查病人的社會生活史。病人痊愈而需要隨訪者,也由學生到病人家庭中拜訪。[20]17醫院每個星期三由程玉麐領導病人討論會,精神病醫生、華西大學醫學院實習醫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師生分別提供材料意見,共同“診治被討論者之病癥”[20]15-16。
1948年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建成,程玉麐任院長。醫院的社會工作同時展開,設有社會服務部,主任由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社會學系湯銘新教授擔任,成員有助教林志玉、鄭詠梅等,均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社會學系畢業生。[21]醫院對臨床心理學也很重視,設有心理工作室,主任為心理學界著名的丁瓚教授。總之,南京精神病院的醫療工作最突出的特點即實行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醫院每周舉行病人個案討論會,“由醫師護士,社會服務員,及心理衛生員等分別報告,分析討論,確定病原,以資治療。[22]”召開病例討論會時,先由社會工作員報告患者的社會史,包括家族史、個人史、現病史,十分詳盡。接著由心理學專家報告心理測查所見,醫生報告病史,然后大家展開討論,分析病案,確定診斷,作出治療計劃,由各有關部門協同配合治療。社會工作者除了負責病人個案史搜集和家庭訪問,參加病案討論,并為出院病人聯系恢復工作及爭取社會福利支持等。[23]此外,醫院同仁還捐助基金,設病人福利基金委員會,為病人購置娛樂用具、雜志書報等。醫院每周四開病人娛樂會一次,每月開擴大娛樂會一次,還邀請已痊愈出院的患者返院參加。
三、“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的延續
南京精神病院成立初期,除了程玉麐和他的弟子陳學詩、陶國泰外,一起工作的精神病專家還有伍正誼、王慰曾等,這些人也在程玉麐的協助下陸續赴美留學。[24]新中國成立后,程玉麐赴臺,這些弟子和同事留在大陸,使精神健康領域的“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得以延續。
王慰曾于1949年被委任為南京神經精神病院院長。在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上,王慰曾主張把精神治療與藥物治療緊密結合,人道主義地對待患者。[25]他帶領全院職工種樹、種花、鋪草,醫院逐漸成為聞名的園林式醫院。王慰曾倡導“解除對精神病人的約束”,廢除約束衣,實行開放病房、工療和娛療,讓病人閱讀書報、打撲克、下棋、做手工勞動甚至看電影和郊游,大大促進了病人的康復。[26]當時醫院負責工療的工作人員,是民國時期該院社會服務部招募的社工陶玲,1947年畢業于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社會學系。1955年,陶玲還根據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工娛療法的實際經驗編寫了一本《精神病的工作和娛樂療法》的小冊子,供國內其他精神病院參考[27]。
陳學詩1942年于國立貴陽醫學院畢業后赴成都華西聯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師從程玉麐教授并任助理住院醫師。1981年,陳學詩始任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組建了集醫生、護士、工娛治療員、心理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為一體的攻關隊伍,在北京安定醫院建立了全國首家心身疾病門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28]他主持研究的“老年抑郁障礙的主動音樂治療”以全新的治療模式改變了原來單一藥物治療的純生物醫學模式,為國內首創。他提出組建的集醫生、護士、工娛治療員、心理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為一體的五支隊伍,徹底改變了精神病院單純的生物醫學管理模式。[29]
1985年伍正誼出任汕頭大學醫學院院長,在醫學院精神病院的建設和管理制度上,實現了他多年的設想。他的學術思想的中心就是精神病人不僅是生物的人,也是社會的人,更是生物性和社會性密切融合的人,他們不僅有生理需求,而且有感知、思維、情感等心理需求,還需要得到人們的愛、需要享受到人生的樂趣,他們有工作的權利、勞動的權利。精神衛生工作要尊重病人的人權,幫助他們的精神(心理)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康復,還要使他們回歸家庭、社會,享受人生的權利。他親自主持于1988年建成的汕頭大學精神衛生中心,一改以往精神病院給人“陰冷、恐怖”的感覺,為精神病人提供了一個優美、舒適、理想的治療、康復和生活娛樂場所。他設計的病房是四合院結構,要求工作人員待病人如家人,上班不穿白大衣,與病人一起進餐,以減少與病人之間的隔閡。伍正誼認為病人在任何時期都不能缺乏心理治療,還必須進行工療和娛療。他主張運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進行心理學、精神病學和生理衛生教育和康復工作。[30]伍正誼提出的“建筑園林化、生活家庭化、管理開放化、治療綜合化”這一新型精神病院辦院模式,主張實施以心理治療為主導,藥物治療為基礎,結合工作治療、行為治療、娛樂治療、體育治療、家庭治療等全方位治療原則,把醫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知識結合起來運用到本學科中,被國內外專家譽為21世紀中國精神衛生新模式的雛形。[31]
還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著名精神病專家粟宗華教授。粟宗華于1932—1935年在北平協和醫院進修神經精神病學,后受到雷曼的推薦于1935—1937年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進修,師從梅耶。作為梅耶的“嫡傳弟子”,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雙百方針”的提出(3)20世紀50年代初,梅耶受到批判,粟宗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發表了認錯反思的文章。參見金德初:對1950年代我國關于麥爾學說討論的回顧——評紀明等《論麥爾精神病學的反科學性和反動性》及粟宗華《我對麥爾的“心理生物學”的再認識》載于《上海精神醫學》2001年第1期。,粟宗華在專題演講中公開宣稱自己是梅耶在中國的代表人,并對梅耶做了比較客觀的正面評價。[6]238-243粟宗華還身體力行傳播梅耶的精神,在1956—1970年擔任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院長期間,“為了詳細了解病人的生活史,建立了社會工作室,由社會工作員至院外調查病史;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有些病人就像司法鑒定對象那樣,從各方面詳細搜查資料;為了了解其人格發展及社會心理因素影響,要病人寫自我分析。……使下面醫生直接悟及麥爾[梅耶]學說的一些真諦,理解到精神病的治療應該包括藥物治療、心理治療、職業訓練、社區防治等環節,從而達到個性、心理、職業、社交的全面康復”[32]。當時的社會服務工作不僅對精神病人進行家庭訪問,并且還與病人的工作單位直接聯系,以便更好地關心和安排病人的工作。對那些慢性病人或者處于康復的精神病人,工作人員在街道里將他們組織起來,做些力所能及的勞動,也可以隨時觀察他們的表現、了解他們的用藥情況,為減少復發提供較為切合實際的措施。[33]
四、結語
正如最早的醫院社會工作是由內科醫生發起一樣(4)目前公認的是,醫院社會工作的創立者是美國麻省總院的內科醫生卡伯特(Richard C. Cabot)教授。,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的起源也離不開精神科醫生的提倡。20世紀上半葉美國著名精神病學家阿道夫·梅耶的“心理生物學”理論,從精神疾病的病因出發,綜合吸收各流派的學說,將個人看作一個心與身的統一體,提出要兼顧先天遺傳和后天環境化育兩大因素,這就為“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開辟了道路。社會工作因此進入精神健康領域,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從此誕生了。
理查德·雷曼是梅耶的得意弟子,在任北平協和醫學院神經精神科主任期間將“心理生物學”理論帶到中國,并在北平精神病院實踐“生物—心理—社會”的治療模式,從而使中國誕生了第一家精神健康社會工作部門。此外,雷曼還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精神病專家,這些專家后來分布到中國各地,也將“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推行到了各地的精神病院。新中國成立后,這些精神病專家和他們的學生們仍然努力實踐著“生物—心理—社會”治療模式,盡可能地保留了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服務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