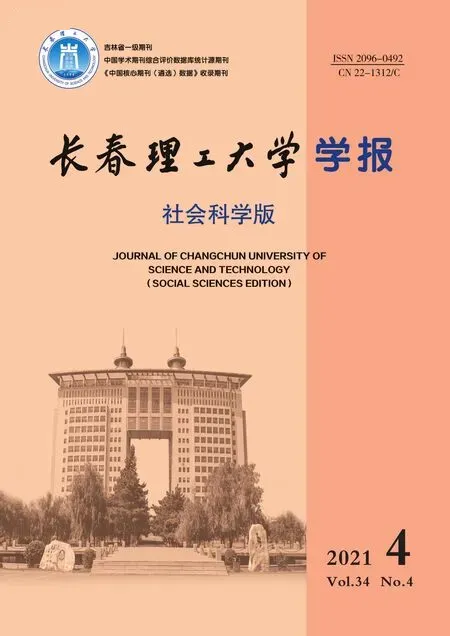茅盾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與傳播(1921—1925)
陳思研,尹曉琳
(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20世紀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是個動態的過程。1906年,魯迅和周作人負笈日本,開始翻譯匈牙利等“弱小民族”文學,對當時的文學、創作和匈牙利文學的“跨語際”翻譯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茅盾承載了這種譯介傳統,1921年,他對《小說月報》進行全面的革新,借助《小說月報》的新平臺,結合自身的翻譯理念成為“弱國文學”翻譯模式的中堅力量。宋炳輝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初步的考證和研究,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除魯迅、周作人之外,對東歐文學譯介最用力、影響最大的當屬著名作家、批評家和編輯家茅盾了”[2]208。從1921—1925年間,茅盾譯介了多種匈牙利文學,既包括文學作品,又包括文學批評。他自己曾言,“自從前世紀以來,匈牙利無日不在強民族的壓制底下,直到此次歐戰終止,德、奧霸力失墜,方才有點挺立的希望。因為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所以匈牙利的文學自然而然的有一種異樣的色彩,和別國文學不同”[3]327。正是匈牙利和匈牙利文學的特殊性,使得茅盾對匈牙利文學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并發現了匈牙利文學具有的異質性。這種“異樣的色彩”體現在哪里?茅盾為什么選擇了匈牙利文學又對匈牙利文學進行了怎樣的譯介和評價?他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活動對后世的影響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茅盾譯介匈牙利文學的邏輯起點與社會環境
五四時期,隨著中國革命語境的變化和民族思潮的興起,許多文學家的文學觀念發生了變化。結合中國內憂外患的現實境遇,很多文人與“弱小民族”產生了共情,開始著眼于中國新文學與“弱小民族”文學的關系問題。反映到翻譯活動中,大規模地譯介“弱小民族”文學成為啟蒙和改造國民性的重要途經,翻譯文學也成為建設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為基礎,許多翻譯家將關注點放在以中東歐為代表的“弱勢民族”文學上,如大量譯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等國的文學作品。因此,只有將翻譯“弱勢民族”文學放在新文學的文化語境中來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茅盾如此系統地譯介“弱國文學”的原因。
在這種社會思潮和文學背景下,茅盾將著眼點放在“弱小民族”文學上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首先,茅盾譯介著眼點繼承了自晚清到五四以來我國譯介外國文學的傳統。正如有學者指出,“清末民初,我國的文學翻譯活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五四以后”[4]。周氏兄弟最早關注到了被遮蔽的“弱小民族”文學,并于1909年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主要是介紹俄國、北歐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及至五四前后,茅盾作為新文學的建設者,接續起晚清以來譯介域外文學的傳統,譯介域外文學和文藝思潮成為建設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匈牙利文學成為茅盾譯介的重要對象,他在談到匈牙利文學時認為,匈牙利“因為是被侮辱的民族,所以他的文學里所表現的民族思想也只不過是要求自由……并不是專想壓伏他民族的民族主義:這要求‘一個公道’的呼吁,也是匈牙利文學的一個特點了”[3]328。可見,茅盾之所以重視匈牙利文學作品的翻譯,關注匈牙利民族的命運,正是基于當時匈牙利“被侮辱”的民族特點。
其次,茅盾譯介匈牙利文學也與他素來所秉持“為人生”的觀念息息相關。他曾明確指出,“我們仍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仍是想不頗不偏的普通的介紹西洋文學”[5]。“我覺得翻譯家若果深惡自身所居社會的腐敗,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國文學作品來抗議,來刺激將死的人心,也是極應該而有益的事。”[6]282以此為支點,茅盾做了很多涉及匈牙利文學翻譯的工作。一方面,在“為人生”文學觀念的燭照下,茅盾更為關心匈牙利文學中關于“人生”的“問題文學”。他所譯介的絕大多數作品均是關注現實社會、指導人生的文學,這些譯作離不開茅盾“為人生”的寫實主義文學觀念。另一方面茅盾對幾位重要小說家、文學家的介紹與評論也是在“為人生”觀念指導下完成的。如愛國詩人裴多菲、浪漫主義小說家約卡伊·莫爾、帶有詼諧諷刺風格的米克沙特等。有學者指出,“在他1920—1923年撰寫的不少譯論和介紹外國文學的大量文字里,為人生,為現實的人生,為未來的人生,一直是他反復彈撥的主調”[7]。可見,茅盾對于翻譯作品的選擇是受“為人生”的文學觀念的指導,“為人生”與匈牙利文學翻譯在某種意義上互為表里。
二、茅盾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歷程
茅盾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茅盾譯介匈牙利文學時將文學翻譯與文學批評相結合,全方位地介紹匈牙利文學,包括作家及作品。同時茅盾對于匈牙利文學的翻譯不是系統地譯介某一個作家的作品,而是采取廣泛選擇的立場,這種翻譯理念不但促進了兩國思想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而且也反映了茅盾整體的文學意識,為中國讀者拓寬了了解匈牙利文學的途徑。茅盾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活動大致分為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茅盾的匈牙利文學譯介涉及小說、戲劇和詩歌等。其中包括六篇匈牙利短篇小說。這六篇小說分別是:安德烈亞什·拉茲古(Andreas Latzko)的《一個英雄的死》(發表于《小說月報》第12卷第3號,1921年3月10日)和《復歸故鄉》(發表于《文學周報》第141-153期,連載,1924年9月),前者控訴戰爭,后者呼吁革命;米克沙特·卡爾曼(Mikszáth Kálmán,1847—1910)的《旅行到別一世界》(發表于《小說月報》第12卷第9號,1921年9月10日);之后又在《小說世界》先后發表了裴多菲·山多爾(Pet?fi Sándor,1823—1849)的小說《私奔》(刊載于1923年1月10日第1卷第1期)和米克沙特的小說《皇帝的衣服》(刊載于1923年1月19日第1卷第3期,而后在1934年《譯文》1卷1期再版,1934年9月16日);約卡伊·莫爾(Jókai Móri,1825—1904)的《跳舞會》(刊載于《文學》第4卷第1號,1935年1月1號),署名芬君。茅盾選擇這幾篇匈牙利短篇小說翻譯是有其“客觀動機”的,即“主觀的愛好心而外,再加上一個‘足救時弊’的觀念”[6]281,反映現實生活的、富于抗爭精神的、戰爭小說等作品是茅盾譯介匈牙利小說主題的首選。
除了小說之外,茅盾還翻譯了匈牙利的詩歌和戲劇。詩歌翻譯包括《匈牙利國歌》和《英雄包爾》。《匈牙利國歌》最早刊載于《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10月10日出版),其作者是匈牙利偉大的愛國詩人裴多菲,被稱為“匈牙利政治復活時代蘇生精神的記錄者,并且做了那精神的指導者”[8]。這首詩的主旨在于反抗專制統治、呼吁民族獨立自由。《英雄包爾》最早刊于《小說月報》13卷5號(1922年5月10日),原作者阿蘭尼·雅諾什(Arany János,1817—1882)是匈牙利詩人,命運與裴多菲一樣波折,詩歌抒發了英雄包爾遠離他的愛人去參加戰爭,最終釀成了愛情悲劇。兩首詩基調高昂,體現了兩位愛國主義詩人的熱情。戲劇翻譯包括莫爾納的兩部戲劇。其一是《盛筵》,最早載于《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1922年7月10日),譯者署名冬芬。其二是《馬額的羽飾》,譯文原刊《小說月報》第16卷第6號(1925年6月10日),署沈雁冰譯。后收在1935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桃園》里,刻畫了天真幼稚的孩童形象。
第二,茅盾在主持《小說月報》期間,除了匈牙利文學的翻譯,還撰寫了對匈牙利文學與文學史的評論文章。包括獨立編寫了關于匈牙利文學(家)的三篇評論文章。其一,《新青年》登載過茅盾編寫的《十九世紀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學》,連載于1921年6月,第9卷2、3號。文章從匈牙利文學發展的三個時期(啟明期、隆盛期和極盛期)尋究19世紀的匈牙利文學發展軌跡,重點介紹了詩人裴多菲、亞拉奈和小說家育珂。其二,茅盾編寫了長篇評論《歐戰給與匈牙利文學的影響》。這篇文章重點介紹了幾位偉大的民族詩人:孚洛司瑪蒂、裴多菲和亞拉奈,進而闡述了歐洲大戰對匈牙利文學的影響。其三,茅盾還編寫了《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菲》,最初發表于1923年1月10日《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署名沈雁冰。后收入1929年9月世界書局出版的《六個歐洲文學家》一書中。文章介紹了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生平經歷和創作特色,重點介紹了其戰斗和反抗壓迫的民族精神。此外,茅盾翻譯了《匈牙利文學史略》,刊載于1924年4月28日《文學旬刊》第119期。文章從匈牙利語的起源講起,著重介紹了匈牙利在中世紀盛行的宗教文學,并繼續挖掘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特點,最后闡述宗教改革對于文學的影響。
茅盾對匈牙利文學的介紹及評論還包括在1921—1923年間發表的206則“海外文壇消息”等信息傳遞式的文章。這些消息對世界文壇現狀和文學家近況進行同步追蹤報道,使國內讀者始終保持與世界文學的聯系。其中茅盾對于匈牙利文學的介紹有三則,分別是:1921年9月,《海外文壇消息:(九十五)匈牙利戲曲家莫奈爾的新作》,刊于《小說月報》第12卷第9號;1921年11月,《海外文壇消息:(一○○)略志匈牙利戲曲家莫爾納的生平及其著作》,發表于《小說月報》第12卷第11號;1924年8月,《海外文壇消息:(二○五)匈牙利小說》在《小說月報》第15卷第6號發表。可見,茅盾不僅譯介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而且專注于譯文的評論和介紹,有論者言,“茅盾自己也從這瑣屑的工作中獲益,他的具有現代意味的專業化的批評也從這比較低層次的書評文訊中得到啟發,打下基礎。事實上在這些零篇碎章的寫作過程中,茅盾東張西望,無形中拓展了批評視野,并逐漸形成他后來那種大處著眼,注重引導,講求功利的批評習慣”[9]。從茅盾開始文學活動到此后的幾十年間,茅盾一直專注且認真地對待文學批評活動,推動了現代文學中的批評方法的建設,這些都得益于早年為建設新文學所做出的譯介外國文學的努力。
三、茅盾所譯匈牙利作家的擇取標準
如前所述,茅盾在1921—1925年間對匈牙利文學家裴多菲、莫爾納、拉茲古、米克沙特等人進行了系統的譯介。那么,茅盾為什么選擇這幾位文學家及其作品進行譯介呢?或者說,茅盾選擇上述作家進行譯介的擇取標準是什么呢?對此問題,茅盾自己曾言,“我們譯西洋文學作品最先應問這作品內的思想是否于我們現在有影響,其次乃問此人是否世界的作家”[10]。可見茅盾也正是注意到了上述文學作品的思想性以及他們在匈牙利文學史上的地位,才將其納入到自己的翻譯視野中。一方面,從作品的文學性來看,茅盾始終抓住批判現實主義這一特征;另一方面,茅盾除了推崇匈牙利文學思想層面的精神性外,對其藝術性也很重視。厘清這兩個方面,就能夠理解為什么茅盾在諸多匈牙利作家內單單選擇這些人進行譯介。理順對茅盾所譯匈牙利作家的擇取標準,也有助于進一步理解茅盾選擇譯介對象的原因。
裴多菲是匈牙利19世紀首屈一指的革命家詩人,在匈牙利文學史上地位頗高。他的詩歌基調昂揚,飽含愛國熱情,具有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這一主題與中國五四時期的新文學有共通之處。茅盾大致從兩方面來介紹裴多菲的詩歌。一是肯定了裴多菲的文學史意義。“他是匈牙利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他的詩歌是他的人格的自然的表現……裴多菲的詩是青年的詩。凡讀了裴多菲的詩,無有不激發起青年的精神的。”[11]619裴多菲在創作中“直訴情緒不加選擇的”,即使在詩中描寫自然時,也是“有情感有精神的自然”[11]619。裴多菲的作品多是充滿叛逆精神的,有鼓舞青年的作用,茅盾對《匈牙利國歌》的譯介就是在此視域下展開的。二是茅盾更關心的是裴多菲世界觀中的平民主義信念。“人類是繼續地在發展的。偉大的人物與理想有最大的影響在民族教育上。但是這教育是一切人的公共工作,各人必須盡他一部分的力。”[11]623茅盾也認為建設新文學應該“使文學成為社會化,掃除貴族文學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學的精神”[12]。可見,正是裴多菲的愛國熱情和平民主義思想成為了茅盾選擇譯介他的標準。
拉茲古是一個反抗戰爭,呼吁革命的文學家。茅盾翻譯的第一篇匈牙利文學作品是拉茲古的《一個英雄的死》,這部小說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反思文學。隨后譯介的《復歸故鄉》通過主人公約翰·蒲丹的慘死,揭露了窮人在戰爭中所遭受的巨大不幸,控訴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罪惡。這兩部小說貫注的精神是反抗與革命,揭示了戰爭下人類的精神狀態和生存困境,體現了對人道主義的呼吁。茅盾在《一個英雄的死》的譯文之后的附記也說明翻譯這部作品是希望人們更加關注戰爭文學,通過翻譯這兩篇戰爭文學來控訴、反思戰爭的不義性。“凡諸長篇短著,中國都不曾譯過,實在覺得有些寂寞,我所以譯了這一篇。”[11]279茅盾早期對“一戰”中產生的戰爭文學加以關注,在《一個英雄的死》譯后注中首次提到戰爭文學,“這一次大戰后所產生的有價值的——也許是永久價值——戰爭小說……都是寫在戰場上的人的痛苦”[11]279。隨后1924年在《小說月報》還特別設立了戰爭文學專號,可見茅盾對戰爭文學的關注,他之所以選擇拉茲古進行譯介,也基于作家本身對戰爭的呈現及其態度。
相比之下,米克沙特和莫爾納詼諧諷刺的寫作風格也深深吸引著茅盾,他結合兩人的文學作品,探究匈牙利文學的審美價值。據載,米克沙特的小說“從情節的安排直到人物形象的創造,顯示出幽默的詼諧的特點。他善于從民間文學中得到借鑒,作品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12]。《皇帝的衣服》正是這種批判現實主義的詼諧諷刺小說。茅盾對米克沙特藝術傾向的評價大致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引用李特爾所著的《匈牙利文學史》,對米克沙特作出評價,“彌克柴斯的檢查力極強,即使在生活之最簡易的境地里,他也找出了引人注意的和詩意的所在,從這檢查力,他的詼諧就得了深沉與有趣”[11]392。同時,茅盾在《皇帝的衣服》譯后記中認為,“米克沙特是約卡伊以后的第一人。他的作品,以尖刻峭拔勝。他是匈牙利第一個詼諧家和諷刺家”[11]624。二是茅盾借鑒了恩特烏德的言論,認為米克沙特刻畫人物的豐富性,涵蓋匈牙利社會的各個階層。文本主題多樣,有“隱譏暗諷”式的,也有敘述田園生活的平淡質樸。可以說,米克沙特的諷刺小說風格和筆下人物的豐富性影響了茅盾對他的譯介態度,并對其作品進行譯介。
茅盾譯介的兩部匈牙利戲劇均出自莫爾納。有學者指出,“莫爾納是匈牙利20世紀上半葉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劇作家和小說家……他在中國最早的譯介者就是沈雁冰”[13]。之所以選擇莫爾納的戲劇進行翻譯,一方面是莫爾納作品的結構“是屬于所謂‘剪嵌的細工’一派。他的句法極簡單,章法極瑣碎,然而極美麗,極刺人。這一種的結構法,德國的近代派曾經試過,可是沒有什么成功。莫爾納算是最大的成功者”[14]378。莫爾納的戲劇描寫的逼真、夸張手法的運用、對主人公性格的諷刺性刻畫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茅盾小說的藝術手法。同時,莫爾納作品中的創作特色是“詼諧帶著樸茂的東方氣……”[14]378,之所以其作品中帶有“東方氣”,是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讀到許多與中國社會相同的普遍人性和與中國現實相似的敘事情節。如在戲劇《盛筵》中,莫爾納用夸張的手法將現實生活中人們諂媚的嘴臉呈現出來,諷刺了人際交往中的虛偽、丑陋。另一方面,茅盾始終堅持的是“現實主義”兒童文學,“在他看來,兒童文學作品應該以清醒的目光直面人生”[15]。《馬額的羽飾》生動地刻畫了兩個孩童內心的童稚美好,純真的思想和富于想象力的心理活動使得孩童的世界充滿了溫情。無論是手法還是內容,都成為茅盾關注并譯介莫爾納的側重點,這也可以看做是茅盾選擇譯介莫爾納的標準。
基于此,可以看到茅盾所譯匈牙利作家的擇取標準大致有二。一是思想上秉持著弱勢民族傳統意義上愛國主義和反對戰爭的作家往往成為茅盾譯介的首先,這與匈牙利文學及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思潮相關,也和茅盾的思想息息相關。二是形式上具有藝術獨特性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家會受到茅盾的關注,他的譯介擇取標準是藝術上的新手法或獨特性。也正因如此,前述匈牙利作家才會進入到茅盾的譯介視野。
四、茅盾譯介匈牙利文學的影響與意義
1921年,茅盾臨危受命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一改鴛鴦蝴蝶派的游戲消遣的文學態度,以“為人生”的創作和翻譯理念開始了全面的革新。在翻譯文學層面,《小說月報》改革后最大的特色是對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文學的重視以及對中東歐等被壓迫民族文學的大量譯介,并推出“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俄國文學專號、戰爭文學專號、海外文壇消息、文學評論等欄目,以報刊為載體開辟了翻譯文學的新路徑。《小說月報》的成功改革,標志著翻譯弱國文學重要陣地的崛起,對當時的匈牙利文學譯介產生了深遠影響。
茅盾譯介匈牙利文學的影響之一是,通過《小說月報》為文學新人積極提供作品發表的園地與平臺,并系統地譯介匈牙利文學。據初步統計,1921—1931年《小說月報》發表東歐文學的譯文多達115篇,是當時譯介東歐文學最多的期刊,其中譯介的匈牙利文學共有15篇。[2]220除茅盾的譯作外,沈澤民在其上發表的譯文有莫爾納的小說《雪人》和《偷煤賊》、裴多菲的詩歌《唯一的念頭》等。此外,還包括胡愈之翻譯的小說《郵局長的信》、胡天月的《棄婦》等重要的匈牙利文學作品。且茅盾的“為人生”的翻譯理念直接影響到一些作家的譯作選擇——即關注和譯介匈牙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問題文學”。茅盾作為《小說月報》的主編,發揮了比其他人更為重要的作用。此后,經茅盾改革形成的翻譯弱小民族文學的翻譯路徑被其后的主編鄭振鐸繼承了下來,鄭振鐸任主編時的《小說月報》,“對于向來的介紹近代的及弱小民族的文學的特色仍繼續的保存著”。鄭振鐸在“為人生”現實主義文學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文學的內涵,深化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茅盾譯介匈牙利文學的影響之二是,激勵了如沈澤民、胡愈之、巴金和胡天月等同時代的很多作家和翻譯家。沈澤民是在茅盾的帶領下開啟了翻譯事業,兩人曾合作翻譯外國科普小說《兩月中之建筑譚》,他譯介的“弱小民族文學”作品刊發在《小說月報》上的最多,有31篇,這可能與茅盾擔任主編有一定的關系。另外,胡愈之是茅盾在商務印書館的同事,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受茅盾影響,胡愈之翻譯“弱小民族”文學,尤其是匈牙利文學,并在1920年擔任《東方雜志》的主編后,以其為陣地,倡導弱國文學的譯介,胡愈之的這種譯介理念或與茅盾有直接聯系,或受茅盾的熏陶和影響。除此之外,文學家巴金也受過茅盾的影響。他在悼念茅盾時曾深情地回憶道,“我特別喜歡讀他翻譯和介紹的‘被壓迫民族’的短篇小說”[16],并自言十幾歲時就讀茅盾翻譯的文學作品,30年代喜歡讀他的評論文章。由此推斷,巴金從中受到了許多茅盾在翻譯實踐中的影響,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了大量的“弱小民族”文學,包括匈牙利文學在內的譯作。自《小說月報》革新以來,在茅盾的幫助和指導下,五四時期的很多文人都開始了翻譯“弱小民族”文學的實踐活動,其翻譯作品得以發表在《小說月報》都得益于茅盾的發掘。
綜上所述,茅盾對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茅盾延續了周氏兄弟的譯介傳統,并對之后的很多作家、翻譯家起到了很好的帶動作用。在主持《小說月報》期間,將其改造成嚴肅的文學刊物,為新文學提供了嶄新的發表園地。此外,茅盾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是建設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推進中國文學及文化的現代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譯介“弱小民族”文學也體現了茅盾在文學上秉持著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譯介思想,茅盾的這一“跨語際實踐”推動了中外文學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史,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