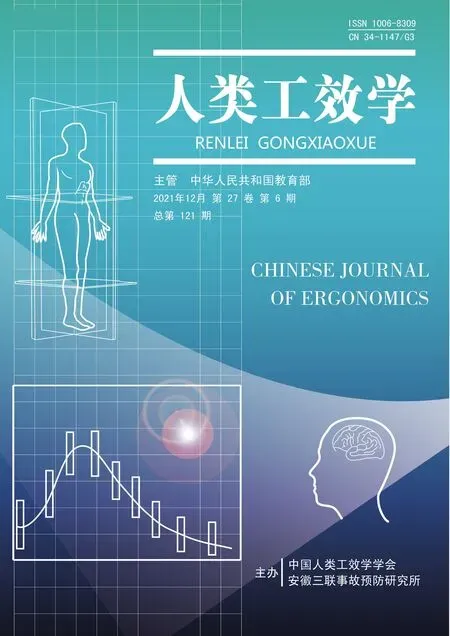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
——潛在剖面分析與社會網絡視角
翁杰,王曉婷
(浙江工業大學 管理學院,杭州 310023)
1 引言
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下屬的核能安全技術研究所90余名研究人員集體離職事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們中的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和事業編制,也從事著在外界看來是屬于待遇好、前景好的工作。該集體離職事件并非個例,隨著組織轉型升級與平臺化變革的推進,團隊組織的模式被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但與此同時以團隊為單位的集體離職事件也在越來越頻繁地上演。有趣的是,研究者們一方面指出,原子式、獨立的招聘錄用過程已轉向整體招聘,該舉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雇傭成本,發揮人員配置的優勢;但從被整體招聘的原企業角度考察,集體離職給企業造成的影響和損失也遠高于個體離職[1],不僅會引起組織專用性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大量流失,對企業生產率和績效也會造成一定負面影響[2]。顯然,對那些應用團隊管理的企業而言,關注團隊的穩定性、防范集體離職的發生已成為一門必修課,而對集體離職的成因和機制開展研究,將有助于企業開發和實施管理實踐以抑制集體離職的發生。
集體離職早期的研究往往將其視為個體離職的加總[3],但作為群體性的行為,多人同時或相繼離職的行為之間必然有內在的聯系,涉及共同的社會過程[4],因此其已遠非個體行為的簡單疊加。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屬于集體離職的一種類型,表示團隊主管離職并尋求下屬追隨而形成的團隊流動[5],由于該集體離職會帶來連帶效應與傳染效應[2],所以其也成為近年來研究與關注的焦點之一。
針對于集體離職的后果和危害需要建立其組織管理實踐的預防機制。在個體層面上,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個體離職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討論,結論也較統一。無論對組織還是對主管的情感承諾均可減少其“同時離開組織和團隊”的個體離職行為[6]。但對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則不然,組織與主管的情感承諾是嵌套關系,而集體離職又可以算作“留在團隊,離開組織”的個體離職,此時主管的情感承諾驅使員工跟隨團隊主管離職,但是組織情感承諾又會使其留職,情感承諾在集體離職情境中出現了目標沖突,且根據個體離職的相關研究無法直接做出解釋。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首先研究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復雜關系,并根據社會網絡的相關理論,考慮到團隊成員認知、態度和行為均會受到網絡結構的影響或被網絡整體規范所限制[7],因此本文在團隊層次引入團隊主管社會網絡,探究情感承諾目標沖突下團隊成員的集體離職傾向。本文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基于員工的異質性,采用以人為本的潛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多焦點情感承諾的分組情況;二是基于分類結果,探索其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關系;三是引入團隊主管社會網絡中心性和結構洞來解釋多焦點情感承諾目標沖突下,集體離職情境中成員的行為選擇。
2 理論與研究假設
2.1 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
根據社會交換理論,情感承諾越高,員工與目標對象的心理契約越高,情感依賴越強,同時也會與重要的組織結果相關聯[8]。而隨著情感承諾研究的深入,多焦點以及以人為本情感承諾分類的研究指出,員工對不同主體均可以做出一定的情感承諾,且對多焦點保持不同的認知、態度與行為,相互之間的社會交換關系也存在差異[9],由于組織和團隊主管存在嵌套關系,在單獨影響員工行為以外,也存在相互作用[10]。根據團隊成員集體離職中涉及到的“組織”和“團隊主管”兩個焦點,可區分的“高”與“低”兩種心態,可將嵌套的組織情感承諾與主管情感承諾分為“高-高型”、“低-低型”、“主管情感承諾主導型”以及“組織情感承諾主導型”四個剖面。
在以人為本的情感承諾分類中,“主管情感承諾主導型”與“組織情感承諾主導型”均存在某一焦點的情感承諾占據主導位置。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對特定焦點的高度承諾,也會導致針對該焦點的更高水平的回報行為[11]。團隊成員集體離職意味著員工通常同時面臨著離開組織還是團隊兩個選擇。結合目標相似框架理論,如果團隊成員對兩者的情感承諾差異不影響其集體離職選擇,目標一致的成員會通過將其態度和行為導向某一方來對感受到的社會交換做出反應[12],并決定是否跟隨主管離職,其中主管情感承諾使團隊成員傾向于跟隨主管,而組織情感承諾使團隊成員傾向于留在組織。
當目標沖突時,意味著團隊成員認為其無法以同時受益于兩個目標的方式做出選擇,但根據解釋水平理論與心理距離的相關研究,即使團隊成員對兩個焦點的情感承諾無顯著差異,仍然會傾向于把對團隊主管的承諾作為具體和接近的目標,導致成員的行為會偏向于主管而非組織[13]。此外,結合資源保存理論,情感承諾作為組織為其提供的有價值社會資源,當有很高的情感投入時,放棄的意愿也會降低[14]。因此,那些表現出低水平情感承諾的員工是無法預測的[15],相對于低-低型情感承諾的子群體,高-高型雖然沒有主導的情感承諾,但由于情感承諾水平較高,也會成為成員選擇時的參考依據。因此,結合以人為本的潛在剖面的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假設:
H1a:主管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為正相關;主管情感承諾主導型比其余三者表現出更高的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
H1b: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為負相關;組織情感承諾主導型比其余三者表現出更低的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
H1c:高-高型與低-低型情感承諾未表現出明顯的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
H1d:高-高情感承諾比低-低情感承諾表現出相對較高的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
2.2 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的調節效應
團隊成員集體離職的復雜性在于其涵蓋的人際互動,而社交網絡所強調的就是行動者之間的人際關系,社會網絡嵌入的關系模式或結構也會決定個體的行為[16]。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的過程放入團隊社會網絡中,可更具體地了解其影響機制。由于在知識經濟背景下,除正式的資源獲取渠道外,團隊成員獲取新知識也開始更多依賴于非正式的、開放的、網絡化的途徑[17],因此主管在非正式網絡中位置的重要性日漸凸顯。
其中,從團隊主管網絡中心性(LDC,Leader Degree Centrality)角度來看,其表示團隊主管的重要性、核心性程度[16]。中心性程度越高,更多的成員會與團隊主管接觸,以獲得與工作相關的建議和指導,主管也會獲得更多的機會并可能控制一些重要的資源,使其他成員對其產生更多依賴與情感承諾,從而可獲得非正式權力[18]。團隊主管相對普通員工,依托正式權力,更易在非正式社交網絡中占據結構上有利的位置,當然也會依靠非正式咨詢網絡中享有聲望而產生的尊重補充其正式權力[19]。因此,主管的網絡中心性也間接反映了其在團隊中的受認可與情感依賴程度,會影響成員行為的選擇。當多焦點的情感承諾出現目標沖突時,員工的行為決策就不會僅局限在情感角度。當團隊主管提出離職想法,并向成員“拋出橄欖枝”時,主管在團隊中的中心地位越高,成員會對主管產生較大的權力依賴,就會促進主管的情感承諾對其離職的影響;相對而言,組織是否值得作為情感投資的目標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20],從而也會減弱組織在員工心里的位置以及組織情感承諾對員工行為的影響。
除中心性所提到的情感與權力依賴外,主管對信息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團隊成員的行為選擇。從團隊社會網絡結構洞(LSH,LeaderStructureHoles)來看,若團隊主管將沒有任何聯系的兩個員工連接起來時,不僅可從兩者之間獲得非冗余信息,還能控制兩者之間的信息流或在其中“挑撥離間”[18]。根據弱連接理論與結構洞理論,在這種情況下,主管在不同團隊成員之間的非正式互動網絡中占據關鍵聯絡位置,會享有更多的結構自主性和不可替代性,亦能夠改變并影響網絡成員行為[19],同時可使團隊成員對其產生依賴,此時的“依賴”更多指信息和資源的獲取。由于情感承諾是識別、參與并實現價值與特定目標一致的過程[21],若主管在團隊中處于結構洞位置時,主管離職后,其掌握和控制的信息資源會損失,同時會在短時間造成信息與資源流動出現錯亂,減弱團隊整體的連通性。結合資源保存理論,團隊主管結構洞位置的重要性會使團隊成員為減少資源的損失,更多的考慮主管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行為,有意識的跟隨主管離開組織,以使目標一致。而同樣的,由于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的目標不一致,若團隊主管結構洞位置越重要,團隊成員組織情感承諾對其團隊成員集體離職行為的影響越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a:團隊主管社會網絡度中心性越強,主管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正向關系越強;
H2b:團隊主管社會網絡度中心性越強,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負向關系越弱;
H2c: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結構洞越強,主管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正向關系越強;
H2d: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結構洞越強,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負向關系越弱。

圖1 理論模型
3 研究一:以人為本的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關系探究
3.1 研究目的
基于團隊成員的異質性,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情境中嵌套的團隊主管情感承諾與組織情感承諾進行重新梳理歸類;然后探究團隊成員集體離職情境中多焦點情感承諾目標相容或目標沖突的問題。
3.2 研究方法
3.2.1 研究對象及程序
本研究的數據收集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團隊為單位進行問卷發放,因實際調查問卷發放過程難度較大,問卷回收后對問卷的篩選和刪除以及有效問卷的保留也有較高的要求,刪除問卷數會偏高。最終獲取有效問卷324份,其中男女性別比約為1.28,多已婚(67.30%),工作年限低于2年最多,占比36.4%。
3.2.2 測量工具
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TTI,Team Members' Collective Turnover Intention)。結合Wombacher等(2017年)[10]團隊導向的離職意圖量表,本研究測量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具體包含“如果團隊主管離開這家公司,我也會馬上離開這家公司”、“即使團隊主管離開這家公司,我也不會離開這家公司”等四個題項,其中1題為反向計分題。
組織情感承諾(AOC,Affective Commitment ToOrganizations)。本文選取Vandenberghe等(2004年)[12]修訂的組織情感承諾分量表。具體包含“組織對我個人有很大的意義”、“我真的覺得對我的組織有歸屬感”等六個題項,其中2題為反向記分題。
主管情感承諾(ASC,Affective Commitment To Supervisors)。本文選取Landry與Vandenberghe(2009年)[22]修訂的“主管承諾量表”,具體包含“我很尊重我的上司”、“我很感激我的上司”等六個題項,其將反向記分題修改為“欽佩”與“依戀”并進行正向記分。
3.3 研究結果與討論
3.3.1 信度、效度檢驗與共同方法偏差
首先,信度檢驗結果顯示,“主管情感承諾量表”,“組織情感承諾量表”以及“集體離職傾向量表”的信度均大于0.8,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其次,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三因子模型的擬合(χ2/df=1.412,CFI=0.992,TLI=0.987,RMSEA=0.013)顯著優于其他模型。最后,單因素檢驗結果顯示,第一個因子解釋率為30.545%(<40%),調研的數據不存在同源性偏差問題。
3.3.2 以人為本的潛在剖面分析中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關系
首先,利用Mplus7.0對主管情感承諾和組織情感承諾進行以人為本的潛在剖面分析。分析結果顯示,隨著剖面個數的逐漸增加,模型從3個剖面到4個剖面信息指數AIC與BIC的減小(ΔAIC=-150.842;ΔBIC=-139.499;ΔSSA-BIC=-149.015),大于從4個剖面到5個剖面AIC與BIC的減小(ΔAIC=-14.574;ΔBIC=-3.232;ΔSSA-BIC=-12.747),呈現下降趨勢;4個剖面模型的信息指數估值與5個剖面的估值相差不大,表明拐點出現在4個剖面處;剖面4的分類質量指標信息熵最高,為0.966,正確率超過90%,而剖面5下降,說明4個剖面分類精確性最高。似然比檢驗亦是如此,結果均顯著,模型支持所有的分類結果,5個剖面的LMR雖顯著,但顯著性有所下降。參考模型簡潔清晰的原則,本文選擇4個剖面應為最優模型,分類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剖面分類結果
然后,構建回歸混合模型進行潛在剖面分類結果的后續分析,以探究以人為本的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關系。依據因變量為連續變量,故選取“修正的BCH法”構建回歸混合模型,個體統計學變量為控制變量。數據結果如表2所示。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在潛在剖面分析結果的四個剖面均存在顯著差異,其中C2、C4、C1、C3的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依次遞減,假設H1a、H1b、H1c與H1d均成立。

表2 χ2檢驗結果
3.3.3 多元回歸分析中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關系
根據前文結果,本文將目標沖突的C1(低-低型)與C4(高-高型)的兩個子群體合并為“高高/低低情感承諾”,將目標相容的C2(主管情感承諾主導型)與C3(組織情感承諾主導型)的兩個子群體合并為“焦點主導情感承諾”。使用SPSS對兩者的關系進行進一步檢驗,詳見表3。
就全部的樣本而言,主管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正相關(β=0.449,P<0.001),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負相關(β=-0.307,P<0.001)。“焦點主導情感承諾”結果與全樣本基本一致,主管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正相關(β=0.520,P<0.001),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負相關(β=-0.253,P<0.05)。在“高高/低低情感承諾”中主管情感承諾與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結果均不顯著,也印證了假設H1a、H1b、H1c的成立。

表3 主效應回歸檢驗結果合并表
4 研究二: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
4.1 研究目的
本文在團隊層面引入團隊主管社會網絡,從團隊領導中心性和團隊領導結構洞兩個角度,探索考慮多焦點的情況下,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關系受團隊主管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的影響情況,進一步補充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影響機制。
4.2 研究方法
4.2.1 研究對象及程序
本研究的調查以團隊為單位,由于社會網絡部分對問卷發放要求較高,團隊內需滿足80%的作答率。由于C2(主管情感承諾主導型)、C3(組織情感承諾主導型)在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關系上均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檢驗。目標沖突情境下的“高高/低低情感承諾”雖是過往研究中被忽視的部分,但其樣本數也達到197,超過半數,因此有研究的必要性。其中,男女性別比約為1.74,略高于全部樣本,已婚占比62.94%,略低于全部樣本,工作年限較少,低于2年占比45.69%。
4.2.2 測量工具
根據本研究選取非正式網絡中的“咨詢網絡”,并對可能重復的友誼網絡加以控制,對其中團隊主管在各網絡中的位置加以測量。咨詢網絡與友誼網絡的測量參考Siciliano與Thompson(2018)[23]研究社會網絡與組織承諾關系時所使用的量表,咨詢網絡題項為“問題求助對象”,友誼網絡的題項為“朋友人選”,并對具體的行為和情境加以限制。
4.3 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檢驗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的跨層調節作用,首先建立僅含有因變量的零模型(Model1),其中ICC=0.173,具有較高的組間差異,可以對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進行多水平分析。先將Level1層次的控制變量進入的空模型(Model2)。然后考慮到跨層隨機效應,多焦點情感承諾在Level1層次對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關系模型(Model3)結果顯示,主管情感承諾(βASC=-0.028,P>0.05)與組織情感承諾(βAOC=0.039,P>0.05)結果均不顯著;從隨機效果來看,組內方差Model1NULL模型的0.237降到了現在0.174,變化幅度f-square=0.478,中等偏高。

表4 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的調節效應
隨后,先將Level2的團隊規模以及團隊類型作為Level2的控制變量單獨放入模型(Model4)。再在Level2層,加入主管社會網絡相關變量后的截距模型(Model5),主管咨詢網絡中心性(βASC=0.024,P<0.001)與主管咨詢網絡結構洞(βAOC=0.010,P<0.05)結果顯著;從隨機效果來看,組間方差Model1模型的0.716降到了現在0.101,變化幅度f-square=0.862,偏高。
最后,檢驗主管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Model6),結果表明,主管情感承諾與主管咨詢網絡結構洞的交互項顯著(βASC=0.009,P<0.05),組織情感承諾與主管咨詢網絡結構洞的交互項顯著(βAOC=-0.009,P<0.05),剩余兩項結果不顯著,假設H2c、H2d成立,H2a、H2b不成立。
5 討論與應用
5.1 討論
結果表明,主管情感承諾和組織情感承諾可分為四個不同的剖面,可進一步研究多焦點情感承諾之間的“權衡”或“替代”關系[24]與不同情感承諾組合下員工的行為選擇。其中本文發現集體離職情境中出現“情感承諾目標沖突”的子群體就達到60.80%,且結合后續主效應的分析結果,全部樣本與焦點主導型情感承諾組結果基本一致,且與單焦點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卻和目標沖突群體截然不同。故目標沖突下,團隊成員無法根據自己的情感依賴情況決定自己是否選擇跟隨團隊主管離職,進一步說明了僅從單一焦點情感承諾的角度,或不考慮多焦點情感承諾的相互作用,去探究對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影響是相對片面的。同時這一部分目標沖突群體,由于沒有行為傾向,在實證分析時也會“淹沒”在大樣本中,該問題在此前的實證研究中也未引起關注,現有研究結果無法解釋超過近半數人群的行為選擇,因而情感承諾與集體離職的研究尚待補充。
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關系的研究結果表明,主管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顯著正相關,主管情感承諾主導的子群體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高;組織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顯著負相關,組織情感承諾主導的子群體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低。與單焦點情感承諾與離職的關系基本相同[25],但與嵌套關系中“留在一個團隊的意圖取決于團隊承諾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對組織的看法的影響[10]”的觀點有所差異,本文的分析結果進一步肯定了即使考慮多焦點情感承諾的相互作用,組織情感承諾依舊可以影響團隊成員集體離職,且若組織情感承諾相對主管情感承諾越高,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就越小。
最后,跨層調節的結果顯示,單從目標沖突的子群體來看,團隊主管網絡結構洞具有顯著的跨層調節作用,其中與主管情感承諾的交互作用正向促進團隊成員集體離職,與組織情感承諾的交互作用則相反。研究結果也從實證的角度進一步解釋了為何離職信息在處于正式組織領導地位的節點初始傳播能力強,當領導也處于結構洞位置時后續傳播能力也會顯著提升[26]的原因。而團隊主管網絡中心性的調節作用并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團隊主管是組織指定的正式領導,雖然是非正式網絡的中心性,但也多與工作相關,中心性所產生的依賴關系與情感承諾形成的心理依賴也較為相似,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員工產生混淆,目標沖突時,主管中心性的影響也會使員工無法做出選擇,也因此在模型中與多焦點情感承諾未產生交互作用影響團隊成員集體離職。
5.2 應用
第一,關注多焦點情感承諾內在的相互關系。不同焦點的情感承諾會產生沖突。根據研究結果,在有限的范圍內,組織可以通過提高組織情感承諾的絕對程度來間接影響組織情感承諾在員工心里的相對位置。同時組織在團隊化與平臺化管理的同時,也需要考慮如何保證組織與團隊內員工的聯系與互動,例如通過HRBP等方式在保證團隊授權和自主管理的同時,加強組織和團隊的聯系緊密性,尤其需注意外包團隊或地理位置分散的團隊與組織的聯系。
第二,關注團隊主管在非正式網絡中的位置。首先,成員追隨主管的團隊成員集體離職需要引起組織的關注和重視。組織需要提高團隊主管的組織情感依賴程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大規模集體離職形成;加之,主管更接近員工,組織亦可以通過主管的行為和觀念來影響成員對組織的情感依戀。其次,組織應及時發現團隊主管的離職意圖,對可能出現的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加以預防。此外,組織也應當避免在授權過程中,團隊主管對信息的控制和“壟斷”,以避免團隊成員與組織的分離與疏遠。
第三,關注團隊內部信息共享情況,警惕“團隊主管結構洞”,搭建“溝通橋”。有效的溝通是團隊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結構洞的存在,會對信息和資源的“壟斷”,也會與情感承諾共同影響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因此,組織應當加強信息共享平臺建設。組織也應當在各團隊獨立工作的同時,也可以適當促進多團隊的系統協調工作,加強各團隊間的溝通與人際互動;在工作以外,組織可以推動團隊建設以及團隊間的互動與交流,例如企業年會、多部門團建等。
6 結論
組織在考慮團隊招聘便利的同時,也要關注到集體離職的危害。與個體離職不同,復雜的情境下隱藏著目標沖突,本文通過以人為本的潛在剖面分析理清了多焦點情感承諾與團隊成員集體離職的復雜關系,通過引入團隊主管社會網絡,對這一目標沖突情境下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的成因進行探究。研究發現,團隊主管社會網絡結構洞可與主管情感承諾共同作用促進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與組織情感承諾共同作用抑制團隊成員集體離職傾向。研究結論對組織有效管理團隊組織、預防集體離職發生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與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