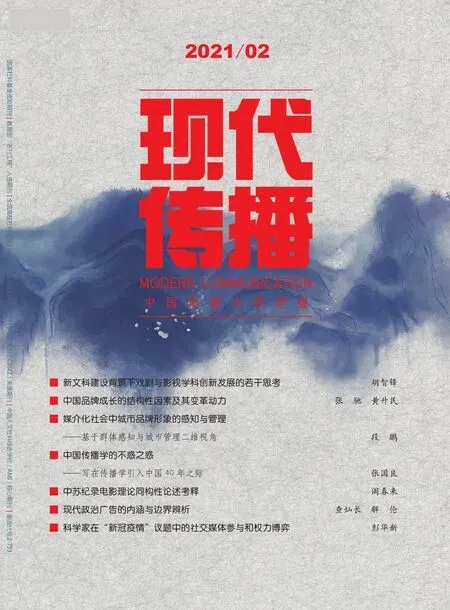跨越情感與文化的鴻溝:國際傳播受眾接受度研究*
■ 陳 功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外宣媒體嘗試通過西方受眾樂于接受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積極推進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al writing),用講故事的方式創造出了不少好的新聞作品。但是,西方受眾是否讀懂了這些新聞報道?西方受眾是否通過我國外宣媒體筆下的新聞故事感受到了中國國情的復雜和我們改革的勇氣和魄力?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有待進一步探索。任何傳播能力的提升,都離不開對受眾的準確把握,都需要了解和研究受眾,知其所知所想,“跨國跨文化的國際傳播更是如此”①。
受眾研究是新聞傳播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但是國內主流新聞傳播研究期刊中國際受眾研究較少。劉燕南、谷征坦言“我國國際傳播受眾研究起步晚,積累少,迄今仍處于初級階段”②。近年來涌現出一批相關研究,例如,楊凱和唐佳梅③對在廣州的外國人使用媒介的方式和信息需求進行了歷時調查;姜可雨④對跨國傳播視閾下受眾研究的嬗變進行了文獻回顧和理論梳理;蘇林森⑤調查了美國受眾對中國英語媒體的使用情況和傳播效果;張梓軒和許暉珺⑥搜集了國際主流視頻播出網站上使用英語的用戶對中外合作紀錄片的評論,分析了國際受眾對中國紀錄片的解碼情況。然而,這些研究多從傳播視角切入展開分析,較少關注傳播內容本身和內容的載體——“語言”。現實中,相關媒體和部門在打通傳播渠道、搭建傳播平臺的同時,同樣也未對構成傳播基礎的“語言”給予足夠的重視。國際傳播的內容和語言質量決定了整個傳播鏈條中“最后一公里”的傳播效果,應該引起學界和業界的重視。伽達默爾(Gadamer)指出,“人以語言的形式擁有世界”⑦。語言不僅僅是工具,還是“一切交流和一切文化依賴的媒介”⑧,它可以“反仆為主”,構建人類世界⑨。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視閾下涉及內容和語言的研究不在少數。例如,王曉路⑩以“龍”和“Dragon”的詞語文化軌跡為例,指出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語境下要思考跨文化傳播的有效性。孫化顯從電影文本的互文性切入,分析了電影的跨文化傳播。但是該類研究忽略了真實受眾的存在,僅在理論上探討了國際受眾應該接受或理解的語言問題,而對受眾的真實想法卻知之甚少。
在新媒體崛起、傳統媒體受到沖擊而不得已轉型的時代,有研究表明,盡管有不同形式的新聞走進大眾視野,傳統新聞報道仍然占主導地位。外宣媒體有必要從受眾的視角審視傳播內容和語言模式,找出新聞寫作中存在的問題。
二、理論基礎
(一)敘事傳輸與敘事經歷
敘事性新聞(narrative news)是“中國故事”國際傳播的天然載體。與信息性新聞(informational news)相比,敘事性新聞加入了故事的成分,對讀者具有較好的勸服效果,拉近與讀者的心理距離,并激發讀者的情感反應。根據心理學相關研究,故事是通過敘事傳輸(narrative transportation)來影響人們的態度的。在看到故事時,讀者會進入故事所描繪的虛擬世界中,體驗故事主人公的經歷和情感,忘記周圍真實的世界。之后,讀者也傾向于將故事中的態度帶到現實世界中來。格里格(Gerrig)在研究敘事體驗時,首次提出了“傳輸”這一概念。他將故事的聽眾或讀者的體驗比作“旅行者離開真實世界一段距離……當他們回到原來的世界時,一些東西已經發生了改變”。格林(Green)和布洛克(Brock)基于這一概念正式提出了“敘事傳輸”理論,并對故事的說服效果進行了測量,驗證了量表的有效性。敘事傳輸是一種獨特的心理過程,是讀者“注意力、想象和情感在事件上的聚焦”,可以很好地考察受眾的心理體驗。為了理解并測量故事對受眾的影響,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描述敘事感受的相關概念,如認同感(identification)、臨場感(presence)、心流體驗(flow)等。巴塞爾(Busselle)和比蘭吉奇(Bilandzic)將這些概念梳理整合成為一個心理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開發出了涵蓋11個維度52個題項的大型“敘事經歷”量表(Narrative Engagement Scale)。敘事經歷包含了被試者接觸到敘事時所產生的所有體驗,該量表也旨在全方位測量敘事對受眾的影響。基于上述理論部分契合維度,我們希望考察,到底是西方媒體還是中國外宣媒體寫的“中國故事”能夠將西方讀者帶入故事,并能產生更多認知和情感上的認同?
(二)高低語境理論
要想“講好中國故事”必然要考慮對外傳播中的跨文化因素。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T.Hall)在《超越文化》一書中提出了“高低語境理論”。在該理論中,高語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處在語境階梯(context scale)連續體的一端,如中國文化;低語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分布在另一端,如美國文化。另外,在同一文化中,語言實際使用場景也有高低語境之分,如家人等親密環境的交流屬于高語境交流,而外交、法律等非親密、正式場合的交流都屬于低語境交流。霍爾指出,高語境交流指的是,“大多數信息或存在于物質環境中,或內化于人心里,需要經過編碼的、顯性的、傳輸出來的信息卻非常之少。低語境交流正好與之相反,就是說,大量信息編入了顯性的代碼之中”。語言學家伯恩斯坦(Bernstein)研究發現,高低語境下交流的代碼(code),如語言,是有區別的;高語境下的交際代碼被稱為“受限代碼(restricted codes)”,而低語境下的代碼為“復雜代碼(elaborated codes)”。具體來說,在高語境下,很多信息不言自明,盡管信息發出者的詞匯、句法和語音都可以壓縮、簡化,但卻不影響接受者的理解,因為雙方共享了預制的內在語境和外在語境;而在低語境下,大多數信息必須包含在傳達的訊息之中,以彌補語境中缺失的信息。如果把中國外宣媒體(信息發出者)和西方受眾(信息接受者)的交流置于語境階梯中,那么無論從文化層面看(中國文化),還是從語言實際使用場景看(非親密場合),兩者的交流都屬于高語境交流。本研究希望通過西方讀者的反饋,考察身處高語境的中國外宣媒體是否可以讓接受者很好地理解“中國故事”。
三、研究方法
為了更好地探究西方受眾對我國外宣媒體筆下新聞故事的接受程度,本研究選取了《中國日報》中一篇關于“戶口”的敘事性報道(580詞),以及《華盛頓郵報》中一篇同主題敘事性報道作為閱讀材料(1032詞),針對西方讀者群體分別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所選取的兩篇報道在結構上基本都包含了克諾布洛赫(Knobloch)等人提到的所有敘事元素,從一個事件開始(問題或沖突),之后是闡述、解釋復雜性,最后達到事件的高潮(事件的結果或解決方案),以確保報道在結構和風格上的相似性,盡量減少干擾讀者反饋的因素。之所以選擇“戶口”作為報道主題,主要有三點考慮:一是戶口問題能夠體現我國國情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能夠較好地檢驗我國外宣媒體把握復雜新聞框架的能力;二是戶口帶有較為明顯的中國文化特征,但是戶口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是西方讀者即便來華體驗,短期內也是無法觸及的,方便我們控制受眾個體文化經歷對敘事傳輸的影響,而且能夠較好地考察我國外宣媒體講述“中國故事”的跨文化意識和語言技能;三是所選的《華盛頓郵報》報道對戶口本身的態度中立偏消極,《中國日報》的態度中立,未回避戶口帶來的各種問題,中西媒體的態度無極端分化,盡可能減少了媒體態度對受眾的明確引導。
問卷調查之后,本研究另外隨機選取了6位來華半年內的英語為本族語者閱讀兩篇報道(未給出報道來源),并進行了半結構化訪談。訪談問題與問卷主體內容基本一致,每個問題回答完后,會要求被試者在報道原文中找出影響其答案的詞語或句子。
基于上述研究設計,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RQ1:西方讀者對哪一方媒體筆下的“戶口故事”接受度更高一些?
RQ2:與西方媒體相比,中國外宣媒體筆下的“戶口故事”是否能夠更好地將西方讀者帶入,并產生更多認知和情感上的認同?
RQ3:與西方媒體相比,中國外宣媒體是否能夠更好地為西方讀者理解報道填補文化鴻溝?
(一)問卷設計
傳播效果常被界定為三個層面:認知、情感和行為(cognitive,affective,behavioral effects)。認知效果主要考察受眾獲得了什么信息,以及受眾頭腦中的信息是如何被重構的;情感效果主要考察受眾態度的形成,或對新聞事件的評價是積極還是消極;行為效果考察的是受眾接觸媒介信息后所產生的行為。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在跨文化語境下,西方受眾認知和情感方面的傳輸,不涉及行為效果的考察。本研究使用的問卷有兩個,一個問卷測量西方讀者對《中國日報》報道的反饋(以下簡稱“問卷A”),另一個問卷測量西方讀者對《華盛頓郵報》報道的反饋(以下簡稱“問卷B”)。
問卷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報道原文,第二部分是量表及被試信息采集,兩個問卷的第二部分完全相同。問卷通常采用李克特5級量表,但是考慮到受眾面對的閱讀材料是新聞報道,有可能傾向于趨中選擇,本研究采用了6級量表計分,以便更加細分讀者的態度和反饋。計分為“1”至“6”,分別代表“強烈不同意(strongly disagree)”“不同意(disagree)”“基本不同意(slightly disagree)”“基本同意(slightly agree)”“同意(agree)”和“強烈同意(strongly agree)”。
關于量表的開發,為了更好地測量西方受眾在閱讀西方媒體和中國外宣媒體關于“戶口”的敘事性報道時所產生的不同的心理和認知體驗,我們結合敘事傳輸已有相關量表和跨文化理論設計了5個維度、21個題目的問卷。五個維度分別是:敘事傳輸(narrative transportation)、移情(empathy)、認知獲取難易(ease of cognitive access)、認知觀點理解(cognitive perspective taking)、跨文化體驗(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維度1:敘事傳輸。該維度的題項來自格林和布洛克開發的經典傳輸量表。原量表共包含15個題項,主要測量讀者在看到故事時的“情感帶入程度、認知投入程度和視覺想象”,信度和效度已經通過驗證。之后有研究對此量表進行了簡化,測量效果較好,如埃斯卡拉(Escalas)將其簡化為3個題項的簡易量表,在消費行為測量中廣泛應用;王(Wang)和考爾德(Calder)將其簡化為7個題項的量表,評估廣告和節目的傳輸效果。為了更好地測量敘事性新聞文體的傳輸效果,本研究也將原量表簡化為7個題項。
維度2—4:移情、認知獲取難易、認知觀點理解。這三個維度的題項來自巴塞爾和比蘭吉奇的敘事經歷量表。該量表綜合了多項研究的成果,測試的敘事體驗較為全面,但是考慮到該量表測量的體裁為純敘事(如小說),且將敘事模態拓展到了電視、電影,與本研究所關注的夾敘夾議的敘事性新聞及其書面閱讀體驗有所不同。多次論證后,我們只采用了其中符合本研究目的的三個維度。其中移情指的是“受眾對敘事主人公情感體驗的反映”,即受眾可以理解并重新體驗故事中角色的情感。麥基和格雷絲指出,故事中“讓人同情可有可無,而感同身受必不可少”。認知獲取難易與閱讀體驗(reading experiences)有關,指的是受眾的大腦在處理故事時,注意力能夠持續保持聚焦的難易程度。如果讀者在閱讀敘事性新聞時,不用刻意為之都能保持專注,那就說明該報道的認知獲取較為容易。認知觀點理解指的是讀者能夠“暫時拋開自己的讀者身份,能站在故事主人公的視角看待問題”,并對主人公有較為強烈的認同感(identification)。以上三個維度各包含3個題項,一共9個題項。
維度5:跨文化體驗。鑒于上述維度在考察敘事對讀者情感和認知的影響時,沒有將跨文化因素納入考慮范圍,因此本研究根據跨文化經典理論,即霍爾的高低語境理論,設計了5個題項,測量讀者在閱讀“他者文化”報道中的跨文化體驗。該理論認為,高語境文化中的用詞傾向于模糊、含蓄、間接(ambiguous,implicit and indirect),而低語境文化中的表述多重視明確、直接、無歧義(explicit,unambiguous and direct)。據此我們設計了以下3個題項:“I feel that the report is written in a quite explicit way”;“I feel that the report is written in a quite direct way”;“While reading the narrative,I feel like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story is somehow ambiguous”。另外2個題項“I think that it would be helpful if more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about the story”和“I think some of the messages the author tries to deliver lie between the words unspoken”主要考察來自低語境文化的西方受眾是否能夠發現他們在敘事性報道中存在背景知識缺失或無法領會報道內容的情況。
以上題項設計完成后,我們根據報道主題和內容對題項的措辭進行了微調,并請英語本族語者進行了兩輪校對,確保所有表述表意準確、語法無誤。
(二)數據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通過美國在線調查網站SurveyMonkey(https://www.surveymonkey.com/)制作并發放了付費問卷。付費項目允許我們更高效地將問卷發放到均質化的目標受眾手里。我們要求目標受眾必須為英語本族語者,性別和教育程度(高中以上)占比平衡。預計收集500份問卷,兩個問卷各250份。兩份問卷的回答者完全無重復,即回答問卷A的讀者和回答問卷B的讀者屬于總體屬性相似,但個體完全不同的兩個群體。實際一共收回問卷516份,問卷A平均完成時長為395秒,問卷B為571秒。之后對無效問卷(漏答問卷、規律性作答問卷、反向題目回答異常等)進行了剔除。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涉及跨文化維度的測試,因此我們在被試信息收集部分設計了篩選問題(你的母語是什么?/ 你在中國待過多長時間?),以便于我們將華人或亞洲文化圈被試者,以及(曾)在中國久居的西方受眾排除在外。前者全部剔除,后者則只剔除在中國待過一年以上的。處理完成后,剩余有效問卷403份,有效率為78%,其中問卷A為198份,問卷B為205份。
盡管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大部分來自成熟量表,且其信度和效度都已經過驗證,但是鑒于我們對其進行了部分選擇、重組和措辭上的微調,增加了自行設計的跨文化體驗題項,因此,要對兩個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的重新測試。經SPSS統計分析,問卷A和問卷B各維度內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系數均達到0.70以上,問卷整體Cronbach Alpha系數分別為 0.851和 0.865,信度良好。因子分析顯示,問卷A的KMO值為0.881>0.7,Bartlett 球形檢驗結果顯著(近似卡方值為149.3,自由度為210,p=0.000<0.05);問卷B的KMO值為0.905>0.7,Bartlett球形檢驗結果顯著(近似卡方值為200.2,自由度為210,p=0.000<0.05);表明兩份問卷收集的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兩份問卷均提取出了五個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0,累計方差貢獻率分別為60.05%和62.28%,可以較好地反映讀者對于新聞報道的認識。
之后,對問卷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從五個維度考察西方讀者對兩篇敘事性報道的認知態度和跨文化差異,并結合訪談結果展開深入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一)讀者的選擇:更偏愛西方媒體報道
為了考察西方讀者對中西媒體“戶口故事”的接受程度,本研究首先對問卷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別匯報兩份問卷整體得分,以及各維度得分的均值(Mean)和標準差(SD)。從表1中可見,問卷A整體均值為3.79,低于問卷B 整體均值4.08,平均值差為0.29。也就是說,整體來看,西方讀者對《中國日報》報道的接受程度低于《華盛頓郵報》。具體從各維度的均值來看,問卷A五個維度的均值全部低于問卷B相應維度的均值。也就是說,不論是報道的敘事傳輸(M=3.75vs.3.96)、認知獲取難易(M=3.81vs.4.20)、移情(M=3.90vs.4.21)、認知觀點理解(M=4.01vs.4.31),還是跨文化體驗(M=3.48vs.3.73),西方讀者都更加認同并接受《華盛頓郵報》筆下的“戶口故事”。其中,西方讀者對《中國日報》報道的“認知觀點理解”得分最高(M=4.01),“跨文化體驗”得分最低(M=3.48),說明讀者對故事主人公有較強的認同感,但卻難以真正理解他者文化中的故事。
表2的獨立樣本t檢驗統計結果顯示,西方讀者群體對中西媒體兩份報道的整體接受情況存在顯著差異(t=-4.22,df=401,p=0.000<0.001)。具體到不同維度,兩份問卷在五個維度上也全部存在顯著差異,其中跨文化體驗(t=-3.85,df=401,p=0.000<0.001)和認知獲取難易(t=-3.69,df=401,p=0.000<0.001)的差異最大,敘事傳輸(t=-2.86,df=401,p=0.004<0.01)、移情(t=-3.01,df=401,p=0.003<0.01),以及認知觀點理解(t=-3.14,df=401,p=0.002<0.01)次之。

表2 獨立樣本t檢驗統計結果
(二)傳者與受者之間存在隱形文化壁壘
在五個維度中,“跨文化體驗”表現出的差異(t=-3.85)表明,在講述“中國戶口故事”方面,盡管《中國日報》在理解報道主題方面存在優勢,但卻難以將故事傳達到受眾的“內心”。相比于《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西方讀者認為我們的報道比較模糊、含蓄、間接,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背景信息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報道內容。事實上,我國外宣記者在進行新聞寫作時,對“戶口”歷史現狀的理解應該比西方記者更加深刻,對沒有“戶口”所帶來的不便也應該比西方記者更加感同身受。對此,除了記者的語言水平之外,另一個更加可能的解釋是“高語境文化”對跨文化新聞寫作的影響。霍爾指出,“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與外部世界之間提供一個選擇性很強的屏障,在許多不同的形態中,文化選定我們要注意什么,要忽略什么”。作為長期甚至終生浸潤在中國文化中的外宣記者,盡管已經有多年的外語學習經歷,并對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對外報道寫作中仍然難以擺脫“語境階梯”的影響,仍然無法自如地在“高-低語境文化”中移動。“戶口”對于中國人到底意味著什么,早已成為我們文化中共享的、預制的內在語境與外在語境,即便沒有提供明確的信息,我們都可以利用內化語境機制(internal contexting)自動補償或校正扭曲或缺失的信息。但是,在跨文化傳播中,這種本來有益于交流的機制卻恰恰成為外宣新聞寫作的“屏障”,讓我們在無意間“屏蔽”掉有必要讓西方讀者知曉的語境信息,呈現出典型的“高語境”交流特征。例如,在閱讀《中國日報》的報道“Man quits well-paid job to pursue Phd for Beijing Hukou”之后,接受訪談的六位西方讀者一致認為,他們對報道標題感到費解。對于共享文化語境的中國讀者來說,這個標題中所包含的“高薪工作、讀博、北京戶口”三個關鍵詞(受限代碼)就足以啟動大腦中的語境機制,領會到標題中所包含的各個層面的無奈選擇。但是對于低語境文化下的西方讀者來說,高語境特征的新聞標題背后潛藏的信息太多,明確告知的太少,而讀者又沒有內在程序化語境(programmed contexting)與外在情景和環境語境(situ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texting)的指引,很難深刻理解標題所傳達的意思。語境是承載意義的;沒有了語境,就會有一部分信息缺失。這也就要求我們的外宣媒體在對外傳播時,要嘗試為受眾提供足夠的語境,尤其是外在的情景和環境語境,從而幫助受眾構建內在的“語境化機制”,并在報道寫作中采用“復雜代碼”,在一切語言層面都做到更加準確、無歧義、易理解。例如,《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標題“In China,chafing under ancient permits;Access to city services Critics say ‘hukous’ are outdated and discriminatory”就采用了典型的低語境下的顯性“復雜代碼”,讀者沒有額外的文化認知負擔和信息加工負擔,所有信息一覽無余,而且“低語境系統更容易受操縱”。
根據上述分析,《中國日報》在“認知獲取難易”維度上得分顯著低于《華盛頓郵報》也在情理之中。跨文化體驗方面的障礙必然會影響到讀者的閱讀體驗。當西方讀者在面對不熟悉的“他者文化”時,他們的大腦面臨著“信息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的問題,這就要求西方受眾在閱讀《中國日報》的報道時需要更加刻意才能保持精力集中,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跟進新聞事件的發展。接受訪談的六位西方讀者一致表示,《華盛頓郵報》在報道中對“戶口”背景進行了介紹,對他們理解報道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這段背景介紹出現在報道的第四、五段,在一個主人公的小故事之后很快便引出,用6句話、117個單詞簡要介紹了什么是“戶口”,以及“戶口”的歷史淵源和主要社會功能。
One of China’s oldest tools of population control,the hukou is essentially a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ermit,akin to an internal passport.It contains all of a household’s identifying information,such as parents’ names,births,deaths,marriages,divorces,moves and colleges attended.Most important,it identifies the city,town or village to which a person belongs.
The hukou dates back at least 2,000 years,when the Han dynasty used it as a way to collect taxes and determine who served in the army.Mao Zedong’s Communist regime revived it in 1958 to keep poor rural farmers from flooding into the cities.It remains a key tool for keeping track of people and monitoring those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troublemakers”.
(來自《華盛頓郵報》2010年8月15日)
仔細閱讀上述背景可以發現,《華盛頓郵報》對“戶口”的介紹是作者帶著“有色眼鏡”精心挑選,并預制的語境。兩千多年的戶籍制度是歷史辯證考量的產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國情下,其利弊均無法一言概之。而該報道對戶口負面信息的篩選最終為西方讀者預制好了外在語境,為讀者理解報道定好了基調。作為完全不了解“戶口”的西方受眾,早在報道一開始就已經被引導而不自知。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引導不僅減輕了西方讀者的認知負擔,讓他們不用花費太多精力便可以融入故事,還在思想上迎合了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偏見和刻板印象,讓本來就對中國知之甚少的西方讀者對中國的認識更加負面,從根本上阻斷了中西“民心相通”的通道。
作為國際交流的渠道和平臺,外宣媒體應該充分利用語言的力量,通過話語構建現實、溝通情感,引導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國。《中國日報》整篇報道沒有提及戶口的任何歷史背景,加重了讀者的閱讀負擔。盡管《中國日報》報道的篇幅僅為《華盛頓郵報》的一半,但是西方讀者卻并沒有認為字數少就可以減輕他們的“認知獲取難易”程度。講好中國故事既是技術問題又是戰略問題。在不注重及時性的非消息類報道中增加一部分背景知識,介紹中國歷史和現實國情,或介紹事情的復雜性和相應的改革措施,不僅可以通過預制語境降低讀者的閱讀負擔,還可以為西方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在國際傳播的輿論戰場上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構建真實完整的中國形象。除了跨文化因素,“認知獲取難易”還受到敘事方式等因素的影響。
(三)受眾難以沉浸其中的閱讀體驗
“深層的文化潛流”構建了我們的生活,塑造了我們的思維方式,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難以擺脫。事實上,除了文化層面的宏觀影響,微觀層面的新聞敘事方式也會影響到讀者的閱讀體驗,對新聞傳播的效果產生較大的影響。具體到本研究,西方讀者面對兩篇報道時在敘事傳輸(t=-2.86)、移情(t=-3.01)和認知觀點理解(t=-3.14)維度上也出現了較為顯著的差異性。
嚴進、楊珊珊指出,影響敘事傳輸效果的因素有三大類:個體因素、情境因素和敘事質量。個體因素指的是受眾的知識背景、認知模式、個性特征等因素,例如,受眾熟悉故事描繪場景、有故事相關知識和經歷等都可以促進敘事傳輸。情境因素指的是敘事信息的媒體類型、敘述形式、信息引導方式等,例如,和視頻相比,文本材料能給讀者帶來更大的傳輸效果。敘事質量則指的是故事結構、語言文采、呈現方式等是否有利于人們形成傳輸。考慮到讀者的個體因素和報道的情境因素對傳輸的可能影響,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比如在選擇被試者時,盡量排除可能了解“戶口”或有相關經歷的讀者;在選擇閱讀材料時,材料來源于權威報紙(書面文本);敘事視角均為第三人稱;敘事模式均為夾敘夾議。在此基礎上,我們著重探討敘事質量本身對傳輸效果的影響。
參與訪談的西方讀者在閱讀《中國日報》“戶口故事”時認為,自己很難自動地、不用花費額外努力就沉浸到故事主人公的世界。除了文化因素的影響,故事中因果關系的推斷也耗費了讀者的精力,弱化了敘事傳輸本可以達成的深度體驗。例如,讀者的問題包括:為什么要放棄高薪工作?為什么要為了讀博而放棄高薪工作?為什么想要北京戶口只能讀博、還不能工作?當然,能夠引起讀者疑問和閱讀興趣的標題是很好的,遺憾的是,讀者在報道中并沒有找到問題的答案。有讀者認為報道標題僅僅概括了報道中一位主人公的故事,另外兩位主人公并沒有嘗試“通過考博獲得北京戶口”,內容與標題不符。另外,一些讀者表示,《中國日報》的報道所包含的故事細節較少,提供的證據不夠充分。埃斯卡拉指出,結構較差、因果關系不清楚等都是敘事質量差的表現,可以明顯減弱傳輸程度,無法讓讀者產生沉浸其中的閱讀體驗。反觀《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其標題中的關鍵詞具有概括性,“outdated(過時的)”和“discriminatory(歧視的)”兩個詞足以傳達文中故事力圖體現的核心價值,且支撐細節豐富,報道的連貫性(coherence)和一致性(unity)較好,讀者不需要額外付出太多努力就可以沉浸在故事場景中。這種近似于心流體驗的敘事傳輸,可以促進讀者認知和情感的處理過程,幫助讀者理解戶口帶來的問題,并體驗沒有戶口的主人公的情感。研究表明,讀者參與、傳輸或沉浸在敘事中的程度,會影響故事相關態度對讀者施加影響的潛力,進而影響讀者的態度。
故事的力量之一是可以喚起受眾的情緒。除了閱讀故事的投入程度,讀者對主人公情感的體驗(即移情)也受限于新聞報道所呈現故事的“入心”程度。讀者產生移情的入口是整個故事所包裹著的核心價值觀,如好壞、正負、對錯、美丑等二元對立價值觀,這些價值標準決定了故事最根本的意義和情感。《中國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報道旨在傳達的價值觀均為戶口的利與弊。《華盛頓郵報》報道全文有31處與“outdated” 和“discriminatory”語義色彩相同或相近的單詞或短語,如chafing(煩惱)、onerous(令人焦慮的)、unsuited(不合適的)等等。但是《中國日報》報道中只有15處,且用詞較為單調,其中4處用了“hard”,2處用了“trouble”,無法向讀者傳遞復雜的情感。同一語義場的詞語較少,無法形成合力,難以承載報道旨在傳達的價值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日報》的報道衍生出了另外一個不同的價值觀,即“主動改變與被動接受”。第一位主人公希望通過“考博”獲得戶口;第二位主人公搬遷到其他城市獲得戶口;第三位主人公未提及主動改變的辦法,但是報道提到了北京行政功能向河北轉移可能會帶來希望。一個對中國文化較為了解的西方讀者將《中國日報》報道中的雙價值觀比喻為“陰陽”,即在承認戶口的弊端的同時,又認為可以通過個人努力克服這個弊端,陰陽相生,明暗相隨。該讀者坦言,大多數西方讀者可能并不會理解“考博”主人公的情感。當然,一個故事可以有多種價值觀,但是它的內容應該緊密圍繞一組核心價值觀。“感同身受”意味著“像我一樣”,當西方讀者閱讀到戶口的弊端時,他們會以“我”為鏡像看待主人公的行為,“利與弊”價值觀會首當其沖成為讀者移情的起點,出現另一個勢均力敵的價值觀,則反而會割裂讀者與主人公的心理鏈接,無法讓讀者產生“感同身受”的情感體驗。
我國外宣媒體在國際傳播中勇于直面問題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在故事價值觀設定,以及語言表現方面,則應該給予充分的考量。對于一些負面新聞,新聞報道可以夾敘夾議。“敘”的部分突出“弊”,正視現實;“議”的部分則重點介紹國情和國策,敢于改革,而不用擔心讀者對“弊”的過度解讀。情感在觀念滲透過程中起著催化劑的作用,易于讀者理解的核心價值觀則是情感加速啟動的催化劑。相反,如果一篇報道中出現多個價值觀,且無法很好地做到主次兼容,就會使讀者感到無所適從,進而影響讀者情感上的共鳴。在敘事傳輸和移情兩個方面出現的問題,必然會加重讀者的認知負擔,影響西方讀者在認知獲取難易和認知觀點理解兩個維度的體驗。
五、結語
我們仍需要在新聞的最終載體——語言和內容上下功夫,跨越看不見的文化鴻溝,以西方讀者易于理解的敘事方式講述好“中國故事”,引導西方讀者產生更多情感和認知上的認同。
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更加關注的深層現實是,外宣媒體記者在國際傳播中是處于劣勢的一方。一篇報道完成之后,盡管有外籍專家對語言進行把關,但是這些專家并不對報道的跨文化傳播效果負責。一篇報道是否可以成功地達到跨文化傳播的目的,有賴于外宣記者本人的跨文化素養。一篇報道刊出以后,記者本人無法及時收到西方讀者的閱讀體驗反饋。西方讀者的疑慮和批評、認同和贊賞即便可以通過新媒體的反饋功能傳遞給記者本人,記者也無法對已刊出的報道進行修改和二次傳播。而這種“一點一滴、支離破碎”的跨文化反饋,也很難讓記者系統了解到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范式如何促進或阻礙新聞報道的寫作,以及在今后的報道中應該如何譯解我們的文化行為。另外,對于如何在國際傳播中講好故事,用好語言這個載體,學界的學術討論仍然較少,業界的關注也較為有限。這些問題都將是今后有待繼續探索的領域。
注釋:
①② 劉燕南、谷征:《我國國際傳播受眾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探討》,《現代傳播》,2012年第9期,第24頁。
③ 楊凱、唐佳梅:《精準對外傳播視角下國際受眾的歷時性研究——基于對廣州外國人媒介使用和信息需求的連續調查》,《現代傳播》,2018年第6期,第70頁。
④ 姜可雨:《跨國傳播視閾下受眾研究的嬗變》,《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69頁。
⑤ 蘇林森:《美國受眾對中國英語媒體的使用與效果研究》,《當代傳播》,2017年第2期,第47頁。
⑥ 張梓軒、許暉珺:《中外合作紀錄片的國際受眾解碼——基于〈改變地球的一代人〉國際網絡用戶的研究》,《現代傳播》,2016年第6期,第106頁。
⑦ [德]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頁。
⑨ 李彪:《霸權與調適:危機語境下政府通報文本的傳播修辭與話語生產——基于44個引發次生輿情的“情況通報”的多元分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年第4期,第27頁。
⑩ 王曉路:《“中國文化走出去”語境下跨文化傳播的基本問題——以“龍”和“Dragon”為例的詞語文化軌跡探討》,《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