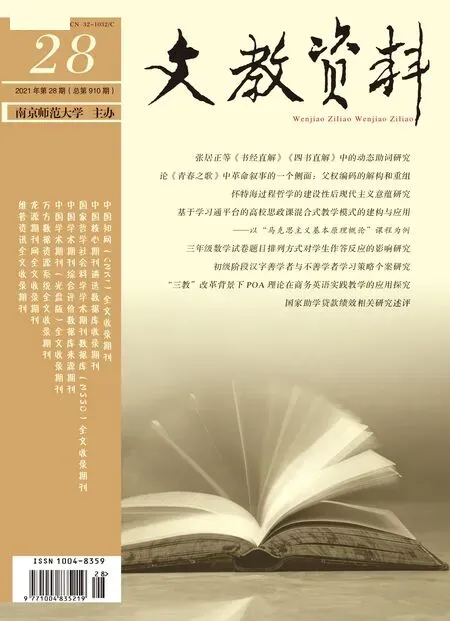語(yǔ)言文化視角下李白《靜夜思》中“床”義辨析及文本解讀
顧勁松
(江蘇財(cái)經(jīng)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基礎(chǔ)教學(xué)部,江蘇 淮安 223003)
李白的《靜夜思》流傳甚廣、婦孺皆知,千百年來(lái)備受世人稱頌。全詩(shī)僅短短4句20字,卻以無(wú)意于工而無(wú)不工之筆,平實(shí)地描述了月華如霜的靜夜之景,巧妙地傳達(dá)了遠(yuǎn)游之客的濃濃月下鄉(xiāng)愁。
時(shí)過(guò)境遷,如何精準(zhǔn)地理解、把握這首詩(shī)的文本內(nèi)容,歷來(lái)人們莫衷一是。特別是其中的“床”究竟指何物,可謂眾說(shuō)紛紜。緣于時(shí)下“床”的常見(jiàn)形制和基本功能,一般多認(rèn)為這里的“床”是一種臥具。不過(guò)從20世紀(jì)80年代開(kāi)始,就陸續(xù)有人提出新看法。學(xué)界目前大致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diǎn):① 臥具說(shuō),顏春峰、汪少華(1998)[1],陸業(yè)龍(2001)[2]等人持此觀點(diǎn);② 坐具說(shuō),持本說(shuō)法的主要有劉國(guó)成(1984)[3]、藺瑞生(2017)[4]等人;③ 坐臥具說(shuō),贊同這一說(shuō)法的,主要有喬松(1985)[5]、范慧琴(2009)[6]等人;④ 井欄說(shuō),朱鑒珉(1985)[7]、王曉祥(1986)[8]等人認(rèn)可此說(shuō)。
然而,這幾種觀點(diǎn)都有可爭(zhēng)議之處。鑒于此,我們從讀者集中的困惑和普遍的質(zhì)疑出發(fā),厘清本詩(shī)中“床”的本來(lái)面目,側(cè)重從語(yǔ)言文化視角,結(jié)合作者寫作背景,以期對(duì)這首詩(shī)進(jìn)行相對(duì)合理的解讀。
一、讀者的共同困惑
(一)主人公的空間位置
《靜夜思》文本中“床”為臥具,這是比較傳統(tǒng)的看法,向來(lái)贊成者甚多。根據(jù)這首詩(shī)本身意境,既然“床”是臥具,那么當(dāng)為供人躺臥、休息和睡眠之用,理應(yīng)放在室內(nèi),所以主人公也應(yīng)在室內(nèi)。不過(guò)這樣就產(chǎn)生了三個(gè)問(wèn)題。
第一,假如是在室內(nèi),很難“床前明月光”。室內(nèi)見(jiàn)到月光,按理說(shuō)要么是屋子無(wú)頂,月光不受遮擋,直接照進(jìn)來(lái),顯然不可能。要么就是窗戶大,月光透過(guò)窗戶照進(jìn)來(lái)并灑落床前,這一說(shuō)也難以立足,因?yàn)樘拼胀ǚ课荽皯艚圆淮螅鹿庹者M(jìn)屋內(nèi)概率很小。第二,假如是初升之月或?qū)⒙渲拢鹿獯_有可能勉強(qiáng)照進(jìn)來(lái),卻又與“舉頭望明月”產(chǎn)生矛盾。月亮在低空,月光近乎平射,根本無(wú)須“舉”頭望月。第三,就算主人公是在室內(nèi),且月光確實(shí)灑落床前,但霜露正常應(yīng)當(dāng)不會(huì)降在室內(nèi),故主人公“疑是地上霜”很牽強(qiáng)。“按生活常理,只有在可能下霜的地方,人才會(huì)聯(lián)想到霜。”[9]
如此推理,主人公空間位置不是室內(nèi)。就這一點(diǎn),“床”的坐具說(shuō)、井欄說(shuō)則較好地解決了相關(guān)問(wèn)題。坐具說(shuō)認(rèn)為“床”乃安坐之具,則不排除是在室外;井欄說(shuō)因?yàn)榫畽诒旧砭驮谑彝猓手魅斯粫?huì)在室內(nèi)。
(二)主人公身姿體態(tài)
詩(shī)中對(duì)“床”的理解不同,主人公身姿、體態(tài)自然不同。這樣難免引起眾人思考:主人公究竟是躺臥于床,安坐于床,還是站立或行走于床前?
若贊同“床”的臥具說(shuō),則主人公躺臥于床;若認(rèn)可“床”的坐臥具說(shuō),主人公可能階段性地躺臥于床,那么總體上應(yīng)該是頭部平放、仰面直視屋頂之態(tài)勢(shì)。這樣一來(lái)主人公調(diào)整視角就極為不便,只能勉強(qiáng)左右轉(zhuǎn)頭,“舉頭望月”和“低頭思鄉(xiāng)”都會(huì)異常困難。據(jù)此,主人公不該是躺臥在床,更可能是坐立或站立。
若支持“床”的坐具說(shuō),則主人公是安坐于床;若堅(jiān)持“床”的坐臥具說(shuō),則主人公可能階段性地坐立;若堅(jiān)持“床”的井欄說(shuō),則主人公是站立或行走于床前,主人公確實(shí)容易抬頭、平視、低頭。然而,主人公“舉頭望月”依然困難,因?yàn)椤芭e”本來(lái)就是將某物由低處轉(zhuǎn)移到高處,位置上有一個(gè)由低到高的過(guò)程。而從本詩(shī)來(lái)看,無(wú)論是坐在“床”上,還是站在“床”邊,主人公都沒(méi)有由低到高的起立動(dòng)作,“舉頭望月”不合情理。
二、問(wèn)題破解思路
基于上述兩個(gè)問(wèn)題的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jié)論:第一,主人公是在室外,故“床”的臥具說(shuō)不成立;第二,主人公并非躺臥,這進(jìn)一步否定了“床”的臥具說(shuō),也不是安坐或站立,而是有一個(gè)起立過(guò)程,故“床”的坐具說(shuō)、坐臥具說(shuō)、井欄說(shuō)皆難以立足。那么,“床”究竟應(yīng)該如何解讀?
(一)“床”的本義及方言義
“床”本是“牀”的俗體,“牀”才是正體。《說(shuō)文解字》:“牀,從木,爿(chuáng)聲。”[10]從造字法看,剖木為兩半,左為“爿”,右為“片”。“爿”本為幾,其橫向字形很像“幾”之外形,本義為“幾”形器具,原為“牀”的初文,為象形字。商代后期,漢字豎向直行排列法確立,很多字改變了字形方向。“爿”字寫法由橫向改成豎向,“幾”的字形與實(shí)物“幾”的外形差距拉大,其本義也有一定磨損,于是人們就在“幾”的基礎(chǔ)上加注義符“木”,強(qiáng)化“幾”的質(zhì)地本為木,故寫成“牀”,從此變成了形聲字。《說(shuō)文解字》中“爿”字失收,不過(guò)在士部“壯”、羊部“牂”、嗇部“墻”、犬部“狀”、戈部“戕”、斤部“斨”、酉部“醬”及木部“牀”等字下皆云“爿聲”,女部“妝”下云“牀省聲”,其實(shí),諸字均為從“爿(牀)聲”。今“爿(pán)”乃“片”字的反寫,與“爿(chuáng)”字同形字,義音皆不同。后來(lái),“牀”俗書改“爿”為“廣(yǎn)”,寫作“床”,又由從木爿聲的形聲字變成從廣從木的會(huì)意字。《玉篇》:“床,俗牀字。”[11]到現(xiàn)代漢語(yǔ)階段,漢字規(guī)范化以后,“牀”作為異體字并入了“床”字。
普通話中臥具是“床”的基本義。在方言中,臥具義也是“床”相對(duì)常見(jiàn)義。“床”的坐具義在晉語(yǔ)中有所體現(xiàn),忻州話謂板凳為“床子”[12],萬(wàn)榮話特指木制低矮的小凳子為“床床”[13]。平遙話、文水話、祁縣話稱普通小凳子為“床床”,清徐話、武鄉(xiāng)話稱小板凳為“床床”,運(yùn)城話稱小板凳為“板床”,盂縣稱小板凳為“床子”。[14]晉語(yǔ)區(qū)恰恰是漢魏之際北方“胡床”傳入中原的前哨,故較多保留“床”的坐具義。“床”字原初的“幾”形器具義較多保留在閩語(yǔ)當(dāng)中,比如廣東汕頭、潮州、揭陽(yáng)、海康、中山隆都,福建莆田、仙游等地就稱“桌子”“臺(tái)子”為“床”。[15]在雷州和海口閩語(yǔ)中,“床”既可指臥具,也可指桌子。雷州話需根據(jù)上下文判斷是睡床還是桌子,海口話多將“床”寫為訓(xùn)讀字“桌”。[16]相對(duì)其他方言,閩語(yǔ)保留上古漢語(yǔ)詞匯特征較多,這是學(xué)界基本共識(shí)。
據(jù)此,我們認(rèn)為,詩(shī)中的“床”是“幾”類器具,擱置物品是其基本功能之一。雖然漢魏時(shí)坐具胡床已傳入中原,但直到唐代,“幾”類器具“床”尚未被胡床完全取代,它依然活躍在當(dāng)時(shí)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二)主人公真實(shí)“坐”法
《說(shuō)文解字》:“坐,止也。從土,從畱省。”[17]“坐”后引申為席地而坐。甲骨文“坐”本像人在席上跪跽的形狀。再?gòu)奈覈?guó)古代坐姿演變史看,古人開(kāi)始皆席地而坐,并非高坐,坐姿本為跪坐。具體坐法為:雙膝跪下著地,臀部下沉靠在腳后跟上。一開(kāi)始跪坐于普通地面,后來(lái)漸漸變成草墊、席墊之類。“胡床”傳入中原后,“胡坐”法隨之傳入,并逐漸為中原人接受,即坐在高處,垂足而坐。“從南朝開(kāi)始,我國(guó)史書上就有了‘胡坐’法的記載。但直到唐末五代,人們還有盤坐或跪坐的習(xí)慣。”[18]
主人公不是躺臥,亦非站立,而是坐,但不是在床上“胡坐”,而是在床邊跪坐或盤坐。這一坐法回答了前述第二個(gè)問(wèn)題:一方面,跪坐或盤坐時(shí)間長(zhǎng)了,主人公變得疲乏,需要臨時(shí)借助外物支撐來(lái)緩解,而身邊的“床”除擱置物品,還能借以倚靠,待體力恢復(fù)后繼續(xù)跪坐或盤坐。另一方面,當(dāng)有特殊需要時(shí),跪坐或盤坐的主人公也可以起身、站立甚至走動(dòng),這樣身體重心就會(huì)由低處轉(zhuǎn)移到高處,頭部上“舉”,“舉頭望月”;站立后也可以下蹲、落地、坐下,從而“低頭思鄉(xiāng)”。
三、詩(shī)歌文本釋讀
(一)詩(shī)歌創(chuàng)作背景
《靜夜思》真實(shí)的寫作背景對(duì)于準(zhǔn)確理解本詩(shī)的內(nèi)容影響很大,當(dāng)然也會(huì)波及其中“床”字的合理解釋和穩(wěn)妥把握。
李白一生漫游天下,年少飽覽蜀地名山大川,閱歷漸趨豐富。開(kāi)元十二年(724),24歲的李白告別家鄉(xiāng),辭親遠(yuǎn)游,東下渝州(今重慶市)。開(kāi)元十三年(725),李白離開(kāi)蜀地,正式出川,遠(yuǎn)赴吳越,欲遍游東南。開(kāi)元十四年(726)春天,26歲的李白來(lái)到會(huì)稽(今浙江紹興),在越地游覽半年之后,于同年秋天北上揚(yáng)州。因長(zhǎng)途跋涉,舟車勞頓,李白剛到揚(yáng)州就突然病倒,只得暫時(shí)滯留以調(diào)理休養(yǎng)。
盛唐時(shí)揚(yáng)州是我國(guó)東南重鎮(zhèn),其繁華不亞于京城長(zhǎng)安。李白本應(yīng)過(guò)得怡然自得,然而事實(shí)并非如此,當(dāng)時(shí)他的處境頗為尷尬。其一,李白并非富家子弟,離家長(zhǎng)期遠(yuǎn)游,沒(méi)有條件攜帶豐厚盤纏,只能“窮游”。到達(dá)揚(yáng)州之時(shí),李白已離家兩年,盤纏無(wú)法得到補(bǔ)充。就算是養(yǎng)病,他也只能寄身于簡(jiǎn)陋的小旅館。其二,此次遠(yuǎn)游是李白初次遠(yuǎn)距離出川,離別家鄉(xiāng)和親人,當(dāng)時(shí)的交通條件使得他根本無(wú)法隨時(shí)返鄉(xiāng)。他遠(yuǎn)離親人和舊友日久,“獨(dú)在異鄉(xiāng)為異客”,對(duì)家鄉(xiāng)和親友的思念與日俱增,卻無(wú)法及時(shí)得以排解。其三,初到揚(yáng)州即病倒,得不到親人照顧和親情撫慰,對(duì)于年輕的李白來(lái)說(shuō),形單影只、孤獨(dú)落寞既是他的真實(shí)處境,也是他的心境。其四,李白并非“煙花三月下?lián)P州”,而是秋意漸濃時(shí)赴揚(yáng)州。作為普通文人,李白像常人一樣,“自古逢秋悲寂寥”,感懷傷情在所難免。
可以說(shuō),初到揚(yáng)州的李白陷入思親卻無(wú)法見(jiàn)親、思鄉(xiāng)而無(wú)從歸鄉(xiāng)的無(wú)奈和矛盾中。心性敏感、閱歷尚淺,初次客居遙遠(yuǎn)異鄉(xiāng),長(zhǎng)期見(jiàn)不到家鄉(xiāng)親友,李白的鄉(xiāng)思之苦、思親之切遠(yuǎn)超一般人。他只能寄情詩(shī)酒,去化解濃濃鄉(xiāng)愁。
(二)詩(shī)歌現(xiàn)實(shí)場(chǎng)景
思念家鄉(xiāng)、親人、舊友是李白初到揚(yáng)州時(shí)的真實(shí)狀況,尤其是無(wú)奈地臥病休養(yǎng)于客舍,恰逢明月當(dāng)空照、夜靜無(wú)可依之景,這種深沉的思念不斷涌上心頭,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愈加濃烈。此時(shí)此刻,李白無(wú)法向親人、友人傾訴衷腸,加之輾轉(zhuǎn)反側(cè)難以入眠,只好“舉杯邀明月,對(duì)飲成三人”。
推測(cè)成詩(shī)時(shí)的場(chǎng)景:明月當(dāng)空,思鄉(xiāng)難耐、孤獨(dú)難眠的李白將一張“床(幾案)”從小旅館的室內(nèi)搬出,安放在室外地上,接著將酒壺和酒杯擺放在“床”上,自己獨(dú)“坐”床邊,借著月光,開(kāi)始自斟獨(dú)飲、借酒澆愁,慰藉揮之不去的苦澀鄉(xiāng)思。半醉半醒時(shí)分,李白已酒勁上頭,醉眼朦朧,明朗的月光灑落于“床”前的空地上。不經(jīng)意中,李白看到“床”前白茫茫的一片。而此時(shí)正值秋季,他不禁有些懷疑是不是秋霜降落。于是他起身站立,踮起雙腳,抬起頭來(lái),可他并未發(fā)現(xiàn)有下霜跡象,反而看到一輪明月高懸空中。李白頓悟,其實(shí)這一輪揚(yáng)州明月也正是自己家鄉(xiāng)的明月,而自己身邊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唯有這一輪明月如此熟悉、可親。思慮至此,本來(lái)已經(jīng)消解殆盡的鄉(xiāng)愁一下子又完全涌上心頭,他沮喪地低下頭,極度失落地趴在“床”邊,一下子又陷入離愁別緒當(dāng)中,許久才抬起頭來(lái)。故鄉(xiāng)、親人、舊友皆遠(yuǎn)隔千山萬(wàn)水,可以遙相思念,卻無(wú)法相見(jiàn)。李白唯有再次斟滿酒,舉起酒杯,仰起頭一飲而盡。就著這月光,李白揮筆寫下了這一首千古名詩(shī)。后來(lái),他還寫就了與《靜夜思》時(shí)間地點(diǎn)幾乎完全相同的續(xù)篇《秋夕旅懷》,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這種漂泊異鄉(xiāng)、浪跡天涯的游子的思鄉(xiāng)懷故之情。
四、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我們傾向于認(rèn)為,李白《靜夜思》中的“床”實(shí)際上是有著幾案一類家具外形的物件,是一種兼有擱置物品和臨時(shí)借以倚靠的雙重功能的置靠具。我們還認(rèn)為,李白寫就本詩(shī)之時(shí)應(yīng)該是在異地他鄉(xiāng)揚(yáng)州的一個(gè)小旅館的室外;推測(cè)當(dāng)時(shí)的場(chǎng)景應(yīng)該是備受濃濃鄉(xiāng)愁煎熬的李白在月明之夜,孤獨(dú)地席地而“坐”,倚靠在“床”前,無(wú)奈而傷感地對(duì)月當(dāng)空,舉杯邀月,解憂消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