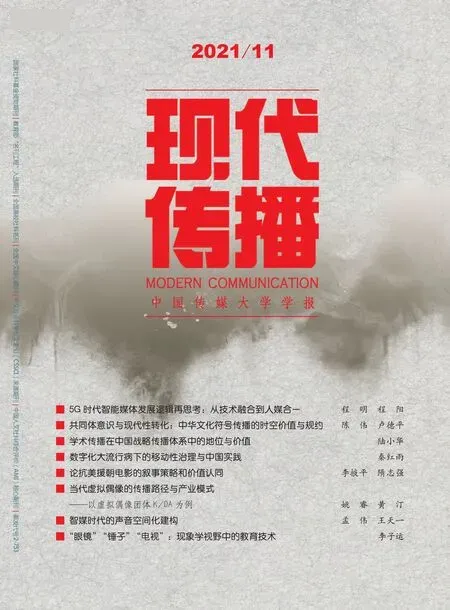皮尤研究中心涉華民調報告之內容特征與話語策略(2015—2020)*
■ 陳雅莉
一、問題緣起
美國智庫作為政策研究機構,主要通過三個程序——議程設定、引領討論、設計政策,來影響精英議程和政府決策。皮尤研究中心屬于民間智庫,“被譽為華盛頓地區三大左翼智庫之一,僅次于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①。皮尤研究中心“智庫”職能的發揮,主要是在其憑借專家團隊科學化研究與高質量分析所形成的“民調”品牌的基礎上,以發布研究報告、出版學術期刊及專著、主流媒體刊文等形式影響公共輿論,進而間接地影響政治議程和決策。
根據新葛蘭西主義的觀點,智庫可以通過發揮自身特定的功能來幫助社會精英集團強化其與不同社會群體間的“非強制性權力關系”;“政治決策體系是擁有共同的社會概念建構體系的一群行為體,借助共同的話語與概念結構表達其利益訴求與政策偏好,而智庫是其中能夠為決策議題進行話語建構的重要行為體”②。民調報告作為智庫研究報告的一種,其既是對“民意”或“事實”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又是對輿情的中介化詮釋,本質上是一種對觀念知識的再生產。“輿論調查雖然以科學性自詡,但是并不外在于偏見和成見,也要受到諸種因素的干擾。因此輿論調查只能是某種客觀現實的不完全客觀的反映,有揭示也有遮蔽,有優點也有缺陷”③。克諾特(Jack Knott)和懷爾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將知識運用的過程分為接觸(reception)、認知(cognition)、參考(reference)、努力(effort)、采用(adoption)、實施(implementation)和影響(impact)7個階段。④民調報告以“民意”和“事實”的名義,向受眾傳遞了關于觀念事實的知識,其對普通受眾的影響至少會在接觸(reception)、認知(cognition)、參考(reference)這三個階段產生作用。
在皮尤研究中心官網的相關研究成果中,其“Topic”(議題)分類下專設“China”專題,多年來持續對多類涉華議題展開了不同范圍的民意調查——這既體現了中國快速崛起背景下美國智庫對中國的關注,又可窺得美國智庫對中國凝視的視角。分析這些民調報告的議程設置、主導框架和話語策略運用,不僅可以了解美國智庫以“輿論”之名數據化呈現中國的偏向,而且可以考察美國智庫的對華態度、“我—他”關系假設等,進而幫助我們理解其建構中國形象、知識、意義的隱性邏輯。本文將以2015—2020年六年間皮尤研究中心涉中國議題的民調報告(n=38篇)為研究對象,基于文本和話語分析,剖析其內容特征與話語策略,進而對其建構中國形象和意義的隱性邏輯進行剖析。⑤
二、皮尤涉華民調報告對中國的雙面建構
綜合分析2015—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涉華民調報告發現,相關報告主要是考察近年來中國在經濟和國際影響力迅速崛起的背景下,國際社會相關國家和地區主體對中國以及對中—美相對實力的觀念認知和態度變化。
(一)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的國際經濟影響力即將趕超美國
一方面,皮尤研究中心圍繞中國經濟增長這一事實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全球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經濟影響力已經或即將趕超美國。其中,對中國經濟增長持積極態度的民眾主要包括歐洲年輕人群體、歐洲部分國家民眾、美國年輕人群體、新興市場國家民眾、拉美國家民眾、俄羅斯民眾等。比如,在2015年2月18日的報告“European millennials more likely than older generations to view China favorably”中指出,一半以上的歐洲年輕人(如西班牙年輕人中有79%,法國67%,英國65%)更傾向于認為,中國即將取代或已經取代美國在全球經濟和戰略上的超級大國地位。又如在2019年12月5日的報告“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stly welcomed in emerging markets,but neighbors wary of its influence”中指出,在新興市場國家,大部分民眾將中國經濟發展視為對本國有利的事情;與美國經濟發展相比,更多的受訪民眾傾向于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更具積極意義,持此態度較顯著的如非洲和拉美國家民眾。再如,在2020年6月10日的報告“In Taiwan and across the region,many support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both U.S.and mainland China”中亦指出,眾多臺灣地區民眾支持同時與美國和中國大陸保持更密切的經濟關系。
另一方面,皮尤相關民調報告在呈現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亦基于對中國國內以及與他國關系中消極命題的關注(議程設置和框架運用),通過凸顯相關的消極態度(如擔憂、疑慮),生產了關于中國的負面知識,同時放大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安因素。比如,在2015年2月18日的報告“European Millennials more likely than older generations to view China favorably”的開篇中即指出,隨著中國經濟顯示度的提升,受訪的大部分歐洲青年都對中國持積極態度,但是他們依然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表示不滿。又如,在2019年12月5日的報告“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stly welcomed in emerging markets,but neighbors wary of its influence”中,其明確指出,雖然中國經濟增長在新興市場很受歡迎,但是鄰國對其影響持謹慎態度;部分國家(主要是亞太地區的鄰國)擔心中國的軍力增長以及大量來自中國的投資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在這里,通過凸顯他國的疑慮,中國經濟發展的正面事實被潛移默化地導向了消極的認知管道。
(二)中國國際地位提高:中美兩國在國際受歡迎程度方面不相上下
一方面,皮尤研究中心圍繞中國國際地位提升這一事實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全球大部分受訪民眾承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已經大幅度提升:(1)中國民眾對本國國際影響力的認知日益積極:3/4的民眾認為中國目前的國際影響力大大超過了十年之前,大約一半的民眾認為中國將趕超美國。(“Americans have grown more negative toward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2017-02-10)(2)他國公眾感知到了并積極評價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比如在2017年8月23日的報告“In global popularity contest,US and China not Russia vie for first”中指出,在全球受歡迎程度方面,中國和美國獲得的好評相當,兩國一同角逐全球國家好感度排名首位。又如,在2018年10月19日的報告“5 charts on global views of China”中指出,雖然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尚未獲認可,但是受訪的25國民眾中有70%的人認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已經大幅度提升。
另一方面,皮尤相關民調報告在呈現中國國際影響力獲得國際認同的同時,亦通過關聯負面議程和框架(如“全球威脅”等)淡化了中國發展對國際社會的積極貢獻,凸顯了某些國家對中國崛起所持的局部疑慮情緒,比如,在數次的“全球威脅”態度調查中,其將“中國影響力”和“與中國的領土爭端”作為“全球威脅”選項,但最終調查結果呈現的只是個別國家的對華負面觀念,如東南亞部分國家基于不對稱均勢(Asymmetrical Balance of Power)⑥和不對稱依賴(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⑦而引發的不安,以及日本基于海疆問題而引發的對華消極態度。
(三)疫情期間美國民眾對華態度呈負面,發達國家民眾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體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皮尤民調中心也迅速開展了一系列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調查,在發布的報告中有三份與中國相關(詳見表1),其中兩份報告發布于2020年5月,集中關注了受訪美國民眾在各國及國際組織抗疫表現、中國政府信息發布的可信度以及疫情對美國、中國、歐盟國際聲譽的影響這三方面問題上的態度。報告通過突出美國民眾在疫情暴發之后對中國的消極態度(包括認為中國應對疫情的措施不利,對中國政府信息不信任等),總體上建構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已經或即將受損的印象。
第三份報告發布于2020年10月(2020年7—8月針對14個發達經濟體民眾的民調結果),集中關注了發達國家民眾對中、美兩國抗疫表現的評價:一方面,新冠疫情期間,許多發達經濟體民眾對兩國的負面態度達到或接近過去幾年來的高點;另一方面,在經濟影響力方面,大部分受訪民眾認為(包括所有受訪歐洲國家),和美國相比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體。⑧
三、2015—2020年皮尤涉華民調報告之內容特點
(一)主要議程:中國崛起、中美競爭、他國疑慮與全球威脅
2015—2020年皮尤涉華民調報告的議程主要是圍繞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兩大主題,考察國際社會相關主體對中國和對中美兩國相對實力的認知、理解和態度變化。其議程可主要歸納為:中國崛起、中美競爭、他國疑慮與全球威脅(詳見表1),具體如下:

表1 皮尤研究中心涉華議題民調報告議程、主要內容與框架綜覽(2015—2020)⑨

(續表)

(續表)

(續表)
一是中美競爭語境下,世界范圍內多國民眾對中、美兩國軟硬實力的認知和態度調查,主要涉及兩國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受歡迎程度等方面的比較。比如,“Key Takeaways on how the world views the US and China”(“影響世界各國對中美態度的關鍵要點”,2015-06-23),“Globally more name US than China as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全球公眾大多認為和中國相比美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2017-07-13),“In global popularity contest,US and China not Russia vie for first”(“在全球受歡迎程度方面,美國在和中國而非俄羅斯競爭頭名”,2017-08-23),“Negative views of both U.S.and China abound across advanced economies amid COVID-19 ”(“COVID-19疫情期間發達國家對美、中兩國的消極態度上升”,2020-10-06)。
二是集中關注某一重點區域人群(如歐洲、亞太、非洲),了解該區域內公眾對中國的認知、態度和意見。比如,“How people in Asia-Pacific view China”(“亞太地區民眾的對華態度”,2017-10-16),“Nigerians living near a major Belt and Road project grew more positive toward China after it was completed”(“居住在大型‘一帶一路’工程項目附近的尼日利亞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更積極”,2020-04-23)等。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經濟議題開始成為美國智庫關注的熱點。尤其是2018年以后,皮尤涉中國議題的多項民調都是圍繞他國民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度而展開。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民調研報告在標題設置上都不同程度地在凸顯他國民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消極認知(疑慮和不安),比如“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stly welcomed in emerging markets,but neighbors wary of its influence”(“中國經濟增長在新興市場很受歡迎,但是鄰國對其影響持謹慎態度”,2019-12-05)。
三是聚焦美國民眾對華態度的變化和疑慮。比如,“As trade tensions rise,fewer Americans see China favorably”(“由于中美貿易沖突升級,美國民眾持對華積極態度的人數減少”,2018-08-28),“U.S.views of China turn sharply negative amid trade tension”(兩國貿易關系緊張背景下,美國對華態度急轉直下”,2019-08-13),“Americans are critical of China′s handling of COVID-19,distrust information about it from Beijing”(“美國指責中國應對COVID-19疫情的措施不利,對中國政府信息不信任”,2020-05-26)。
四是關注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系,集中考察諸如俄羅斯、日本、菲律賓等國民眾對中國的態度。比如,“Russia warm to China as relations with US cool”(“俄羅斯與中美兩國的關系:對中國熱情,對美國冷漠”,2015-07-08),“Hostile neighbors:China VS Japan”(“不友好的鄰居:中國與日本”,2016-09-13),“People in Philippine still favor US over China,but gap is narrowing”(“菲律賓民眾對美態度比對華態度更積極,但是差距正在縮小”,2017-09-21)。
五是中美雙邊關系框架下,集中關注中國/美國民眾對中美關系的認知及對彼此的態度。“6 facts about Americans and Chinese see each”(“中美兩國民眾對彼此態度的六點現實”,2016-03-30),“Chinese public sees more powerful role in world,names US as top threat”(“中國公眾對中美國際地位的認知: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美國是最大威脅”,2016-10-05)。
六是設置各類“疑慮”(concerns)議程,凸顯中國國內問題,對中國發展進行“問題化”建構。這類調查報告在2015年尤其突出,主要涉及貪腐、環境、人口、住房等問題,比如,“Building outpaces population growth in many China′s urban areas”(“在中國的許多城鎮,房屋的新建速度快于人口增長”,2015-11-19),“Without one-child policy,China still might not see baby boom,gender balance”(“即使沒有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仍有可能無法出現嬰兒潮和性別比例平衡”,2015-11-20)。
七是在“全球威脅”議程之下,將涉中國的相關命題(如中國的影響力、中國的領土問題)作為選項,與氣候變化、ISIS(恐怖主義)、網絡黑客攻擊、朝鮮核危機等問題并置為“全球威脅”,進而生產關于“中國威脅”的印象和知識。近年來皮尤一直在持續開展此類調查,比如“Climate Change seen as Top Global Threat”(“氣候變化是全球最大威脅”,2015-07-14),“The world facing Trump:public sees ISIS,cyberattacks,North Korea as top threat”(“ISIS、網絡攻擊以及朝鮮是全球最大威脅”,2017-01-12),“Climate change still seen as the top global threat,but cyberattacks a rising concern”(“氣候變化仍被視為是全球最大威脅,對網絡攻擊的憂慮也在上升”,2019-02-10)。
(二)框架運用:關系框架、問題框架與競爭框架
英特曼(Robert Entman)指出:“框架是對被認知現實的某些方面的選擇,以使得這些方面在傳播文本中被凸顯,進而使得對議題的某種定義、原因解釋、道德評價以及處理方式被提升”。“對于每日發生的大量國際事件,民眾所接觸的僅僅是被媒介信息進行結構化改編的二手現實”。民調報告作為基于社會科學調查而形成的系統化數據,其框架的選擇和凸顯更容易影響受眾認知國際事件的路徑和方向,進而引導受眾對相關國家主體的知識/觀念進行“類型化”建構。分析文本發現,皮尤涉華民調報告在框架運用方面有以下特點。
首先,“中國”是在不同的“關系”框架下作為調研客體而被設置的,這些關系包括:中美關系、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如日本、俄羅斯、菲律賓等)、中美兩國與其他國家、地區的相對關系(如非洲、歐洲)、區域間關系(亞太地區)。這些關系框架的設置,側面反映了美國智庫對中國在上述諸類關系中角色日益重要這一現實的感知;其急需了解和確認該關系中各國民眾對中國國家形象、影響力的觀念認知和態度傾向,進而把握中國崛起背景下,中美兩國在國際關系中的相對軟實力的變化。
其次,“中國”作為調研客體,是被置于美國智庫所設置的“問題”“憂慮”等消極框架之下的,如美國人的對華憂慮、中國人對國內外問題的憂慮、全球主要威脅、其他國家對中國發展的憂慮。在“憂慮”框架下,某些來自問卷設計者基于觀念層面的涉及中國消極想象或假設,由于被設置為問卷選項,而無意中生產和傳播了關于中國的負面知識,進而建構或強化了被調研者關于中國的消極印象;而且,在“問題”框架下,一些問題本身因為被凸顯而被放大,另一些問題則由于被疊加而生產了關于中國“問題重重”的印象。
再次,“中國”是被置于“美—中”“中—日”“中—印”等二元對立的競爭框架之中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皮尤涉華民調中,中國多次以“挑戰”美國國際地位的“競爭者”身份出現:中美競爭領域包括經濟、國際威望、處理國際事務能力、受他國歡迎的程度等。這種中國“競爭者”的預設身份和對中美競爭關系的假設,被或直接或隱晦地植入了皮尤民調的問卷設計和結果分析之中,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美國面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零和競爭”意識(zero-sum competition),尤其是近年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經濟競爭的議題持續成為了美國智庫關心的熱點。新冠疫情的突然暴發,使得民眾對中美兩國抗疫表現的評價,及其對未來兩國的國際影響力變化的判斷成為皮尤民調中兩國新的競爭領域。
四、皮尤涉華民調報告呈現中國的話語策略
話語是一種對話關系(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話語被情境、機構和社會結構形塑,但也形塑著后者”,“它構成了情境、知識對象以及人與群體的社會認同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基于話語的建構能力,文本往往會催生一系列隱而不見的權力關系,話語“通過再現事物和確定人的位置等方式,幫助生產和再生產(比如)社會階級之間、女性和男性之間以及種族群體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并試圖將任何一方面的社會生活的相關假設(通常是虛假的)偽裝成只是常識而已”。
在國際社會中,人們對于國家主體間的關系、性質和地位的認知和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借助話語的中介化詮釋形成的。這些話語形式多樣,比如媒體內容、政府文件、專業書籍、智庫報告、學術論文,等等。話語與意識形態的相關研究指出,在對與我者不同的他者進行呈現時,其往往會通過“意識形態方陣”的方式來對意識形態圖式的群體關系范疇進行再現;意識形態圖式包含了四種互補的話語策略:即強調“我們”好的地方,淡化“我們”壞的地方,強調“他們”壞的地方,淡化“他們”好的地方。基于“意識形態圖式”這種話語元策略,話語實踐者在涉及“我們—他們”群體關系的話語實踐中,可以進一步地運用特定的子策略來完成對正面的“我們”和負面的“他們”的再現,這些子策略主要包括:(1)運用“負面話題”描述“他們”,(2)運用差異化的“描述程度”和“完整程度”呈現“我們—他們”兩者的負面特征,(3)對“他們”的相關命題運用負面的“言外之意”,(4)以消極的“命名”標識“他們”,(5)“預設”有關“他們”的負面命題為真等。基于此,下文將對皮尤研究中心涉華民調報告對“中國”進行消極呈現的話語策略進行分析。
一是“負面話題”的運用,即,“將他們描述為違背我們的規范和價值觀的任一綜合性的話語話題,如越軌、威脅、不安全、犯罪、無能等”。在皮尤涉華民調報告中,許多報告不論是在標題還是正文部分,都有使用這種話語策略的情況,標題如“Corruption,pollution,inequality are top concerns in China”(“貪腐、污染和社會公平是中國民眾最擔心的問題”,2015-09-24),“As smog hangs over Beijing,Chinese cite air pollution as major concern”(“隨著霧霾現象持續,中國人認為環境問題是最大憂慮”,2015-12-10)等。又如,在報告“How people in Asia-Pacific view China”(2017-10-16)的開篇提到:“Many in Asia-Pacific countries say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power.”(許多亞太國家的受訪民眾擔心中國正在增長的軍事實力),其將“中國的軍事實力”與“亞太民眾的憂慮”這一負面命題關聯,進而建構了“中國軍力”的消極意義。
二是負面特征在“描述層次”和“完整程度”方面的呈現差異,即,對于同樣的負面特征呈現,話語實踐者傾向于以泛泛而談(高層次的)的表達方式來描述“我們”(如美國),而以更具體(較低層次的)的方式、更準確的詞來描述“他們”(如中國);而且,“有關他們的負面特征或行動的更多細節會在描述的每個層面上被提及”。比如,有報告在描述全球受訪民眾對美國和中國的負面意見時,其涉及美國的負面輿情是以一種概括性的進行方式表述的:“在被調查的拉美、中東和北非地區,更多的民眾視美國為最大威脅”;而同時在涉及中國的負面輿情時,其相關陳述則要具體地多:“在亞太地區的情況就大大相反,受訪民眾視中國為最大威脅,其中包括40%的澳大利亞受訪者、50%的日本受訪者和62%的菲律賓受訪者;這些國家的受訪者也傾向于認為中國的軍力增長對本國而言是壞事——18個受訪國家中大約58%的民眾對中國的軍力增長持負面態度”。
三是通過“言外之意”(implication)來明確表達話語中的命題所隱含的消極意義。比如,有報告在結論部分以假設的方式明確地表達了命題本身未說明的消極意義:“基于城市化和經濟發展帶來的限制,中國許多家庭可能以后還是只愿意生一個孩子。如果這樣的話,從短期看,重男思維可能繼續導致中國的人口性別比例失衡”。
四是“命名”(domination),對“他們”命名或標識出與“我們”不同的特征。比如,在報告“People in less democratic coun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say China and Russia respect personal freedoms”(“民主程度較低國家更傾向于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尊重人權”)中,其基于美國政治文化的自我優越感,以西方民主標準對他國進行類型化命名,將那些與美國政治文化不一致且對中國具有好感的國家,表述為“less democratic”,在這一過程中,其既將西方民主默認為“共識”和“普世價值”,又同時將“less democratic”與中國關聯并進行突顯,進而生產出了關于中國的類型化印象和知識。
五是“預設”(presuppositions),即“預設那些(有關他們的負面)命題,卻并不知其為真與否”。比如,在“全球威脅”的民調議程之下,將“中國的影響力”與氣候變化、ISIS、網絡黑客攻擊、朝鮮核危機等問題并置為“全球威脅”,而對于此命題是否為真避而不談。
五、結語
綜合分析2015—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涉華民調報告可以發現,相關文本對“中國”的再現是一種基于議程設置、框架運用和話語策略而進行的雙面建構過程:其一方面通過“中國崛起”與“中美競爭”的議程,肯定了中國在經濟和國際影響力方面取得的成績;另一方面,則通過“他國疑慮”與“全球威脅”的議程以及問題框架,淡化了中國發展的積極意義,凸顯了少數國家面對中國國力增長和經濟影響力上升時的局部不安情緒。“中國形象作為一種權力話語,是西方現代性話語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皮尤民調涉華文本進行話語解讀的過程中發現,相關文本一定程度上通過“意識形態圖式”的話語元策略和相關子策略的運用,對作為意識形態群體關系中“他者”的中國進行了相對負面的詮釋。
波德里亞指出,“民意調查參照的僅僅是公眾輿論的仿象”,“即使是有關民意調查最精細的分析也總是給假設的可逆性留出了位置”;“民意調查具有一種‘真實’的策略價值”,其帶來的問題是“它在整個社會實踐范圍內建立操作仿真的問題”。民調報告雖然是對“民意”的數據化呈現,但是同時離不開議程設置和對數據結果的中介化詮釋。長期持續地基于一國的價值標準進行議程設置、框架呈現和話語建構,一定程度上容易將受眾對特定國家主體的認知維度導向某個狹窄的空間,進而導致所涉國家主體相關形象和知識的類型化。
注釋:
①③ 馬凌:《以輿論調查的名義影響輿論——皮尤研究中心的前生今世及其影響》,《新聞記者》,2011年第12期,第27、29頁。
② 忻華、楊海峰:《英國智庫對英國對華決策的影響機制——以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為例》,《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第124頁。
④ 王桂俠、萬勁波、趙蘭香:《淺析思想庫研究的理論視角與方法》,《科技促進發展》,2014年第10期,第24頁。
⑤ 研究文本來源為皮尤研究中心的英文版官網:http://www.pewresearch.org/。
⑥ Robert D.Kaplan,TheVietnamSolution:HowaFormerEnemyBecameaCrucialUSAllyinBalancingChina′sRise,The Atlantic.no.7,2012.p.57.
⑦ Christopher R.Hughes,NationalismandMultilateralisminChineseForeignPolicy:ImplicationsforSoutheastAsia,The Pacific Review,vol.18,no.1,2005.p.119.
⑧ “More see China as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 than the U.S.;In every European country surveyed,a plurality or majority say China is the top economy in the world”.出自Laura Silver、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Negative views of both U.S.and China abound across advanced economies amid COVID-19,(皮尤民調報告),http://www.pewresearch.org/,2020-10-06.
⑨ 資料來源: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英文版網公布的涉“China”主題的民調報告內容整理,http://www.pewresearch.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