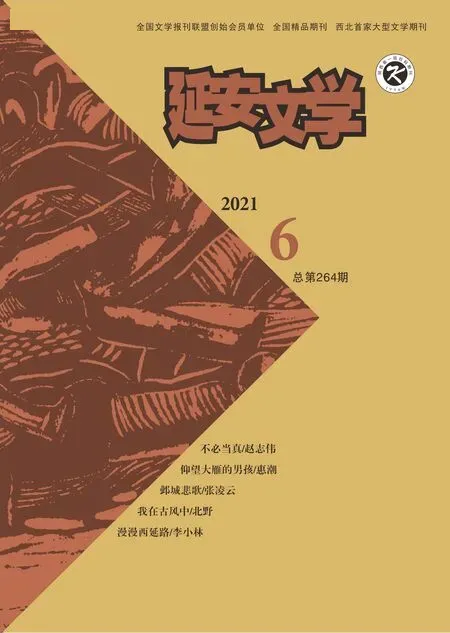講故事的人,與我們日漸疏遠
——狄馬《歌聲響處是吾鄉》讀后
惠雁冰
在閱讀尼古拉?列斯科夫的作品時,本雅明曾言:“在當下,講故事的人,已變成了一種與我們日漸疏遠的存在”,能夠把故事講好者及愿意聽故事者更是稀少,即使開講也容易陷入“四座尷尬”的情狀。本雅明的困惑,當然是出于現代工業文明整體興起后傳統藝術形態急速凋敝的現實,體現出對“現代”這一時間維度、現代性這一精神品格、現代化這一物理性景觀的深沉反思,內含著與傳統藝術光暈被動惜別的特殊況味。其實,這種反思也同樣滲透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文化演進的歷史進程中。尤其在新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傳統民間藝術如何存在與怎樣保護不但成為文化熱點,也成為時代難題,由此引發了知識界人士集體性的呼告與守望行動,并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形態、不同民間藝術中進行了相應的理論探索與藝術實踐,為民間藝術的復歸、重釋與傳承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其中,在陜北民間文化的行吟者行列中,狄馬顯然是不容忽略的一位。其新著《歌聲響處是吾鄉》就是在文化現代性反思的前提下,對陜北歷史文化飽含鋒銳的鉤沉與新掘,同時又伴隨著一種無言無解的憂思。說其鋒銳,是指他在言說陜北歷史文化時不是線性梳理歷史的頁面,而是聚焦最能表征地域性格、地域精神和地域血性的歷史片段,以此來打通地域、歷史、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這種言說方式看起來是散點透視的,卻有一種直抵文化內里的光芒。說其新掘,是指他在解讀陜北民歌、陜北說書、陜北方言、陜北藝人時,始終灌注著真切的生活體驗與深重的悲憫情懷。其中,真切的生活體驗讓民間藝術從櫥窗或舞臺真正落回它所依存的煙火人間,還原了藝術發生的原始場域;而深重的悲憫情懷則讓民間藝術背后的鮮活個體一躍而出,從而使紙面上、口頭上的藝術具有了生命的質感。歸結起來,其實彰顯的還是以“人”為中心的意識,為底層生命立傳的意識,為民間藝術正名的意識。正是這種強烈的人的意識的始終在場,陜北民間藝術的汁液開始涌動,陜北的苦難歷史浮現出了英氣勃勃的面影。說其憂思,是指他在面對市場化背景下民間藝術影響力日益縮微的狀況所發出的陣陣感慨,又是指他對非遺保護過程中民間藝術漸漸滑入商業性演出現象的種種反思。這副愁容如秋露一樣滲滿這部書稿的邊邊角角,映射出一個陜北民間藝術守夜人的復雜情感。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與他筆下的韓起祥、張俊功、賀四一樣,狄馬也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在經驗和交流中講黃土地上的歷史文化,講底層藝人的生命故事,講陜北民間藝術不被年輕人認同的窘狀,也講他從中看到的某種不太明朗的希望。盡管他以特定的視角來呈現自己的觀感與迷茫,也以一種有選擇性的敘事手段來刻繪這個時代的表情,但通過這部書所反映出來的“陜北”無疑是有地域骨血的陜北,也是有生命體溫的陜北。
在閱讀的過程中,狄馬的部分論述也引發了我的一些思考。如大傳統和小傳統的關系問題。狄馬對于小傳統的解讀甚為精準,用“靜水深流”來指稱,并言“大傳統不大,小傳統不小”。就我看來,所謂的“小傳統”是指一種相對封閉的自足性的文化結構,用威廉姆斯的話來說,則是特定歷史場景下特定族群的一種整體性的生活方式。置于陜北,就是與深溝大山、苦難生活相關聯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地理樣態,如忙時田頭唱曲解心焦,閑時扭秧歌鬧社火,晚時圍坐炕頭聽說書,喜時嗩吶橫吹酒曲聲起。至于過年過節、生老病死,更有一定的文化儀式。正因為其覆蓋了這塊土地上個體生命延續與終止的全程,并作為一種重復的經驗不斷在代際之間伸延,這才體現出文化本身的世俗性,也坐實了小傳統之“大”。但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關系其實又并不清晰。盡管大傳統在封閉的區域影響不大,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何況小傳統中部分環節對大傳統也有呼應之處;盡管大傳統以規訓話語為主,似乎難以涵蓋小傳統注重個體生命張揚的特征,但小傳統中又同時存在著對個體生命張揚限度的規訓與勸誡。這種同時在場的抑揚態度,又足以把小傳統視為區域化的大傳統。這樣來看,作為自然分割的地理有邊界,作為文化結構體的大小傳統之間并無嚴格的邊界。
又如如何看待民間藝術的生態問題。面對舞臺上日益走紅的陜北民歌,狄馬敏銳指出“一首歌的旋律可以搬上舞臺,生態怎么搬上舞臺?”此言我深表認同。但我由此想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理性看待這種商業化演出爆熱、民間生活遇冷的現象。正如狄馬一再強調的,陜北民間藝術依存于傳統農業時代,是傳統農業時代的文化符碼。現在這個時代早已一去不歸,舞臺上不斷翻唱的民歌只是一種旋律的再現,至于民歌的原始生態及其中關聯的個體生命意識早已消亡,何來原生態之說?所謂的原生態民歌不過是對某種未受現代音樂體制明顯規訓的原生嗓音、歌詞、情感的綜合表現而已。這樣的詰問扣準了本質,的確值得反思。不過,現代社會的發展已如東流之水,不可逆回,要讓陜北再次復歸到那個封閉艱困的狀態更屬枉然。換句話說,我們也不能單單認為只有讓陜北孤絕于現代社會之外,重返“七筆勾”的狀態,陜北民歌才能真正回到寄生的土壤,并保留其鮮活的原質。相反,在順應時代變遷的前提下,正視當下陜北民間藝術的生路問題,才是較為理性的做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以為以舞臺表演來顯現陜北民歌的存在,也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盡管舞臺的間隔使講故事的人與受眾之間缺少一種經驗的傳遞與交流,甚至“觀眾也成為一位心不在焉的主考官”,但起碼能激活陜北民歌的生命力,也能使之保持與當代生活的聯系,還能通過廣泛的流布影響與培養一代新人。本雅明曾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痛感電影、照相藝術對傳統藝術的斷裂性影響,但又不能不接受現代藝術對傳統藝術的徹底覆蓋及技術性革新這一嚴峻事實。那么,在針對陜北民歌、陜北說書的現狀時,我們是否也應該在有本雅明這種現代性憂思的同時,對傳統藝術光暈的消散持一種更為理性的態度?
最后一個問題涉及陜北民間藝術的出路問題。記得上世紀80年代,《人民戲劇》雜志曾提出“京劇向何處去”的話題,一時爭鳴不斷。當時,劉厚生提出了“四條路”的論斷,即“第一條路是進‘八寶山’,就是競爭不過別的藝術形式,衰亡了……第二條路,往博物館去,就是類似日本歌舞伎的路……第三條路,向自由市場去,國家不管,愛怎么演就怎么演……第四條路,經過我們大力革新,大力推陳出新,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走上一條適應現代生活的新路”。如果將這一答案推及今天陜北民間藝術的話,前三條道路無疑是不可取的,只有第四條才是真正保護、發展陜北民間藝術的必由之路。但怎樣保護,誰來保護,保護什么,保護得怎么樣,依舊是個問題,我想這也是包括狄馬在內的所有熱愛陜北民間藝術、并期望它能一直伴隨自己心史、心路的所有陜北人共同關注的問題。對此,我無力來解答,只能寄希望于國家層面的相關政策及非遺保護者的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