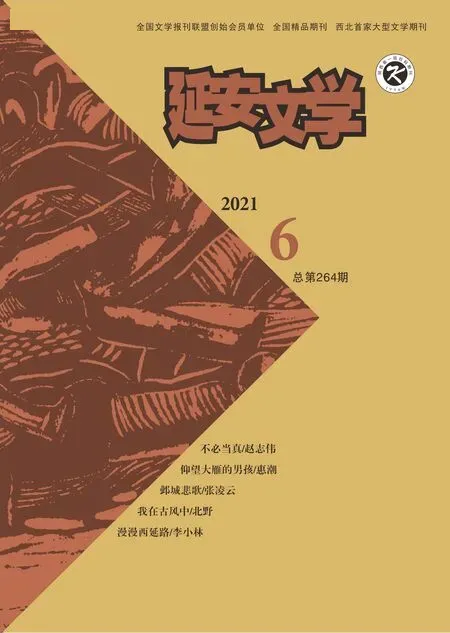發(fā)現(xiàn)陜北,發(fā)現(xiàn)不一樣的中國(guó)
——狄馬新著《歌聲響處是吾鄉(xiāng)》讀后
王天定
當(dāng)今文壇,狄馬以雜文馳名;在大江南北的朋友中,狄馬以唱歌著名。鄢烈山老師有一篇文章,談到有次在查干湖畔的篝火晚會(huì)上聽(tīng)“西安來(lái)的小伙子”狄馬唱歌,雄渾、蒼涼的歌聲讓聽(tīng)者如癡如醉。不過(guò),我聽(tīng)狄馬唱歌,基本都是在飯局酒桌上,外地有朋友來(lái)西安,聚餐時(shí)只要狄馬在,一定是舉座皆歡,也就是說(shuō),在西安待客,狄馬才是最美味的一道菜。也正因?yàn)槿绱耍谱莱闪说荫R演藝生涯的主要舞臺(tái)。狄馬端起酒杯,猶如歌手拿起了話筒,他的習(xí)慣是先講后唱,連唱帶講,從歌詞大意、逸聞趣事到曲調(diào)歌詞的演化歷程,詼諧風(fēng)趣的三言兩語(yǔ),是他歌聲最和諧的伴奏。狄馬唱得好,但論唱功,至少他趕不上西北歌王王向榮,但是,但論對(duì)陜北民歌的理解,恐怕還沒(méi)有任何一個(gè)陜北歌手比他更好,所以,在演藝界,狄馬邊說(shuō)邊唱,說(shuō)得比唱得好,可謂別具一格。我每次聽(tīng)狄馬唱歌,被歌聲打動(dòng),也總被他要言不煩的講解吸引,看最新出版的《歌聲響處是吾鄉(xiāng)》,我欣喜地發(fā)現(xiàn),那些酒桌上的奇言妙語(yǔ),都已變成見(jiàn)解不凡20多篇錦繡華章,讀這本書(shū),你會(huì)發(fā)現(xiàn),在作家、歌手之外,還有一個(gè)作為文化學(xué)者的狄馬。
民歌里的野性
陜北是紅色圣地,無(wú)人不知,無(wú)人不曉。強(qiáng)調(diào)陜北的紅色與革命元素,當(dāng)然是非常正確的,但是,長(zhǎng)此以往,卻有意無(wú)意間忽略了陜北的豐富性。陜北是紅色,也是多彩的,它是革命的,也是多元的。狄馬《歌聲響處是吾鄉(xiāng)》的價(jià)值,恰恰是能夠讓我們看到一個(gè)不一樣的陜北。有一首陜北民歌,叫《老祖先留下個(gè)人愛(ài)人》,歌詞大意是這樣的:
六月的日頭臘月的風(fēng),
老祖先留下個(gè)人愛(ài)人。
天上的黑云套白云,
世上的男人愛(ài)女人。
天上星星排隊(duì)隊(duì),
人人都有個(gè)干妹妹。
百靈鳥(niǎo)過(guò)河沉不了底,
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寧讓皇上的江山亂,
不叫咱二人關(guān)系斷。
這首歌,狄馬唱來(lái)如泣如訴,是多年來(lái)西安朋友聚會(huì)時(shí)的保留節(jié)目。表白男女情愛(ài)大膽直接,這是人所共知的陜北民歌特征。但是,即使如此,細(xì)品這首歌詞,仍讓人吃驚。比如最后幾句“百靈鳥(niǎo)過(guò)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寧讓皇上的江山亂,不叫咱二人關(guān)系斷。”直接挑戰(zhàn)傳統(tǒng)儒家最核心的價(jià)值觀,在衛(wèi)道士眼里,這是最典型的不忠不孝,狄馬說(shuō),他曾經(jīng)和陳忠實(shí)先生一起探討過(guò)這幾句歌詞,陳忠實(shí)聽(tīng)了也很吃驚,他說(shuō)關(guān)中一帶最流行的秦腔中,絕對(duì)不可能出現(xiàn)類似這樣的表述。從地理位置上看,陜北與關(guān)中山水相連,陜北最北端與關(guān)中平原,也就數(shù)百里之遙,但是,從歷史上看,陜北處于農(nóng)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結(jié)合部,特殊的自然環(huán)境與歷史境遇,也阻擋了儒家文化的擴(kuò)張,雖然這里長(zhǎng)年征戰(zhàn),加之地瘠民貧,百姓生活悲苦,但是,由于儒家文化的侵蝕力量減弱,為人性的舒展留了一點(diǎn)空間,讓這片土地在最貧瘠的時(shí)代培育了生機(jī)勃勃的藝術(shù)之花。陜北民歌信天游早已火遍大江南北,但陜北的地方藝術(shù),民歌只是一種而已,還有比如像陜北說(shuō)書(shū)、腰鼓、陜北嗩吶、剪紙繪畫(huà),等等,他們都不只是作為一個(gè)概念存在于歷史文獻(xiàn)中,而是至今在陜北民間,都有相當(dāng)?shù)纳Γ酥列纬梢粋€(gè)文化共同體,這在中國(guó)北方,至少是一種比較獨(dú)特的現(xiàn)象。狄馬這些年來(lái)致力于挖掘、記錄、研究陜北文化,正是用現(xiàn)代的眼光與方法,揭示了陜北各類風(fēng)俗與藝術(shù)中潛藏的文化密碼。細(xì)讀《歌聲響處是吾鄉(xiāng)》的每篇文章,你都能感受到他的努力和不同凡響的見(jiàn)解。
漢族人不善歌舞嗎?
馬茹則圪垯,這個(gè)聽(tīng)上去有點(diǎn)怪怪的名字,是陜北一個(gè)普通的村莊。西部歌王王向榮就出生在這里。為了了解王向榮從藝道路,狄馬和朋友曾去這里尋訪。在村口遇見(jiàn)一個(gè)準(zhǔn)備外出拾柴禾的76歲老婆婆,他們和老婆婆聊王向榮,問(wèn)她會(huì)不會(huì)唱歌,老婆婆剛開(kāi)始還有點(diǎn)不好意思,但架不住他們?cè)偃?qǐng)求,76歲的老人家開(kāi)口就唱:
一對(duì)對(duì)鴛鴦一對(duì)對(duì)鵝,
一對(duì)對(duì)毛眼眼瞭哥哥。
哥哥吃煙我點(diǎn)火,
哪噠噠把哥哥難為過(guò)?
曠野之中,這種質(zhì)樸的歌聲,自有特別的驚艷動(dòng)人之處。狄馬在文中感慨:“路上行走的一個(gè)普通老婆婆,隨便拉出來(lái),都會(huì)唱兩句,在這個(gè)普通老人身上,隱藏著王向榮成長(zhǎng)的所有秘密。”
這種秘密,也隱藏在一個(gè)叫劉席強(qiáng)的鄉(xiāng)村老漢身上,這老漢家境極貧,除幾口酸菜缸別無(wú)他物,但老人一生弦歌不輟,趕著驢往地里送糞,歌唱不完,糞不從驢身上卸下來(lái)。狄馬說(shuō),在這個(gè)老漢看來(lái),唱歌和送糞,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價(jià)值,如果不把歌唱完,糞送到地里就沒(méi)啥意義。
讀這些故事,總給我很多觸動(dòng),我常在想,在中國(guó)當(dāng)下,說(shuō)到能歌善舞,無(wú)論是大眾媒體還是人們?nèi)粘UJ(rèn)知中,都把它視為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符號(hào)。而對(duì)廣大漢族人來(lái)說(shuō),歌舞似乎只能是個(gè)別有受到訓(xùn)練的演員臺(tái)上表演的事情。
我曾在家中和長(zhǎng)輩談起這個(gè)問(wèn)題,但是,長(zhǎng)輩們都說(shuō),他們小時(shí)候,也就是民國(guó)三四十年代,至少我老家隴中一帶,尤其麥黃六月,滿川都是此起彼伏的歌聲,而我也記得小時(shí)候和奶奶在一起,奶奶在家干活時(shí),也一直歌聲不斷,只不過(guò)是低聲吟唱。
我也記得大約是70年代,村里來(lái)了一戶從山上搬遷下來(lái)的人家,他們家的老二,是個(gè)高個(gè)漢子,無(wú)論走路還是干活,都歌聲不斷,那高亢宏亮的聲音,至今記憶猶新,唱什么,我聽(tīng)不清,但肯定不是當(dāng)時(shí)的紅歌。不過(guò),這可能是他們?cè)谏嚼镳B(yǎng)成的習(xí)慣,下山后的生產(chǎn)生活,對(duì)他們可能是無(wú)形的規(guī)訓(xùn),慢慢地,他們的歌聲也消失了。
那么,什么時(shí)候起,我們的民族性格中慢慢失去了奔放熱烈的一面,我們失去了能歌善舞的能力,甚至把日常生活中的歌舞看成不正經(jīng)、不莊重?而我們常見(jiàn)到底層的人民,總是木訥的、沉默的,甚至眼神都是空洞的,這種變遷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狄馬說(shuō),陜北民歌,是陜北人生命中的鹽。看到這個(gè)比喻,我突然想起,我小時(shí)候我曾祖母常說(shuō)一句話:“男娃吃鹽重,‘打錘’硬”,“打錘”在我們隴中方言中,就是打架的意思,吃鹽重,意思就是愛(ài)吃鹽,吃鹽多。這個(gè)俗語(yǔ),意思是鹽能給人力量,這也是最樸素的生活常識(shí)。
我由此想,包括陜北民歌在內(nèi)的各類張揚(yáng)人性的藝術(shù),給人宣泄,也給人撫慰療傷,也會(huì)給人力量,猶如鹽能給人力量一樣。苦難中,他們?nèi)棠汀⒈瘒@、哭喊,在忍無(wú)可忍時(shí),敢愛(ài)敢恨的陜北人勇于選擇抗?fàn)帲儽睔v史上多英雄豪杰,后來(lái)能成為哺育中共革命的搖籃,或許也有文化上的原因吧。
為陜北民歌寫(xiě)書(shū)
從上個(gè)世紀(jì)30年代中后期開(kāi)始,隨著紅軍進(jìn)駐陜北,革命文藝就開(kāi)始了對(duì)陜北民間藝術(shù)的征用。民間藝術(shù)成為革命文藝的過(guò)程中,產(chǎn)生了像《東方紅》《擁軍花鼓》《繡金匾》、新秧歌運(yùn)動(dòng)等代表性作品,擴(kuò)大了陜北民間藝術(shù)形式的影響力,也讓一些民間藝術(shù)如盲人說(shuō)書(shū)匠韓起祥等因熱情謳歌新人新事而受到領(lǐng)袖接見(jiàn),有了獲選全國(guó)政協(xié)委員的榮耀。
但是,真正的陜北民間藝術(shù),其生命之源在壟畝之間,坑頭之上;而從歷史上看,陜北民間藝人都是最普通的販夫走卒,他們中的許多甚至肢殘目盲,走村串巷,靠說(shuō)書(shū)賣唱為生,但也正是他們成就了亂世中民間藝術(shù)的繁榮。
韓起祥的人生,只是他們中的傳奇,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的名字,并不見(jiàn)載于官方的正史典籍中。狄馬這些年致力于史料中搜尋、田野中尋訪,努力追尋那些被正史遺忘的陜北藝人。狄馬寫(xiě)出他們的故事,許多都極為生動(dòng),比如寫(xiě)盲藝人封樹(shù)生被選中給電影《巍巍昆侖》中的韓書(shū)匠配音的故事:
韓書(shū)匠在電影里共說(shuō)了四分鐘,為這四分鐘,封樹(shù)生整整忙活了兩個(gè)月。人家把他拉到延安賓館,一字一字摳,一句一句練。每天給12元,天天能吃肉,能洗熱水澡,就是有時(shí)水太燙,他看不見(jiàn),不會(huì)調(diào),喊劇組人幫忙,人家又聽(tīng)不懂他的子洲方言,就對(duì)他說(shuō):“老人家,你唱吧,一唱我們就懂了。”于是他就在澡堂里用陜北說(shuō)書(shū)的調(diào)子“裸唱”起來(lái):“今晚上我準(zhǔn)備去洗澡,澡堂的水有點(diǎn)燒,我少眼無(wú)目不會(huì)調(diào),同志們過(guò)來(lái)行行好。”
我讀到這里,先是笑了,但笑過(guò)就覺(jué)得心酸,想掉眼淚。生活中常人易如反掌的事,在他們千難萬(wàn)難,而學(xué)藝賣藝中的千難萬(wàn)難,更難與外人道。
狄馬在書(shū)的后記中說(shuō):“沒(méi)有這些名字,一代一代的陜北人當(dāng)然也春種秋收,生兒育女,但有了這些名字,干旱而苦焦的高原變得靈氣十足,神氣十足。”
《歌聲響處是吾鄉(xiāng)》一書(shū)中介紹到的人物,有20多人,這其中有大家耳熟能詳?shù)模热珀儽备柰跬跸驑s,但狄馬筆下更多的,則是像一代說(shuō)書(shū)大師韓起祥、張俊功,傘頭苗永敘、歌手常雙高、說(shuō)書(shū)藝人封樹(shù)生等。這些人的名字,正如狄馬書(shū)中所說(shuō),他們更多地“活在窮人的口頭上,活在孤兒寡母的夢(mèng)中”。
如今,《歌聲響處是吾鄉(xiāng)》出版了,這些名字,將會(huì)活在狄馬深情的文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