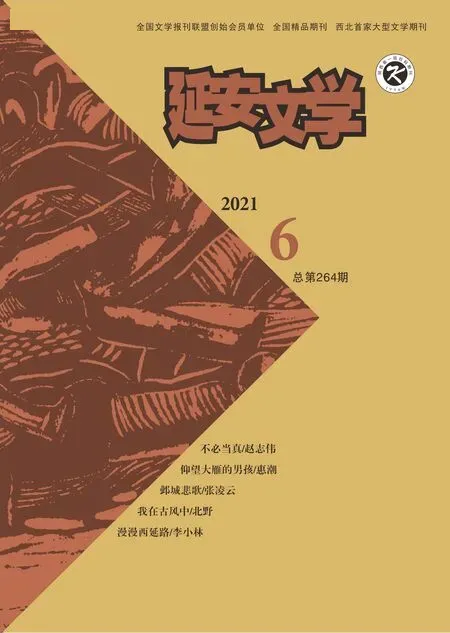陜北黨史回憶錄(連載五)
趙通儒 遺著
魏建國 整理
自 傳
1951年
編者注:按子長市檔案館保存的手稿刊印。時間是編者判定的。
一、自1935年以來,并不敢以黨員自居
就是說,自己并沒認為自己是個共產黨員。自己只覺得是一個陜北安定人,在苛捐雜稅及日本節節進攻華北、蔣介石“圍剿”西北紅軍的情況下,失學失業的青年,在投奔共產黨而又遭受打擊后,以一己之力,在黨的領導下,同陜北人共同度過苦難日子,求個生存之計。一直到今天,不知自己腦子和行動上都未覺得自己是在為共產主義或共產黨。只覺得自己連個個人主義都不夠個聰明、能干的個人主義者。聰明、能干的個人主義者,現在都成了民主人士。
我這國民黨不要、共產黨不要、民主人士不是的人,現在生存有何保障?自己有何把握?誰能替我將苦我者解除?誰能主持我或為我向苦我者爭斗?處在如此境地之我,尚何暇去當個共產黨呢?
至于為什么1935年到1946年要跟隨共產黨呢?原因很簡單:1927年夏,我當了兩個月安定縣教育局長,沒有拿一文薪金,在病中的藥錢還是家中開銷的。1930年到1934年,每年走北平用安定人民的三百元,家中的一百元,五年之中欠下安定及家中父母血汗錢一千數百元,在內戰和抗戰期間既無力還錢,只有盡點心力而已。1949年以來,又為什么要跟共產黨呢?榆林不讓住了,以武裝和馬匹遣送,不走不行。見了共產黨,只能跟著,等待復原,解除榆林加害于我的東西。等待清算誰送我去榆林,榆林苦害我的苦害如何解除。
聽說共產黨解除了許多種人民的苦難,我的苦難,也解除吧!
為什么自1935年以來自己不以共產黨自居呢?原因很簡單,1930年恢復陜北黨和華北黨的關系后,華北黨的一些負責人忽視西北的革命歷史與傳統。我從1935年被書面通知留黨察看、口頭通知開除黨籍,自己在接到通知爭到蘇維埃公民權仍保留時起,直至今日,無論從思想或行為方面,沒有把自己當作一位共產黨員。
一切行為,以這樣為標準:不犯法,合情理,先公后私。從這樣的標準,不放棄私人利益。這樣的思想,又以這樣的生活背景做自己一切包袱和一切抱負的出發點。就是說,我自己雖是一位學生,但父親是少年脫離家庭,赤手空拳,自力生產,從為舊社會所看不起的屠夫、小木匠、熬糖、推粉、喂豬、宰豬羊、給人做飯、開小飯館,母親一生做豆腐、生豆芽、做針線、起雞叫、睡半夜、苦磨苦掙,在家鄉是出了名的受苦過光景出身的,他們夫婦從貧無立錐,至土地革命時,雖有了住所,但欠別人高利貸千余元,(合今日約三千多萬元)。自己從小學到大學,都是窮讀書,小學學費是自己的勞力及販賣小食品所得,中學是人民血汗的津貼占一半,大學是人民血汗占五分之四的公費。因此,雖然自己沒有到上海工廠做過工,兩代赤手空拳,在一切困難中生活和長大起來,雖不無產階級,總不能不算貧苦人群中的一分子。這樣的成分包袱和抱負是我的第一個一切錯誤思想行為來源。
第二個包袱和抱負的錯誤根源便是,自己從小學時代便反不稱職校長、教員以至貪官污吏,那是既沒黨的領導,又沒團的領導。從小學時代便結交下許多朋友、同學,也和下許多親戚、鄰居、同鄉,在任何條件下,常能得到這些人的支持與援助。自參加團與黨以后,在陜北的黨與團內是比較最早最老的一個,而且是國民黨在西北——陜甘寧三省省黨部發起人之一,孫中山1924年改組后之國民黨之義務黨員,我任國民黨陜北特別黨部常委,蔣介石尚未任北伐軍總司令,是孫中山北上召開國民會議的支持人之一。對中共黨與團的家當最清楚,從四師學生黨員及教員中的錯誤斗起,一直經過陳獨秀、李立三等,算起一些總路線錯誤時自己還不在他們之列。舊中國的西北的人情風俗懂一點,在大革命時,也曾進行過武裝力量的培養與抓取,也曾培養工農干部去擔任陜西省農協主席,武漢政府召集的全國農籌委常委,也曾將大批青年黨團員送給黃埔、北伐軍、上海大學、國民一、二、三軍,也曾親到綏德、安定農村去搞農民運動,公審土豪劣紳及反對貪官污吏。
在白色恐怖之后,抱病、只身、借債進行恢復陜北工作,當時既未得到省委或中央的任何指示。以后別人的來陜北,一切經費關系都經過我供給,那時還正是敵人通知延安駐軍以及安定豪紳緝捕和陷害我的時候。而且在清澗起義和后九天起義中也曾盡了我能盡的力量和領導布置。
在陜北黨與陜西省委失卻關系、陜北特委出現瓦解狀態下,1930年經過特委軍委常委緊急特別會議,負命去北京,恢復北方局與陜北的直接關系。
在北平五年,和蔣介石的不抗日,和黨內的盲動、幼稚,在監獄中不屈,營救在獄同志,挽救一些幼稚、盲動、錯誤的同志。“9?18”后的“請愿”、“臥軌”和察哈爾抗日,自己的正確意見均遭受抵抗。
為了挽救華北黨和西北黨的危機,在抗日同盟軍失敗之后和謝子長同志檢討“為什么還有個老謝繳老劉的槍呢?”謝說:“未繳老劉的,為改造部隊,為軍紀問題。”我說:“太不策略,敵友我界限未清,心是好的,方法錯了。”謝說:“對!為了這走了一次上海,問題還未清楚。這下,清楚了。”接著檢討全國形勢:“東北已被日本占了,華北這一下又失敗了,西北是空子,這次回去好好搞一下。”這樣,鼓勵了謝之返回西北。
為了挽救“圍剿”西北,接濟華北黨渡過困難,帶著“土地革命與抗日結合起來”的指示和給華北的北方局送人送錢的任務,通過“封鎖”與“圍剿”碉堡線,冒生命之險,回西北蘇區,以生死性命去完成救助華北的任務,結果換得了“開除黨籍”。
陜北六年,人家罵我“黨在老趙口袋里裝著,走到哪里,哪里便是縣委、特委”;一切失敗后無方向無辦法了的同志又來找我;一切受反革命殘害了的家屬也找我。北平五年,一切失敗后找不到關系、辦法、生活無法的也找我。
假文憑給國民黨軍事、文化學校送了一些學生,交朋友交到留外國的學生和空軍中,麻麻糊糊了五年,自己的身體健康和流鼻血也治了。自問良心,別人拿盧布、拿黨的津貼過活的人,好的堅持下來了,不好的不只自己叛黨而且大加破壞革命,自己所幸,既未用過盧布,又未用過黨的錢,以安定人的血汗支持了自己和一些同志,這筆債自己還不起,也只有厚顏拖著過去。
到蘇區后為延長問題被教條主義者目為為蔣介石辦事。自以為1934年末及1935年提出“南方是蔣介石圍剿紅軍、蘇區、共產黨,西北將是共產黨、紅軍、蘇區圍剿刮民黨。南方是他們逼得我們連鹽都吃不上,西北將是我們逼得他們沒糧、沒炭、沒水的局面”,“陜甘寧晉綏”,“騎黃河,打游擊”……等方針、政策以及烈士紀念碑、制度、作風。
如果不是陜甘區黨委不批準而且責斥的話,安定在1927年農歷六月初即公歷7月初,便在繼綏德公審馬團總之后,用謝子長的軍事和全縣農協代表大會舉行軍民武裝起義了。已經將全縣五個最大惡霸和劣紳關起三個,兩個在群眾監視下,縣長在軍隊軟禁下。這個起義是準備實際回答南方的“4?12”和北京的“4?28”的。這個起義要比“南昌暴動”早二十多天或一個月,比“清澗起義”要早兩個多三個月。要不是這個起義被阻止,我也不會幾乎病死,也不會去汾陽治病,也不會趕去參加清澗起義遲了一日夜。
當1926年“三月二十日廣州中山艦事件”的黨內秘密文件傳到綏德之時,黨內對當時的“國民革命”已有三種態度:一種是聽之任之,一種是上級文件怎說怎辦,一種是不能那樣,應早自為計與備。陜北及西北黨之未像全國各地黨那樣失敗,是這第三種路線第三種人的支持。這一精神,這一傳統的人,自己也不算其外之人。
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上,在利用新軍閥混戰問題上,在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問題上,在對蔣介石刮民黨統治必須進行“造反”問題上,在發動武裝斗爭、群眾斗爭及在敵人區域敵人統治下必須實行“賊爺爺保賊老子的”共產黨員互相包庇、長期埋伏、與武裝斗爭配合的方針策略上,在白色恐怖后仍應有計劃向全國各個角落中打入活動……多是單身匹馬首先提出與工作的。
在右傾、盲動路線下,保持了自己,也保存了幾位同志,可惜是當時條件,自己未能暢所欲為。中央書記從陳獨秀頂戴過瞿秋白、向忠發、米夫……直至有了瓦窯堡,招待了北上的中央,等至延安將毛主席的領導建立與鞏固起來,隨波逐流,也算的確含辛茹苦,眼淚不知向人前、背后、肚里流了多少。就只一點,沒有走二萬五千里,沒有打夠百戰百勝。這些包袱,阻礙了自己。1943年以前,常覺得黨內有“張士貴”問題,以后又以為不只“張士貴”問題。
敵人監獄中,萬念俱空。
回來后,又覺得對別人倒還可以,對自己又不只一次地出現了“敵我不分”,甚至“表面是好心好意,實際卻使我萬分為難甚至痛苦、傷心。”最基本的問題是敵人加于我的暗害,無人為我解除,卻當我要治病及解除困難的時候,遇到種種阻撓和為難。人們覺得我這是有失原則的牢騷話。然而,有什么辦法讓我不說這樣的事實呢?在1946年以前,我正是年富力壯、人強心盛的時候,卻將我當作不健康的人看待。到現在,我被敵人暗害到體力常感疲倦,智力受到暗害不能自由思索,不能思謀與應付工作之時,卻要求我成個共產黨員。敵人的暗害,尚未解除,明里又拿一些對待牛馬的羈絆來苛求,表面看來,的確像似一些原則、政策,實際作用,卻與敵人之暗害,內外互應,兩下夾攻,其道路是一致逼人往死。
回來快三年了,敵人加害于我者,如何解除?誰來解除?沒有一位英雄好漢或能人,擔負這點一舉手之勞的小事。要求我這樣、那樣的卻紛至沓來,甚至要求我像石頭一樣給他做一塊墊腳石。其實,我何嘗不愿給人做墊腳石,而是敵人加于石上的損害先如何解除呢?可又沒人理了。別說人,當一回牲口,也該看看這牲口被別人加上了什么,我先給如何解除。現在,還不見這樣一位。黨要求我右傾給他們,專門去了一次,可又不要,嫌“黨父”名詞太右了,不能接受。共產黨我是化外之人,也可以說我這,說我那,現在我到過的一些地方和見過的人,除了死了的,活的人都在,何嘗不可以一一對證?自己思想上從1935年自己就沒有個黨的觀念,又一再經王永清開除——去榆林由他開除,到解放區又經他們開除,如何還能算個黨員呢?
至于身上被人家加上什么,自己無法解除,別人無能為力,拼此一身,什么地方什么人也沾染沾染,求個水落石出,有何不可?除此之外,有何辦法呢?最使我為難的是一些好心人,在具體問題上,對我,實使我感覺這些人明或暗,或實際作用與榆林曾經敵對我的人很難分別。這些人的心可能是好的,其作用,的確頗令人不敢恭維。
至于這十多年,存在的一些問題,有的已經解決,有的現在可又發生。從1931年起,敵區敵人天天在講“朱不死,毛不拔,天下不得太平。”到了1935年至1943年親與毛朱接觸后,怎么黨內對這個問題總是搖擺不定呢?到1943年至七大后,正式宣布毛澤東為全國全黨領袖,毛澤東思想為黨的領導思想,認為這下問題咋解決了,事情好辦了。因此,榆林在武裝脅迫下公開答復他們說:“1935年以前未將中共消滅,1944年以后,更不可能了,因為中共思想統一了,領導確定了,有了明確易行的方針,也有了多才多能的人……”。
回來之后,又有一些事情,令人很疑惑。1945年已經聽到有毛澤東主義之說,也在蒙地向干部和群眾宣傳過,敵區又有敵人在解放戰爭以“反毛澤東主義”為號召,并將毛朱罵成這樣那樣。回來之后,卻怎么又不見講毛澤東主義,而講思想,思想又是時而講時而不講,此處講彼處不講。北京城里,缺了好多東西,好不對勁和不夠味。安東談到應幫助朝鮮,不待全國幫助,先應有工作,慢或緩是不當的。遭到有的同志拒絕,趕到戰爭一起,又慌得手忙足亂。朝鮮戰爭,現在是爭到勝利了,可是戰爭之初及過程中表現的一些預見不足,不穩,不冷靜,事雖經過,經驗值得記取。美帝的武裝日本未止,日本革命未起,隱憂隱患,臺灣尚未解放,應該不諱,免得臨事張惶。
自己的偏見,我國現在“窮”得很,大難未已,外患而言,家當最“窮”,在世界強國之中。有的人不同意我這說法與看法。又是自己錯了?
三次大戰不可免,我們不愿它有,有信心有力量可以制止、延緩。但根本否認,是否自欺欺人呢?三次大戰的一些導火線在二次大戰結束時已經種下了,正如一次大戰一樣,這種歷史重復不是誰個人或某集團之愿否問題。
是不是想以功臣自居,企圖享受王公貴族的公爵或什么將軍、大人的高官厚祿、驕奢淫逸呢?自己常常以為自己沒有這樣打算過。
目前及三年來的生活,在西北農村雇工的境遇說來,是如同在天堂了。比起1930年至1934年北平敵區五年的窮苦生活來,有的地方好得多,基本上是好得多,有的地方還差得很遠。這是難以令人滿意,也難以令自己滿足的要害,但我認為這不是主要的,因為這比起沙漠生活,比起在敵人監獄中的生活,已是無可比較的時代與環境了。這種來回想,阻礙了我的進步。
聽到、看到、覺到一般人認為我是十足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了,向墮落發展了。實際生活感到的是書籍不足用,用品欠缺,醫藥困難,往往是解決醫藥比解決吸紙煙難得多。至于人家在放我之前后,給我布置下多少人?多少陷阱?我只能在生活中一一發現,雖然有個底數,但難保險人家不孽生。
根據我的經驗,民主人士,進步不少,也有限度,人家既有國家上份待遇,又有私產,何必不清高清高?有些老黨員走了貪污、蛻化的路,也有一些老老實實的老黨員的確有人把他當鱉看待,連個騎兵戰士對其馬的關心都不夠。據我知道,每位戰士對其騎馬每半月必須梳洗一次,最多三個月換一次馬蹄鐵,至于鞍轡、籠頭、馬勒……裝具更是及時而補充,隨環境條件而裝配。1928年至1929年國民黨大打內戰,新軍閥混戰打得天怨人怒之時,我曾擔心,得天下不難,共產黨一旦得了天下,也來個你罵我,我罵他,內戰得民不聊生,更害死人。從1931年以來,共產黨懲死共產黨的事,也不是沒有過的。這兩年雖然還沒見到誰懲死誰,但的確也自己人甚話好說,不順眼的人,崮你就崮你一下,崮死你,我何嘗不愿意的氣氛不是沒有。高級行政領導機關中的成分,也的確得注意一下,一些老實人的切身具體問題也的確應注意一下。騎馬的人,爭不分明,馬活去?死去?如何使馬健康恢復起來?制度、這個、那個的擋箭牌可以有不只一二。
當首長,當領導不是沒人,而且唯恐被別人爭了先,被領導的那個家伙怎么動不起來,是我給如何了?敵人給如何了?沒人愿意思索或關心一下,遑論解決與否?我們的確有人自以為高明得很,不知自己做下“親痛仇快”、“敵我不分”的事卻使人哭笑兩難。1927年國民黨曾出現過郭春濤懲惠又光的事,惠確死了。郭春濤現已死了,本不該再談此事,不幸我們也有類似郭一流的人,不只一位。可惜今日之惠卻非昔日之惠。
我覺得把一些給人做祖輩的人,放到一些嬰兒群中,偶爾一次也不要緊,再三再四,有些值得考慮。試想一下,一位長者放在一群孩子們的群中,不受小手手打,不當阿Q,不在挨打之后對孩子們撫摸撫摸甚至親一親說:“好好往大長”!有什么辦法呢?然而,近視眼們又說:“那人,孩子們都要打他,可見他不對呀!”
北平五年的常進當鋪的窮生活,我常常回味、懷念。別人的生活,能不依依?我們自以為一切很好,很好,人家為什么不敢說呢?其實我何嘗丟不開我的回念窮生活。人們總以為我的包袱丟不開,其實連抱負也沒有什么丟不開的。塌不塌我一個,死不死我一個,有什么丟不開想不開?到底什么人內外互相響應,弄回來個什么,加之我身,一再不肯解除呢?一再不肯告我呢?
二、關于給女同志寫信和一些女人往來的問題
可分兩類:一類是屬于別人對我有陰謀的,我也只能以別人對我擺下什么陣,我也應付一下這一戰陣的態度去進行,不如此,求不出個是非所在,水落石出。一類是屬于自由戀愛范圍的。我覺得從1924年至1934年的十年間,是別人的天下,沒有我們戀愛自由的法律保護;1935年至1946年是日本和蔣介石的摩擦使我謀衣食之不暇,無暇計及家室;1946年至1949年初是生存無保障之處;1949年至1950年是人人忙戰爭忙工作,我也急于體力等恢復之際。1951年的下半年了,體力稍復,一些朋友們也一再勸告之下,才開始戀一下,是否能得到愛人,是否有了愛人后恢復得更快更好一些,在這樣的意圖下寫了幾封信。信寫得好不好,其他人的看法如何,我也曾在不計算中計算過。謀害我的人,什么上也要謀害,不只在婚姻問題上。誰是為我,誰是害我,我也有個尺度。我在害誰,我也有個尺度。這個尺度,可能有人能接受,可能有人不能接受。我有個界限,是這些言行一不犯法一不反共。
至于當愛誰不當愛誰,我從自己的人生經驗上了解到,“強扭的瓜不香”,勉強不得。不只現在,連過去一樣,自己愛的別人不一定愛,別人愛的,自己也不一定愛。據我的經驗,干涉別人的戀愛,與己無益,與人無益,與黨與國也不一定有益。我的經驗是不干涉別人戀愛。至于受信者之態度或其他人之態度,我以為,在我自己只能聽之、任之,而不能有其他。戀愛、結婚是否享樂、腐化,我覺得肯定地說不是。生物有兩個目的,一為生存,一位傳種。反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他們要逆天背理,只許自己少數人享有生物的權利不許多數人享有生物權利。
階級斗爭的目的是為多數人主宰世界。
三、關于我給寫信要錢要東西的問題
我寫信要錢要東西的人分三類:
一類是他們確知我尚未恢復,確實需要那些書、物、零用以幫助我恢復。他們也確實有力量解決那些困難。彼此互相間也有過共財物共患難之誼。這期間既無串通舞弊,又無私相勾結,僅僅屬于幫助克服困難,渡艱辛的范疇。
一類是有責任有義務的人,如楊林。1946年我已動身返回之際,他留我多住,致我遭難。難已遭過,迄今不能恢復之根由,他不應逃避追究之責。他應為公證人,公訴人,向黨與政府起訴加害于我的人,追討此債,清除此債。在他不能盡此之責之時,我活一天,困難一天,他就有設法補助之責。這不只是天理人情,也是國法、黨紀、軍紀。類此的,如伊盟工作的同志,我在榆林未進行對伊盟工作的破壞,我留在他們處的物品如皮包、圖章之類既不屬地主、軍閥反革命的私產,應歸還我。因此,他們給我和我要了的,并未超此界限,這我還沒有認我到屬于貪污、浪費、揩油性質。這些東西,別人不能給原物給還,只以其價值之一部分給點錢,使我另買,這可能是新問題,可能有人以為怪,我覺得倘使我一旦恢復能工作,這些用品還是為國為民服務的東西,倘若我不能恢復,不能工作,得此也只是一些傷心紀念物而已,別人也沒有眼紅必要或爭奪必要。
一類是有糾纏不清的政治債,人命債的人,過去他們有權害我苦我,今日他們既然革命,對全國人對黨應有具體表現,對我的關系上,也應有具體確實明白的表現:首先,是認賬不認賬。認賬也表示他們欠債,不認賬也表示他們欠債。這是我的看法。其次,是如何清債。我的要求是他們清除加害于我的東西,這是最迫切、需要與基本的。在其不愿清除加害于我的東西之際,以其剝削自人民身上的民脂民膏,在他們不愿全數獻給國家之際,我也得一點幫助我解決我的零星困難,這是下策,但在無人能為我解除苦害我的東西,我未恢復之際,也只能如此。只要別人能解除加害于我者,我有信心與把握在我恢復之后,可以清還對他的借貸或其贈與的。
對第三種人的要錢要東西,不屬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性質。
前二者并未超過同志、朋友、同鄉關系的界限。
現有的書籍,和我在子長縣及延安所失者尚未及半。北平所失,綏德所失,尚未計及。燒毀者并未計。
年 譜
1951年
編者注:按子長市委黨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刊印。時間是編者判定的。
1910年 2月5日(宣統己酉十二月二十六日) 誕生于安定趙家臺。
1912年 隨父、母、姊四人移居于陜西安定望瑤堡。
1915年 隨外祖父認字。外祖父教首屆女學。玩的時間多,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魯論》。
1916年 2月18日(民國五年正月十六日) 一時至九時逃避高忽子靖國軍支隊,民間當時稱土匪,途中被狗咬了大腿,負傷去故鄉。高部于17日午夜(正月十五晚)進攻望瑤堡。來復步槍之戰爭,首次出現于當地。
3月 郭金榜部來駐防,民間驚惶,疑為土匪,又隨母親等逃避鄉間。
10月 隨舅父到外祖父鄉間井家溝侍讀。外祖父年老、病,要我去溫習并侍以慰解暮年。玩一個月,開始溫書。溫完以后,從《魯論》讀起,《齊論》讀了一半,因過年返回望瑤堡。
1917年 2月 隨三叔父和二弟,三人同入基督教小學校。因不出學費。三叔父因入教,曾去延安,受洗禮。
6月(農歷端陽節前) 隨舅父和母親去看外祖父病。和孫蘭馥姨兄、姨母等相會。外祖病危,欲吃蜂蜜,到十里外去找,我與孫同往,取到已吃不下去了。外祖壽終正寢,舅父無子女,要外孫當承重孫。閻、孫兩家因各只一男,按中國習俗,不肯再給別人當承重孫。公議及推讓結果,由我給外祖父任承重孫。此事本應父親和祖父母、叔父母等集議后才能決定,父親未在當場,母親主持。戴孝后,次日,父親來了,也同意。由此開始知道一點中國喪禮及家譜、家族系統等知識。
1920年 轉學安定縣立第二高初兩級小學校,編入初小三年級第二學期為插班生。學校為清末“正誼書院”所改設。舊書院之一切基本規制尚存在。學校為七年制,初小三年,高小三年畢業。民間叫“官學堂”,每年每一學生在初小納二千文銅錢,分兩次交納,春秋入學開始,至放假前必須納完。學費老百姓叫“學資”。高級每季納二千文。學校開支有三種來源:一、學田所收地租;二、基金所得月息;三、學費收入。學校開支有三:一、校長、教員、職員、院夫薪資;二、炭、茶水、打掃用具、設備開支;三、教授書、公文開支。
書院為同治年征剿回民暴民的左宗棠部下有“哨官”,名龍仁亥,在駐軍望瑤堡時,見當地人民死傷流亡很厲害,乃捐軍費,修筑望瑤堡城(原叫瓦窯堡,因出炭,燒磚窯供附近用出名)叫龍公城。將一些沒收下的土地,交歸書院,做基金,另外不知如何籌得一筆錢,貸給商、農、工作本生息,月息二分。以月息及地租收入作書院開基,不得挪用資本或出賣土地。士紳為之建一“龍公祠”于書院內,每年春秋開學,與孔子同受全校校長及師生員工公祭二次。書院修建富麗堂皇,非常講究。有一“正誼書院”匾額,記載經理人員。校門有碑記始末。民間稱“龍大人”。
我的學費及書筆紙墨費用來源:一、父親所給;二、暑假拾殘煙、賣西瓜、賣果子,寒假年節中賣瓜子、糖果、干果……所得利潤。
1923年 十八人結合去榆林參加“陜北各縣學生聯合運動會”于陜北各縣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校。為杜斌丞所召集。
控告安定縣長王正宇(陜西鳳翔人)貪污,得惠又光之助,獲勝。
暑假,用“偷走”方式去投考陜西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因土匪未果。
1924年 祖母病歿。旱災。父親又欠巨債。升學問題遭受各種阻礙與困難,終被克服。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四一二”前后,提出“不能公開與公布黨團名單,招致不必要的意外損失。”全國白色恐怖籠罩。陜北白色恐怖降臨時,提出“恢復各地黨與團,恢復一切工作。”
1928年 年初,“八七”決議后,提出“不做無成就的盲動,普遍恢復各地黨與團組織,教育全黨與團,作思想準備,向全國各地散布能散布出去的黨員,利用有利時機發動斗爭,鍛煉黨團員與群眾,爭取革命勝利。”
春,“發動反封建統治為主的革命活動,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鼓舞遭受白色恐怖鎮壓后的群眾及黨團員的情緒與精神。從表現突出的青年男女間的婚姻問題,農民間的旱災問題與反對統治階級的貪污□□等。”
起草《新三字經》,提出我們的革命應與國民黨所標榜的“革命”有所區別,我們現在是“造反”問題……。
1929年 六大決議后,提出“爭取一省或數省革命首先勝利問題。在革命低潮時期建立根據地,積蓄力量,利用國內新軍閥戰爭發展與創造自己的力量問題。”
1930年 陜北特委紊亂,陜西省委遭破壞。黨與團必須恢復與北方局之領導關系。西北革命必須有新布置。西北確是與別處有些特殊之處。
年底提出,秘密機關不敢那樣建立,必須由別處供養充足。
1930——1931年 “糾正盲動路線,必須黨內進行。離開原有組織,另立‘籌備會’不對……”
1931年 “九一八”事件一爆發,提出一定要抗日,抗日必先責南京國民黨政府,應當適應全國各階層情緒。白區秘密黨,須領導公開、合法(實不合法,合人民情緒的)的請愿、游行、示威,鍛煉與團結革命群眾,促動全國抗日。向敵人陸、空軍中打入。
1932年 親赴冀東一帶前線,視察不抗日及抗日部隊及人民情況,和一個腳戶談話。
1933年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提出:一、進行各種群眾工作;二、向冀東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號召東北、華北及全國的抗日戰爭。
察哈爾同盟軍后,與謝子長提出:一、東北日偽,華北新敗,南方風土人情不悉,還是西北的空隙最大,將來全國又非西北不可。二、除了紅軍、政權之外,要會掌握與使用科學武器,首先是無線電與南方中央及蘇聯之第三國際關系。
1934年 《兩個士兵談話》。“南方圍剿失敗,全國抗戰必來。”
1935年 一、培養干部;二、黨的領導問題;三、根據地建設;四、黨、政、軍建設、關系問題;五、沖破圍剿的政略、戰略;六、經濟戰爭;七、統一戰線;八、答復三個問題;九、答復分析階級與家庭成分和斗爭問題。
一、瓦解敵軍;二、陜甘寧晉綏區黨委;三、建立烈士塔;四、改造游民,戒煙、賭;五、救濟戰爭災難民;六、優待烈、軍、工屬及改造、教育、互助;七、民間互助問題;八、財經政策,文教宣傳政策。
一、解放瓦窯堡;二、解放清澗與襲擊綏德,進行陜北及陜西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三、玉家灣祝捷大會《兩個對比》;齊家灣,洛甫“反關門主義”報告時提出“防止資產階級新的搗鬼”;四、對北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途之估計;五、對二弟等三次出發之看法;六、對東北態度;七、對中央到來之觀感;八、給鄧發抄文,加入“鑼鼓喧天聲中蔣介石死亡”的問題。
1936年 一、離開瓦窯堡;二、教民工作;三、蒙古工作。
1937年 一、對“雙一二”之看法;二、統戰問題;三、出兵準備;四、出兵綏西。
1938年 一、榆林講話,神木,興縣;二、出兵,七旗工作布置,全綏工作布置;三、騎兵團問題;四、募捐問題;五、臨河之行;六、新部隊的創建;七、自衛軍的創建,統戰,蒙B,那素;八、與郭關系,誓會平津;杭王府之行。
1939年 一、杭旗自衛軍;二、五原之行;三、牛剛問題;四、伊盟工作;五、反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典型;六、包頭日偽奸細曾謀刺我未遂,被發覺,避開,敵自殺。
1940年 一、歷史問題;二、與王鶴壽談“與個人損失無幾”;三、郭洪濤回來。
1941年 一、五一綱領;二、城川問題;三、三五九旅問題。
1942年 一、特產問題;二、民族學院問題;三、英雄主義問題。
1943年 一、整風;二、沙王問題。
1944年
1945年
1946年
1947——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