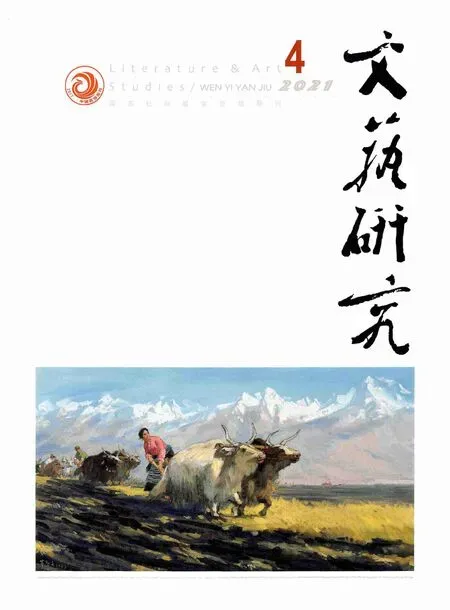作為政治寓言的人道主義情節劇
——重讀謝晉的《芙蓉鎮》
張旭東
《芙蓉鎮》是古華在1981年創作的小說,發表后立刻引起轟動,翌年獲得第一屆茅盾文學獎。小說雖自出版以來就受到讀者的歡迎和喜愛,但公平地講,其存在感和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歸功于電影改編。這部同名影片由謝晉導演,1986年完成拍攝,第二年在全國上映。盡管在審查、宣發、出國參評等環節上不無坎坷,但影片依然得到當時中國電影業界和觀念的高度認可,獲得1987年第七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和第十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加之在海外斬獲的戰績,《芙蓉鎮》一度成就了“文革”后中國電影史上罕有的盛況。謝晉作為一個“電影作者”,影片作為一個“社會文本”,也遠遠超出了單純的電影史和電影批評的范疇,獲得了某種獨立的地位和重要性,成為歷史化、理論性批評分析的對象。本文將以謝晉的電影為主要文本和分析對象,在電影的敘事中切入問題、展開討論。
一、一般結構特征
電影《芙蓉鎮》有以下六個結構性特征。
第一,它幾乎完全通過二元對立的邏輯建構起敘事和風格的空間——善與惡、美與丑、人性與非人性、理智與瘋狂,等等。這種二元對立不但體現在作品總體上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念和寫實主義- 情節劇的美學構架上,也反映在故事細節和人物形象設計等方面,比如“日常的”經濟導向與“非常的”政治導向、普通人身上的勤勞和懶惰、女性人物圖譜內部的女性化和非女性化傾向。這是謝晉電影一般手法的延續,從“文革”前“新舊對比”的主題(如《女籃五號》 《紅色娘子軍》 《舞臺姐妹》) 到“文革”后影片(如《天云山傳奇》 《牧馬人》) 貫穿的撥亂反正、“噩夢醒來是早晨”的總體敘事傾向,都有這種創作手法的體現。
第二,這是一部高度類型化或典型化的電影。在《芙蓉鎮》的七個主要人物中,謝晉明確突出男女主角的絕對重要性。他說過,“胡玉音與秦書田的塑造,是影片成敗的關鍵”,“而胡玉音在片中是最重要的”①。這繼承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的革命現實主義電影和戲劇的表現手法②。這種外在的典型化手法,一旦同內在的基于二元對立原則的戲劇沖突設計結合起來,就給電影語言系統帶來強烈、鮮明、具有感染力的戲劇效果,更進一步在觀念、價值和意識形態上表達特定的認同,并承擔起特定的承載與再現的功能。
第三,影片帶有明確而強烈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傾向性③。可以說,《芙蓉鎮》是一部帶有強烈教諭性質的情節劇,一部力圖讓人思考、督促人摒棄某些價值而認同另一些價值的娛樂片,一部知識分子代表全社會應有的意識形態共識而拍給大眾看的嚴肅電影。它為觀眾提供了關于人性及其對立面的系統辨析,從而不但對80年代后期“當下”的“改革”和“人道主義”意識形態有所介入甚至評價,而且觸及了這個“當下”的歷史正當性、相關的社會本體論乃至“人性”的價值基礎。
第四,《芙蓉鎮》訴諸大眾或全社會的觀賞性、娛樂性。正因為影片的價值指向和道德指向非常明確,而且帶有強烈的教育、宣傳和引導性質,所以它的人物設計和敘事發展就一定要借助外在形象的感性豐富性和強烈對比,同時通過深層社會心理、價值取向、審美趣味乃至前在的政治訴求,去訴諸、呼應、撩撥、激發和“籠絡”觀眾,在此過程中明確并完成電影符號結構內在的意識形態編碼。這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寓教于樂”。這個“樂”尚不是充分商品化時代和大眾消費意義上的,而是旨在提供社會情感和公共道德意義上的認同、升華,從而重建善與惡、美與丑、理性與癲狂、幸福與苦難、人性與非人性或反人性之間本體論意義上的終極區分,在此過程中生產一種社會性、政治性的集體滿足。
這種滿足既是引人思考的,又是感性的、訴諸欲望和欲望實現的。作為這種集體性道德選擇和價值認同的審美報償,觀眾可以在觀影白日夢的象征空間中得到一個好女人的愛情,一個好男人的才華、浪漫與忠誠,建立在誠實勞動基礎上的財富積累和家庭,一套正常、安穩、為普通人追求幸福而設計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壞女人和壞男人走到一起,這些過度政治化的人物不但失掉了自身的性別特征和吸引力,在生產和財富積累意義上也是“不育”、枯竭的。《芙蓉鎮》“快樂原則”的實現,必須通過堅決不妥協地否定和排斥一切反人性的、過度政治化的社會觀念和人生意義來增強其自身的戲劇效果、審美吸引力和內在道德政治強度。它帶來的滿足感和審美愉悅,從反面來自那個有待被否定、克服、超越的對立面,即那些同自然、常態的人性處于緊張關系的外在異己性因素。
此外,還有兩個特征需要展開,因此單列小節。
二、想象的共同體
第五,《芙蓉鎮》是“文革”后一部由知識分子主導、略顯越權地“代表”國家或時代意識形態主流向大眾發言的故事片。這個想象性的大眾也包括知識分子群體本身,甚至包括作為其政治意志表達的國家。這部電影生產的體制性因素以及制作過程的每個環節,都具有同國家體制(并不總是順利的) 磨合④、與想象中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在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取得廣泛協商和共識的特點⑤。
從這一點看,謝晉電影創作的流程,客觀上成為好萊塢模式(公司管理層集體決策、制片人制、創作過程外包、廣泛征求專家咨詢意見,等等) 的社會主義對應物。這種集體性不一定對應一個有組織的寫作班子,毋寧說它是某種社會主流或社會共識的意識形態編碼和再現,是一個社會性文化生產的過程和組織,其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趣味和判斷。古華雖然是一位優秀作家,但尚不能像謝晉這樣,從電影工業的國家體制內部,站在社會心理和知識分子意識的結合點上,借助電影這樣的具有大眾媒介和“藝術作品”雙重特性的文化生產方式,通過意識形態編碼、審美中介和敘事安排,把某種呼之欲出的集體政治無意識呈現為具體的銀幕形象,從而不但推動、制造了某種社會性的思想性和準政治性議題,而且在電影語言的符號秩序內部為這種爭議預先設定了答案。
在這個意義上,《芙蓉鎮》是一部預設了自身符號空間同國家主導的社會空間完全同位并且相互滲透的電影作品。與此同時,謝晉本人作為在具體的文化社會空間里占有明確、固定位置的老一代電影導演,在新時期社會文化快速更新的節奏下,特別是在“第五代”導演帶來的新的電影語言沖擊下,在“朦朧詩”“尋根文學”甚至“先鋒小說”帶來的新的語言感受力和語言倫理的環境里,在文藝批評和文藝研究領域日益活躍起新方法、新理論、新觀念的氛圍中,似乎也不得不尋求風格升級和審美創新,以在新的文化、趣味和批評眼光中保持自身創作的質量和標準⑥。這要求謝晉尋求同當時文藝界、文學界和知識界的廣泛對話,以取得并確認一種意識形態共識和審美標準上的前期認可。這是一種經過藝術生產和意識形態編碼加工而形成并放大的知識分子內部的“同語反復”。
所謂“謝晉模式”⑦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面向大眾的知識- 思想話語,這同20世紀40年代左翼電影有一種繼承和呼應關系。一方面,左翼電影是知識分子話語,另一方面,它們又通過影像媒介面向大眾,有類似類型片或商業片的效果。在這個以介入國家民族的社會文化重大問題為己任的電影生產和消費循環中,或許正因為謝晉的高度藝術化、個人化和充滿激情的“越俎代庖”,“官方”的位置反而變得曖昧而尷尬,甚至被極大地外在化、邊緣化了。這部電影從早期選題、攝制、審查,到公映、參加國內外電影節,再到被輿論接受并引發討論,在各個環節都遭遇到一些麻煩,一度連小范圍的內部學術討論也被叫停。這些“折騰”雖沒有最終影響電影的制作和發行,卻仍可作為一個重要提示。正是因為這種“共享”和“同位”關系,《芙蓉鎮》對它在創作意識層面上認同、肯定并力圖通過反思加以完善的制度及其歷史合法性和道德正當性的沖擊,也遠比電影審查可以剪除掉的細節更為激烈。當“第五代”導演大舉進入“現代電影語言”和“集體無意識”的內部風景時,中國電影在介入社會性思想議題的意愿和能力上,在思考的政治性和歷史性方面,事實上是從謝晉的立場上后退而非前進了。
三、喜劇而非悲劇
第六,《芙蓉鎮》雖然就導演的主觀意圖而言是在追求一種悲劇風格和效果,但就其整體戲劇結構、戲劇效果、戲劇與現實的關系而言,客觀上卻具有一種喜劇的基調。最終,是喜劇性而非悲劇性,成為電影情感升華、道德反思和審美愉悅的主要手段。
謝晉在導演手記《悲劇,對一個時代的反思》中,曾談到在電影中營造悲劇性的意圖:“(《芙蓉鎮》)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嚴峻深沉的悲劇,一部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結合的令人思考的悲劇,一部歌頌人性、歌頌人道主義、歌頌美好心靈、歌頌心靈搏斗的抒情悲劇。”⑧顯然,導演是在一種接近社會常識和是非標準、與“文革”后集體心理相呼應的日常語言的意義上談論思考和抒情“嚴峻深沉”的悲劇底蘊。這種憂思焦慮的主觀感受的另一面表現為“歌頌人性、歌頌人道主義、歌頌美好心靈、歌頌心靈搏斗的抒情悲劇”。當市場經濟、消費社會和資本主義全球化逐步到位后,頌歌式的抒情失去了目標或關聯性,電影的“悲劇”色彩隨之變得模糊起來。導演手記中特別提到秦書田這一角色應帶有“悲中幽默的性格”,并指出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影片的風格”⑨。謝晉雖然極富洞察力地抓住了“悲”(悲劇、悲情、悲苦、悲憤) 和“幽默”這對矛盾在影片中的對立統一,卻似乎沒有料到電影完成后其內在的喜劇性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不僅因為電影的大團圓結局或對反面人物的喜劇性夸張設計,也基于作品自身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構造。
《芙蓉鎮》的喜劇性不是導演主觀上追求“悲劇性”的意圖所能抑制的,因為它歸根結底來自作品對普通人生活世界內在的正當性和生機的肯定和信心;來自對所有同這種正當性和生機對立的因素,特別是對時代政治因素的荒誕、內在脆弱性和癲狂狀態的鄙視和不屑;最終來自對這個普通人生活世界的自我修復能力、勞動- 積累能力、滋生繁衍能力,以及這種生活方式自發的欲望滿足邏輯的體認和贊美。正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把喜劇定義為“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壞的人”⑩,《芙蓉鎮》正面人物所代表的人道主義道德審美原則盡管在導演主觀意圖中被抬高到“悲劇”境界,但究其具體的歷史性價值理想而言,卻是一種回到地面、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物質和“欲望滿足”意義上的“追求幸福”的集體訴求。在這個水準上重新建立起來的社會領域中的人,在戲劇空間里對應的必然是一個“低俗”的、不求完美卻無可指責的“感性的人”的喜劇形象,而不是那種因高貴的性格堅定性而在抽象或神性的原則沖突中被撕裂的“大寫的人”的悲劇形象。
“秦癲子”自出場就帶有強烈的喜劇性。他要求大隊支書把他頭上的“右派帽子”改作“壞分子”帽子,為此主動坦白交代,說自己“沒有反過黨和人民,倒是跟兩個女演員談戀愛,搞過兩性關系,反右派斗爭中他這條真正的罪行卻沒有被揭發,所以給他戴個壞分子帽子最合適”?。他在小說和電影里出場時,在身體動作和語言表述上的表演性,已經為一種喜劇性的顛覆和關于人性定義更深一層的抵抗和解釋權爭奪做好了鋪墊。
胡玉音和秦書田其實是一對“浪漫喜劇”和“諷刺喜劇”的主角。他們都是普通人而非王侯將相,他們的戲劇性來自對于財富、愛情、幸福、安全合情合理的追求,以及在逆境中仍不熄滅的樂觀精神;他們在觀眾中引起的觀影效果是認同感、移情,觀眾希望他們安好、快樂,這與“必須在觀眾身上引發憐憫和恐懼”?、令他們“景仰”、自身卻有足以導致其毀滅的個人錯誤和決斷的悲劇英雄的行動大相徑庭。而《芙蓉鎮》里的反面人物盡管令人厭惡,卻并不是純粹的惡的體現,而是帶有鬧劇式的丑角性質,最終是可笑可憐的形象。如果一定要追究這部作品的悲劇因素,就古典悲劇包含的諸如悲劇的認知、悲劇的過錯或失誤、悲劇的狂妄、悲劇的復仇和悲劇的反轉等因素看,倒是其主要反面人物,即在運動中當權、整人、過度概念化和政治化的“革命派”王秋赦和李國香,更具有上述經典意義上的悲劇性。準確地說,他們被導演不自覺地分派了更多的悲劇成分,雖然這種悲劇性更多只是在角色本身“片面的主體性”意義上才成立,而在小說和電影的整體性喜劇效果里,最終僅僅作為可笑的東西,通過做人意義上的徹底失敗和被歷史拋棄的結局而獲得其道德訓誡意義。
作品客觀和結構意義上的喜劇性,事實上是由導演對經歷了“文革”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常態”和“本性”的重建企圖所預先決定的。它與傳達一種普通人生活世界生生不息的世俗樂觀主義及其內在的韌性、自尊和對幸福的追求高度一致。這種追求本身出自一種情感、道德、習俗和文化的“不言自明”的確信,因此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特征。觀眾看到,盡管男女主人公所體現的“人的本質”和“歷史發展的大勢”在劇情中被表現為一種人與不幸命運的搏斗,但這種或可稱作“命運”的超自然力量,作為外在因素,最終不過是歷史的鬧劇和過場;它是偶然而不是必然,是特殊而不是普遍,是無妄之災而不是基于自然正當和人性本位的常態和規律。然而這樣一來,“悲劇”也就因其對立面的孱弱、滑稽和缺乏普遍性而被削弱到不成其為悲劇,反倒蛻化或“上升”為“普遍人性”為自己肯定自己而設置的喜劇元素了。
四、常態與非常態
《芙蓉鎮》小說與電影的戲劇性展開都以一種風俗化、準自然狀態的日常生活常規為基點。這種非歷史化、非政治化的“常態”作為意識形態和審美預設,為隨著人物形象、情節和戲劇沖突而不斷明晰化、尖銳化的價值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二元對立,提供了穩定堅固、更容易博得讀者/觀眾同情與認可的歷史框架和文化氛圍。也就是說,它們都將其對立面放在了某種不自然的、武斷生硬的、由外在于人性和日常生活形式的抽象教條主導的“秩序的挑戰者”位置。古華在小說第一章《山村風俗畫》第一節《一覽風物》中的描寫,已經把自然經濟性質的勞動和交易交換建立在一種人類學觀察水平上的社會風俗框架之中。在芙蓉鎮上經營米豆腐攤子的女主角胡玉音,不僅因為女性化的容貌體態成為小本生意的活招牌,經營思想也帶有經濟范疇之外的風俗和倫理性質。然而到小說第三章《街巷深處(1969年)》,讀者看到的已經是一個徹底被政治標簽“格式化”的階級社會的縮影。小說里描繪的民俗意義上的自然經濟的自發性集市貿易,在電影里被集中表現為這種集市交換活動背后私人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勞動和財富積累。
這一切最終圍繞并服務于一對核心矛盾,這就是在“文革”中達到高峰并被歸謬化的階級斗爭、社會運動邏輯,同一種非歷史的“人”的概念和非政治的“生活”概念之間尖銳的、難以調和的對立。根據電影敘事結構中確立的命名體系,前者是一種丑劇化、鬧劇化的“折騰”或跟老百姓“過不去”的抽象概念和原則,包括反右運動、社會成分劃定、“文革”、李國香領導的保衛土改成果(“二次土改”)、鏟除資本主義尾巴,一直到電影最后王秋赦變瘋,敲著鑼在業已恢復常態、一片祥和的芙蓉鎮街道上獨自呼喊“運動嘍!運動嘍”。與此相對立的另一面就是平實安穩的“過日子”,包括其中暗含或公開宣揚的正常的七情六欲和對私人領域里的安全、自由、財富和幸福的追求。“過日子”這個概念雖然“低而俗”,但對推動開放與變革的8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及其文藝表述來說,卻是奠基性的“政治無意識”,也是“改革共識”的社會基礎和集體想象與訴求的核心內容。
常態不僅是感性的,也是勤勞務實的、從事生產的、積累性的;非常態則是一種純外來的、抽象的干預和擾亂,它像不合理的稅收和徭役,強加在鄉村生活自然化、風俗化的社會肌體之上。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自然化、風俗化、感性化甚至女性化的生活世界,同時被賦予了一種生產性和經濟學屬性,這通過小說和電影的敘事、戲劇和視覺形象效果,在潛意識層面上反過來促成了經濟范疇本身的自然化、人性化以及同“欲望—欲望滿足”邏輯的融會。在表象的世界里,屬于常態的人物都是忙碌于自己的小營生、小安全、小幸福的“俗人”,他們向往的是安穩富足的生活。相反,非常態或政治世界里的人物雖然能量十足、不停“折騰”,卻都是不從事生產、不創造財富的“懶人”或“零余者”。從內在于常態范疇的勤勞/懶惰的二元對立出發,還可以進一步引申出一種價值判斷、道德判斷和審美判斷,即在“政治世界”里討生活的人不僅一無用處,而且帶有不同程度的無恥、丑陋和貪婪,他們的人性是不自然、扭曲甚至邪惡的。
以王秋赦為例。無論在小說還是在電影里,這個“土改根子”都懶惰好色,家里骯臟不堪。電影里有一個特寫鏡頭,給觀眾展示一個可以拿在手上把玩的木雕女菩薩,王秋赦顯然把它用作一個見不得人的性玩具。這個階級譜系里的“雇農”,實則是一個常態社會或自然社會的邊緣人,一個標準的“痞子”或流氓無產者?。王秋赦為李國香所用,李國香為更高的隱性的權力所用,但他們也都是隨時可以被拋棄的工具和棋子。這就是在“文革”后期被普通老百姓鄙視地稱為“吃政治飯”的那種人,其形象在“文革”結束后最初幾年的文學和影視作品里比比皆是。從今天歷史化、中立化的角度看,這種底層或邊緣人的政治野心,在“土改”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之后,實際上也是一種在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上追求翻身和“承認”的欲望。但在《芙蓉鎮》里,王秋赦從一開始就被固定在“二流子”的社會范疇內,其經濟、社會、政治、道德、文化、審美和人性實質,在小說和電影的自然- 風俗化結構中完全被非歷史化、非人性化了。
五、“算算經濟帳”:勞動、積累與財富的合法性
李國香對胡玉音的突然造訪是電影《芙蓉鎮》敘事發展中的第一個戲劇緊張,它把電影導入了矛盾和沖突逐漸激化、高潮迭起的情節劇節奏中。我們看到,常態化的、自然的、人性的、“自在而非自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旦暴露在一種由抽象理論指導的社會分析、價值批判和階級命名中,就無處藏身、無從辯白、任人宰割。
這種戲劇張力的表層由李國香與胡玉音女性形象上的反差和對比完成,但深層的原則性沖突,卻是李國香代表的政治思維要來給胡玉音代表的“過日子”的生活領域“算算賬”。觀眾心中明白,這并不是會計學意義上的加加減減,而是一種高度概念化、直達階級成分認定、具有嚴峻政治后果的社會分析。這里的戲劇性恰恰在于觀眾耳熟能詳的“上綱上線”套路,即通過政治經濟學和階級分析的“直通車”,把小本經營的流水賬一步步揭示和還原為剝削、財富再分配和階級社會卷土重來的“敵我之辨”。
通過李國香的“算賬”大敘事,胡玉音夫婦不自覺的日常積累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一步跨進了新生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的行列。片頭渲染的小生產者吃苦耐勞、一心一意建設小康生活世界的努力,在政治邏輯面前頃刻間土崩瓦解。更為嚴重的是,胡玉音夫婦似乎全然沒意識到,由于房子建在從“土改根子”王秋赦手上買來的土地上,所以這份資產和家當可以說已經不是建在小鎮的土地上,而是矗立在中國農村土地重新私有化和新一輪社會不平等的斗爭形勢里了。李國香“算賬”的關鍵并不在于點出胡玉音夫婦經營米豆腐攤“每月還純收入二百元”,“達到了一位省級首長的水平”?,而在于在這種商業經營和財富積累的終端點出了農村貧富分化問題和土地再分配問題。至此,矛盾從經濟范疇激化并過渡到政治范疇。
隨著抽象概念和政治思維的引入,這種社會實質和階級識別上的轉化同時也是從合法到非法的性質變化。蠶食土改成果、逆轉集體化進程、積極踐行商品經濟和自由財富積累并最終成為新的土地占有者和“剝削者”的種種“帽子”,都像是為胡玉音夫婦量身訂制一般。由此繼續“上綱上線”,二人的經營甚至可以被指認為加速貧下中農失地和土地再集中的行為,是在直接動搖土改成果、破壞共和國的合法性根基。而這一切竟然只是以“小本生意”“糊里糊涂過日子”的方式達到的,更進一步說明所謂自然經濟、日常生活常態和對于“幸福生活”的想象本身就內在地具有政治意味和政治后果,因為它每時每刻都在生產出一種新的社會存在和法權主體。
六、生命政治的翻轉
《芙蓉鎮》強烈的政治性只有在這個新的總體性、本體性范疇內才能被有效地探討。正是這種深層的意識形態構造以及它所包含的矛盾沖突的深刻性和激烈程度,決定了這部作品、特別是謝晉的電影改編匠心獨運的戲劇框架和審美感性外觀。小說和電影在敘事、戲劇性、形象和形象化表現/再現的空間里,細致而鮮明地表現了那種同“經濟人”(homo economicus) 的人性本質相適應的社會、道德、倫理、情感和審美規范。《芙蓉鎮》在革命合法性空間內部帶來的反思或批判的力度甚至超過了“第五代”電影和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在當時帶來的新一輪沖擊,因為后三者只是把自己設定為新的社會現實的象征秩序,對“算舊賬”并不感興趣,而古華和謝晉的思考、情感和想象,則與他們所表現的那個剛剛過去的歷史世界和社會- 意識形態領域完全同位、同構、休戚與共,他們仍然在那個社會思想空間里生活、思考和想象。相對于80年代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和文化更新,謝晉的電影美學未免顯得有些“落后”“不時髦”,但重要的是,古華的小說在80年代初問世時還帶有新時代發韌期的那種“噩夢醒來是早晨”的樂觀主義,可是短短六七年后,謝晉的電影已經在執著地試圖表現,那個剛剛過去的歷史時代其實并沒有真的過去,它仍然潛伏在社會土壤和社會心理深處,時刻有可能卷土重來。
把這個“過去”問題化、“永恒化”,正是電影《芙蓉鎮》戲劇結構和審美風格最內在的儀式感、藝術激情和象征意志。其內在原因是謝晉電影風格固有的情節劇模式、新舊對比結構和“為人民代言”的社會介入態度。而讓《芙蓉鎮》從類似的“反思文藝”作品和“社會介入”格式中脫穎而出的,是電影大刀闊斧地將文學文本中的戲劇沖突推向一個新的道德強度和審美強度,從而形成了這部電影謝晉式“悲劇反思”的哲學深度和戲劇極點,即一種在人性本體論內部的“人與非人”的辯證轉換,以及這種轉換所暗示的存在的政治和存在的斗爭。
當秦書田、胡玉音因“非法同居”被批斗的時候,謝晉的電影語言是對革命偶像學和形象學的翻轉、挪用和無意識的戲仿。兩個“黑五類”“壞分子”像革命烈士被綁赴刑場前一樣站在雨中,在聲討和口號聲中交換訣別前的深情注視和最后囑托。胡玉音已經懷孕。秦書田對她說:“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
同小說相比,電影更加突出中斷了自然生活常態的這場運動的嚴厲和肅殺,突出在這種強大、威嚴的敵我矛盾判決下,兩個無望的小人物動物般的、生理性的抵抗。這個場面的視覺儀式感和悲壯感為一種突破常識、經驗和一般社會化人性價值的震驚做好了鋪墊。這個震驚來自經驗世界、常識世界甚至理性世界的崩塌,來自一種新的存在本體論、意志論和價值觀的突然降臨。在這最后的抵抗中,人的存在已不再能以人的方式、人的觀念和人的尊嚴為基準,而只能以其反面,即非人性、動物性或“牲口”般的存在為參照。在這個微妙而重大的區別里,所謂的“謝晉模式”從原先的藝術套路出發,最終長驅直入地探入一種關于生命政治的存在本體論的內在辯證思維?。
“像牲口一樣活下去”在此不再僅僅是控訴非常態、抽象、概念化的政治對自然、常態狀態的人性所施加的壓迫和摧殘,因為“牲口”顯然已不再是一般人道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社會規范和“文明本身”意義上的“非人”范疇。恰恰相反,“牲口”已經決定性地轉化為人性和人的存在的最后條件和最后形式。也就是說,“牲口”或概念意義上的“非人”業已被“人”的概念內在化為自身本體論意義上的實質。“像牲口一樣活下去”并不意味著一種“低于人”的茍活狀態,而是由人的存在本體論內部結構性的“例外狀態”所激發出來的存在的強度和真理內容。這種強度和真理內容平日隱藏在常態的曖昧、優柔和自我迷信之中。但這樣突如其來的轉變取消了、而非僅僅是加強了人/非人的二元對立,因此,它的到來具有一種思想和生命層面的解放和啟蒙意義。這種固有二元對立的打破帶來了對生存狀態和生存本質的一種全新的認識和領悟。它不僅僅提供了一種“活下去”的辦法和形態,而且真正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關于“活著”的生命政治概念,一個有關“活著”的新的普遍性范疇。
七、生命政治的往復運動
在《芙蓉鎮》里,“活”或“活下去”的生命政治的存在本體論,正是通過男女主人公對“人”和“人性”社會化范疇的出讓、退避、清空和重新占有建立起來的。具體地說,一旦高度政治化和概念化的外部環境使得人和人性的自然或常態化范疇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尊嚴、權力、自由、情感需要、欲望滿足、基本物質保證,等等),一個更具有存在強度的、本體論意義上新的“人”的概念就在“活下去”的意志和選擇中被激活并行動起來。它的單純的理性行為只能是放棄人的范疇,而在非人的范疇內恢復和重建自身,此時“牲口”這樣的非人范疇也就失去了它在常態下本來的實質(作為人的范疇的對立面、作為一種低于人類生存基準線的茍活,等等),而在例外狀態下被一種外來的、新的生存意志及其理性嚴格性和政治強度所占據、充滿,由此獲得新的實質和意義。“牲口”成為一種更高、更具有本體論的實在性和政治強度的“人性”概念的流放地、庇護所和反攻根據地。在這個低于人或非人的范疇里,人性在告別人性之后重新獲得了一個在偶然、武斷的社會政治結構之外和之上,重新認識自身存在的生命強度和政治強度的機會。
這樣一種外化、對象化和異化投射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動的。它在具體的歷史轉折的意義上,為再次到來的“人性的復歸”,即從它的流放、壓抑、異化狀態和“成為非人”的例外狀態向一種新的規范和常態的復歸,提供了歷史經驗和精神財富。這種內在于人的范疇的內在區別和外部空間一旦建立起來,“牲口”或非人范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原所帶來的就不再是原來人道主義的“人”,而必然是帶有不同道德和政治實質的存在者。這個人性概念的游動和擴展是電影《芙蓉鎮》的藝術奧秘和意識形態編碼。它甚至不受謝晉本人固有的政治意圖和審美意圖的影響,而在電影的戲劇結構和符號結構中被客觀地實現和構建出來。
不言而喻,這也是通過放棄“人”的資格、以“牲口”自居而退出一個完全被政治教條下的無情斗爭占據的社會領域和價值領域的策略。這里的辯證邏輯及其意識形態的顛覆性是顯而易見的:當人的自由意志最后以放棄人的社會政治屬性和文化標識作為人性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 和自我尊嚴的最后選擇時,人性的本體論真實就已經遷移到一個非人的范疇里。一如當無休止的、空洞教條的政治斗爭掏空、瓦解了常規政治范疇內部矛盾的具體性和歷史實質時,真正界定“人”和“生存”本質的沖突和矛盾,即那種存在的政治,就轉移到最低限度的經濟領域,即一種動物水平的生存范疇里去,并在那里等待、孕育、發展出一種能夠打破既有社會框架和概念框架的新的矛盾統一體。
當一切人的東西都變成非人的東西,非人的東西就變成了人的東西。這個戲劇瞬間的意義絕不僅限于謝晉刻意營造的人道主義“嚴峻深沉的悲劇”,因為它具體的歷史政治含義,只有在人性本體論實質重返一個自然常態的社會- 政治空間時才能夠被全面把握。當秦書田和胡玉音團聚,芙蓉鎮恢復了當年塵世生活的韻律時,在這個看似“復原”的社會空間里對新的常態生活充滿向往的芙蓉鎮的男男女女,在概念上已經不再是自然的、由風俗決定的傳統中國人,也不是由早期社會主義經驗決定的作為“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化“新人”(他們在《芙蓉鎮》里都作為負面形象和中間人物出場和結局),而是業已從非人范疇中獲得了有關人性的政治本體論擴展和強化的、經濟學-生物學意義上“后新人”或“新時期人”了。
更具體地看,當被政治社會驅趕進“動物”范疇里的人重返社會領域、重新占據“人”的符號空間和想象空間的時候,這個“人”就已擺脫原有政治和道德范疇的束縛和界定,變成嚴格意義上的“經濟人”。因為就其追求幸福、安全、自由和自足的“欲望滿足”而言,“經濟人”或抽象化的中產階級的神學原型正是動物——這在歐洲中產階級興起的知識譜系里面是非常明確的?。從中世紀、文藝復興一直到啟蒙時代,“經濟人”概念的歷史實質,就是以在大地上生存的動物肉身及其自我保存的生命意志為名,把人從上帝之名和神性秩序中解放出來,變為自己的最高目的。這個最高目的反映的是一種具體、特殊的市民階級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再經由一種生物/生命- 經濟理性話語體系予以進一步明確和規定。
“像牲口一樣活下去”這個自我宣言和愛人間的攻守同盟,既是一種具有實際可操作性的生存技術,也是一種有關人性本質的頓悟和自我啟蒙。謝晉的《芙蓉鎮》客觀上回應了新時期知識思想界內部一種若隱若現、不絕如縷的訴求,那就是在“后革命”氛圍中以“補課”的方式建立歐洲市民階級人本主義的政治教養、經濟學思維和道德基礎。這當然也包含了對整個20世紀中國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反思“文革”為切入點,對于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來說,不過是通過一種歷史敘事再次回到一場未完成的革命現場,以謀求在新的“人的本質”基礎上探討和想象一種新的有關未來歷史發展的社會愿景。作為社會學起點的“人”是一個“政治人”,不是亞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動物”意義上的政治人,而是在當代政治國家和泛政治社會下被過度規范、壓抑以至垮塌的人性范疇。它與其說捍衛人“更高的”道德實質,不如說排斥具體的人的基本屬性和作為“自為的”(而非僅僅“自在的”) 人的最基本的政治,即存在的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的政治。因此,這種政治邏輯不但是反欲望、反經濟的,而且究其實質也是非政治、反政治的形式主義和抽象的教條,因為政治范疇賴以成立的內部矛盾在這里脫離了它們在具體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中的形成條件,無形中把“政治性”的社會實質讓渡給了一個原本是非政治性的“動物”范疇。
《芙蓉鎮》的結尾已經展示出“從動物到人”的復歸運動。在落實政策、撥亂反正的表面情節之下,我們看到“非人”范疇早已不限于電影開頭“牛鬼蛇神”“黑五類”等用于階級識別和剝奪政治權利的標簽,而在一個新的歷史出發點上成為一種最低限度的經濟范疇(勞動、生產、積累、流通、消費、財產與財產權) 和社會范疇(社會地位、社會交往、社會資本、日常生活、公共性、私人生活、性別特征),它們規定了即將被重新占據、充滿、具體化和實質化的“人”的范疇及其內在的新的政治性(所有權、政治權利、價值觀、對新的政治秩序期待和參與)。在“經濟人”對于“政治人”最后勝利的意義上,《芙蓉鎮》不是一部朝后看的“反思”電影,而是一部走在時代前面的作品。支撐著“向牲口一樣活下去”信念的是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這個“活下去”的概念可以直接連接到余華的《活著》 (1993),以及此后流行至今的關于“生存斗爭”的“自然權利”和“公理”假定。出人意料的是,在謝晉這里,我們能為這些當代生活哲學的內在困惑找到更為鮮明、激烈的政治寓言。相比之下,90年代以來的“生存哲學”反而更像淡化了的通俗版,似乎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里,“活下去”也已失去了它的本體論意義上的內在緊張,而只剩下職場競爭、商品消費、房屋貸款、教育、醫療等日常領域常態化的奔忙和疲憊了。
八、語言游戲與意義爭奪
電影中接近“崇高”審美范疇的悲劇場面只是一幕甚至一瞬間,雖然它在作品的政治寓言結構里占據中心位置,但卻無法覆蓋整部電影的情節劇性質或內在于情節劇戲劇結構和表現手法的喜劇色彩。
首先,秦癲子完全是一個喜劇角色。對他的種種古怪逗樂的表演,大隊干部或許只覺得好笑,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不但知道這個“壞分子”是本鎮的“學問家”,也對他的真實面目、或者說他外表之下的復雜性和“內在性”有著精準的觀察和結論。小說借助群眾的口吻將其定義為“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的“窮快活,浪開心,活作孽”?。這不但為人物形象確定了基調,也在電影影像符號學層面上為“人與鬼”“人與非人”乃至“像牲口一樣活下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側面補充說明。雖然做鬼的歲月是痛苦的,甚至使人徘徊在自殺邊緣,但這個被打入且自愿自居在“鬼”的范疇里“窮快活,浪開心”的人卻笑到了最后。他和他的女人一起,一錘定音地提供了《芙蓉鎮》人性本體論的最終闡釋。
《芙蓉鎮》喜劇性特質的決定因素并不在于電影中幾個諷刺性的小品段落或演員的喜劇化表演,而是貫穿于電影敘事,它來自同那種生命本體論的內在政治性緊張相呼應、在符號和意義的界定和解釋權爭奪上展開的嚴肅的游戲性。與悲劇性的從人到非人、再從非人到人的生命本體論政治相比,我們在《芙蓉鎮》里更多看到的是喜劇性的符號游戲和意義爭奪的政治。李國香正確地指出,芙蓉鎮的宣傳其實都掌握在“黑五類”手里。革命標語是秦書田寫的,甚至字體都由他定。從電影開頭,他請示村干部寫標語要用仿宋體還是等線體,這個喜劇調子和它逐漸彰顯出的政治寓意就已經確定下來。在芙蓉鎮,政治語言在符號層面早已被充分空洞化,其宣傳掌握在專政對象手里,被后者在雙重意義上奪走了實質和“真理”:與秦癲子作為一個被管制的腦力勞動者的日常工作相對照,芙蓉鎮意識形態和宣傳領域的領導者在憑借權力和暴力無償役使和享有他人勞動時,逐步失去在文化思想和符號領域的生產力和領導權,變成脫離生產實踐、技能和組織的頹廢者,越來越深地陷入自身空洞、無能的自欺和白日夢中。
在此,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獲得了一種“后革命時代”的經典理論示范意義。就兩種獨立、對立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通過否定對方來肯定自己,在對方的臣服中獲得自己存在的客觀性“承認”而言,這種“生死搏斗”無疑也是“生命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但黑格爾“主人與奴隸”特殊的辯證意味卻更接近于馬克思主義“勞動創造歷史”的教導,因為奴隸的存在雖然在整體上被籠罩在主人的權力陰影下,但恰恰是這種被宰制、支配、征服者占有其勞動價值的服從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卻使得奴隸進入到一種“一切固定的持存的東西”都在其中“變化流轉”的“純粹的普遍的運動”,因為奴隸不得不為主人工作、服務,“在這種過程中在一切個別的環節里他揚棄了他對于自然的存在的依賴性,而且他用勞動來取消自然的存在”。黑格爾“對主人的恐懼是智慧的開始”的論斷不是基督教“對上帝的畏懼”的簡單翻版,而是在表述一種積極樂觀的近代觀念,即人通過具體的勞動完成對自然、對自身的自然屬性(包括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狀態和權力關系) 的克服與超越。因此,黑格爾“主人的真理在于奴隸”的論斷準確講應該是主人的對象“構成他自身的確信的真理性”,或“獨立的意識的真理乃是奴隸的意識”?。
在符號生產的特殊領域,由社會權力和主流政治- 道德體系確立的表意體系則在“秦癲子”的私人生活領域和私人語言里被剝奪了實質、篡改了意義,在純粹戲謔化的過程中變成自己的反面。在《芙蓉鎮》里,這是一場政治社會條件下小小的“智慧的起源”,但它象征的卻無疑是黑格爾意義上的那種“純粹的普遍的運動”;在這種隱形但不可遏止的運動中,自由與不自由、現象與本質都在發生變化。名與實在社會空間和符號空間里的位置在悄然對調、互換。與那種“從人到鬼、再從鬼到人”的往復運動相仿,當政治語言的社會性和嚴肅性在私人領域通過種種偷換、嫁接和創造性誤讀、誤用,被翻譯成一種玩世不恭但更符合更高、更具有經驗實質和表意功能的符號和意義體系時,一場認識領域和價值領域的顛倒和顛覆就已經處于完成狀態了。當這種不具有合法性的“私人語言”從私人領域重新進入公共領域時,整個社會經驗和政治觀念的結構都隨之改變,新的語匯、敘事、形象和道德出現了,它們對應一種已經具有事實性的潛在現實,一種新的社會主體,以及對世界的重新界定、描述和闡釋。
這種喜劇性的語言游戲出現在“像牲口一樣活下去”的悲劇瞬間之前,在情節上是主人公受到刑事懲罰的直接導火索,在寓言層面上則通過引入“人鬼之辨”而為那種富于生命哲學的存在本體論意義做好了鋪墊。在小說里,我們看到被打成“黑五類”的男女主人公申請結婚,鎮干部王秋赦打起了官腔:
他看了看秦書田呈上的“告罪書”,仿佛碰到了政策上的難題:“兩個五類分子申請結婚……婚姻法里有沒有這個規定?好像只講到年滿十八歲以上的有政治權利的公民……可是你們哪能算什么公民?你們是專政對象,社會渣滓!”
秦書田咬了咬嘴皮,臉上再沒有討好的笑意,十分難聽地說:“王支書,我們、我們總還算是人呀! 再壞再黑也是個人……就算不是人,算雞公、雞婆,雄鵝、雌鵝,也不能禁我們婚配呀!”?
在這一幕里,“敵我”雙方都有意把戰斗保持在語言的“字面”層面,玩起心照不宣的文字游戲。秦書田最后只得到了“兩個狗男女,一對黑夫妻”的對聯作為批示。知道這個結果后,胡玉音坐在灶臺邊哭,秦書田卻頗高興。他指出,“一對黑夫妻”,不管黑的白的,反正咱們是夫妻了。這里電影版本與小說版本幾乎一字不差,足以顯示這個段落的重要性:
“玉音,你先莫哭,看看這對聯上寫的什么?對我們有利沒有害呢!”秦書田邊開導邊把對聯展開來,“大隊干部的文墨淺,無形中就當眾承認了我們的關系。你看上聯是‘兩個狗男女’,下聯是‘一對黑夫妻’,橫批是‘鬼窩’。‘一對黑夫妻’,管它紅、白、黑,人窩、鬼窩,反正大隊等于當眾宣布了我們兩個是‘夫妻’,是不是?”?
在此,讀者和觀眾明確無誤地看到了“文革”激進意識形態在日常治理層面語言的失敗:因為“敵人”通過把自己“降低”為禽類,抓住的是生活的實質(男女婚配);而壟斷政治正當性的語言,則在“主人”意識中被完全空洞化、表面化,墜入形式主義的夢囈。隨著這種符號秩序的顛覆,一種新的生活實質和關于生活的理解占據了意義和意義解釋的舞臺。這種玩世不恭的智慧和語言符號層面游戲性的展開,不但使“意義”脫離了空洞的指涉框架而在一個新的闡釋空間里重新找到了具體性和實質性,一種新的關于“人”和“人性”的定義也把壓迫性、控制性的生命政治不動聲色地轉化為抵抗、反對、超越這種控制體系的思想自由和行為自主。這種“地下語言”或意義生產機制經由堅定不移的對生命的肯定而閃耀出人性的光輝。
作為反襯,語言游戲也出現在李國香與王秋赦的性挑逗中。李國香身為女性和領導的雙重身份,將二人推入一種對作為他們合法性基礎的嚴肅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戲仿和利用,即言不及義地把政治語言(“形勢”“匯報”“階級斗爭動向”“階級感情”等等) 用作私人情欲表達、試探和挑逗的密碼和委婉語(euphemism)。在電影里,這一切僅僅是一場掩耳盜鈴、欲蓋彌彰的情欲戲俗套,一種政治人物在言語行為上的“公款私用”和“假公濟私”。在這樣的喜劇安排下,占據合法性地表陣地的話語方式,在私人生活領域取消了自身的合法性,事實上變成了一種不可告人的地下活動。
九、多元決定的主角結構
與秦癲子“陽奉陰違”的堅韌主體性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原村支書、胡玉音的第一個愛人黎滿庚幽靈般的在場。這個人物雖然占據優勢地位,但自始至終顯得憂郁、優柔、意志薄弱、能量不足、精神渙散。電影開始,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治理方式讓鎮上的宣傳工作徒有其表,觀眾或已得出結論:這是一個對自己為之效力的崗位失去信心的干部。劇情交代的具體原因,是他失掉了愛的對象,準確地說,是為個人政治前途而主動放棄了愛的追求。如果把黎滿庚比作一個在政治和愛欲范疇里都被“去勢”的人,我們就能夠進一步欣賞電影男女主人公在經典人道主義意義上顯示出的生命力、勤勞、樂觀、積極進取。他們甚至在被剝奪了“人間”居留權的時候,也能夠毫不猶豫地在一個低于人的、“牲口”般的地下層繼續活著、欲求著、希望著。然而對于黎滿庚這樣的干部,“明天”卻已經在符號、意義、價值和希望的層面,像一個器官一樣被摘除了。
如果我們以這個次要卻關鍵的“中間人物”做一個中立的參照點,或可以為電影的結構特征再追加一個特點,即這部作品具有一種多元疊加的主人公結構,或主角的“多元決定”(overdetermined):它的四個主要人物都具備成為一號主人公的可能,作品可以圍繞其中任何一人來組織和結構敘事;或者說,《芙蓉鎮》可以有四種講法和讀法,它們圍繞一個共同的題材,卻能夠展示出不同的歷史面向、經驗構造和道德寓意。
《芙蓉鎮》可以是一個秦書田的故事,即從一個“下沉”或“埋伏”在小鎮上的“右派”知識分子的視角體驗民情、感受民間疾苦、體認政治文化同生活“自然常態”間的諷刺性矛盾的故事。我們在分析這部作品內在喜劇性的過程中,已經涉及這樣一個知識分子敘述的內在視角,在此不贅述。
《芙蓉鎮》也可以是一個李國香的故事。該人物在算“政治經濟”賬時不可謂不犀利,但在女性形象這個符號層面卻失去了感性具體性和倫理親和力,淪為芙蓉鎮世界里中性化的、外來的、抽象的異己性力量的體現。這個人物形象的戲劇性焦點在于其作為女性時的生硬、尷尬和別扭,而這實際上是被電影預先設定的:李國香形象一開始就從根本上違反了社會習俗和傳統中的女性社會角色和審美期待。這種被保守的習俗暗中規定的性別定位、審美趣味(“丑”),進一步在電影中轉化為一種道德和政治上的裁判。所以,李國香所代表的“左”的政治觀念,其挑戰自然的生活世界秩序的企圖注定失敗。這樣的戲劇/喜劇設置也顯示出謝晉“女性電影”的嚴厲一面:它服從并服務于意識形態立場和政治寓言無情的邏輯。
《芙蓉鎮》是一個胡玉音的故事。但胡玉音雖然被謝晉確立為頭號主角,卻是四個主要人物中唯一完全缺乏喜劇因素、也缺乏戲劇深度或豐富性的角色。她作為人道主義人性的化身,本身的形象塑造反倒只能是概念化、扁平、單向度的。它依賴于普通觀眾對政治事件的一般性理解,甚至依賴于女演員的明星效應來實現。胡玉音的主角資格事實上只來自敘事結構:她是故事中所有人欲望投射和日常“窺視”的焦點,是黎滿庚思而不得的前女友、黎桂桂的賢妻、秦書田的愛人、王秋赦白日夢的對象、李國香的競爭對手、谷燕山乃至所有芙蓉鎮居民抱有好感和同情的“芙蓉姐子”。在《芙蓉鎮》的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符號系統中,胡玉音是一個獎品性質的設置,誰得到她,誰就在這場關于“人性”“人道”和“幸福”意義的“有獎競猜”中成為勝利者,從而得到象征性的獎賞和回報。
一旦勞動、財富積累、土地所有權和社會- 政治權利再分配這些問題從人道主義情節劇的感性表象背后走到前臺,《芙蓉鎮》主要人物中最后一位———王秋赦的形象也就在意識形態空間里獲得了一個明確的位置和符號學解釋。這個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又在隨后“自然而然”的貧富分化過程中失去土地的人,在“文革”的激進政治運動中沖在第一線,成為李國香的搭檔。但他所代表的“第二次翻身”在小說和電影中都同生活世界的自然正當性、風俗傳統以及更深刻的人性概念相抵觸,因此必須被打入另冊。只有在王秋赦這個人物身上,謝晉主觀上刻意追求的那種人道主義的“深沉的悲劇”方才諷刺性地——也就是說,從反面——得以實現。只有這個人物最終在字面上突破了理性進入非理性,突破文明進入“癲狂”,從而在身份歸屬上被真正地固定在一個“非人”“鬼”或“幽靈”的位置上?。
相對《芙蓉鎮》童話般的結局,王秋赦因變瘋而被永遠從常態世界中剔除出去是一個更值得玩味的象征事件和時代標志,因為它從反面預示了“文革”結束后的新時期在日后行將展開的歷史內蘊和道德實質。與李國香不同,王秋赦雖然投身政治運動、不惜與整個自然社會為敵,但沒有正式的干部身份,因而也得不到體制的保護或接受。他是一個真正的赤裸裸的獻祭品或犧牲品,如今更須作為癲狂的樣本被放在進步的歷史時間的祭臺上示眾,借以警示和阻嚇一個瘋狂年代的借尸還魂。他存在的肉身意義上的“實”同秦癲子名字中“癲”字這個“(虛) 名”恰好構成了一對戲劇性的所指/能指間的對應、借用、轉移和歸位關系。每一個轉折時期都需要借助這樣一種驅魔儀式,通過制造一個新的歷史斷裂來否定和克服上一個歷史斷裂,從而把自身確立為自然、常態、人性的歷史秩序和價值秩序。在此,新的生存權概念和所有權概念的相互作用、結合,一同產生出新的人的理想和它在社會主體層面的合法性基礎。
基于新時期的社會意識,必須將一個“非人性”“反理性”“無法無天”的“舊時期”(即特定時代語言里的“新時期”能指) 打入謬誤、瘋狂、黑暗和邪惡的領域并使其永不得翻身,再將它永遠鎖閉在一個停滯、封閉的時空和精神狀態內。在小說和影片的結尾,我們看到的正是對“文革”政治語言和政治邏輯的符咒性質的終極戲仿?。
從王秋赦到王瘋子的戲劇性轉變,是一種意識形態編碼和時間敘事學意義上的歷史寫作(historiography) 合流的結果。通過把激進、造反、抽象的概念思維和政治思維打入與文明截然對立的“癲狂”范疇,通過人與非人(鬼魂)、正常與非正常的區別和辨識,《芙蓉鎮》把一個政治社會的符咒變成了一個經濟社會的符咒,以用來壓制和震懾一切可能出現的歷史回潮。王秋赦變瘋既象征了“左”的社會能量內部的教條化、空洞化和枯竭,也通過將其意識空間的突然崩塌戲劇化而同時引入下一個歷史時代及其價值體系的歡慶場面,即在小說結尾處芙蓉鎮居民“送瘟神”的儀式?。
沿著當代史的歷史軌跡倒回去看,我們認識到20世紀的幽靈在財富增長和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商品化過程中被不斷驅散。通過人道主義戲劇化呈現與定格,“經驗教訓”業已變成通過否定過去而將社會向前推進的動力;這被賦予了一種歷史的起點或時間重新開始的寓意。這個起點需要構建一個絕對的斷裂來確立新的時間感、方向感和新的價值本體。上一個歷史時代的圖騰于是經由“人性”與“人道”的轉換而變為下一個歷史時代的禁忌。這種禁忌同樣帶有威嚴的、不容挑戰的、區分敵友并將“非人”或“反人性”因素排斥出“人民”范疇的意志和能力。雖然這個禁忌彌散于“新時期”知識分子意識和話語之中,客觀上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但它仍然只有在同國家本身的正當性歷史敘述相匹配并重合在一起時,方才充分顯露出內在的政治強度。在此過程中,“人”的概念連同它所需的制度保障和社會本體論“意義”,都在商品交換、私有財產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規范、倫理和生活方式里被系統地構建出來。
①⑧⑨ 顧志坤:《大師謝晉》,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頁,第112頁,第114頁。
② 這一傳統最集中的表述是“文革”期間圍繞“樣板戲”制作形成的“三突出”戲劇原則。
③ 古華在自述文章《話說〈芙蓉鎮〉》中介紹了這部小說與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路線的執行等“文革”后重大歷史轉折的共生關系。參見古華:《芙蓉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頁。
④ 《芙蓉鎮》拍攝過程中曾遭遇一些“折騰”,對此,導演本人的反應是:“我的每一部片子幾乎都經過折騰……但有一點我卻感到特別的欣慰,我的所有這些經過折騰的片子都跟人民群眾所關心的重大問題息息相關的,我的片子說出了中國人民的心聲,揭露了中國社會中尖銳的現實矛盾,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是打不倒的。”(《大師謝晉》,第113頁)
⑤ 為了使劇本更加完善,制作方于1985年在長沙召開了改編學術討論會,陳荒煤、康濯、徐桑楚、古華、董鼎山、李陀、黃健中、阿城、許鞍華等文學藝術界人士與會,為改編出謀劃策。參見《大師謝晉》,第108—109頁。
⑥ 比如在《芙蓉鎮》編劇的人選上,謝晉沒有找合作過多次的李準,而是選了比自己低一輩的作家阿城。
⑦ 所謂“謝晉電影模式”由朱大可在1985年7月發表于《文匯報》的一篇文章提出,隨即在電影批評和電影研究界引發一系列討論。參見倪祥保:《三十年后“謝晉電影模式”再思考》,《當代電影》2016年第9期。
⑩?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Malcom Heath,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6, p. 5, p. 17. 中譯參考了羅念生譯文(亞理斯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頁,第30頁)。
?????? 古華: 《芙蓉鎮》,第32頁,第52—53頁,第157—158頁,第34—35頁,第150頁,第151頁。
? 關于王秋赦的人物形象,參見《芙蓉鎮》,第19—24頁。
? “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在西方語境里有不同的概念內涵和發展脈絡,此處指的是福柯在《性史》第一卷《知識意志》中提出、日后在法蘭西學院系列專題講座中進一步闡述和發揮的概念,即那種直達生命肌體的肉體、生物、生理層面,對之施加積極影響,謀求“管理、完善、繁衍,使生命從屬和臣服于嚴密的控制和全面調節”的社會力量和政治權力。福柯認為,相對于傳統的“主權-司法-話語”權力系統,生命政治代表一種對肉體生命整個生物性存在過程及其社會條件更為系統、深入、無所不及的生死予奪及徹底改造的裁定權、戒律權和規范權。與此同時,“生命政治”概念也應該包含個人和集體對國家、資本、市場所掌握的“生命權力”的激烈抵抗。本文主要在后一種意義(即抵抗) 上使用這個概念。Cf.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1976,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pp. 135-139.
? 雖然“經濟人”概念在19世紀后期(比如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里) 才被頻繁使用,但它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已經出現。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把人的利己本質作為一種經濟理性原則同利他、互惠的道德原則并列。homo economicus在拉丁文文獻中可以追溯到更早,一般認為是同homo faber(制造工具的人)、homo sociologicus(社會人) 等并列的基本屬性,直接從屬于homo sapiens(人類)。“經濟人”的特定含義是一種經濟理性和功利思維,即運用一切必要手段去追求和獲得物質/金錢意義上的利益、安全和幸福。本文強調這個概念廣義的、歷史長時段中的“人本主義”含義,即這種“經濟理性”同一種近代意義上的生命哲學和存在本體論之間的重合,而不是直接在當代新自由主義意義上利益最大化、成本-收益計算和市場調節等技術和教條層面使用它。
? 參見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26、129—130頁。
? 據與會者李陀口述回憶,在1985年長沙討論會上,阿城堅持一個與眾不同的看法,認為電影《芙蓉鎮》的主人公應該是王秋赦,劇本應該以這個人物為核心來結構和組織情節。
? 參見古華:《芙蓉鎮》,第220—232頁。電影版里簡化為王秋赦敲鑼喊“運動嘍!”
? 參見古華:《芙蓉鎮》,第1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