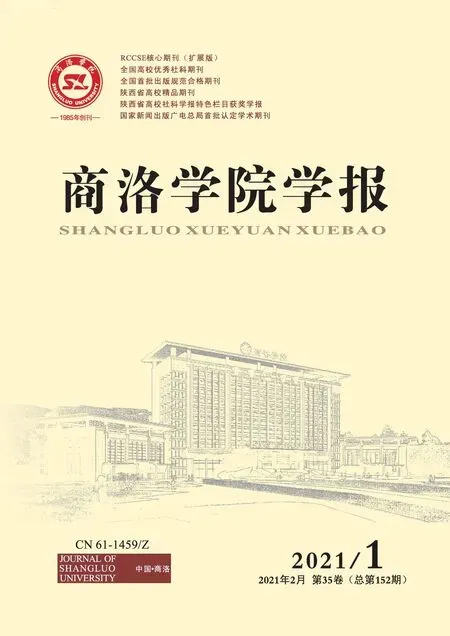《暫坐》:女性情誼與城市、男人及權力的關系
李雨庭
(陜西國際商貿學院文學與教育學院,陜西西安 712046)
賈平凹一直有“為生民立命”的追求,他從不間斷地用文學記錄時代風貌,同時也在努力開掘自我書寫的疆域。迄今為止,賈平凹的17部長篇小說,不管是記錄時代變革的《浮躁》,探尋農村問題的《秦腔》《帶燈》還是反映城市問題的《廢都》《土門》,亦或書寫農民進城問題的《高興》,以及革命問題的《古爐》《老生》,都可以看出作家發掘各類題材來探尋社會發展問題的時代責任感,也可以看出賈平凹謀求建立自我話語體系、文化價值、時代價值的文學理想和追求。因此,他無論是寫鄉土還是寫城市都有一種厚重而質樸的生命力量。《廢都》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秦腔》對故鄉頹敗的挽歌,《山本》的凡人英雄命運,無不是由瑣瑣碎碎的生命印記勾連起社會的大問題,廢都、廢鄉、廢人,賈平凹都做過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而總體風格上,賈平凹是以鄉土小說示人,對城市的書寫也帶著一股鄉土氣息,無論是《廢都》中的西京城,還是《高興》中的西安市,都是土墻陋巷人力車、大蒜就饃油潑面。那么,寫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的故事就成為賈平凹寫作必然的突破口和拐點。這便是《當代》2020年第3期全文推出的《暫坐》。有研究者認為“《暫坐》與以往兩部長篇《廢都》《山本》具有多重互文關系[1]” ,“敞開了女性與日常生活相互激發的生產性空間”[2],是“現代都市女性的紅樓余韻”[3]。《暫坐》拓展和深化了日常生活詩學,用不到一年的時間背景,提供了理解近十年日常生活的意義,并由此折射出精英大眾社會地位與精神姿態的此消彼長。
“《暫坐》寫城里事”[4]。賈平凹說:“在西安已經生活了四十多年,對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從客廳到廚房,由這個房間到那個房間,無論多少拐角和門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4]這四十多年,賈平凹早已經從農村小伙子變成了西安城里年近七旬的老居民。而且,喜歡在各個年齡節點上用作品來做標記的賈平凹,必將在此傾注更多的心血。“《暫坐》就試著來做撐桿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4]因此,小說除了一貫的“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敘述之外,尤其注重對城市現代化、時尚性等符號化的展現,揭示現代城市女性閨蜜情誼、生存狀態與資本、權力等的關系,為全面認識城市提供了一份時代紀錄。
一、城市與女性
城市是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而形成的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的居民區。城市的發展不僅為女性提供了接受教育與多樣化就業的機會,而且其開放性為女性廣泛參與社會生活的各行業領域以及個體能力的提升都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與選擇余地。尤其重要的是城市為女性的價值觀與自我意識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場域和物質形態。《暫坐》中賈平凹使用一貫的“密實流年”敘事手法,用人物加地點的空間構型來呈現西京城里一群經濟獨立、生活體面的女性的日常狀態,如“海若·茶莊”“陸以可·西澇里”“羿光·拾云堂”“希立水·西明醫院”“虞本溫·火鍋店”,以及“應麗后·香格里拉飯店”等。《暫坐》以“伊娃·西京城”開始,又以“伊娃·西京城”作結,對生活于西京城的十幾位單身女性進行幾乎平均著力的敘寫,冰糖葫蘆式地串起全文三十五章共18個人物的故事。
賈平凹通過這種冰糖葫蘆式結構將西京城的空間與歷史、文化、消費時尚、女性欲望直接連接起來,并借助這些符號的呈現和隱喻,使古老的西京城變得更加現代、生動和性感。小說開篇“伊娃·西京城”一章,以俄羅斯留學生伊娃為主角人物,講述了西京城的人情關系和日常生活:房東大媽一大早去菜市場買材料為伊娃作糊爛餅、大爺打罵叫春的貓、丁字路口汽車追尾罵仗,一派鬧鬧嚷嚷的人間煙火氣。隨后伊娃便去找老朋友海若。海若是暫坐茶莊的老板,不僅人長得漂亮,還很有錢,辦事利落大方,以她為核心團結起了西京城各行業的美女老板:能力廣告公司老板陸以可、銷售醫療器械的嚴念初、汽車專賣店老板希立水、火鍋店老板虞本溫、藥店老板向其語、包租婆應麗后、全市最大的紅木家具店老板司一楠、華縣劇團演員徐棲、病美人夏自花、出國旅游的馮迎、與港商曖昧的辛起。這些美女老板在西京城都有著傲人的事業和優質的人脈資源,每天主要內容就是吃喝娛樂跑關系——茶、酒、咖啡、養生、美容、聚會、豪車、保齡球、高爾夫。她們的日常就是出入高消費的中大國際商廈、豪華的香格里拉酒店、繁盛的購物廣場、西餐廳、火鍋店、美容院、健身房、桑拿能量倉,而且閨房談天也是養生、美容、時尚、消費,以及各種人情關系。
從賈平凹的城市書寫來解讀,可以把《暫坐》看作是《廢都》的姊妹篇。《廢都》寫農村出生的大作家莊之蝶在各種關系網絡中疲于應付,創作力衰退,只能以偷情獵艷來刺激自己麻木的人生和創作的靈感,小說對城市的浮躁和功利批判色彩很濃郁。而《暫坐》是寫名作家羿光周圍聚集著一群因為各種原因而離異或單身的城市女人,她們通過各種關系網絡在城市謀求事業和愛情,最后雙重失據的故事。這些女性每天都神采奕奕地出入于西京城的高檔娛樂和消費中心,無拘無束地走街串巷。發達的物質文明讓她們充分享受城市的便捷,實現物質滿足的快樂——流行的“奶奶灰”,陸以可的手模般的保養,嚴念初的輕奢極簡風,徐棲用澳洲深海魚油,向其語的太赫茲能量理療,紀梵希、蘭蔻、玻尿酸、膠原蛋白、蘋果肌、美甲等。這些代表著現代城市的消費符號,直接組成了西京城頗具現代色彩的物質人文景觀,其中的城市味道也自然比此前的任何一部小說都來得鮮明。與涉及城市的《廢都》《白夜》《土門》《高興》相比,《暫坐》所表現的城市,不僅僅只是展現男性欲望的場域,更是一個張揚女性欲望的舞臺。
當然,女性為追求時尚和美貌所付出的精力與代價,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取男性的垂涎,以及由此而得到更多的社會資源。也就是說,她們的美是一種獲取社會資源的手段。隨著故事的發展,人物的秘密和命運被一一揭示,這些幾乎每天都碰面的“閨蜜”都隱藏著不能為外人道的地下情和秘密情人。很自然,金錢、權力、身體交易是其地下情的基本內容。如,身具異域之美的伊娃與名作家羿光茍且,嚴念初騙婚教授的同時與別的男人生孩子,夏自花是已婚男人的情人也有私生子,司一楠和徐棲的同性戀,辛起被港商包養,這些女人在時尚高消費背后是心照不宣的錢色交易。也就是說,現代城市的基本特征是以女性的身體作為商品來交換與消費的。這些腳踩高跟鞋,走路帶風的“成功”女人光鮮的背后都有無數不可告人的秘密。賈平凹借人物司一楠之口大發議論:“是什么讓我們褪色呢,是貪婪?是嫉妒?是對財富和權利的獲取與追求?”[4]這番靈魂之問代表了作者對女性欲望的理性審判與適度節制的敬告。這與《廢都》的頹廢和性狂歡展示有明顯的區別。《廢都》整個文本氛圍是一種壓抑的又頹又喪的氣息和尖銳的暴露鋒芒,而《暫坐》的現實描摹性大于批判性,也沒有將城市的虛偽、浮躁、功利、墮落等選擇性地托出的酣暢淋漓,而是回歸于一種平實——講幾個關于女人的小故事的平實。不管是記錄城市歷史和當下的人文景觀,還是把握一種社會風氣和追尋,作者都對其給予理解和同情,并且有一種“饒恕一切”的寬容。
《暫坐》從日常瑣事的發現中書寫西京城的精神氣質,雖寫的是城市,卻有一股濃郁的鄉土氣、平民氣。這種鄉土氣、平民氣既是《暫坐》的特質,也是作為陜西文學代表作家的典型特質,是西北內陸城市的特質。賈平凹對西京地域人情的描繪融于一點一滴的生活瑣事中,用雅俗共賞的市井氣折射出十三朝古都的實質內涵。“西京十玉”做美甲、涂蘭蔻,烈焰紅唇喜歡吃的常常是葫蘆頭和羊肉泡。“饦饦饃端上來后,把碗放在腿面上,雙手掰著”[4],這是王院長、嚴念初約應麗后談還款合約后在閱江樓上的午餐,有錢有地位的名人和兩大美女的正餐土氣、實在。辛起一心想過上有錢人的生活,做了香港老板的情婦便和老公鬧離婚,悄悄將家里的東西轉移出來存放在海若聯系的倉庫里:小馬扎、竹籃子、燒水壺、錘子、鏟子、鉗子、鍋碗瓢盆,甚至連洗腳盆都提著,實際到了斤斤計較的程度。年輕貌美,打扮個性的同性戀司一楠有著全市最大的紅木家具店,為眾姐妹買的零食也離不了瓊鍋糖。寫詩的高文來把口水吐在茶杯,報復范伯生對自己的傲慢。純凈無邪的人才有潛質成為詩人,而這個西京城詩人卻充滿了市井小人的無賴行徑。這就是西京城,作為西北內陸大城市,經濟活動追逐現代,人們骨子里依然是傳統的農業特色,而這一群單身女人又集美貌時尚于一身。如此,西京城的“土”與現代女性的“洋”便奇異地結合在一起,使《暫坐》呈現出別樣的城市景觀和獨特韻味。
總體而言,從《廢都》《白夜》《土門》到《暫坐》,隨著對城市以及城鄉關系的審視、思考,賈平凹的城市書寫,有一種明顯的平實和從容。即使帶有夫子自道性質的關于字畫價格和城市名人的言談都多了幾分坦然、幾分從容的自我調侃與解嘲。賈平凹“對城市題材的寫作從個人城市生活的心靈苦楚跳脫出來”[5],關注到中國城市的普遍而真實的生存樣態,表現出對今后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懷。
二、在男性與權力中變形的女性情誼
《暫坐》相對于賈氏其他小說,最為突出的特點便是對城市女性群像的塑造。《暫坐》成功地描繪了一群現代城市中經濟獨立、生活體面的女人的生活日常與對情愛的追尋。小說對人物的塑造不再集中于某一個男性或女性,而是對每個人物幾乎平均用墨,其章節主要用十姐妹、伊娃、辛起、茶莊的服務員小唐、小蘇以及三個男性的名字和活動地點作標題,由此可以看出,賈平凹的現實主義觀念是基于生活本身的,是融于日常小人物的。也就是,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中,人前的光鮮與人后的卑微才是真實的人生。對城市中的“白富美”群體,賈平凹集中于她們的姐妹情誼,一如既往地構筑生活的世俗化和世俗化中的脈脈溫情。
姐妹情誼是城市女性在你死我活的商戰和男性之戰中結成的遮風擋雨、相互取暖的港灣,是她們退回自身、相互傾訴,尋找自己的方式。《暫坐》的主要線索是“西京十玉”的姐妹們輪流著到醫院看望、照顧生病的夏自花。美人夏自花患了白血病,需要換血小板,陸以可便在自己員工中重金尋找血型符合的人,海若還將獻血小板的小高收編到自己的茶莊上班。姐妹們不僅生活起居上照顧夏自花和她的家人,還時常帶著她的老母和兒子去秦嶺里散心。夏自花逝后,又給夏自花買上好的藍田玉骨灰盒,安排其老人和兒子的生活去處。虞本溫請姐妹吃飯用的都是上好的材料。希立水幫助鬧離婚的辛起,收留她住宿并給她出謀劃策。徐棲將自己積累并親測有效的養生秘方無保留地傳給眾姐妹。司一楠兩肋插刀地幫助應麗后解決碰瓷的無賴。十姐妹常常串門逛街聊天聚會,暫坐茶莊老板海若送給她們每人一塊價值幾萬的玉佩,像大姐大一樣將眾姐妹團結到一起,每到新茶,都是不計成本地送給她們嘗鮮。而這些姐妹送客往來也總是照顧海若的生意。她們的姐妹情誼是全書最為動人和溫暖的,在賈平凹一貫的寫實風格中,不管是城市高樓、巷道的變化,還是人物言辭、衣著的發展,在鬧鬧嚷嚷的生活流中,都獨到細致地展現了城市生活的瑣碎性、豐富性以及人際關系與交往原則,體現了賈平凹對城市的理解和對女性間閨蜜情誼的稱贊。
隨著故事的展開,她們的姐妹情誼的可靠性和純潔性又被作者不斷地拆解和否定。雖然不能否認這種姐妹情誼有真誠和真摯的成分,但是一旦涉及經濟利益和男性情感,這種閨蜜情感又異常地脆弱。城市的物質、經濟、權力、男權等利益是間離、侵蝕這種情感的利器——經濟利益受損、對優質男人的占有、城市的異化、男權的入侵等隨時可能瓦解這種看似很深“很鐵”的“閨蜜”的感情。正如陳染所書寫的姐妹情誼“就像一束懸置半空的凄艷之花……只能永遠地半懸于空中,升華燃燒或摔碎消亡都是奔赴絕境和毀滅”[6]。
賈平凹在敘述城市女性的獨立體面時,也看到了她們的種種“病癥”和情感的不長久性,并揭示了生存和欲望本能下女性的個體體驗和困境,挖掘生命個體精神世界的困頓與迷失,從而更貼近城市以及城市中生存的女人們。嚴念初任擔保人,介紹應麗后將一千五百萬借給了醫院王院長的朋友,王院長從中分得利息的抽成,嚴念初也因此將醫療機械賣給王院長的醫院進而獲利。后來因為王院長的朋友資金斷鏈跑路,嚴念初便退出直接擔保人的角色而將應麗后置于錢財兩空的境地。親密的閨蜜成了不愿同處的仇人。向其語為走近范伯生將司一楠和徐棲的同性戀關系作為談資笑料說給范伯生,讓司一楠和徐棲被范伯生譏笑。而范伯生走近向其語不過是為了給自己的書畫協會拉贊助。眾姐妹對名人羿光各懷心思。她們中無論哪一個,只要和羿光單獨相處時,都會不由自主地有其他姐妹會怎樣的猜想。女人間的防備和嫉妒一直穿插在熱熱鬧鬧的關系中,當下女性在城市中謀生與謀愛的風采與艱難都流淌在字里行間。
賈平凹對城市中這一女性群體的展現、審視,做出了關于女性生存的有益思考。一方面,城市的多元價值觀念,讓她們視野開闊,有清醒的商業頭腦,看待人生和事業的方式和眼界都與傳統女性不同,尤其懂得利用年輕貌美的優勢換取生活資料——利用身體優勢尋找優質的人脈資源和攀附有錢有權的男性。海若長得漂亮,又因為開了西京城的上好茶莊,便和市長秘書關系密切,能接到市政活動用茶的高額訂單,也經常幫市政官員兌換黃金,你來我往中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應麗后把錢借給王院長,本想獲得豐厚的利息,當然最后連本金都沒有收回來是意料之外。辛起急齁齁地與香港老板上床,是想借他的經濟力量迅速實現階層跨越,過上像希立水她們一樣有錢有閑的生活。由此,我們看到了商品經濟時代城市女性在物質上的豐富與精神支撐上的脆弱,看到了女性進入城市、立足城市的艱難。事實上,充滿欲望和權力關系的城市以及城市中投機獵艷的男性是無法支撐起女性的情感安慰與事業需求的。他們身上沒有女性救贖的希望,這就更加劇了女性在追求過程中的悲劇性意味。
另一方面,城市女性在追求現代化物質和享受的過程中,物質和金錢的極大豐富和滿足并沒有讓她們真正感受到快樂和在城市中安身立命的歸屬感,反而是孤獨、焦慮和各種復雜的關系背后那種煩人的咬嚙充斥了內心。應麗后因為在王院長處損失了一大筆錢,高價請到了要債公司,不僅錢沒有要回來,還被要債公司的章懷糾纏;章懷私自將王院長的醫院和門店鬧得雞犬不寧,還不斷勒索應麗后。嚴念初嫁給了收集玉石的老教授,分得家產后便迅速離婚,尋求新的對象,被圈子里的人賤看。辛起為了香港老板與老公鬧離婚,關系變僵之際,香港老板卻已經走人了,辛起落得個賠了夫人又折兵。左右逢源的茶莊老板海若因為市長被雙規而成了西京城權力網上的炮灰。這些人心的不足和貪婪的悲劇,讓讀者看到了城市女性在消費主義思想下的異化,這種異化又加劇了生命的孤獨和荒蕪感。所以應麗后即使擁有“全市最貴的精裝修豪宅”,有專門的麻將室和“香港產的電自動麻將桌”[4],也填補不了她內心的寂寞空虛。海若天天盼著西藏活佛來點化自己,時時彈奏古琴,也無法掩蓋自己焦慮、慌張的狀態……這一群城市女性,看似每個人都有著極為紅火的生意和事業,有上等階層的消費能力和風光,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權利,住房寬敞、裝修豪華,但她們依然沒有歸屬感,依然將多金的男人作為自己人生的最后歸屬。她們為一直保持水嫩的肌膚、立體的面孔煞費苦心,為打造姣好的身材、美妙的曲線以保證身體不貶值而殫精竭慮。“霧霾這么嚴重啊,污染精神的是仇恨,偏執,貪婪,嫉妒,以及對權力、財富、地位、聲名的獲取與追求”[4],就是對她們的精神的寫照。她們的內心是孤獨和空落的,籠罩在全城的霧霾像魔咒一樣籠罩著她們的命運。需要指出的是,女性真正的時尚是追求漂亮自信的人生態度、追求美好生活的生活熱情,是自身生存質量的提升,而不是取悅男性的某種性意味之美。
總之,《暫坐》的底色依然是傳統的現實主義,整體風格也沒有變化,依然是以定型的人物形象來承載作家對現實與歷史、物質與精神世界的思考,略有不同的是敘述視角的變化,即賈平凹嘗試在現實主義的基本技法上用不同的立場觀察女性日常,以全方位展現社會生活的面貌。《廢都》是傳統全知視角敘述,《白夜》是對《廢都》中城市閑人的繼續書寫,依然是全知視角,而《高興》則是從進城討生活的社會底層視角“看”城市審視現實,反映社會問題。《暫坐》對城市的書寫,注重用生活的日常、瑣碎和混雜展現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以及生命在復雜的關系中趨于荒蕪的沉重,既有貼合實際的生活質感,也有尋求精神飛揚的指向,是一副溫馨與凄涼交織、平民性與享樂性共存的西北城市圖景。
三、名人優越感
《暫坐》在展示女性的獨立風采和不幸之際,還有對男權和名人的傲慢與得意的不自覺的維護。從賈平凹的各種訪談錄和后記中能夠看到他對女性的喜愛和尊重,也有擺脫男性中心主義思想的努力,但是他的小說又無處不在地充滿了男性中心主義思想。《廢都》中的莊之蝶,《高老莊》中的古漢語教授子路,《秦腔》中的作家夏風,《帶燈》中的元天亮……這些人無不是名氣震天、美譽遠播。同樣,《暫坐》表面上講了十幾位城市單身女性的事業和感情,貌似想讓男性退場,讓城市文明所包含的欲望、爭斗、算計、虛偽、圈套,被單身的女人團展示出來,但是,其核心依然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實質是以大作家羿光、書畫研究會的范伯生、醫院王院長等為核心而組成的一個關于資本與權力相互糾纏的“寡婦俱樂部”。
從章節安排來看,全文三十五章,用了五章寫羿光及其拾云堂,比“西京十玉”占的篇幅都多,不僅如此,即使羿光沒有出場,而圍繞眾姐妹展開的話題都沒有離開過他。羿光成了這一群驕傲的女人之中的驕傲。他是西京市的名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作家,隨便出手都是美文,書畫作品在西京的官界、商界、民間都暢通無阻、價值不菲,他所到之處必定是蓬蓽生輝。文中羿光與這一群女人都有程度不一的曖昧關系,他把自己的名氣和成就當成向女性示好、誘惑女性的工具。文本明顯表現出羿光對“西京十玉”的性欲眼光,占有的氣息很盛。
與其早期的《廢都》比較,就會發現,《暫坐》與《廢都》在對名人的迷戀上并無二致。這一方面源于作者思想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資本與權力的關系、無處不在的對女性的美貌和身體的覬覦及消費現象。莊之蝶和唐宛兒偷情之后,唐宛兒說:“你玩兒女人玩兒得真好!”[7]羿光第一次見到伊娃便霸道地“壁咚”,“卻一下子,把伊娃推靠在柜面上,吻住了嘴”[4],并索要了伊娃的一根頭發收藏在小瓷瓶里。第二次見面便給伊娃畫像,“從頭吻到腳,從腳吻到頭”[4]地撩逗起了伊娃的“獻身”欲望,讓伊娃事后想起“他才華出眾,談吐風趣,是這個城市的名人啊,并不覺得自己吃虧受屈”“也有了那么一絲兒的得意”[4],像極了古代帝王寵幸嬪妃后的授與受的滿足。羿光半夜三點給海若打電話“你來吧,你來吧,需要你來!”[4]曖昧的語言讓單身的海若“感覺到一種熱流從腳到了頭頂”[4],便開始洗澡、穿上“黑色的網狀的緊身內衣”[4]欣然前往。羿光也收藏了夏自花的頭發,他給夏自花寫的挽聯,眾姐妹都看不懂,羿光卻說夏自花能懂,個中的意味可謂深長。管中窺豹,長相普通卻浪漫多情、名氣大的羿光和這些單身女性都有故事,他的女性朋友無一不是非香即艷。在這些由美而及性的香艷故事里,他看重的是女人的姿色,他把女人看成尤物和性的符號。讀者也可以明顯看到羿光的搭訕藝術極具誘惑性,他無比地憐香惜玉,將收藏女人的頭發、把玩女性的身體當成是對女性的“真情”和“欣賞”,其實質都是以體諒對方和“知己”的名義,行了猥褻和性侵的事實。他的“體諒”是一種高級的PUA(搭訕藝術家,泛指很會吸引異性的男女),是一種性的欲望和沖動,真愛的成分要打很大的折扣。
四、結語
從當代文學表現女性情誼與生存空間的主題來看,《暫坐》可以當作賈平凹以文學的方式記錄城市生活和時代女性的一個典型文本。《暫坐》以一種男性視域展示了城市女性在商品經濟生活中所達到的成就與不幸,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當代女性及其成就與困惑。《方舟》(張潔)表達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濟轉型時期女人強烈渴望以平等的人格獲得事業上的成就,以確證自己的女人之智慧和能力的時代愿望。張潔以其敏銳的視角看到女性獨立生存的困難所在:整個社會難以用一種平等的姿態接納與評判女人,所以即使女性教育程度高、事業成功,但是她們的悲劇命運卻很難得到改變。《兄弟們》(王安憶)從女人的妻性和母性出發,探索女性的個性和事業如何在男性世界被軟硬兼施地剝奪掉,因為那無處不在的男權規范和思想話語,必然讓女性陷入自我懷疑與自我解構的境地。新世紀之初的《小姐,你早》(池莉)依然是描寫年齡、經歷、層次截然不同的三位女性因遭遇了被男人欺騙、玩弄、拋棄的命運而結成的姐妹情誼,她們相互扶持,制定針對男性的“反玩弄”計劃,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生活。還有《無處告別》(陳染)、《相聚梁山伯》(徐坤)等,包括《暫坐》,都共同指出了女性在城市生活中的艱難,他們既展示了女性情誼可以作為她們生存孤寂的心靈安慰和溫暖,又意識到它的脆弱和可疑性,靠它在男權社會立足,顯然是不靠譜的。《暫坐》中,與西京市的名片羿光和市長秘書關系不一般的海若最后不是被中紀檢委帶走了嗎?她安身立命的茶莊不是被炸毀了嗎?面對城市女性的不幸與煩憂,看來不管是男作家還是女作家都無法給出一個光明又可靠的前景。女性的生存與情感歸依,將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總之,《暫坐》以溫情的筆調記錄了生活于西京城的時尚女性的煩惱人生。相比于傳統男性筆下女人之間的爭風吃醋、勾心斗角(如蘇童的《妻妾成群》《婦女生活》),賈平凹寫到女性間感人至深的姐妹情誼,是一大進步。但是,這種情誼在賈平凹的筆下又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文學中的男權色彩。小說中這一群單身女性不約而同地拜倒在男人的錢包和權力下,暴露出諂媚與精神“缺鈣”的病相,對名人“羿光”的愛慕和維護讓她們集體患上“花癡”病。賈平凹雖然寫出了這一群獨身女性的時尚瀟灑,但是她們的愛美觀與那種將美麗漂亮當做一種生活態度、追求女性權利的女性觀相比,還是有一定的距離。當然,這種表現一方面源于作者思想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生活中確實存在對名人的投機利用,希望通過結識、奉承名人而讓自己攀上某種人脈關系,借此從中獲利的現實,反映出現代社會追名逐利的功利和浮躁。在此意義上,《暫坐》在城市女性書寫之外,還揭示出一種另類的文化價值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