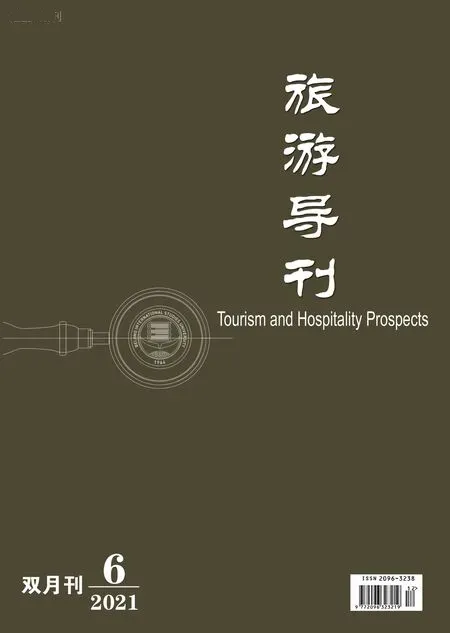自然災難地居民風險知覺與旅游支持度的關系研究
——以汶川大地震重災區北川和都江堰為例
鄭春暉 張 捷
(1.廣州大學旅游學院 廣東廣州 510006;2.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 江蘇南京 210023)
引言
大規模自然災害的負面影響往往持續時間較長。大規模自然災難的爆發,會破壞已有和諧(自然、社會與身心和諧)(Tuan,1979)。在一些城市的災后恢復重建過程中,旅游業被認為是經濟恢復和文化重建的重要方式而受重視。那么,生活在次生災害高風險區的居民是如何看待災后旅游業的產生與發展的?對未來災害風險的判斷、對已發生和未來可能發生災害的復雜情感、對風險的防御行為傾向等,是如何影響他們對地方的情感依戀和旅游支持度的?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者思考。以往研究多從“旅游影響”角度切入,從旅游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影響方面來分析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近年來,學者們呼吁從“旅游感知”的視角來識別各種影響居民旅游感知的內外部因素,如從更廣義的生活質量/安全感維度來探討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Wright & Sharpley,2018)。對風險的感知是災區居民生活的重要方面,直接影響居民的幸福感。因此,從更廣義的社會現實和居民生活質量維度出發,探究風險知覺對地方依戀和災后旅游支持度的影響,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我國屬于地震頻發地區,地震的社會地理影響與災后恢復、危機知覺與地方感的關系等是地理研究的重要課題。汶川大地震是我國繼唐山大地震之后傷亡最嚴重的一次地震,其負面影響及災后恢復會延續較長時間。鑒于對災后社區旅游態度的研究相對缺乏(Wang & Luo,2018),本研究旨在探究北川羌族自治縣和都江堰市居民對災后發展旅游的支持度,以及這一態度如何受到更廣義的社區生活質量(風險評價、風險防御和地方依戀)的影響(莊春萍、張建新,2011;Wang,2019)。社區居民既是災后旅游凝視的對象,也是旅游發展的主體,本研究有助于豐富居民視角的災后旅游研究,有助于厘清旅游發展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災后恢復的機理(Wright & Sharpley,2018)。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自然災害與旅游發展
我國是自然災害多發的國家之一(何景明,2012)。伴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和強度逐漸增加,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影響。自然災害與旅游業的關系復雜而微妙,一方面自然災害的爆發會對旅游業產生巨大的沖擊,另一方面又可能催生出一些新的旅游地(Wright & Sharpley,2018)。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自然災害與旅游業發展的關系(Wang,2009;Hughey & Becken,2016),研究議題包括自然災害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Becken & Hughey,2013)、旅游業的脆弱性與恢復力(Tsai,Wu & Wall,et al.,2016;Guo,Zhang & Zhang,et al.,2018;Lin,Kelemen & Tresidder,2018)、旅游接待業的災害規劃和風險管理(Laws & Prideaux,2006)、自然災害地的黑色旅游研究(Tang,2014;Yan,Zhang & Zhang,et al.,2016)等。對自然災害地的旅游研究主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大方面展開。供給方面的研究多從宏觀層面探討災后旅游的開發與管理(吳春濤、李熙、段金莉,2016),需求方面的研究則多圍繞旅游者為什么參觀災害發生地(陳星、張捷、盧韶婧等,2014;王金偉、張賽茵,2016)、災后旅游體驗(顏丙金、張捷、李莉等,2016)、滿意度(Tang,2014)和旅游意向(Qian,Zhang & Zhang,et al.,2017)等展開討論。
總體而言,當前從居民視角關注災后旅游的研究相對缺乏(Sun,Zhou & Wall,et al.,2017)。自然災害發生后,旅游發展將對社區及災后恢復過程產生直接或潛在的影響(Wright & Sharpley,2018;Wang,2019)。社區是面對自然災害的重要社會結構單元,在災害風險應對與災害防御中具有基礎性作用。因此,加強居民視角的研究尤為重要。
2.黑色旅游與社區旅游支持度
Foley 和Lennon(1996)首次提出“黑色旅游”(申健健、喻學才,2009)概念,把黑色旅游定義為“前往與死亡、災難和邪惡有關的地方的旅游”。依據成因機制的不同,可以將黑色旅游劃分為人為災難型和自然災害型兩種。國內關于黑色旅游的研究起步較晚,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才逐漸增多(王金偉、王士君,2010;何景明,2012;方葉林、黃震方、涂瑋等,2013;謝彥君、孫佼佼、衛銀棟,2015;王金偉、張賽茵,2016;顏丙金、張捷、李莉等,2016;Yan,Zhang & Zhang,et al.,2016;Qian,Zhang & Zhang,et al.,2017)。
大規模自然災害后,在災難遺址地發展旅游業引發了不少質疑。一些學者認為災后發展旅游業有助于經濟恢復(王金偉、王士君,2010;羅青苗、高聯輝、唐艷,2011),而另一些聲音則從倫理的角度認為將受災居民的傷痛之地商業化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可能帶來居民情感上的二次傷害(Wright & Sharpley,2018),但很少有研究從災難旅游的凝視對象——社區居民的感知出發,實證分析居民對災后發展旅游業的態度。Kim 和Butler(2015)是最早研究黑色旅游社區居民態度的學者,他們發現不同居民對黑色旅游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和看法,并指出這一差異可能是由居民地方依戀的強弱不同導致的。Wang 和Luo(2018)分析了居民對黑色旅游影響感知與旅游態度的關系,指出北川羌族自治縣居民盡管受災嚴重,卻傾向于支持發展旅游業,認為黑色旅游有助于社區文化重建、環境保護和經濟恢復。Chen、Wang 和Xu(2017)探討了災害旅游中,居民地方依戀、旅游影響感知與旅游態度的關系。
以上研究多采用“旅游影響”的視角,對災區居民災后旅游感知與態度的研究較為缺乏(Wright & Sharpley,2018;Wang,2019)。近年來,有學者呼吁不僅要從傳統的“旅游影響”視角,還應該基于對社會生活現實的深入理解來探究居民對旅游的態度(Wright & Sharpley,2018)。
3.研究模型與假設
(1)環境風險認知
環境風險認知研究始于20 世紀70 年代,已形成許多具體理論和方法,如啟發范式、心理測量范式等,其中心理測量范式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環境風險認知指個體對存在于生活中的環境風險的主觀感受和認識,且強調個體的直觀判斷和主觀經驗對個體認知的影響(謝曉非、徐聯倉,1995)。B?hm 和Pfi ster(2000)提出了一個環境風險認知評價模型,認為風險評價通過影響風險情感而形成行動傾向。Devine-Wright(2009)認為人們對環境變化和風險的感知會激發情感并促使其采取風險防御措施。Sun、Zhou 和Wall 等(2017)以云南省元陽哈尼梯田遺產區為例,發現旅游社區的居民對災害風險更為敏感,更愿意采取災害風險應對措施。據此,本研究提出風險評價、風險情感與風險防御行為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假設,具體如下:
H:風險評價正向影響風險情感
H:風險情感正向影響風險防御傾向
H:風險評價正向影響風險防御傾向
(2)風險知覺與地方依戀
對環境因素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地情感聯結(Jorgensen & Stedman,2006)。段義孚提出的“恐懼景觀”(Tuan,1979),Porteous 和Smith(2001)提出的“地方毀滅”等都反映了自然災害能夠影響居民對地方的記憶與情感。大規模自然災害發生后,物質環境的破壞、控制感的缺乏和對未來風險的擔憂可能會導致居民地方依戀的瓦解(Onuma,Shin & Managi,2017),而社區居民重建社會關系、重構地方意義等風險抵御行為則有助于災后地方依戀的恢復(Silver & Grek-Martin,2015)。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風險評價負向影響地方依戀
H:風險情感負向影響地方依戀
H:風險防御傾向正向影響地方依戀
(3)風險知覺與旅游支持度
Nian、Zhang 和Zhang 等(2019)研究發現,危機響應對社區居民的旅游業參與意愿產生正向影響。居民逐漸認可發展旅游業對災后恢復的潛在作用,旅游發展為其提供一種在情感層面共擔災難傷痛以及與外界交流困境的方式(Wright & Sharpley,2018)。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風險評價正向影響災后旅游支持度
H:風險情感正向影響災后旅游支持度
H:風險防御傾向正向影響災后旅游支持度
(4)地方依戀與旅游支持度
已有不少研究探討居民地方感與旅游支持度的關系。一些研究認為居民地方感越強,對發展旅游業的支持度越強(Mccool & Martin,1994;汪德根、王金蓮、陳田等,2011);另一些研究則認為居民地方感越強,越不支持發展旅游業(Um & Crompton,1987);還有研究認為經濟發展形勢會對居民地方感與支持度的關系產生影響(王詠、陸林,2014)。許振曉、張捷和Wall 等(2009)實證研究了四川省九寨溝風景名勝區主要社區居民地方感與旅游發展影響感知的關系。Kim 和Butler(2015)以南澳大利亞雪鎮為例進行研究,指出居住時間與情感依戀會顯著影響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Wang 和Xu(2015)強調在研究居民旅游態度時,地方認同是一個不錯的理論視角。Chen、Wang 和Xu(2017)研究發現地方認同通過黑色旅游的影響感知作用于旅游支持意向。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地方依戀正向影響災后旅游支持度
本研究提出的理論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風險知覺 地方依戀 旅游支持度的假設模型Fig.1 Hypothetical model of risk perception,place attachment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二、研究方法
1.案例地
2008 年5 月12 日14 時,一場里氏8.0 級特大地震暴發,共造成69 227 人死亡、374 643 人受傷、17 923 人失蹤(國家減災委員會科學技術部抗震救災專家組,2008)。北川羌族自治縣是汶川大地震的極重災區之一,縣城在地震中被夷為平地,共有15 645 人遇難、26 915 人受傷、1 023 人失蹤(北川羌族自治縣地方志辦公室,2011)。都江堰市也是地震極重災區之一,遭受損失慘重(成都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成都調查隊,2010)。震后,旅游業作為恢復重建的重要方式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視。 探討這兩個地區的居民對于地震及次生災害的風險知覺對地方依戀和旅游支持度的影響,對于災區災后恢復工作有重要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
2.數據獲取
本研究在文獻回顧、對北川羌族自治縣和都江堰市實地調研及深度訪談的基礎上設計研究量表。其中,對地方依戀的測量引用Williams 和Vaske(2003)的量表,包括地方依賴和地方認同兩個維度;對風險知覺的測量參考了B?hm和Pfi ster(2000)等學者的研究,風險評價指居民認為發生潛在自然災害和負面影響的可能性及嚴重性(Yates & Stone,1992),風險情感指對已發生和未來可能發生災難或損失的情感反應(B?hm & Pfi ster,2000),風險防御傾向指個人減輕已發生災害的影響及防御未來風險的意愿(Tatsuki,Hayashi & Zoleta-Nantes,et al.,2004);對旅游支持度的測量借鑒Nunkoo 和Ramkissoon(2011)的量表。問卷進行初步設計后,還通過專家意見反饋等方式進行了完善。問卷采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1~5 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2014 年5月6 日至25 日,以北川羌族自治縣和都江堰市居民為對象,采用半結構式問卷調查的方法開展實地調研,共發放調查問卷680 份,剔除填寫不完整及所有選項答案均一致的問卷51 份,共回收有效問卷629 份,其中涉及北川羌族自治縣的問卷為342 份,涉及都江堰市的問卷為287 份。本研究綜合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 21.0 和結構方程建模軟件Amos 21.0 對樣本數據和假設模型進行分析。
三、實證結果分析
1.樣本描述性統計
樣本中,性別比例較為均衡,男性占46.1%,女性占53.9%。從年齡分布來看,21~50 歲的中青年占比共計80.8%。民族構成中,漢族人口占到樣本的74.9%,羌族、回族和藏族人口占總人數的25.1%。從出生地來看,75.0%的受訪者出生于當地。從文化程度來看,61.4%的居民只接受過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教育(見表1)。
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08 年北川羌族自治縣和都江堰市約70%的人口屬于農業人口,而地震導致數萬頃農田被毀,大量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和經濟來源,因此案例地災后恢復過程中居民對旅游業的態度具有較強的典型性。

表1 樣本的社會人口特征(N=629)Tab.1 Socio-demographic profi le of samples(N=629)
2.因子分析
對量表的測量項進行信度分析,發現克隆巴赫系數(Cronbach’s α)均在0.708 至0.818 之間,說明各變量具有較高的信度。由于風險知覺和地方依戀的測量量表具有較強的理論支撐,因此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FA),而旅游支持度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結果顯示,觀測變量的標準因子載荷均大于0.5,并且6 個因子的組合信度值(CR)均大于或等于0.719,高于標準閾值0.7,表明測量指標之間具有較高的關聯程度,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或接近標準閾值0.5,說明總體判別效度較理想(見表2)。
從均值來看,風險評價因子中“個人受災可能性”“災害對我造成很大的威脅”的均值較高,而風險情感因子中“感到非常擔心”“非常傷心”的均值較高,說明災后居民的風險評價較高,且負面情感較為強烈。旅游支持度中有3個測量項的均值都大于4,說明居民對于災后發展旅游業的支持程度較高。

表2 測量量表因子載荷與可靠性系數Tab. 2 Factor loadings(PCA)and Cronbach’s alphas for each scale
3.風險評價、風險情感、風險防御與地方依戀、旅游支持度的關系
(1)測量模型檢驗
運用Amos 21.0 軟件對模型進行識別與檢驗,總體擬合情況見表3。一般認為,RMSEA <0.08、GFI >0.9、IFI >0.9、CFI >0.9、PNFI >0.5,則模型的擬合度較優(吳明隆,2010)。本文假設模型的χ/df、RMSEA、CFI、TLI、IFI、PNFI、GFI 和PGFI 均較為理想,說明概念模型與數據的總體擬合度較為理想。

表3 模型的擬合指數Tab.3 Goodness-of-fi t indices of hypothetical model
(2)風險知覺、地方依戀與旅游支持度的關系
圖2 顯示了風險評價、風險情感、風險防御傾向與地方依戀、旅游支持度之間的影響關系。其中:①風險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鏈為風險評價—風險情感—風險防御傾向,接受假設HH,拒絕假設H;②風險防御傾向對地方依戀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0.354),而風險評價和風險情感對地方依戀的影響不顯著,即拒絕假設H、H,接受假設H;③風險防御傾向對旅游支持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0.094),接受假設H,拒絕假設H和H;④地方依戀對旅游支持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0.730),接受假設H。(見圖2 和表4)

圖2 結構方程模型標準化參數估計Fig. 2 Standardized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表4 結構模型假設檢驗結果Tab.4 Results of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model assumptions
結論與討論
大規模自然災害發生后,次生災害等生態環境風險持續威脅著災區居民的生活質量與安全感。旅游業作為一種恢復力較強的產業,是災后經濟恢復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往研究從宏觀視角分析了災區遺址發展旅游業對經濟恢復的作用(王金偉、王士君,2010;吳春濤、李熙、段金莉,2016),但較少有研究從居民感知的視角來分析社區對災后發展旅游業的態度。本文創新性地從更廣義的社會現實與居民生活質量出發,探究風險知覺對于居民地方依戀和旅游支持度的影響。研究發現:①風險評價會顯著正向影響風險情感,而對風險防御傾向的影響不顯著。②風險情感對地方依戀的影響不顯著,而對于風險防御傾向的正向影響有助于地方依戀的恢復。這與通常意義上認為風險情感可能會沖擊地方依戀的觀點看似矛盾,但這與地震發生后居民努力采取實際行動防御風險的實踐密不可分,即當災區居民越擔心未來可能發生風險時,越傾向于采取更多的風險防御行為,而這些防御行為有助于地方依戀的恢復。③風險防御傾向對地方依戀和災后旅游支持度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當居民災后恢復和抵御風險的愿望越強烈,就越傾向于支持災后發展旅游業。盡管經歷了毀滅性的大地震,災區居民也在努力嘗試用各種積極的方式來恢復重建,走出過去的傷痛。風險防御行為包括鄰居之間的互助、社區支持(Guo,Zhang & Zhang,et al,2018)等,有助于災區居民重獲日常生活的控制感,從而促進人 地情感的恢復。如在經歷了東日本大地震之后,當地居民采取了更有效的措施來防御未來災害(Onuma,Shin & Managi,2017)。災區居民對次生災害等風險的防御傾向會促使他們更認可旅游業在促進經濟恢復、情感慰藉、持續獲得公眾關注與社會支持(Wang,2019)等方面的作用,更認可災后旅游業相對于工農業等具有更強的恢復能力,從而更傾向于支持發展旅游業。由于旅游業的許多就業形式(如旅游紀念品售賣、景區工作等)進入門檻較低,對于失地農民而言,是一種有效恢復經濟來源的方式。④地方依戀對災后旅游支持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以往研究也指出經濟形勢會對地方依戀和旅游支持度的關系產生影響,自然災害發生后,地方依戀程度較強的居民,更傾向于支持地方發展旅游業。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①從更廣義的社會現實和生活安全感切入,揭示了影響生活質量的風險知覺如何影響居民對災后發展旅游的支持度,深化了居民感知視角的災后旅游研究。Wang 和Luo(2018)研究發現,在汶川地震中受災程度不同的人對于災后旅游的支持度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發現,除了考量居民在地震中受災程度差異的影響,還應關注居民對未來災害風險和后果的感知如何影響其旅游支持度。盡管有些人在災害中受災程度非常嚴重,但從抵御未來風險和災害的角度出發,他們也傾向于支持發展旅游業。②聚焦居民對災后整個旅游業發展的態度,而不局限于居民對黑色旅游的態度。從災后旅游的發展實踐來看,僅僅強調自然災害遺址旅游的發展難以持續,黑色旅游呈現下滑態勢(Wang,2019)。因此,從更一般意義上的旅游業來探討居民支持度,具有較強的實踐意義。本研究也為災后旅游實踐提供了一些啟示:盡管災后次生災害等風險可能會激發居民的擔憂等負面情緒,但也會增強居民抵御風險的行為傾向,從而推動災后地方依戀的恢復。因此,為災區居民提供更多風險防御的對策與社會支持,有助于增強居民對日常生活的控制感和對地方的依戀感,為從事旅游行業的居民提供經營建議,促進災區從單一災害遺址旅游向民俗文化旅游、自然生態旅游升級(王金偉、謝伶、張賽茵,2020),可使旅游成為有效促進災后恢復和抵御風險的一種生計方式。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Wright和Sharpley(2018)指出災后旅游的社區支持度是一個從災害發生到災后恢復不斷動態變化的過程,該過程受到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也是一個復雜的心理博弈的過程,未來應加強對災后恢復不同階段數據的搜集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