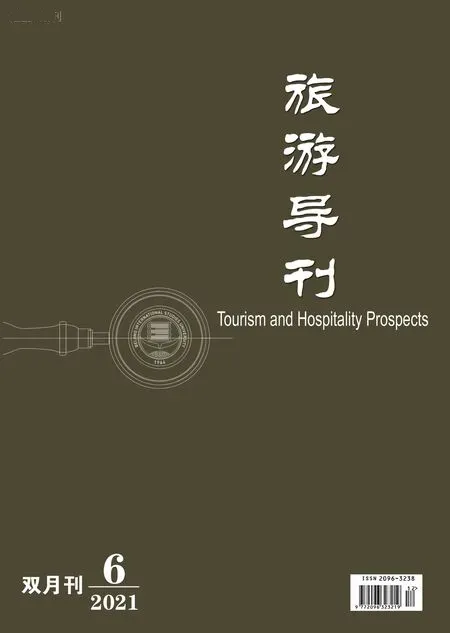黑色旅游的批判性反思與理論建構
王金偉 王國權 王 欣
(1.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游科學學院 北京 100024;2.北京旅游發展研究基地 北京 100024)
引言
悲劇比別種戲劇更容易喚起道德感和個人感情……人們在可恐怖的事物面前往往變得嚴肅而深沉。他們或者對生與死、善與惡、人與命運等等問題作深邃的哲理的沉思,或者在悲劇情節與他們自己的個人經驗有相似之處時……便沉浸在自己的悲哀和痛苦之中。
——《悲劇心理學》(朱光潛,2012)
黑色旅游是在特定空間中對死亡、災難、恐懼等黑色事象的悲劇化情景體驗。在旅游“舞臺”上,各種黑色事象和情感要素交織纏繞,一幕幕“悲劇”被不斷展演于眾。游客通過具身化參與或互動式觀演,不僅能夠從中認識歷史真實,汲取悲劇教訓,而且還能進一步反思生命價值,重塑生與死的倫理道德體系。同時,也能通過特定的情境和教育方式,激發愛國情懷與民族意識(Strange & Kempa,2003;Stone,2012;Tinson,Saren & Roth,2015)。毫無疑問,黑色旅游是一種基于悲劇化手段喚起正面哲理性沉思和重構個體價值觀的精神性旅游活動形式。近年來,它變得愈加流行和富有情感(fashionable and emotive),并成為利基旅游市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Sharpley,2005)。
黑色旅游市場的不斷升溫,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們對黑色旅游的概念內涵、倫理道德關系、旅游體驗、目的地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諸多研究(Sharpley & Stone,2009;Light,2017)。在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的同時,相關理論建構問題也愈發急迫,主要表現為:第一,雖然目前學術界對黑色旅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大量探討,但是相關概念之間仍存在模糊混淆、界定不清的情況;第二,關于黑色旅游者的研究不斷豐富和深化,但學術界尚未全面梳理出黑色旅游者的類型及其多維度動機,相關討論仍在進行;第三,學者們對于黑色景觀類型與黑色旅游地的認知邊界不斷拓寬,但對二者之間的關系和范疇等缺乏統一認識。與此同時,對于現有研究理論的批判性反思和評論還相對較少。這不僅不利于厘清黑色旅游現有理論脈絡,同時也不利于該領域的學術發育和理論建構。
基于此,本文將在深入梳理黑色旅游概念與內涵的基礎上,對“黑色旅游”術語的適宜性進行學術性辯證,同時試圖從“需求者”視角描摹黑色旅游者的游客畫像和動機譜系,再從“供給者”視角梳理黑色景觀及黑色旅游地的特征,并提出“黑色旅游地色度衰減曲線”,以期對今后黑色旅游的理論建構和相關研究有所裨益。
一、黑色旅游的概念與內涵
20 世紀90 年代初,學者們逐漸注意到旅游與死亡、災難等之間的密切關系。1993 年,Rojek 發現,遭遇突發性死亡和暴力死亡的地點以及墓地等黑色景點(black spots)成為吸引游客到訪的重要場域。為了進一步描述“到與死亡和災難等相關的地方參觀游覽”的現象,Foley 和Lennon(1996)提出了“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的概念,并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與此同時,Seaton(1996)提出了“死亡旅游”(thanatourism)一詞,意指部分或者完全地出于對死亡實際(或象征性)地接觸的愿望,而前往相關旅游目的地的行為。
隨著黑色旅游的持續發展,學者們開始關注到更為豐富的旅游形式,陸續提出了戰場旅游(battlefi eld tourism)、監獄旅游(prison tourism)、災后旅游(post-disaster tourism)、大屠殺旅游(holocaust tourism)、病態旅游(morbid tourism)、種族滅絕旅游(genocide tourism)等相似概念(見表1)。黑色旅游的外延范疇和研究領域逐漸擴大,研究內容也更為具象化。盡管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從多個側面理解黑色旅游現象的本質,但是由于概念眾多,容易形成理論標簽的碎片化,進而稀釋黑色旅游“本體”。同時,基于這些下位概念的學術研究,也大多局限于某個(類)具象化的案例,很少就黑色旅游概念本身及理論框架進行系統化研究,進而導致概念內部歧化現象逐漸加深。
從表1 可以看出,學術界關于黑色旅游的定義(術語)眾說紛紜,難以一統。但是,從中卻可管窺這些術語的釋義規律,并可以據此將其大致劃分為兩類:(1)基于黑色旅游客體(吸引物)的概念術語。這類概念往往著眼于死亡、災難等黑色事象本身,以及它們在旅游活動中的“他者”角色身份(被觀覽或被體驗),例如:戰場旅游、監獄旅游、災害旅游、大屠殺旅游、鬼怪旅游、刑罰旅游。(2)基于黑色旅游主體(游客)特定情感體驗的概念術語。此類術語強調旅游主體在黑色場域的具身體驗和情感映射,尤其凸顯出黑色旅游中獨特的悲情化和負向化的情感類型,例如:悲傷旅游。不難看出,主體和客體的黑色性是界定黑色旅游的兩個重要指標。
據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從廣義和狹義視角分別對“黑色旅游”進行界定。廣義上,黑色旅游指前往黑色事象展現地進行的旅游活動。旅游目的地(黑色事象展現地)既可以是災難、死亡等黑色事象的直接發生地,也可以是紀念地和展陳地、演繹場所(如災難模擬體驗館)等間接相關的空間。狹義上,黑色旅游指旅游者懷持黑色性動機并前往黑色事象展現地進行的旅游體驗活動。黑色性動機是一種色度(darkness)較深或負向情感性較強的動機類型,包括緬懷、紀念、悲憫等。狹義上的黑色旅游,除了關注黑色客體空間之外,更加強調主體和客體的互動關系,尤其是在黑色空間中特有的情感性體驗。因此可以說,廣義的黑色旅游概念是一種“客體論”,而狹義的黑色旅游概念則屬于“主客互動論”(王金偉、王士君,2010)。兩者是針對同一構念進行的不同學術表征。

表1 黑色旅游相關概念Tab.1 Related concepts of dark tourism

續表
為了進一步區分不同類型黑色旅游的特征,本文從黑色事件的影響強度(事件強度)、黑色事件發生距今的時間間隔(時間間隔)、距黑色事件發生地的空間距離(空間距離)3 個維度對其進行剖析。在圖1a 的坐標系中,以事件強度為縱軸、時間間隔為豎軸、空間距離為橫軸,在每個坐標軸上分別劃定了3 個不同等級:短/強—中—長/弱。由此,將象限空間分割為27 個小正方體。事件強度、時間間隔、空間距離3 個要素共同決定了黑色旅游的色度。具體而言,黑色事件的影響強度越大,距離事件發生的時間越近,旅游地距離事件發生地的空間距離越近,則黑色旅游的色度越深,其蘊含的悲傷、痛苦、憂郁等黑色/負面情緒越濃厚。反之,黑色旅游的色度則越淺(越趨向于白色),其蘊含的愉快、慶幸、興奮等白色/正向情緒成分越多。
同時,根據事件強度、時間間隔、空間距離3 個要素的不同組合方式,可以將黑色旅游分為7 種不同的組合形式,即7 類色度形式(見圖1b)。參考Stone(2006)對黑色旅游的六分類法,本文將黑色旅游劃分為7 種類型,分別命名為:最黑色旅游(darkest tourism)、更黑色旅游(darker tourism)、黑色旅游(dark tourism)、過渡黑色旅游(transitional dark tourism)、白/淺色旅游(light tourism)、更白/淺色旅游(lighter tourism)、最白/淺色旅游(lightest tourism)。其中,過渡黑色旅游(transitional dark tourism)是本研究新提出的一類黑色旅游形式,其色度居于黑色旅游(dark tourism)和白色旅游(light tourism)之間,其色譜是一種介于黑和白之間的過渡色,所蘊含的情感類型也大多屬于中性情感(介于黑色情感和白色情感之間),如平靜、淡然等。這一類型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Stone(2006)分類方法“非黑即白”的局限。

圖1 黑色旅游的類型譜系Fig.1 Type spectrum of dark tourism
二、黑色旅游、墨色旅游與紅色旅游
1.黑色旅游,還是墨色旅游?
目前,“黑色旅游”在國內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中已經成為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術語,但是相較于英文中的“dark tourism”一詞,這一術語翻譯的準確性和適宜性仍有待商榷。2018 年出版的《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ornby,2018)中,“dark”具有以下形容詞詞義:(1)光線暗淡(with little light);(2)顏色為深色的、暗色的,如深藍色、墨綠色、深紅色等(not light; closer in shade to black than to white:dark blue/green/red etc.);(3)頭發、皮膚、眼睛:褐色的、黝黑的、烏黑的(brown or black in color);(4)神秘(mysterious):神秘的、隱秘的、隱藏的(mysterious;hidden and not known about);(5)邪惡(evil):邪惡的、陰險的、兇惡的(evil or frightening);(6)無希望(without hope):憂郁的、不快的、無望的(unpleasant and without any hope that sth good will happen)。同時,具有以下名詞詞義:(1)無光(not light);(2)暗色、陰影。可以發現,“dark”更多地側重于顏色上的深和暗(色度),并非單純指“黑”色(顏色)。據此可以認為,“dark tourism”除了表達“旅游”中的“黑色”(顏色)成分之外,還可能表達了一種內在色度之“黑”(深色度、暗色度),也涵指心理和情感層面上的神秘和憂郁等。
與此對應,中文中的“黑色”在《新華漢語詞典》(《新華漢語詞典》編纂委員會,2007)中的釋義為:近似于墨或煤那樣的顏色。同時,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黑色”和“紅色”往往是一對對立概念。“黑色”具有反動或反革命、倒霉(忽視)、陷害(坑害、欺騙)、破壞(攻擊、侵入)等負面象征和比喻意義(王玉英,2008);而紅色有成功、革命、喜慶等象征意義,同時還是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的象征(劉琨,2013;李行健,2014),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家意識形態,如五星紅旗、紅軍、中國紅。如此一來,如果將“dark tourism”翻譯為“黑色旅游”,不僅沒有精確地呈現其多元化的詞源內涵,同時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為“dark tourism”帶來不必要的文化誤讀和倫理制限。基于此,筆者認為應該進一步辨析上述概念的利與弊,篩選出更加符合我國本土情境的專業術語。
通過綜合考量,筆者認為,在中文語境下,“墨色旅游”比“黑色旅游”具有更好的適宜度。首先,在詞源上,墨色,即墨的色澤,亦泛指如墨之色(《現代漢語大詞典》編委會,2010)。根據《新華漢語詞典》(《新華漢語詞典》編委會,2018)的解釋,“墨”字在表示顏色的時候,意指“黑色或近于黑色的”,如墨菊、墨鏡、墨綠。其中,以“墨”搭配顏色詞,如“墨黑”,指非常黑、很暗;“墨綠”指深綠色。而在古代,以墨代色,產生了“墨分五色”的說法,唐代張彥遠在其著作《歷代名畫記》提到:“運墨而五色具。五色,即焦、濃、重、淡、清,而每一種墨色又有干、濕的變化”。從某種角度上來說,5 種顏色(焦、濃、重、淡、清)更能反映“dark tourism”的多樣性。理由包括:首先,Stone(2006)提出“dark tourism”可以依據旅游者動機、旅游開發目的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分為6 類不同顏色的譜系,分別為最黑/暗色(darkest)、更黑/暗色(darker)、黑/暗色(dark)、白/淺色(light)、更白/淺色(lighter)、最白/淺色(lightest)。而中文情境下的墨色所包含的5類顏色,可以與“dark tourism”形成天然的對應關系。其次,在字形上,“墨”中有“黑”。“墨色旅游”能夠較為容易地讓人聯想起已被廣泛使用的“黑色旅游”一詞,在心理上容易過渡性地接受這一新的術語(翻譯),同時,“墨色旅游”又巧妙地避開了可能引發的文字歧義和文化沖突等問題(如與紅色旅游的文化性對弈)。鑒于此,筆者更推薦使用“墨色旅游”一詞,來作為對“dark tourism”這類特殊旅游活動的譯稱。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墨色旅游”替代概念的引入并不是為了挑戰主流的學術研究體系,只是為了更加貼切地闡釋相關概念內涵,且使其在我國本土情境中具有更好的適宜性。同時,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筆者并不提倡所有的相關旅游地都貫之以一地使用“墨色旅游”,而是應該加以區分性地選擇,使用當地人心理和情感上更容易接受的概念。如筆者早年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縣和汶川縣調研“5·12”汶川特大地震遺址旅游的過程中發現,當地居民更愿意將其稱為“地震遺址旅游”,而非“黑色旅游”。因此,在實踐發展中,各地應該立足實際,有甄別性地選擇適宜的概念對旅游地進行命名。
2.黑色旅游與紅色旅游的異同
黑色旅游與紅色旅游(red tourism)同屬于精神類旅游產品,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區別,是一對情感性的共生概念。從旅游主體、旅游客體、發展驅動力3 個方面,可以對二者做出廓清:
(1)旅游主體方面,黑色旅游與紅色旅游都是旅游者具身參與的高度情感化的旅游形式(何景明,2012),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們還是一種精神朝圣旅游(pilgrim tourism)。同時,二者在動機方面也有重疊之處,如緬懷逝者、紀念先烈、祭奠遇難同胞等。但不同的是,游客前往紅色旅游地更多是接受精神洗禮和愛國主義教育,屬于正向的情感體驗;而前往黑色旅游地則更多追求一種黑色愉悅,屬于一種更為悲情化的情感行為。需要強調的是,黑色愉悅并非一種病態的“幸災樂禍”或負面行為,而是一種借助于死亡觀照獲得黑色愉悅的心理特征(謝彥君、孫佼佼、衛銀棟,2015)。
(2)旅游客體方面,黑色旅游與紅色旅游在旅游吸引物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疊,如戰場遺址、紀念館、公共墓地等。它們既可以是紅色旅游基地,也同屬于黑色旅游地范疇。只不過,它們的使用情境有所差異,即紅色旅游地更加強調愛國主義基調,而黑色旅游地則更加凸顯其悲情和沉重的一面。此外,在我國情境中,一些與英雄主義、人民精神相關的紅色旅游地也常常被排除在黑色旅游地之外,如革命偉人故居、社會主義偉大工程建設地(武漢長江大橋等)。與此對應,在黑色旅游之中,也有諸多目的地不屬于紅色旅游的范疇,如鬼屋主題公園。總的來看,黑色旅游目的地更加強調悲情化和負向情感基調的營造,而紅色旅游目的地則更加傾向于正向情感與愛國情懷的表達。
(3)發展驅動力方面,黑色旅游和紅色旅游通常都會通過“歷史”及相關事象達到教育啟迪和情感升華的目的。不同的是,紅色旅游的政治傾向更為明顯,以黨政愛國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為主題基線,其旅游開發經營活動更多地屬于政府公益性的行為。而黑色旅游則偏重于“市場”,常常需要通過市場手段來構建產品體系,并通過商業化的方式進行黑色事象的營銷。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黑色旅游中也包含一些公益性的行為,例如奧斯維辛 比克瑙集中營遺址所進行的反法西斯教育及和平教育。總的來看,紅色旅游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源于公益化的力量,而黑色旅游更多地依賴于商業化的驅動(晏蘭萍、洪文文、方百壽,2008)。
總之,黑色旅游和紅色旅游并非一對天然的對立概念,而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獨立旅游活動類型,紅色旅游更加強調政治傾向和革命教育,而黑色旅游更傾向于情感的深沉性和游程的“神秘感”。在學術研究中,應該科學辯證地看待二者的關系,而不能簡單地抱以“好惡”。
三、黑色旅游者
1.黑色旅游者的身份識別
旅游者是黑色旅游現象中的核心主體,對其“身份”進行識別是理解黑色旅游現象本質的關鍵。黑色旅游者是流動在黑色空間的一類特殊人群,身份復雜、標簽多樣。一般來說,黑色旅游者不僅包括對特定地點有強烈興趣或與之存在緊密聯系的個體,而且還可能包括一些出于其他較為常見動機(如休閑游憩)而到訪的群體(Lennon & Foley,1999/2000)。Winter(2011)指出,訪問比利時戰爭小鎮伊珀的旅游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來哀悼和紀念的人,另一類是前來休閑的人。此外,也有學者將黑色旅游者分為“朝圣者”(pilgrims)和“ 一 般/ 其 他 游 客”(general/other visitors)(Austin,2002;Richards,Ashworth & Hartmann,2005)。可以發現,黑色旅游者并非一個勻質的群體,而是存在諸多內部差異。
為了進一步厘清黑色旅游者內部的身份差異問題,本研究認為可以將其劃分為廣義的黑色旅游者和狹義的黑色旅游者兩類。其中,狹義的黑色旅游者指持有黑色動機并在黑色場域進行情感性體驗的游客,而廣義的黑色旅游者指在黑色空間進行旅游活動的游客,包括持黑色動機的游客(狹義的黑色旅游者),還包括持一般性動機(如休閑、游憩)的游客。“黑色動機”指具有悲情化或負面傾向的情感性動機,如緬懷逝者、直面災難(詳見后文“旅游動機”部分)。
正是由于黑色旅游者的特殊性,他們常被媒體或者社會大眾描述為“離經叛道”的人,其旅游行為則是對“逝者的不敬”,有悖倫理道德(余里、海明威,2009)。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黑色旅游者真的是一群“異類”嗎?為了回答這一問題,筆者嘗試以我國代表性的黑色旅游地——汶川大地震紀念地(汶川縣、北川縣等)為案例,選取以該地(區)作為研究對象的5 篇中英文學術論文來揭示黑色旅游者的真實身份(見表2、表3)。

表2 汶川大地震紀念地黑色旅游相關代表性研究Tab.2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on dark tourism in Wenchuan earthquake memorial sites
從表3 中可以發現,汶川大地震紀念地(黑色旅游地)的游客基本信息如下:性別方面,男性和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53.4%和46.6%(與5 篇文章的游客人數總和之比),男性略多于女性;年齡方面,主要集中在20~45 歲,以中青年為主;受教育程度方面,主要為大專/本科;職業方面,學生群體所占比例較大;來源地方面,四川省內游客居多,約占73%。為了進一步對比黑色旅游者與一般性游客的特征差異,筆者查閱了《2019 年第一季度四川旅游大數據報告》以及《2018 年四川旅游大數據報告》(川味旅游,2019),發現2019 年第一季度,四川省接待的國內游客當中,性別方面,男性游客占比為63.82%,女性游客占比為36.18%;年齡方面,游客年齡段占比前三名的分別為30~35 歲、40~45 歲、45~50 歲,占比分別為16.15%、14.73%、14.48%。此外,2018 年四川省鄉村旅游接待游客3.49 億人次,接待省內鄉村旅游游客2.43 億人次,占比69.73%,接待省外鄉村旅游游客1.06 億人次,占比30.27%。
在不考慮出游時間等外部因素的情況下,可以發現黑色旅游者與一般游客存在以下差異:(1)黑色旅游者中的女性游客比例略高于一般旅游形式。這可能與黑色旅游是一種情感性的旅游活動有關。一般來說,女性相對于男性在情感方面的心理訴求和行為表征更為強烈。(2)黑色旅游者中的青年游客群體(尤其是20 歲年齡段)占比略高于一般旅游形式。這可能與年輕人(主要為學生群體)對于地震災難及地質知識的學習和探索心理,以及較強的好奇心有關。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黑色旅游是青年群體(尤其是學生)進行教育研修的一種重要方式。(3)黑色旅游者主要為與黑色事件有關聯的群體。汶川大地震紀念地的黑色旅游者絕大部分來自四川省內,且其比例高于鄉村旅游。盡管受災程度不一,但是他們大多經歷了汶川大地震,有著共同的創傷記憶,與地震災難關聯密切。總的來看,汶川大地震紀念地的黑色旅游者與一般游客相比,匯集了更多的女性和青年群體,同時他們與黑色事件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某種關聯,在游程中更加注重情感和精神意義。綜上所述,“黑色旅游”是一種高度精神化的情感活動,沉浸其中的游客是一類來自世俗社會的情感“朝圣者”。

表3 汶川大地震黑色旅游地相關研究人口統計學信息Tab.3 Summary of touris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 5 papers on Wenchuan earthquake memorial sites
2.黑色旅游者的動機
旅游動機是理解黑色旅游者心理和行為特征的“原點”。黑色旅游動機是一個包羅眾多情感要素的心因性驅動力,決定了旅游者展露在外的“黑色行為”。王金偉和張賽茵(2016)以汶川大地震的重要紀念地“北川地震遺址區”(“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為案例地,將黑色旅游者的動機歸納為“緬懷與探尋地方特色”“公益與科考教育”“娛樂與自我發展”3 類。Seaton(1996)探究了游客參加死亡旅游的動機,他認為部分游客是完全出于對死亡本身的迷戀,而不考慮涉及的參觀對象是誰,只關注死亡本身的形式或規模,例如參觀墓地、墓穴、災難場景。與此相對,也有部分游客會因“逝者”而游,他們既為逝者而來,也珍視他們與“逝者”間的情感聯系。而Isaac、Nawijn 和Van Liempt 等(2019)將參觀荷蘭集中營紀念館的游客動機分為“記憶”(memory)、 “獲取知識和意識”(gaining knowledge and awareness)、“特有性”(exclusivity)。Biran、Poria 和Oren(2011)認為黑色旅游者的動機不僅包括想要“眼見為實”(see it to believe it)的心理,還包括一種學習和了解該地及其所發生的黑色事件的需求,以及對著名死亡地點的普遍興趣。此外,Cooper(2006)還指出,游客經常出于教育和娛樂的原因參觀與戰爭有關的景點,他們可能希望在假期體驗一些不同的東西,也可能希望以病態的好奇心來獲得對過往的了解。
可以看出,黑色旅游動機不僅包括緬懷逝者、紀念災難事件等“正向”情感投入型的“悲情化”動機,同時也包括一般意義上的休閑和社交型的動機(王金偉、張賽茵,2016)。為了進一步理解黑色旅游的動機類型,筆者將其抽象為圖2 所示的概念化譜系,即將黑色旅游動機分為核心動機(Core Motivation)、過渡動機(Transitional Motivation)、邊緣動機(Peripheral Motivation)3 類。具體為:(1)核心動機。處于螺旋圖中心、色度較深,為悲情化或負面傾向的情感性動機,如紀念災難、直面創傷,是黑色旅游的核心動機,也是判定該次游程是否為“黑色旅游”的關鍵。(2)邊緣動機。處于外圍的則為較具娛樂化的淺色動機,如獵奇、休閑。它們游離于黑色度(darkness)外圍,屬于黑色旅游的邊緣動機。這些動機盡管不是所有黑色旅游都具備的類型,但在很多黑色旅游地都會出現,是黑色旅游動機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3)過渡動機。居于兩者之間,屬于一種較為中性化的動機類型,它雜糅了核心動機和邊緣動機的情感要素和行為特征,是深色動機向淺色動機的過渡地帶,較為典型的過渡動機有教育學習、社會責任等。

圖2 黑色旅游動機譜系Fig.2 Motivation spectrum of dark tourism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3 類動機有時并無明顯的劃分界限,它們之間的過渡也并非“涇渭分明”,而是一個漸變的連續色譜。同時,對于某一類旅游者(或旅游者個體)來說,他們也并非只是單純地持有某一種(或一類)動機,而更可能是兼具多種動機類型,只不過在某個特定的時段或情境中,這些動機要素中的某(幾)種起主要作用,進而決定了黑色旅游者所展露在外的行為(王金偉、張賽茵,2016)。
四、黑色旅游目的地
黑色景觀是黑色旅游得以開展的根本。從景觀形成的原因來看,黑色景觀可以分為自然類黑色景觀、人文類黑色景觀以及自然 人文綜合類黑色景觀3類。其中,自然類黑色景觀包含了自然原始風貌以及災損景觀;人文類黑色景觀涵蓋了歷史遺址和人造景觀(如主題公園鬼屋)兩類;自然 人文綜合類黑色景觀,以文化景觀為典型表現,同時還包括部分自然災損景觀(如地震遺構)和人為災損景觀(如森林火災事故紀念館)。
以黑色景觀為核心的黑色旅游目的地蘊含著死亡、悲傷、恐懼等黑色要素。這些黑色要素通過不同的形式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多元化的黑色空間。黑色旅游目的地的黑色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著時間的演進呈現出一定的變化趨勢(見圖3)。一般來說,在自然狀態下,黑色旅游目的地的色度會隨著時間的演進而呈現出持續衰減的狀態。但是,一些黑色旅游目的地可能會伴隨著一些二次干預(人為干預或二次災害等),使其黑色度出現一個再增濃的過程,繼而出現“二次峰值”。二次峰值的高低取決于二次干預的強度及持續時間。這種二次干預既可以是旅游地管理者進行的旅游環境再造或“黑色歷史”的再挖掘,也可以是黑色旅游目的地遭受到的二次創傷(如地震遺址地的二次遭難)。但需要強調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沒有持續性的二次(或多次)干預,黑色旅游目的地的色度仍然會呈現出一個隨時間推移而持續衰減的過程。圖3 中,Ⅰ區、Ⅱ區、Ⅲ區分別呈現了黑色旅游目的地的色度在自然狀態下的衰減階段、二次干預后的增長階段及之后的再次衰變階段。通常來說,每個演化階段之間的轉變并不是一瞬間完成的,而是存在著一個漸染的過程。

圖3 黑色旅游目的地色度衰減曲線Fig.3 Darkness attenuation curve of dark tourist destination
同時,“黑色旅游目的地色度衰減曲線”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反映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演化歷程。通常來說,旅游目的地的成長演化會經過6 個階段:探索階段、起步階段、發展階段、鞏固階段、停滯階段、衰落或復蘇階段(Butler,1980)。但是,如果在其出現衰落跡象的時候,及時加以干預(如品質再造),則可能出現二次復蘇。類似地,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發展也會經歷上述生命周期過程(探索—起步—發展—鞏固—停滯—衰落/復蘇)。伴隨著這種演化更迭,目的地的黑色度也會出現一個自然衰減的過程(見圖3a)。但如果加以干預,則目的地黑色度可能會出現一個二次峰值,“生命周期”也將迎來二次復蘇。需要強調的是,黑色旅游目的地“色度衰減曲線”與“生命周期曲線”的演化規律并非完全一致。通常在黑色旅游目的地發展初期,其黑色度最高,而“生命周期”則處于探索階段的萌芽狀態(最低),之后,兩者在演化過程中呈現出不同的起伏交替變化。
為了保持黑色旅游目的地的持續色度,相關部門有必要盡可能保持黑色遺產的原真性(Boateng,Okoe & Hinson,2018)。不可否認的是,黑色旅游目的地在發展過程中,有時為了滿足某些群體的利益或訴求,而選擇過度商業化和娛樂化的方式對遺產進行開發。Strange 和Kempa(2003)研究發現,惡魔島監獄遺址為了滿足游客需求而采取了商業化和娛樂化的解說手段,致使其部分歷史價值被埋沒。Foley 和Lennon(1996/1997)同樣指出,黑色旅游目的地在開發或銷售的過程中經常存在被美化抑或被歪曲的現象。因此,如何平衡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成為黑色旅游目的地管理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此外,黑色旅游目的地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還需要考慮倫理道德問題。通常來說,旅游開發在帶給當地社區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諸多社會文化和倫理道德方面的負面影響,進而招致社會非議。為了避免黑色旅游目的地陷入倫理困境,有必要綜合考慮當地居民的情感,以及社會倫理道德的可接受范域,平衡多方利益相關者的訴求。王曉華、白凱和馬耀峰等(2011)指出,針對災難旅游實踐中的倫理矛盾和沖突問題,只在道德層面呼吁或譴責是遠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的,必須建立一種協調的結構關系和公平的參與及分配機制,使各利益主體在災害旅游的發展過程中找到利益平衡點。同樣地,王金偉、謝伶和張賽茵等(2020)也提出,對災難紀念地進行旅游開發時,有必要綜合考慮倫理道德問題,以及當地人的情感和心理承受能力。同時,需加強對游客行為的引導和規范,以避免對當地居民造成不必要的“二次心理傷害”。
結語
自20 世紀90 年代開始受到學術界普遍關注以來,黑色旅游及其學術研究發展至今,呈現出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一方面,黑色旅游有助于打破傳統倫理道德的藩籬。長久以來,人們對于死亡與災難等談及色變,諱莫如深。而黑色旅游為人們直面死亡和災難提供了一個“平臺”,不僅有助于人們進一步清晰認識死亡和災難的本質,同時也有利于全面理解生與死、歷史與現實、人與自然之間的關聯。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黑色旅游對于打破傳統倫理道德的禁忌、重構更為包容多元的現代社會倫理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黑色旅游研究有助于消解傳統社會對“黑色旅游”的偏見。實踐中,諸多黑色旅游地由于受到傳統倫理道德的束縛,發展舉步維艱,甚至遭到不應有的非議。但是通過學術研究,發現黑色旅游并非“離經叛道”,而是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諸多方面都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說,學術研究不僅為黑色旅游的實踐發展起到了導引作用,而且還不斷地為黑色旅游“正名”,推動人們對黑色旅游的客觀認知。
黑色旅游是對傳統旅游理論體系的突破與再造,是后現代主義在旅游學科內的一個重要表征。為了有效推動黑色旅游的理論建構和實踐導引,未來研究可以從4 個方面著手:
(1)加強基礎理論與現象本質的研究。黑色旅游自進入學術視野至今,其概念與內涵、現象本質一直是學者們持續關注的熱點話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現有文獻對于黑色旅游的定義、內涵及其內在關系等基礎性理論框架仍然眾說紛紜,尚未完全厘清,這不僅阻礙了黑色旅游的理論建構,同時會對黑色旅游的縱深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未來,學術界應進一步加強對黑色旅游的概念內涵與現象本質的研究,以夯實該領域的理論根基。
(2)明晰黑色旅游與社會文化的關聯。與傳統的旅游形式不同,黑色旅游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后現代特性的旅游活動,與社會文化常產生復雜關聯。與此同時,在一些目的地,黑色旅游與倫理道德、社會規范等交織纏繞,對其相互關系難以用現有理論和方法進行廓清。基于此,未來有必要進一步探析黑色旅游與社會文化(含倫理道德)之間的關聯路徑及影響機制,為黑色旅游的縱深化發展和理論體系建構提供支撐。
(3)深入探究黑色旅游者的心理情感。旅游者作為黑色旅游的參與主體,近年來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不同于追求愉悅旅游體驗的大眾游客,黑色旅游者的心理和情感具有個性化的內在特征和復雜的內在影響機制,有待進一步通過科學研究對其進行解析。今后,有必要進一步聚焦黑色旅游者的心理活動過程及影響因素、情感特征與行為表征等問題,以更好地從微觀視角管窺和解讀黑色旅游者的行為特征。
(4)創新黑色旅游研究理論方法體系。黑色旅游研究的縱深發展離不開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不斷創新。縱觀現有文獻可以發現,現有黑色旅游相關研究雖然日趨豐富,但研究方法較為傳統、研究理論較為單一,缺乏創新,難以達到理想的研究深度。未來,應注重引入新興研究方法(如實驗法、大數據方法等),以更好地促進對黑色旅游的深入研究。同時,引入相關的跨學科理論,如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等的研究理論,為全面剖析黑色旅游現象及其本質提供理論支撐和有益視角。
本文對黑色旅游相關研究問題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對于該領域的理論建構和相關學術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啟示意義。首先,本文對黑色旅游的相關定義(術語)進行了全面梳理和辯證解析,并從廣義和狹義兩個角度提出了黑色旅游的定義與內涵,有力地回應了現有研究中黑色旅游相關概念之間模糊混淆、界定不清的問題。同時,本研究對黑色旅游者的群體身份、旅游動機進行了歸納、對比與探討,并在此基礎上描摹了黑色旅游者的游客畫像與動機譜系,有利于深刻認識和理解這一特殊群體的身份特征及出游動機。此外,本文還從“供給者”視角梳理了黑色景觀及黑色旅游地的特征,并創新性地提出了“黑色旅游目的地色度衰減曲線”,有利于加深對黑色景觀類型與黑色旅游目的地二者之間關系和范疇的綜合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