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倫理學思考
梁云 蘇葆榮
法國著名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研究員弗里德里克·勒諾瓦(Frédéric Lenoir)所著《蕓蕓眾生:致動物和愛動物者的公開信》,是作者多年來從事動物保護事業、與動物親密接觸有感而發之作。因此,該書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科普書籍,而是融合了科學、歷史、哲學、宗教以及個人經歷和體驗的小品文。書中《序言》末尾的這段話,可視為讀者閱讀和理解此書的一把鑰匙:

這束信首先要解釋一下人類對你們動物和對于人類自身的看法。然后再講述人類和動物之間的歷史淵源,以及人類如何想方設法征服你們、利用你們,以至于今日大規模屠殺你們的狀況。同時這束信也要講講那些向來都拒絕,并且繼續拒絕這種利用和屠殺動物的人。最后這束信想要說明,人類作為地球上最強大,自然也是道義上最該負責任的物種,到底應該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尊重你們動物。
因此,“只有盡可能尊重地球上所有有感知的生命,人類才能成長為真正可感、可知的人”。
正是循著這樣的思路,作者展開了有條不紊的敘述和論證。從人類的進化史切入人類對動物從馴養到利用再到剝削乃至虐待的過程,起底了動物生存狀況惡化的現實,并援引眾多作家、動物心理學家和動物行為學家的觀點,指出人與動物的諸多相似點,無情拆穿了人類具有“獨特性”的神話。正是在這種物種平等、去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下,作者指出人類的特點在于:“人類是唯一能夠形成普世倫理責任的物種。”因為善待動物,不僅僅對動物有益,我們人類自身及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同樣是受益者。
正如《蕓蕓眾生》直接或間接引用的資料顯示,為動物辯護的聲音歷來一直存在。印度史詩巨著《摩訶婆羅多》中就宣稱:“動物的肉就如我們自己孩子的肉身……”古希臘羅馬哲學家,如畢達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提奧弗拉斯托、普魯塔克等,均在其生活中身體力行,杜絕肉食,主張食素。近現代的歐洲哲學家洛克、盧梭、康德、邊沁、叔本華等發展了真正意義上的動物保護的思想。于是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最先興起動物保護運動,并于一八二二年通過世界上第一部動物保護法《馬丁法案》,法國則于一八五○年投票通過旨在使動物免遭虐待的《格拉蒙法案》。

但是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著作《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以具體翔實的數據揭發農場動物的悲慘處境和實驗動物的駭人遭遇,才引起全世界對動物生存狀況問題的廣泛關注,動物保護才擁有了堅強的現代理論后盾,并隨之在西方引發新一輪動物保護運動,該運動持續了長達三十余年。
一九八三年,湯姆·雷根(Tom Regan)《動物權利研究》(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以其精深的哲學根基和嚴謹的論證方式,系統闡述動物意識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動物權利思想,認為所有動物都有生命、自由和身體完整的權利。此后,瑪麗·沃倫(Mary Anne Warren)提出“溫和動物權利”,主張人類的權利高于動物權利,但動物權利仍然不可忽視。美國法學家弗蘭西恩(G. L. Francione)在《沒有雷聲的雨:動物權利運動的思想》(Rain Without Thunder: The Ideology of the Animal Rights Movement)中則指出,美國的動物權利運動因為只贊同對動物的利用進行合理的管制,并沒有真正從動物權利的角度提出廢除剝削動物的制度,從而背離了動物權利運動的初衷。
以上著述及觀點可劃歸為“動物權利”派,這些著作直接催生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動物權利運動,并使這場運動于九十年代達到巔峰。但是這一派理論家和實踐者“都根據動物權利主義所應用的平等原則,主張完全取締和廢除集約化養殖模式和動物實驗”,這很容易導致極端,這可能也是后來的動物權利運動逐漸衰退的主要原因。
相比于激進的“動物權利”派,另一種動物保護論的觀點和主張主要基于同情動物的非理性情感,可稱為“動物福利”派。其實早期(十八十九世紀)的動物福利運動,與動物權利運動在概念上很難區別,大多數動物保護法案均可納入“動物福利”的標簽下。比較而言,動物福利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既包括動物生理上和精神上兩方面的康樂,也有學者認為是指動物從身體上、心理上與環境的協調一致,等等。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動物福利學逐漸發展成為一門公認的學科,擁有專門的學位課程、教科書、期刊、研究部門和專家學者。二○○○年,動物福利的另一倡導者,英國學者考林·斯伯丁(Colin Spedding)出版了《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一書,首次從哲學的高度對動物福利學中的倫理問題做出理論探索。
“動物福利”派的核心思想是動物的“五大自由原則”,即:免于饑渴的自由,免于不舒適的自由,免于痛苦、傷害和疾病折磨的自由,表達正常習性的自由,免于恐懼和悲傷的自由。此外,不同的動物群體還有不同的福利,如實驗動物的“三R原則”—“替代”“優化”“減少”。可以看出,“對于動物本身,福利被定義為生理、行為得到滿足,沒有虐待,而對于人類則意味著安全、健康的畜產品”(孫忠超、賈幼陵《論動物福利科學》,《動物醫學進展》2014年第12期)。也正是出于這些或人道或科學或實用的目的,世界上大部分動物保護組織都更多強調“動物福利”,如世界動物保護協會(World Animal Protection)就將“在全球提高動物的福利標準”作為其首要任務。
顯然,動物權利與動物福利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理念:前者主張“放空籠子”,后者要求“擴大籠子”。但兩者均可以納入動物倫理學的范疇,并已得到眾多哲學家、法學家和動物行為學家、動物心理科學家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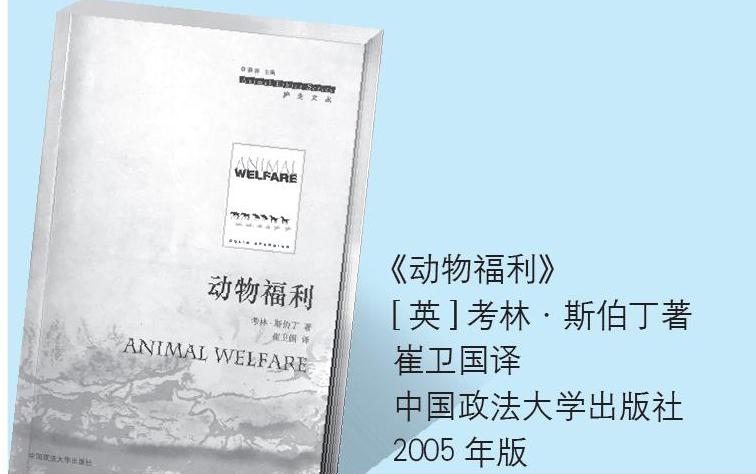
勒諾瓦身為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顯然不是呼吁開籠放雀式地解放動物,也不是要卷入“動物權利”或“動物福利”之爭,本書作者更多的是在“動物倫理”的框架內向普通讀者提出若干可以身體力行的措施和建議,旨在溫和又堅定地推進這項事業。
除了動物倫理學的視角之外,《蕓蕓眾生》一書以下幾個特點,同樣值得關注。一是角色置換。一般情況下,致信的對象為人類,而在此書中,則換作了動物。從書的副標題“致動物和愛動物者的公開信”中就可以看出,致信的第一讀者為動物,第二讀者才為愛動物者。但是按照作者在信中的表述,動物是不懂人類的書面語的,那么這種置換意義何在?這樣的置換,顯然旨在彰顯動物與人類的平等關系,同時也啟發人類在思考人與動物的關系問題時換位思考,而不是一味循著人類的思維習慣。

二是問題意識。全書針對人類與動物的關系,敘述存在的問題,提出要解決的問題,也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這樣的問題意識,有諸多的好處。既便于閱讀,讓讀者很容易清楚本書在講什么,也容易理清思路;同時也具有實效,提出問題可以讓讀者明白存在哪些問題,解答問題更是對讀者的具體引導和建議,也就是讓讀者清楚為什么做和該怎么做。改善人類與動物的關系,一方面要出于道德向善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結合科學事實和科學原理,這樣更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
三是旁征博引。勒諾瓦在書中的引用可分為兩類,事實性的材料與觀點性的材料。事實性的材料中,有描述也有數據,如工業化養殖和工業捕撈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觀點性的材料,則包括了各界人士對動物的看法,以及對人類與動物關系的認識。這些論據源于多個學科,可謂豐富。同時,勒諾瓦作為哲學家,熟悉哲學也擅于運用,從哲學的高度,對動物倫理學進行論述既深入根源,也觸及終極。書中大量哲學論據的引用,為本書增加了不少厚重感。
當下,以動物為主體的作品很多也很流行,既有科普作品也有文學作品,文學界還有“動物小說”這一提法。美國科學家、生態學家,同時也是自然文學作家的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在其作品《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中提出“土地倫理”理論,主張將倫理道德運用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倡導保持“生態良心”,指出要“像山一樣思考”(即從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思考)。認為人類是土壤、河流、植物、動物等組成的“土地社區”(the Land Community)中的一部分,人類與其他生物結伴而行,所以要互相尊重,互相愛護。這與《蕓蕓眾生》一書的觀點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科學技術不斷發展、人類越發強大的今天,這些作品顯現出來的遠見卓識尤為可貴。閱讀此類書籍,可謂恰逢其時,也更能激發我們認真思考和界定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