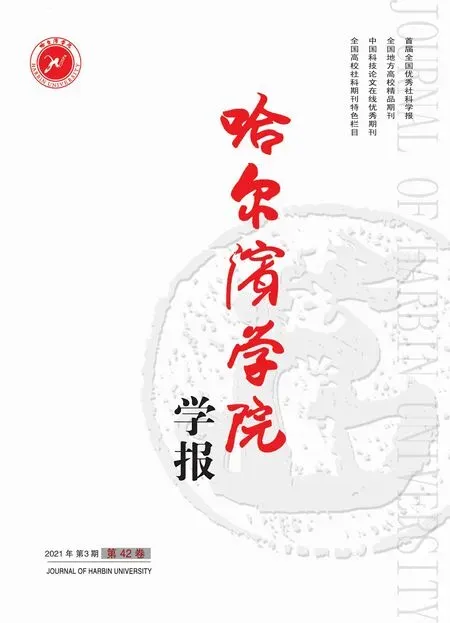論《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完善與銜接
李夢瑤
(甘肅政法大學 環境法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一、野生動物保護立法及實施情況檢視
(一)野生動物立法保護范圍狹窄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是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國際公約,該公約系于1973年6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所簽署,其中規定的瀕危野生動物名錄歸類成三項附錄。但是名錄所涉范圍僅限于部分珍稀野生保護動物,而忽視了一般野生動物的保護,從而成為廣大野味市場“鉆漏洞”的法外之處。
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于1988年頒布實施,歷經四次修訂,對于珍稀重點野生動物進行分層級保護。其中第十條規定了法律所保護的野生動物都被收錄于《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中,這三種名錄以外的野生動物不受該法保護。
當然,我國還有其他提到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法規,如《環境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漁業法》《畜牧法》《草原法》《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國務院關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陸生野生動物資源保護法管理費收費辦法》《國家重點保護馴養繁殖許可證管理辦法》等。但這些法律法規都把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局限于部分珍稀動物范圍內,而不在名單上的動物則沒有任何明文限制。從長遠野生動物生存環境來看,對野生動物的保護不應該僅停留在其生物價值上,還應該考慮到人類的防疫性價值。一般野生動物也是具有保護價值的,同時其身上也具有可能威脅人類生存的病毒。
(二)《野生動物保護法》與相關部門法的銜接不足
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與相關部門法沒有更為有效的銜接。一方面,與《刑法》的銜接不足。該法屬于環境法部門,而要實現環境刑法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加強環境法與刑法的銜接,讓環境法的精神和理念在刑法中得以體現,才能更好地發揮法律效用。而銜接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因為《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范圍僅限于部分珍稀動物,導致《刑法》中規定的保護范圍過于狹窄。例如,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和非法收購、運輸、出售、走私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罪,均主要保護的是珍稀野生動物,而對于一般野生動物的捕獵等違法行為未有確切規定。其二,未有關于非法食用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無法落實罪行法定原則。對于食用野生保護動物,《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及第四十九條均規定禁止個人食用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及其制品和違反義務所應負擔的責任。但是《刑法》僅在第三百四十一條中規定了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對送上餐桌流程中的生產制作、經營與私自食用野生動物等罪名卻未有體現,對于經營制作及出售和食用所導致的大規模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應當如何處置規定也處于空白狀態。其三,入罪標準過于片面。目前《野生動物保護法》關于野生動物的價值衡量考慮的大部分是其經濟價值,而遺傳價值、生態價值未得到特別重視,銜接到《刑法》入罪標準也是過于側重經濟價值,如非法獲利金額等財產性犯罪較多。但是野生動物具有多重價值,對于非正當來源的野生動物,即使其經濟價值可能不高,但是難免具有一定的疾病傳播性,若不加以刑罰措施,難以震懾相關違法行為和犯罪分子。另一方面,《野生動物保護法》僅可以約束野生動物。而家養動物對于潛在疾病的引發也具有一定風險性和可能性,因此,應當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增加相關家養動物的檢疫、管理等一系列內容。
(三)野生動物行政許可制度
目前,無論是國家或地方的重點野生動物保護還是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只要符合規定的馴養條件,就可以取得許可證進行經營、馴養等行為。目前,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共規定了5項行政許可,①但是并未明確規定許可的取得程序、條件、信息公開途徑等,而是將權力下放給地方縣級以上行政機關進行自我規定,這就導致許可證機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容易被一些濫用權力的公職人員所利用而進行不法牟利。例如,2018年江西省森林公安局公布的一起販賣野生動物案中,涉案動物1.7萬余只,銷售網絡覆蓋全國15個省份。據專案組透露,一些公職人員參與販賣,為不法分子非法開具運輸證明文件,充當保護傘,為犯罪活動提供便利。
由于許可證制度存在的巨大漏洞,被不法商家利用建立了黑色利益鏈條:從捕獵野生動物開始,捕獵人員將獵到的野生動物賣給中間收購商,中間收購商往往再出售給更高級別的收購商(高級別的收購商一般具有林業相關部門頒發的馴養繁殖野生動物許可證),從而將不法商品洗白流入市場。可見,許可證制度的漏洞與執法羸弱、散漫,造成了野生動物買賣黑色利益鏈條的形成。
二、《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構建與完善
(一)擴展野生動物保護范圍
日本對于野生動物的保護,不僅關注于瀕危野生動物,還會對其他野生動物進行整體的監控和管理。但在具體應用時,按照本國野生動物的保護和管理層次,劃分為滅絕種、瀕臨滅絕種、瀕危種、稀有種、區域個體群五個種群,將大范圍的野生動物都劃定進法律的管制范圍之內。[1]意大利將野生動物的保護分成兩種,一般保護動物和特殊保護動物,其中特殊保護動物嚴禁被狩獵,但是一般保護動物的捕獵則被詳細規定在《體育狩獵法》等法律規章中。因此,針對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范圍狹窄的現狀,建議將野生動物的范圍擴大。
而針對野生動物的食用,本文認為難以真正取締,因為其屬于傳統流傳而來的,想要真正做到對食用野生保護動物的防控需要具體細化明確。如:我國臺灣地區制定的《原住民族基于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再殺野生動物管理辦法》附上了規定有野生動物的種類、時間、期限和捕殺方式以及捕殺后去向等內容,對于野生動物的捕獵和后續食用等也進行了進一步的嚴苛限制。[2]我國應當將食用的野生動物范圍明晰化,建立制定許可食用動物品種正面清單,以及禁止捕殺、加工、運輸、銷售和食用的動物的非許可清單。同時出臺針對許可食用動物的捕殺時間、期限、捕殺方式等細化的管理辦法,使得從捕獵野生動物到被食用的全過程透明化、規范化,也可參考荷蘭、德國指定專門的公司進行野生動物產品加工利用,從收購到制作銷售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操作體系。[3]
(二)與其他部門法內容應有所銜接
如上文所述,《野生動物保護法》僅能對野生動物進行調控,但對家養動物的防控則超出了調整范圍。因此,應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增添相關家養動物的管理與防疫辦法,包括寵物飼養許可證、疫病預防接種辦法以及在特定區域內要求強制拴控,如果家養動物具有潛在病毒疫病危險時,相關防疫部門有權對其采取扣留、代管、接種疫苗等強制措施。
《刑法》應當將野生動物的保護范圍擴大至一般野生動物,將加工、制作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用于食用,故意食用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故意食用一般野生動物有引起病毒傳播危險等行為進行入罪處理。同時,對于野生動物的入罪標準不應僅考慮經濟價值,還應考慮野生動物的病毒傳播可能性與生態價值。當制作、售賣、食用等過程中出現的不法行為可能危害人體健康時,應給予此類不法行為較高的刑罰與罰金懲處。對于明知有違法經營或食用野生動物的情況,知情不報造成嚴重危害結果時,也應給予相應的懲處。應以更加嚴厲的刑罰和更加完善的罪名體系,警示借野生動物實施危險行為的犯罪分子及潛在的危險分子。
(三)野生動物許可證制度標準化、法律化
首先,野生動物許可證的頒發門檻應當予以提高。目前,我國野生動物產業呈現出大范圍、多廣度的經營狀況,如此巨大的經營面反映出三個問題:其一,我國野生動物經營許可證頒發的門檻較低;其二,頒發許可證的門檻低導致經營者數不勝數,相關行政部門管理困難;其三,經營許可證頒發后的監督機制和信息公開機制缺失。所以,提高許可證的門檻是十分迫切的。[4]
本文建議許可證門檻的提高主要從四個方面入手:其一,前提是加強審查程序流程的公開透明法律化,這樣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就會降低官員趁機牟利的可能性,將權力曝光在陽光下。其二,統一全國各地的許可證頒發標準,改變各地核發許可證標準不統一的現狀。由中央相關部門直接頒布統一的野生動物許可證,各地方政府僅具有增設條件或者細化條件的權力,但不得濫用權力刪減標準內容。其三,將許可證核發的權力集合于地方行政機關的林業部門,防止地方政府部門推權諉責現象出現。其四,取得許可證前,要求經營者簽訂進行定期信息公開的承諾,內容包括馴養野生動物的種類名單、具體規模、是否經過檢疫、新出生幼獸的數目、每種野生動物的發展情況以及繁殖野生動物養殖標準。若不履行定期公開的義務,則處以一定的罰金。[5]
許可證頒發后,相關林業部門要定期組織工作人員對后續許可證使用情況進行評估監督,并制定評估報告。如果存在違法亂象,則及時予以糾正和整頓。同時,設立社會監督舉報制度,對未取得許可證仍經營野生動物或取得許可證但違法操作的經營戶進行舉報的社會人士予以一定的精神和物質獎勵,讓群眾參與到保護野生動物的行動中來。
三、結語
野生動物無分貴賤均是大自然的產物,是與人類共存亡的生命共同體一般,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系。因此,《野生動物保護法》及相關部門法的完善和銜接是必不可少的,是廣大人民創造野生動物美好家園所迫切期冀的。最后,希望相關部門和社會組織也能夠加強宣傳教育,并創造機會讓群眾參與到保護野生動物的活動中來。
注釋:
①參見《野生動物保護法》第16-18條、第22-23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