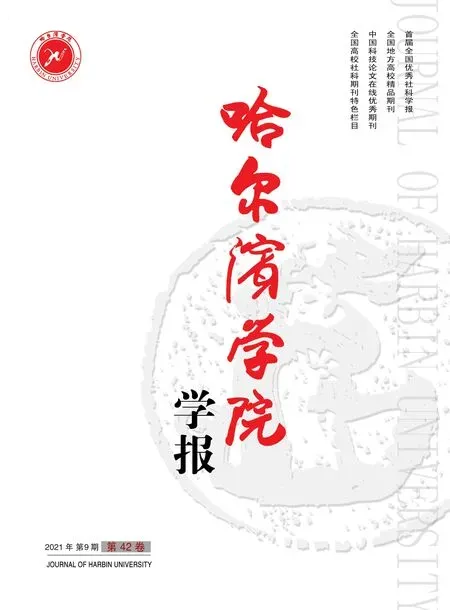傳統社會白族婦女勞動生活探微
李戎戎
(大理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 大理 671003)
一、傳統社會白族婦女勞動生活的內容
從總體來看,各地白族婦女勞動生活內容雖然有所差別,但忙碌和辛勞程度大同小異。
1.家務勞動
白族婦女每天早晨四五點起來勞作,晚上九十點鐘才得歇息,每天要從事的家務勞動包括煮飯、照顧孩子、服侍老人、飼養家畜家禽等。此外,十月縫制衣服,冬天貯藏和準備過年的食品(磨面、碾米、腌制食品),遇年節時,還要殺雞烹牛,灑掃庭院,招待親友。
2.生產勞動
白族婦女在農業生產中起著重要作用,她們不僅從事一些輔助性勞動,還直接從事田間農業生產。如:“凡力作男女偕而女數常贏,二月布種,三月收豆,四月收麥,五月插秧,六七月耘,凡耘必三遍……每歲僅得兩月隙。”[1]喜洲地區“男女在勞動上有一定的分工,一般是男活較重,女活較輕。如男子做犁田、耙田、挖田、翻垡、開溝、運肥出糞、播種、放水、砍柴等;婦女做撥秧、薅秧、打豆麥、打稻草等;栽秧、收割稻谷、豆麥男女都做”。[2](P29-30)《滇南新語》載:“蓋劍(川)土饒瘠,食眾生寡,民俱世業木工,滇之七十余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近則仲夏孟冬栽獲兩歸,遠則亦收獲為期必一返,獲畢仍往,是以劍之耘蓐樵牧盡屬村妝,男既遠游,女當門戶,催糧編甲,亦多婦代夫役,皆能練事無誤。”[3]
除田間勞動外,家庭手工業也是白族婦女日常勞動的重要內容。如喜洲地區,“全鄉婦女凡15歲以上均會織布,1949年前共有木機500多架,產品多為自產自銷,也有為商人加工而獲取工資的。”[2](P44-45)再如,《鄧川州志》有:婦女擠完牛奶后,“以牛乳杯許煎鍋內,點以酸汁,削二圓箸,輕蕩之漸成餅,拾而指攤之,仍以二箸輪卷之,布于竹架成張頁而干之,色細白如輕殼。售之張值一錢,商販載諸遠,為美味香脆,愈酥酪。凡家委四牛,日作乳扇二百張,八口之家足資俯仰。”[4]
在白族家庭中,婦女還是畜牧業的主要勞動力。據寺上村調查,“豬、雞飼養收入相當于農業收入的二成左右。”[5](P201)
跨境電商企業在跨境交易過程中,由于企業所處的不同國家之間在經濟、文化、制度上存在的差異導致信用級別各不相同。目前國與國之間并未開放企業信用共享平臺,這也使得在跨境交易過程中不同國家企業對于對方的信用評估很難做到有效,這就使交易的雙方企業很難做到互相信任,從而讓企業出現逆向選擇的后果,進而影響整體跨境電商的開展。
3.雇傭勞動
近代以來,在白族封建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存在著雇傭勞動。在1949年以前,喜洲勞動力市場每天有三四百人至五六百人之多,其中婦女占到三分之一。除了地主從市場上直接雇傭勞動力之外,各鄉農民間也會由于農業季節的安排有彼此調節勞動力的需求。例如,喜洲一帶晨登村栽秧時,沙村、河涘城村還不能栽秧,晨登村就會雇傭沙村、河涘城村的農民;而到了沙村、河涘城村栽插時,同樣會雇傭晨登村的勞動力。這些栽插隊伍中多半是婦女。
除農業生產的雇傭勞動外,白族地區的大地主家一般都雇有奴仆,從事挑水、煮飯、灑掃、種花、守房、領小孩等家務勞動,一部分白族婦女成為地主家的奴仆。
4.貿易經營活動
自古以來,白族主要居住地洱海區域是滇西北物資交流和貿易中心。據《云南志略》記載:白族地區“市井謂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6](P34)白族婦女活躍在集市中,“俱結棚為市,環錯紛紜。千騎交集。男女雜沓,交臂不辨。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蠻物無不至。”[7](P318)白族女孩“除了幫助農婦在家里忙忙碌碌外,她們還要背上農產品去趕集。早在十三四歲,她們就到市場上去賣農產品,晚上把收入帶回家。民家(指白族)女孩成天穿梭于忙碌的城鎮街道和鄉村集市”。[8](P136)“漁潭會上人山人海,90%是民家農民和他們的家庭,尤其是婦女。”[8](P59-60)可見,白族婦女是集市貿易的主要經營者和參與者。
另外,劍川、鶴慶等地的婦女經商也很活躍,俗稱“背背子”。劍川婦女經常背著針線等日雜用品進麗江、中旬等地換回(背出)皮毛、藥材等,有的則背運木器家具到大理、下關等地銷售,還有的背著雜貨深入山區或村莊收購香茵、藥材等山貨和各種農副產品,促進了邊遠地區、山區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白族婦女勞動生活的特點
1.時代性
近代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族婦女的家庭手工業產品部分流入市場,使手工業生產與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惟吾邑自咸同以前,初無所謂洋貨。光緒初,洋貨始漸輸入,洎越亡于法,緬淪于英,是洋貨充斥。近則商所售,售洋貨,人所市,市洋貨。數千年之變遷,未有甚于今日者。’‘矧今外貨輸入,既美且廉。茍以一手一足之人造物,而欲與如火如荼之機造物相抵制,優勝劣敗,無待贅言。’絕大多數從事傳統手工作坊紡織的婦女‘自外洋縫衣機器輸入,衣帽靴鞋尤為工省價廉,女工因以坐困。’”[9]大理的“入境貨以洋紗、木棉、絲、茶、藥材為大宗;出境貨以礎石、土布為大宗。”[10]大量廉價洋紗的傾銷使手工紗紡的生產環節逐漸被取消,加重了生產者對洋紗市場的依賴。可見,西方殖民主義入侵中國,使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步瓦解,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道路,與此同時,白族婦女從事的家庭手工業也有逐漸解體的趨勢。
2.民族性
白族地區雖然有壩區和山區的差別,有階級的差別,但白族婦女中絕大多數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極為貧乏。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經濟的逐漸解體,白族婦女的生活雖然也發生了變化,但變化速度和幅度都極小。可以說,在整個婦女群體中,農村婦女,特別是白族農村婦女是滯留于封建社會時間最長的一部分人。
白族地區婦女也有階級之分,地主、富商、官宦之家的婦女與城市漢族上層婦女一樣,過著安逸舒適至少是豐衣足食的生活,并且由于經常隨夫短期赴任,或是在外的丈夫經常回鄉探視,她們能更多地接觸到近代文明。中等階級的白族農村婦女,雖然能維持溫飽,但必須從事家務勞動以佐家計。而下層白族婦女則過著勞苦之極、貧困之極的生活。
3.地域性
自古以來,白族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在洱海流域的白族經濟核心區,近代以前就已進入封建地主經濟社會,生產力處于較高水平,農業和手工業商品生產經濟較為發達,“幾與內地并駕齊驅”。[6](P88)而怒江地區的瀘水、六庫等地則處于封建領主制經濟狀態中。怒江地區的福貢、碧江等地直到近代還處于原始公社殘余時期。因此,處于不同經濟社會形態的白族婦女勞動生活狀況也具有差異性和多層次性。居住在洱海流域、平壩地區的白族婦女,由于處于封建地主經濟形態中,她們的勞動生活狀況與中原地區漢族婦女較為接近。這些地區白族婦女的生產和生活最早受到近代化的沖擊,農業、家庭手工業也最先受到資本主義商品傾銷的影響。當然,這些地區的白族婦女也最先受到進步思想的沐浴,得到受教育的機會,獲得職業和技術培訓,并最先走出傳統家庭,實現社會就業。
與洱海流域相比,怒江地區的瀘水、六庫和福貢、碧江等地白族婦女勞動生活的辛苦程度和貧困程度要嚴重得多。由于這些地區相對閉塞,與內地聯系少,受到的近代化沖擊相對較輕,所以,這些地區的白族婦女過多地保留著傳統社會的勞動狀況。甚至在福貢、碧江地區還有少部分白族婦女充當著奴隸,過著與近代化毫無聯系的生產和生活。
三、傳統社會白族婦女勞動生活的意義
傳統社會,白族婦女的勞動不僅維持了家庭的生存,還推動了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第一,家務勞動是家庭生活和社會生產賴以存在和進行的一個必要條件。恩格斯指出:“在包括許多夫婦和他們的子女的古代共產制家戶經濟中,由婦女料理家務,正如由男子獲得食物一樣,都是一種公共的、為社會所必需的勞動。”[11](P84)男子的田間勞動和其他工作只有在婦女承擔家務勞動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沒有白族婦女所提供的生活服務和輔助勞動,男子很難順利進行大田農作。
第二,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傳統社會,農業生產需要大量人手,僅僅依靠男勞動力根本無法完成,婦女們也必須參與到農業勞動中去。由于婦女們的參與,增加了勞動人手,有助于農作物的適時耕種,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滿足了家庭對糧食、蔬菜、副食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第三,白族婦女通過紡織、刺繡、飼養禽畜、參與漁業等經濟活動,在滿足家庭需要的同時,將剩余部分轉化為家庭收入,既減少了家庭開支,又補充了田間收入的不足。此外,婦女把手工業品、蔬菜、家禽、蛋類、奶制品等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補貼家用,提高了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的農民家庭的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收入,對維持家庭的生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意義。
第四,白族婦女通過參與農業雇傭勞動,不僅補貼了家用,也為農業發展提供了自由勞動力,對農業發展起著促進作用。白族婦女各種形式的經營與貿易活動,不僅促進了鄉村經濟的發展,也加強了鄉村的聯系,對活躍鄉村市場和滿足社會需求,都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四、結語
馬克思曾說過:“每個了解一點歷史的人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衡量。”[11](P480)所以,當我們研究白族社會的時候,必須正視白族婦女的勞動對文明的奉獻。同時,提高對婦女勞動生活重要意義的認識,對于提高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