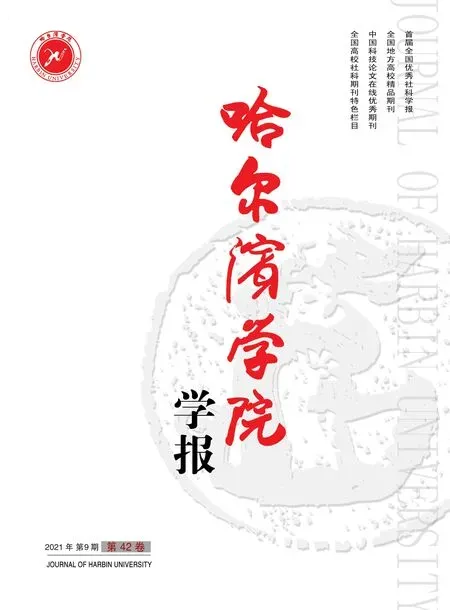從一滴水透視整片海洋
——《蒙塔尤》的史學理論與方法管窺
權春燕
(貴州師范大學 歷史與政治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開始,并波及到法國,布洛赫和費弗爾為適應時代形勢的發展,以經濟和社會研究為中心取代政治領域研究,創立了刊物《經濟和社會史年鑒》和年鑒學派。作為第一代年鑒學派代表人物,他們除了關注經濟和社會領域外,還倡導跨學科研究,研究范圍涉及人類活動一切領域即總體史研究,倡導問題導向史學。1956年布羅代爾接手年鑒學派,倡導總體史觀,將總體史分為長、中、短三時段,強調長時段對人類發展起支配作用,重視宏觀結構、注重分析,排斥敘述、排斥文化心態、輕視政治史。[1]
二戰后,年鑒學派在西方史學界占據主導地位。布羅代爾的總體史認為,歷史中最重要的最占支配地位的是長時段,進而注重宏觀結構,忽視微觀研究,忽視個人和事件。此時,年鑒學派走向鼎盛時期。但由于第二代年鑒學派過于關注結構,使史學研究成為數據列表的組合而陷入唯科學論,到20世紀70年代,總體史遭受嚴重質疑。[2]之后,勒華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等接手年鑒,放棄了對經濟和社會的研究,“扮演起了人種學家的角”,注重反復性事物和個人的曲折經歷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的記憶,研究變得更為個體化和局部化,由此推動了微觀史的興起。[1]以勒華拉杜里為代表的第三代年鑒學派,運用人類學方法介入史學研究,放棄了布羅代爾長時段結構理論,從微觀研究入手,視角轉向底層普通民眾,問題導向從經濟、社會轉向文化和心理。
這種轉變在史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勒華拉杜里的鼎力之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簡稱《蒙塔尤》)成為西方史學轉型的標志之作,也是歷史人類學的經典之作。
《蒙塔尤》主要講述了法國南部一個名叫蒙塔尤的小山村在1294—1324年間的歷史。該書由勒華拉杜里根據一份14世紀富尼埃宗教裁判所審訊資料的拉丁文手稿寫成。自1975年問世以來,深受歡迎,成為風靡多國的暢銷書。下文中,筆者嘗試對《蒙塔尤》的史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剖析,希望能夠給史學轉向新文化史提供借鑒。
一、《蒙塔尤》將人類學介入史學研究
(一)從人類學視角考察整合史料
從史料處理上看,雖然《蒙塔尤》中的史料早已被他人用過,但勒華拉杜里“依照人類學家常常撰寫的社區研究的方式,將嫌疑人向審問人提供的信息進行重新編排”,[3](P76)也正是因為他以跨學科人類學的眼光和方法來考察這份歷史資料,因而看到了資料背后的東西。這一跨界的思維方法——將史料與人類學的緊密結合,使得《蒙塔尤》的研究方法耳目一新,推動了史學研究的發展,形成了新的學科領域——歷史人類學。
(二)從人類學視角進行“共時性”考察
“共時性”是指在同一時間內,對社會的整體性考察。人類學注重運用全面考察法進行研究,《蒙塔尤》亦如此。其研究包括:對環境的考察;對蒙塔尤村掌握權力的克萊格家族的權力及地位考察;對經濟的關注,如牧民的轉場生活和經濟狀態分析;對文化心態考察進行的細致描述。這些都體現了人類學的全面考察法,是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最好體現。
(三)借用人類學生態與考古方法考察
“在人類學研究中,對調查地生態環境的考證是揭示社會結構、文化、人類生活狀態的前提。”[4]《蒙塔尤》首先對蒙塔尤小山村的環境進行考察,然后揭示普通民眾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狀態,明顯運用了人類學的方法。尤其是第二部分的考古不是歷史學上的考古,而是人類學上的考古,也就是心態的考古、文化的考古,作者通過一系列舉止、規則、態度、儀式習俗等心態和感知方式的考察,揭示當時民眾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
(四)采用了解釋人類學“深描”方法
解釋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深描”,源于人類學家格爾茨借用賴爾對“眨眼睛”的分析。格爾茨沒有給出“深描”明確的定義,而是用四種眨眼來說明“深描”的內涵。他認為“四種眨眼就構成不同的文化層面,包含了不同的文化意義,深描就是要區分這四種眨眼的意義”。[5]“必須以他們用來界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那些事的習慣語句來表達。”[6](P19)格爾茨的“深描”是建立在公共文化意義前提上的,其最終目的是對公共文化背后的特定文化意義的解釋。可以說,“深描”重在對研究對象深層次的描述,如:集體心態特征、日常事務的看法、習俗儀式等的深層挖掘,凸現“深描”對象背后的文化意義,使讀者讀起來有血有肉、形象生動,便于擴大史學的影響力。由于“深描”要求站在研究者角度進行研究,促進了民族志田野調查的發展。但“深描”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深描”是描述性的,其客觀性遭到一些學者的質疑。
(五)人類學結構功能主義融入《蒙塔尤》創作
勒華拉杜里曾經說過,他是馬林諾夫斯基功能主義的專業實踐者。[7](P5)這在《蒙塔尤》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蒙塔尤》第一章,勒華拉杜里分析了蒙塔尤地方權力的分配,以及權力外散到與它相關的“等級社會”和“領主制度”及“領主權問題”,充分地體現了其深受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另外,《蒙塔尤》中對家庭的構成及變化,家中的各種關系以及家如何作用于家庭成員等的分析,也都體現了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
二、《蒙塔尤》運用微觀史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
(一)《蒙塔尤》中微觀史學的運用
1.研究范圍微小。微觀史學是“本質上以縮小觀察規模、進行微觀分析和細致研究文獻資料為基礎。”[8](P99)微觀史學側重于“微”,即入手處小、放眼處大,選小范圍時空內獨特歷史作為切入點,可以是一個字、一個物、一個人那么微小,也可以是一個村莊、一個地區的規模,進行細微觀察,通過這種以小見大的手法展現曾經的歷史。[9]勒華拉杜里在審視14世紀宗教裁判所史料時,用微觀史的理論發掘了不一樣的歷史,他通過蒙塔尤這個小村莊的一個個普通牧民折射了當時法國的歷史。
2.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提名法和證據范式。(1)按照微觀史學的說法,提名法是“縮小歷史考察的規模到可以確切地確認身份的個人”。[10]提名具體名字,尋找圍繞名字展開的關系網,個人也在這個網中。[11](P2-10)由此可以看出,提名法就是鎖定研究對象具體細微到有名有姓的個人身上,以提名個人為線索,發散到與這個提名人有關的周圍的社會生活關系網絡。由此對史料進行搜集和整理研究,進而還原當時時代的生活原貌、內心世界及生活軌跡等。《蒙塔尤》中,如對本堂神甫克萊格提名,再發散到他的兄弟、他的父母親及家族、他的情婦、與他對立的阿澤馬小集團,等等;再如,對牧羊人皮埃爾·莫里的提名,到他的家人、他轉場的牧民生活朋友以及和他來往的種種異端人物,等等。《蒙塔尤》中這樣的提名較多,不再一一列舉。(2)證據范式又稱“推測范式”,“通過分析、整理將散落在檔案文獻中的瑣碎證據組織起來,復原和構建歷史的研究方法。”[9]《蒙塔尤》中,勒華拉杜里先生通過對14世紀宗教裁判所的審判記錄進行分析,將記錄里每一個人物的證詞口供等看似零散的證據組織起來,重新進行排列組合,復原了當時法國南部蒙塔尤小山村的歷史面貌。這種方法使得用過的材料綻放出新的活力,展現了推測范式的魅力。但也正因為推測范式是基于跡象和零碎證據的推測,其受到質疑,特別是運用科學計量方法研究歷史的史學家的嚴重質疑。
3.研究對象主要關注下層民眾的微觀文化生活。“微觀史學更傾向于通過分析意識形態、集體心理、風俗儀式、信仰認識等文化因素來解釋歷史。”[12]《蒙塔尤》也是如此,主要表現有:(1)作者所側重的內容不是政治軍事等宏觀史學所關注的,而是微小范圍內的微小人物,即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蒙塔尤》里體現微觀史學側重的意識形態有很多,如對純潔派采取中立態度,“皮埃爾·莫里甘愿以經常性的貧窮為伴。對他來說,貧窮甚至是一種理想和價值體系。當然,這種理想是新福音文化以各種方式傳播的。那些自愿受窮者、善人們或方濟各會修士在奧克西坦尼到處宣揚這種文化。但是,皮埃爾和蒙塔尤的許多純潔派牧民都接受了這一理想。”[13](P168)還有對婚姻的看法,認為“在短期內,結婚無異于一種貧困化的威脅”。[13](P259)(2)《蒙塔尤》中有很多關于集體心理的描述,如對時間心態的描述:“無論精確與否,農民的時間觀念總是游移不定的,這些不同的說法表明了這一點。”[13](P436)“蒙塔尤的村民似乎并不依靠教堂的鐘聲來準確地區分時間段,因為對于一種時間觀念不甚強的文明來說,沒有必要嚴格區分時間段。”[13](P430)再如對空間心態的描述:“用來表示空間概念——包括身邊的、地理方面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空間——的基本觀工具是身體,特別是手和臂。”[13](P442)(3)《蒙塔尤》中也有很多關于風俗儀式的描述,如“各家都有自己的‘星座’和‘運氣’,‘死去的人也在其中’。為保持這種星座和運氣,一家之主死后人們便把他的指甲和頭發珍藏在家中:指甲和頭發若能在人死后繼續生長,它們就可以帶來極強的活力。由于這種習俗的流行,‘人的神奇性滲透到’家庭中。接著家便可以把這種神奇性傳給其他成員。”[13](P50)(4)《蒙塔尤》中關于信仰認識也很多,如“她的老母親叫她不要相信善人,因為他們不能使靈魂得到拯救。”[13](P484)
可以說,《蒙塔尤》是勒華拉杜里對微觀史學的一次偉大嘗試。作為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受第二代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長時段”影響,“他的第一部名著《朗格多克的農民》明顯反映出‘長時段’理論的影響;他也曾大聲疾呼‘史學中的計量革命’;直至1973年11月,他在法蘭西學院的發言還以《靜止不動的歷史》為題。”[14]因為史學過于看重長時段、計量法等,導致出現了“沒有人和事件的歷史”,20世紀70年代年鑒學派受到嚴重質疑。于是,如何對歷史進行研究被重新思考和探討。在史學家質疑、史學危機日益嚴重及國際趨勢漸向微觀史發展的背景下,法國第三代年鑒學派代表勒華拉杜里積極反思和探索,放棄計量式研究歷史的方法而轉向微觀研究,寫出了微觀史學的代表作《蒙塔尤》。可以說,《蒙塔尤》是勒華拉杜里積極探索和反思的成果,他將眼光從長時段宏大敘事轉向了有限歷史時間段內的微小民眾身上,關注普通民眾的言行舉止、集體心態、風俗習慣等,通過對民眾入微的觀察和描寫,來折射那個時代的歷史。
(二)《蒙塔尤》中微觀史學研究的意義與不足
《蒙塔尤》轉向微觀史學研究的意義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是對宏觀史學的一個有益的補充。由于微觀史學研究的對象是一個有限的歷史范圍,并且是對微小的個人或社區進行的細致入微的敘述,這就導致其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問題。史學家在實踐過程中,所研究的大多個人或地區往往不能代表所有的歷史。因而筆者認為,微觀史學只能是宏觀歷史的有益補充,同時拓展了史學的資料范圍。因此,《蒙塔尤》很明顯是對法國南部地區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和補充。第二,《蒙塔尤》研究細致入微,敘事生動,擴大了讀者對史學的興趣。特別是對愛情婚姻、牧民行為舉止、生活習俗儀式等內容的生動、詳細的敘述,使這本書更為讀者所喜愛,成為風靡多國的暢銷書籍。第三,《蒙塔尤》打破了以往只關注精英階層歷史的格局,使史學家的眼光聚焦于普通民眾身上,擴大了歷史研究的范圍。第四,《蒙塔尤》轉向微觀史學,關注一定范圍內普通民眾,對史學研究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即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豐富了史學理論研究方法。
盡管如此,《蒙塔尤》轉向微觀史學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蒙塔尤》關注特定歷史區域的微小人物的研究,而這些微小人物在歷史上很少被記載,所以在史料方面資料比較少,作者只能對有限的零散的史料進行蛛絲馬跡式研究,找到相對比較可能的解釋和結論,這就使得轉向微觀史的《蒙塔尤》在科學真實性上遭到質疑。第二,時間的連續性沒那么強。《蒙塔尤》的微觀史轉向以及后來其他國家很多的微觀史,雖然生動易讀但過于零碎,再加上不是按時間順序組織史料撰寫的,所以讀起來感覺時間的連續性沒那么強。
三、《蒙塔尤》運用社會心態史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
法國年鑒學派比較關注心態史的研究,年鑒學派一代、二代人物費弗爾、布洛赫和布羅代爾都試圖對民眾的心態進行探討,布洛赫曾多次提出歷史事實的本質是心理的事實。到第三代年鑒學派勒華拉杜里更是將心態史和社會文化史聯系在一起。
(一)《蒙塔尤》中社會心態史的運用
據勒戈夫考證,法語“心態”借自于17世紀英國哲學,指的是“‘人們,一個特定人們集團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15](P273)后來,受文化人類學影響,它是一種無意識的集體現象。[15](P274)《蒙塔尤》第二部分主要是心態史,書中詳細分析了蒙塔尤人的集體心態,如對婚姻和愛情的描述、對自然和命運的態度、對死亡的看法以及人們的行為舉止、習俗宗教儀式的描述,加上對心態工具時間和空間的敘述,都體現了心態史理論方法的運用,是勒華拉杜里運用心態史方法介入史學的研究。當然,他并不是首創者。費弗爾和其弟子芒德魯以及杜比都曾關注和探索心態史領域,后來勒華拉杜里、勒高夫也加入其中。心態史在西方沒有公認的權威概念界定,對心態史的看法也不完全相同。勒華拉杜里注重集體心態研究,注重群體無意識的研究。無意識是因為這些是大家習以為常的、司空見慣的,比如禮儀風俗、道德規范、慣例和禁條等,不能虛幻表達。[16](P195)所謂群體無意識就是大家對老生常談的、司空見慣的禮儀風俗、日常生活、愛情、對兒童情感、宗教信仰等事物的態度。從《蒙塔尤》中可以看出,勒華拉杜里眼里的心態史也就是民眾對一些最習以為常的事物觀念的看法和態度,如對時間和空間的心態看法,對兒童情感的看法,對死亡的看法,對貧窮財富的看法,當然也包括一些價值觀,以及行為舉止背后所反映的心理意識,等等。
(二)《蒙塔尤》中社會心態史研究的意義與不足
《蒙塔尤》中社會心態史研究的意義有兩個方面:第一,運用心態史的方法使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開創了史學研究的跨學科領域,使史學能和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等)密切結合,為史學研究注入了新活力。第二,心態史為史學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史料研究范圍。勒戈夫認為:“心態史的特征表現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資料上,所以什么資料都可以使用。”[15](P276)“一切資料(包括以前被史學家棄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為心態史所用。”[17]
《蒙塔尤》中社會心態史的運用仍有不足:心態史若不和整個大時代的歷史緊密相聯系的話,過于細微的研究容易導致史學更加碎片化;微觀史學和心態史若運用不當的話,很容易為后現代主義思潮所利用,成為否定理性的槍手,或成為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幫手,這違背了微觀史學補充宏觀敘事的初衷。
四、結語
《蒙塔尤》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這部作品是在史學特別是布羅代爾長時段理論出現危機時,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勒華拉杜里不斷思考和探索的結果。勒華拉杜里想解決史學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他不持守舊理論停滯不前,吸收了年鑒學派前輩的長處又不拘于此,積極借鑒世界歷史學科之外其他學科的方法和理論,不斷地探索和思考推進史學問題解決的辦法。他將人類學方法介入史學研究,關注宏大敘事之外的微觀史,關注歷史風云中一個個鮮活跳動的生命的內在精神世界和心態特征,從而窺看法國歷史的時代狀況。勒華拉杜里在《蒙塔尤》中展現給我們的是:一滴水是微小的,一個細胞是微不足道的,但一滴水折射的海洋是如此的鮮活美麗,一個細胞所構成的龐大社會生物體是如此的栩栩如生。《蒙塔尤》的小山村所折射出的13世紀末14世紀初法國南部的民眾集體心態狀況,成為眾多法國史中的一部分。一滴水之美是因它是匯成海洋的重要因子,它沒有脫離海洋而存在。《蒙塔尤》的美也正在于此,雖然它也有瑕疵,但作者給予《蒙塔尤》這部作品猶如它在扉頁所寫的那樣“初衷是美的”。然而,史學界卻出現了一股后現代主義的思潮,來勢洶洶地解構整片海洋,使史學研究更加碎片化,更加碎得摸不著史學的中心,碎得不知道海洋為何物。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下,史學危機更加嚴重。筆者認為,無論是宏大歷史的敘事還是微觀歷史的研究,都要把握好宏觀歷史和微觀歷史之間的關系,不能脫離這種關系而完全倒戈一邊;要把握歷史研究和書寫的分寸,使宏觀歷史和微觀歷史結合起來,在宏觀歷史中加入微觀民眾的歷史部分,在微觀歷史中強調微觀和宏觀之間的關系;不能脫離宏觀而僅僅為微觀而微觀,要用“兩條腿”走路,注意史學研究的平衡性和度的問題。或許這樣,未來的史學發展既不會迷失中心方向,又不乏鮮活有趣。管窺經典之作《蒙塔尤》,一滴水的歷史猶如一顆明珠一樣珍藏在歷史的寶匣中,它璀璨美麗、熠熠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