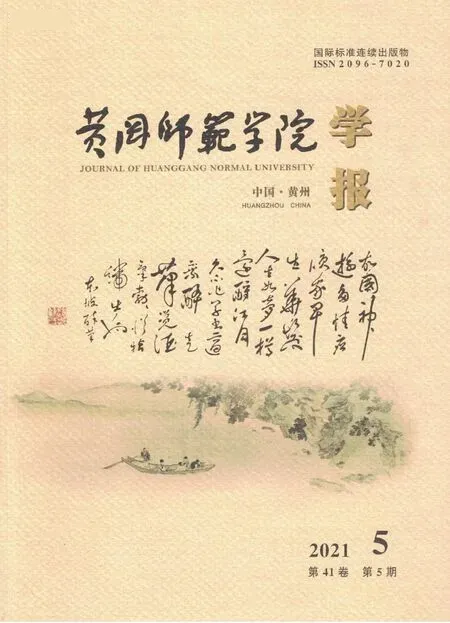文化視域下《江城子·密州出獵》的創(chuàng)作動(dòng)因
白銀銀
(淄博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人文科學(xué)系,山東 淄博 255100)
熙寧七年(1076),蘇軾罷杭判知密。這是蘇軾為避免朝廷黨爭(zhēng)波濤,“通守余杭”后“求為東州守”[1]265。蘇軾知密期間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政治才干和務(wù)實(shí)精神,“勤于吏職”[1]373、“不計(jì)勞逸”[1]31,在詞學(xué)創(chuàng)作上也取得了令人矚目成果——“密州三曲”。“密州三曲”之一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被學(xué)術(shù)界認(rèn)為是蘇軾豪放詞風(fēng)的發(fā)端之作。一個(gè)經(jīng)典文學(xué)作品的產(chǎn)生,是時(shí)代風(fēng)潮、學(xué)術(shù)思想和個(gè)人才華等多方面因素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故所謂性靈抒寫(xiě)者,雖出于此一作家之內(nèi)心經(jīng)歷,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傳統(tǒng),大體系,所謂可大可久之一境,源泉混混,不擇地而出。在其文學(xué)作品之文字技巧,與夫題材選擇,乃及其作家個(gè)人之內(nèi)心修養(yǎng)與夫情感鍛煉,實(shí)已與文化精神之大傳統(tǒng),大體系,三位一體,融凝合一,而始成為其文學(xué)上之高成就。”[2]因此,筆者試從宋學(xué)經(jīng)世濟(jì)民思想對(duì)詞創(chuàng)作導(dǎo)向的推動(dòng);“尊王攘夷”華夏中心主義情結(jié)的凸顯;密州自古以來(lái)崇武尚兵地域文化的影響三個(gè)方面,探討《江城子·密州出獵》出現(xiàn)于蘇軾知密時(shí)期的原因。
一、宋學(xué)經(jīng)世致用思想對(duì)詞創(chuàng)作導(dǎo)向的影響
蘇軾生活時(shí)期正是宋學(xué)勃興之時(shí),是儒學(xué)繼漢朝“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以后的又一次全面復(fù)興。在宋代,宋學(xué)是最著名的一代之學(xué)術(shù),詞是最璀璨的一代之文學(xué),兩者之間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一種學(xué)術(shù)思想,便是那一時(shí)代的人,在那一社會(huì)環(huán)境中,對(duì)社會(huì)人生問(wèn)題的一種新的解說(shuō)。”[3]由唐入宋以后,詞的創(chuàng)作主體逐漸轉(zhuǎn)變?yōu)槭看蠓颍~在題材、內(nèi)容、風(fēng)格等方面都產(chǎn)生巨大變化,除了詞體自身演進(jìn)過(guò)程以外,宋學(xué)勃興對(duì)詞創(chuàng)作導(dǎo)向的巨大影響不可忽視。
宋學(xué)以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為發(fā)端,流派眾多:王安石父子的“荊公新學(xué)”;蘇軾三父子的“蜀學(xué)”;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xué)”;張載、張戩兄弟的“關(guān)學(xué)”等。宋學(xué)雖流派眾多,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各異,但都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要突破傳統(tǒng)、經(jīng)世致用,將學(xué)術(shù)探索和社會(huì)實(shí)踐結(jié)合起來(lái),有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宋學(xué)作為一種新儒學(xué),其探究的一個(gè)主要命題,是人在天地自然之間、社會(huì)人倫關(guān)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視人‘與天地參’的自主自覺(jué)性。所謂‘內(nèi)圣外王’,所謂‘圣賢氣象’,就是要把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國(guó)平天下的帝王之學(xué)結(jié)合起來(lái),把道德自律和事功建業(yè)統(tǒng)一起來(lái)。”[4]宋學(xué)帶來(lái)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風(fēng)貌的沖擊和影響,促使宋詞格局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突破一己小我、風(fēng)花雪月、羈旅愁思藩籬,注重反映廣闊、深沉的社會(huì)內(nèi)容和思想。
宋學(xué)開(kāi)創(chuàng)者之一的范仲淹,率先將宋學(xué)經(jīng)世致用思想用于詞的創(chuàng)作,擴(kuò)大了詞的題材,“頗述邊鎮(zhèn)之勞苦,歐陽(yáng)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5]。他的名作《漁家傲》(塞下秋來(lái)風(fēng)景異)格局宏大、氣勢(shì)豪邁壯美,描繪邊塞粗獷風(fēng)光,展現(xiàn)守邊將士艱辛,表達(dá)憂患邊塞、壯志難酬的復(fù)雜情緒。夏承燾說(shuō):“北宋詞壇出現(xiàn)這樣感情深厚、氣概闊大的小令,是五代以來(lái)婉約柔靡的詞風(fēng)轉(zhuǎn)變的開(kāi)端,從詞史的角度看,范仲淹的《漁家傲》是蘇軾、辛棄疾詞派的先聲。”[6]宋學(xué)另外一位開(kāi)創(chuàng)者歐陽(yáng)修,則在宋學(xué)影響下擴(kuò)大了詞境,塑造了“深厚宛轉(zhuǎn)”的美學(xué)空間。他的《玉樓春》(尊前擬把)中“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guān)風(fēng)與月”,表達(dá)了一種“歷盡仕途滄桑以后的一種交雜著悲慨與解悟的難以具言的心境”[7]。宋學(xué)中期主要代表人物王安石,把詞內(nèi)容推向更為深廣闊大,以詞詠史懷古,從根基上拓展了詞的表現(xiàn)功能。如《桂枝香·金陵懷古》(登臨送目,正故國(guó)晚秋,天氣初肅)站在歷史角度抒發(fā)對(duì)王朝興替的感慨:“念往昔,繁華競(jìng)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xù)”,表達(dá)自己作為政治家渴望經(jīng)世致用的人生理想。王安石對(duì)詞所作嘗試對(duì)蘇軾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詞學(xué)上王安石與蘇軾之關(guān)系,一般是將王作為蘇的導(dǎo)夫前路者。”[8]
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蘇軾初試詞筆始于熙寧倅杭時(shí),從熙寧五年(1074)春作《浪淘沙·探春》,到熙寧七年(1076)秋離杭赴密所作的《減字木蘭花》,共計(jì)49首。總體觀之,這些詞都是應(yīng)歌體,“以‘謔浪游戲’的態(tài)度,應(yīng)歌填詞,以作一般的佐歡取樂(lè)之用。”[9]這與“吳越俗尚華靡”的杭州地域文化,擅長(zhǎng)婉約詞創(chuàng)作的詞壇名宿張先的影響,以及蘇軾初涉歌詞創(chuàng)作難逃舊習(xí),都有密切關(guān)系。但是可以想見(jiàn)的是作為一代文豪的蘇軾在熟練掌握詞創(chuàng)作技巧后,不可能滿足于這樣歌筵酒觴風(fēng)格的作品,離開(kāi)彼地、彼時(shí)的外部影響,求變是必然的事情。并且,蘇軾所代表的蜀學(xué)也是宋學(xué)重要分支,蜀學(xué)內(nèi)容比較龐雜,對(duì)《六經(jīng)》和先秦眾多著作都有研究,實(shí)現(xiàn)了儒釋道的廣泛融合,“老泉文初出,見(jiàn)者以為《荀子》……蘇氏出于縱橫之學(xué)而亦雜于禪……”[10]。朱熹輕視蜀學(xué)原因,就是認(rèn)為蜀學(xué)缺乏一個(gè)固定思想體系。但正是蜀學(xué)不承師和博采眾長(zhǎng)付諸實(shí)踐的做法,更有利于蘇軾發(fā)揮主體精神,改變?cè)~的創(chuàng)作導(dǎo)向,將詞作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范仲淹、歐陽(yáng)修、王安石等人對(duì)詞題材、格局、功能積極開(kāi)拓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離開(kāi)杭州的蘇軾將宋學(xué)中經(jīng)世致用思想運(yùn)用到詞的重構(gòu)當(dāng)中,對(duì)詞創(chuàng)作進(jìn)行探索、求變與創(chuàng)新。蘇軾密州任上作詞19首,其中15首為豪放詞,與其在杭時(shí)期詞作相比,一掃柔媚之態(tài),可以說(shuō)密州時(shí)期是蘇軾詞風(fēng)格巨變的開(kāi)始。“密州三曲”中,《江城子密州出獵》豪邁奔放,壯志凌云;《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婉約深情,被譽(yù)為千古悼亡第一詞;《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shí)有》曠達(dá)超脫、充滿哲理,可以作為佐證。《江城子·密州出獵》寫(xiě)作之后,蘇軾在寫(xiě)給朋友的信中說(shuō):“近卻頗作小詞,雖無(wú)柳七郎風(fēng)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shù)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頗壯觀也。寫(xiě)呈取笑。”[11]1560蘇軾明確表示自己詞創(chuàng)作方向要 “自是一家”,風(fēng)格上與宋詞原來(lái)的“柳七郎風(fēng)味”相區(qū)別。蘇軾已經(jīng)意識(shí)到,宋詞原本的“柳七郎風(fēng)味”不適合,也無(wú)法承載宋學(xué)“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wàn)世開(kāi)太平”宏大主旨,因此嘗試對(duì)詞體和詞風(fēng)做出變革——“自是一家”。《江城子·密州出獵》率先體現(xiàn)了這種改變,蘇軾把詞作為自己抒懷言志的工具,“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表達(dá)的正是“蘇軾借此表示希望朝廷委以邊任,能奔赴邊疆抗敵”的理想[12]。
總之,作為貫穿整個(gè)有宋一代的學(xué)術(shù)思潮——宋學(xué),其經(jīng)世致用觀念對(duì)于宋代文風(fēng)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并通過(guò)文人士大夫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改變流向作品。在范仲淹、歐陽(yáng)修、王安石等人嘗試基礎(chǔ)上,蘇軾最終完成了詞體改造,“新天下耳目”。劉熙載在《藝概》中說(shuō)“東坡詞頗似老杜詩(shī),以其無(wú)意不可入,無(wú)事不可言也”,《江城子·密州出獵》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尊夏攘夷”的華夏中心主義情結(jié)驅(qū)動(dòng)
“華夷之辨”觀念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重要內(nèi)容之一,是在中國(guó)古代文明漫長(zhǎng)發(fā)展過(guò)程中逐漸產(chǎn)生的,在西周至春秋時(shí)期已具備雛形。《禮記·王制》記載:“中國(guó)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fā)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fā)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3]先秦時(shí)代的華夷之辨不僅僅是方位上的含義,文明程度不同也是區(qū)分華夷的主要標(biāo)志,“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諸夏實(shí)在另有一個(gè)分別的標(biāo)準(zhǔn),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不是‘血統(tǒng)’而是‘文化 ’。”[14]“華夏”,“華”指文化高的人,“夏”指文化高的周禮地區(qū),“華夏”合起來(lái)就是指中國(guó),“中國(guó)”主要含義是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處于核心地位,是天下之中,“被發(fā)文身衣皮”是夷,被認(rèn)為不開(kāi)化的象征。這種觀點(diǎn)在先秦、兩漢和魏晉南北朝時(shí)候一直占有主導(dǎo)地位,盡管在唐代唐太宗提出了華夷一家、一體的理論:“……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dú)愛(ài)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15],但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長(zhǎng)久以來(lái)“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的傳統(tǒng)觀念。
北宋是在唐末五代、藩鎮(zhèn)割據(jù)的紛亂中建立起來(lái)的,為了避免武將專權(quán),宋建國(guó)后實(shí)行右文政策,對(duì)北宋士風(fēng)養(yǎng)成有巨大涵育作用。因此,北宋的知識(shí)精英起身為士大夫之時(shí),便有著以“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自覺(jué)精神”[16]。歷史上長(zhǎng)期華夏一統(tǒng)的文化熏染,使宋人有著強(qiáng)烈恢復(fù)故國(guó)榮光的愿望,而實(shí)際國(guó)情卻殘酷的打破了他們的幻想,不僅如此,“宋元之際,北方少數(shù)民族經(jīng)濟(jì)、文化有了長(zhǎng)足的進(jìn)步,完成了從部落到國(guó)家的轉(zhuǎn)變,實(shí)力大為增強(qiáng)。”[17]面臨嚴(yán)重的國(guó)家安全威脅,宋人首先在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上有著鮮明反應(yīng):北宋時(shí)期的華夷之辯有了較大改變,不再是主要強(qiáng)調(diào)中原地區(qū)與少數(shù)民族之間文化層面上的差別不同,宋代士大夫開(kāi)始嚴(yán)格區(qū)分“中國(guó)”與“四夷”,大力提倡“尊王攘夷”。宋代知識(shí)分子對(duì)國(guó)家社群的維護(hù),體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尊夏攘夷”的華夏中心主義情結(jié),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明侵?jǐn)_中原抱有強(qiáng)烈仇恨,“‘中國(guó)’終于失去了‘天下國(guó)家’海納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18]174在宋代,“中國(guó)”不再僅僅是一個(gè)關(guān)于文明的概念,而是一個(gè)標(biāo)志明確國(guó)界的政治地理概念。清華大學(xué)葛兆光就認(rèn)為宋代是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gè)遠(yuǎn)源。“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他具有強(qiáng)烈民族意識(shí)的《中國(guó)論》中,不僅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與“四夷”的文明差異,而且在方位上區(qū)分華夷:“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guó),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嚴(yán)格要求“四夷處四夷,中國(guó)處中國(guó),各不相亂”[19]。歐陽(yáng)修也在《正統(tǒng)論》里極力論證大宋王朝作為華夏正統(tǒng)的歷史定位。蘇轍在《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中說(shuō):“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yǔ)綢繆禮亦虔”,顯示強(qiáng)烈的“尊王攘夷”思想。隨著宋、遼、金三者關(guān)系的不斷變化發(fā)展,宋朝士大夫“尊王攘夷”思想也隨之進(jìn)一步發(fā)展,朱熹說(shuō):“誅亂臣,討賊子,內(nèi)中國(guó),外夷狄,貴王賤伯”[20],黃仲炎甚至把中原以外的少數(shù)民族比作禽獸:“夷狄蠻戎近乎禽獸,奈何使與中國(guó)齊也。”蘇軾本人也有很強(qiáng)的“尊王攘夷”思想,在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所作的《教戰(zhàn)守策》中說(shuō):“今國(guó)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wàn)計(jì)。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wú)厭,此其勢(shì)必至于戰(zhàn)。”考察史料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gè)時(shí)期宋與遼、西夏的關(guān)系較為平和,沒(méi)有大的軍事沖突,蘇軾卻仍然認(rèn)為“其勢(shì)必至于戰(zhàn)”,這種觀點(diǎn)一方面是提醒北宋統(tǒng)治者不能耽于承平無(wú)事,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其強(qiáng)烈的尊王攘夷情緒。
尤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蘇軾知密期間正是宋遼之間重大政治事件“熙寧劃界”的存續(xù)期。宋遼熙寧年間的河?xùn)|邊界談判,是宋遼關(guān)系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頁(yè)。從熙寧七年( 1074 年) 夏四月:遼樞密副使蕭素議疆界于代州境上[21]6177,到(熙寧)十年六月:“(韓)縝以分畫(huà)之勞,賜金帶。十二月癸巳,上地圖”結(jié)束[21]6936。 “熙寧劃界”前后漫延長(zhǎng)達(dá)四年之久,最終以宋“棄地七百余里”[22]153,一說(shuō)“棄地五百余里”[22]156的屈辱結(jié)束。“熙寧劃界”引發(fā)兩國(guó)政治勢(shì)力的博弈曠日持久,遼國(guó)使者蕭禧故意滯留宋都開(kāi)封,時(shí)間上超過(guò)了“使者留京不得過(guò)十日”之規(guī)定,顯示出不達(dá)目的決不罷休的強(qiáng)硬態(tài)度。面對(duì)遼人軍事與外交上的施壓,宋神宗開(kāi)天章閣,組織宰執(zhí)官討論劃界事宜,在整個(gè)熙寧劃界過(guò)程中一直遙控指揮。這次中原政權(quán)與游牧民族的邊界厘清,再度引發(fā)宋人強(qiáng)烈的“尊王攘夷”觀念。而“熙寧劃界”的膠著時(shí)期,蘇軾正任職密州,密州屬于京東路,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熙寧劃界中雙方爭(zhēng)論的地理矛盾中心。雖然知密時(shí)期是蘇軾政治上低潮時(shí)期,但比照后來(lái)的黃州、惠州、儋州時(shí)期,蘇軾知密是其初任地方最高行政長(zhǎng)官,內(nèi)心充滿奮發(fā)有為的情感。這一點(diǎn),我們不僅可以從他密州任上的種種積極作為中可以看出,其實(shí)最早在他赴任密州途中創(chuàng)作的《沁園春·孤館燈青》“有筆頭千字,胸中萬(wàn)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中就已經(jīng)展露,全詞英氣勃勃,充滿對(duì)朝廷政治的厚望[1]340。在這種思想主導(dǎo)下,密州期間蘇軾創(chuàng)作了不少洋溢尊王攘夷、保家衛(wèi)國(guó)情感的作品。《和梅戶曹會(huì)獵鐵溝》“山西從古說(shuō)三明,誰(shuí)信儒冠也捍城”[1]151,蘇軾將自己的“近梟數(shù)盜”看作是“捍城”,保衛(wèi)國(guó)家。《祭常山回小獵》中“圣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1]150更是強(qiáng)烈表現(xiàn)了蘇軾安邊守疆的豪邁情懷。
可以說(shuō),宋遼久懸不結(jié)、多種政治力量卷入的熙寧劃界事件,進(jìn)一步激化了包括蘇軾在內(nèi)的宋代士大夫“尊王攘夷”的華夏中心主義情結(jié),這種情感成為他創(chuàng)作《江城子·密州出獵》主要?jiǎng)右蛑弧LK軾表達(dá)了自己雖為文臣但也要披甲射虎的愿望:“親射虎,看孫郎”,而且只要朝廷任用自己,就要“會(huì)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就是指西北的少數(shù)民族契丹和西夏,其“尊王攘夷”的華夏中心主義思想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三、密州地區(qū)崇兵尚武的地域文化熏陶
密州地區(qū)有著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兵文化。密州地區(qū)最早是驍勇善戰(zhàn)的東夷族群居住地,這個(gè)部族首先發(fā)明使用金屬工具和兵器,有很強(qiáng)軍事力量。被后世視作“兵主”“戰(zhàn)神”祭祀的蚩尤,是東夷繼少昊之后的族邦首領(lǐng)。歷史上關(guān)于蚩尤的傳說(shuō)多和制作兵械以及戰(zhàn)爭(zhēng)有關(guān),“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23];“黃帝伐蚩尤,未克。西王母遣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24]東夷人以崇兵尚武、勇猛善戰(zhàn)而著稱,三代時(shí)期夏王朝就是因?yàn)樯倘撕鸵娜私Y(jié)盟而失國(guó)[25],也有人認(rèn)為商人就是夷人的一支[26],周人和東夷人的戰(zhàn)爭(zhēng)更是連綿不斷。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密州受齊影響,齊是中國(guó)古代“三大兵學(xué)文化”發(fā)源地之一,齊的開(kāi)創(chuàng)者姜尚、管仲、齊桓公是著名軍事家,其他如孫武、吳起、孫臏、田單、蒙驁、蒙恬等人也是名聲赫赫的軍事家。姜尚的《六韜》一向被認(rèn)為是古代兵學(xué)的開(kāi)山和奠基之作,《孫子兵法》《司馬法》《吳子》也是公認(rèn)的兵學(xué)巨著。在密州地區(qū)的民間信仰中,可以看到明顯的兵文化崇拜,除武成王廟供奉齊國(guó)開(kāi)創(chuàng)者姜尚,還有常將軍廟供奉東晉將領(lǐng)常玄通。
從先秦至北宋,密州一直是兵家必爭(zhēng)之地。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與密州地理位置相關(guān)的著名戰(zhàn)役有長(zhǎng)勺之戰(zhàn)、城濮之戰(zhàn)、鞌之戰(zhàn)、馬陵之戰(zhàn)、樂(lè)毅破齊等。秦漢時(shí)期,楚漢之間的轉(zhuǎn)折性戰(zhàn)役——濰水之戰(zhàn),主要戰(zhàn)區(qū)就在密州。三國(guó)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密州地區(qū)權(quán)屬變動(dòng)頻繁,先后屬于后趙、前燕、前秦、后燕、南燕、東晉、劉宋、北魏、東魏、北齊、北周,戰(zhàn)事不斷。唐安史之亂到五代時(shí)期,后梁、唐、晉、漢、周都統(tǒng)治過(guò)這個(gè)區(qū)域,仍然是戰(zhàn)爭(zhēng)高發(fā)區(qū)①。北宋王朝建立以后,密州屬京東路,“至道三年,以應(yīng)天、兗、徐、曹、青、鄆、密、齊、濟(jì)、沂、登、萊、單、濮、濰、淄、淮陽(yáng)軍、廣濟(jì)軍、清平軍、宜化軍為京東路。”[27]2107宋王朝建都開(kāi)封,中國(guó)封建王朝的政治和軍事中心由關(guān)中轉(zhuǎn)移到中原,因此京東地區(qū)成為北宋王朝北部防御前沿地帶,成為拱衛(wèi)政治中心開(kāi)封的“東大門”。與以前封建王朝相比,宋王朝地緣政治環(huán)境十分惡劣,西北部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比以往更為強(qiáng)大,“‘契丹’勁兵驍將長(zhǎng)于中國(guó),中國(guó)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zhǎng),中國(guó)不及。”[21]3641由于石敬瑭向契丹割讓幽云十六州,中原政權(quán)的長(zhǎng)城防御體系被打破,北部邊防門戶大開(kāi),北部千里都需要防范敵軍。因此,京東路的軍事重要性凸顯,“山東自上世以來(lái)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系社稷安危。”[1]269為了加強(qiáng)京城的藩衛(wèi),北宋把密州所在的京東地區(qū)劃分為防御州,并不斷提升京東路的軍事地位,加強(qiáng)京東地區(qū)的軍事力量,“(政和)五年有旨升登、菜、濰、密四州為次邊。”[28]宋人所說(shuō)的極邊,是指宋統(tǒng)治疆域最外圍的區(qū)域即邊防一線;次邊,是指俯逼邊界[29]。長(zhǎng)期的戰(zhàn)爭(zhēng)環(huán)境和北宋時(shí)期防御州的戰(zhàn)略位置,使密州地區(qū)的兵文化一直長(zhǎng)盛不衰。
宋王朝定都開(kāi)封后,出于首都戰(zhàn)略,宋王朝統(tǒng)治者在“天意”之下最終聽(tīng)任黃河改道北流,不再流經(jīng)京東路故道:濮州-鄆州-齊州-淄州-棣州-濱州[30]。黃河北流的積極后果是長(zhǎng)久以來(lái)的京東河患得以基本解除,消極后果是大量河北流民涌入京東地區(qū),“河北水災(zāi),其流民盡來(lái)京東界內(nèi)。”[31]大規(guī)模流民涌入使京東地區(qū)的社會(huì)秩序受到嚴(yán)重沖擊,京東地區(qū)在北宋中后期成為著名“盜區(qū)”,有史料可查的北宋時(shí)期京東地區(qū)農(nóng)民起義就達(dá)43次之多,“齊魯盜賊,為天下劇。”[27]1058蘇軾本人也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自來(lái)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11]1058出于防御“盜賊”目的,密州地區(qū)民俗中豪爽勁悍的風(fēng)氣一直延續(xù)、保留和發(fā)展下來(lái),“民皆長(zhǎng)大,膽力絕人,喜為剿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yáng)跋扈之心。”[11]
密州地域文化對(duì)蘇軾影響很大,梳理蘇軾知密期間作品,我們發(fā)現(xiàn)相當(dāng)數(shù)量與狩獵有關(guān)作品,與蘇軾其他宦游地的作品相區(qū)別。蘇軾借狩獵活動(dòng)反映保家衛(wèi)國(guó)、抵御外辱的感情,詩(shī)歌如《和梅戶曹會(huì)獵鐵溝》與《祭常山回小獵》等,詞首推《江城子密州出獵》。《江城子密州出獵》中明確展現(xiàn)了密州地區(qū)“武悍”的民風(fēng):“傾城隨太守”“千騎卷平岡”,在這樣的陽(yáng)剛氣概鼓舞下,蘇軾“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渴望投身疆場(chǎng)、效力邊防,“持節(jié)云中,何日遣馮唐?”[1]345。可以毫不夸張地說(shuō),《江城子密州出獵》的出現(xiàn)與密州地區(qū)崇兵尚武的地域文化熏陶和渲染密不可分。
“作家和作品都是文化的載體,研究文學(xué)從根本意義上來(lái)說(shuō)就是研究文化。”[32]宋王朝特殊的立國(guó)環(huán)境,促使儒學(xué)復(fù)興并成長(zhǎng)為蓬勃的宋學(xué),復(fù)歸醇儒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進(jìn)一步深化了宋代士大夫“尊王攘夷”的華夏中心主義情結(jié),疊加密州陽(yáng)剛雄壯的地域文化,三者共同作用促使天才蘇軾寫(xiě)出《江城子·密州出獵》這樣不朽的作品。
注釋:
①后曉榮.秦代政區(qū)地理[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9;周振鶴.西漢政區(qū)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李曉杰.東漢政區(qū)地理[M].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王蕊.魏晉十六國(guó)青徐兗地域政局研究[M].北京:齊魯書(shū)社,2008;周振鶴.中國(guó)行政區(qū)劃通史(隋代卷)[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