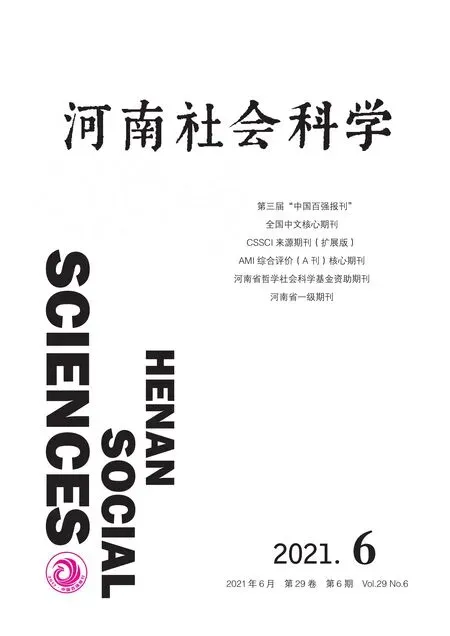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的自我救贖:真相的再歸與主流媒體話語權的重塑
張愛軍,王首航
(西北政法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2)
在技術賦權下,信息內容的傳播主體逐漸多元化,主流媒體傳播權和話語權被一定程度分流與消解,激烈的信息市場競爭環境和一些媒體把關意識的缺失使得虛假新聞、反轉新聞接連出現。“后真相”的本質含義在于人們的情緒性勝于事實的真實性,人們傾向于忽略事實真實性,根據自身的“情緒需求”來對信息內容進行判斷和處理,在魚龍混雜的信息環境中選擇符合自身認知的信息內容進行接觸與反饋,真相變得不再那么重要。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下新聞的真實性被消磨,新聞業也陷入了一種“信任危機”。主流媒體作為新聞業中的中流砥柱,是社會系統和政治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媒體機構。因此,主流媒體更要肩負起更多的公共責任,在發生重大事件或熱點事件時通過打造高質量新聞來樹立權威話語權,重塑媒體公信力,增益傳播環境,讓真相更好地“歸位”。
一、后真相時代:真相讓位于情緒
2016年,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等充滿爭議性的政治事件使得后真相一詞走紅世界。后真相一詞最早出現在1992年美國《國家》雜志一篇文章里[1],由拉爾夫·凱斯2004年在其著作《后真相時代:當代生活中的不誠實與欺騙》中正式提出[2]。后真相被賦予一種“情緒影響力超過事實”的含義,但當時后真相一詞并未走進公眾視野,在2016年牛津詞典官方將其推選成為年度詞語“Post-truth”(后真相)之后才正式走向公眾[3]。后真相時代本質是情感與信念勝于真相,使得真相變得不再重要[4]。后真相時代是一個以情感與信念為主導的時代,真相變成了情感信念的附庸,甚至可有可無。“情緒影響力超過事實”的時代,情感信念凌駕于事實真實性之上。英國哲學家羅素曾指出:“真相是由信仰和事實一致的一些形式組成的。”[5]在此層面上,后真相的一個顯著特點即事實弱化于信仰,后真相本質上反映了情感與信仰勝于作為“根基”的事實。
基于情感和信念訴求的個體是否將事實納為已有認知有著心理學基礎。“理性推理”和“方向性推理”是個體信息處理的兩種方式,社會心理學者珍妮弗·勒納和菲利普·泰特勞克用“探索性思考”和“確認性思考”來概括處理信息的兩種策略,前者是指在沒有形成偏好時個體對信息持有探索的心態來進行信息的處理,后者則是偏好一種觀念,在有較為明確的方向指引著個體時,個體維護某種觀念為目標對問題的結果已經有了答案,處理信息的過程僅是為其尋找支撐,即推理過程中有很明確的方向性[6]。從心理動機角度來講,在后真相時代,人們將情感和信念放在首位,在網絡平臺上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觀點。情感與信念成為首要維護目標,在這種方向性認知的指引下,新聞事實的真實性逐漸被虛化。事實的真實性等目標不再是個體的首要動機,取而代之的是個體的情感與信念,成為一種真相弱化情緒的推理過程。換句話說,后真相時代人們的“情緒需求”勝于真相本身的重要性,人們會根據自身的情緒需求來進行選擇性的信息接收與互動,一些能夠符合人們的情緒需求的信息內容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傳播。正如尼采所言的“沒有事實,只有詮釋”,從基于動機性推理的這一心理學角度來講:“沒有事實,有的僅僅是經過大腦有選擇性、有偏向性、有情感性過濾的解釋。”
二、后真相視域下新聞業的困境
最初后真相被視為政治概念,在此之后,后真相漸漸超越政治領域,并由政治領域擴散到社會其他領域。后真相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對新聞業產生影響。在技術賦權下,海量的信息涌入網絡平臺,人們暢游在魚龍混雜的信息環境中,不僅可以通過傳統主流媒體來獲取和傳播信息,還可以借助社交媒體、自媒體等新興媒體平臺來獲取信息,反觀現實,人們更多地青睞后者來滿足自身的信息需求。
(一)主流媒體話語權被一定程度地消解
新聞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公器,起到了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新聞媒體擁有信息內容的生產權、傳播權、把關權以及話語權等,能夠通過對事實的篩選建構一種社會圖景,這種社會圖景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的認知思維與價值選擇。因此,在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之外,媒體還需要承擔相應的公共責任,促進社會的良序發展。
在“前真相時代”,信息內容的生產傳播操作流程被專業的媒體機構所壟斷,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媒體機構的這些權力被逐漸“分流”,一些新興媒體平臺也擁有了信息內容的生產傳播權。在信息泛濫的網絡時代,公眾的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相比過去傳統媒體時代,公眾的注意力也被極大程度地分散,主流媒體的話語權被一定程度地消解,這種消解又在后真相時代中被強化。后真相時代,情緒勝于真相,公眾更愿意去“宣泄”某種情緒,繼而根據這種“情緒需求”來選擇和處理信息。由于假新聞能夠激發恐懼、失望等情緒,它比真新聞更有吸引力[7]。在后真相時代,一些真實性的信息反倒沒有虛假信息的轉發量或互動量多。此外,新興媒體相對于主流媒體擁有更為自由的傳播環境,并且在對新聞事實的把關層面也相對沒有主流媒體嚴格,一些自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的注意、搶占公眾注意力資源,在發掘熱點事件時,這些媒體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吸引眼球和流量,如何搶到獨家新聞,甚至為了迎合部分受眾的“情緒需求”去揣摩和臆想所謂的真相,不惜采用刺激眼球的標題和戲劇化的內容來吸引受眾注意力。
在社會效益首位的前提下,主流價值觀念與專業主流媒體機構一脈相承。當一些具有偏向性的信息內容影響著公眾的認知判斷和態度行為時,這種傳播環境下的主流價值觀念容易被邊緣化。因此,主流媒體更應通過對新聞報道的高質量書寫在真相缺失的時代中樹立權威話語權,增益正向的傳播環境。
(二)新聞生產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信任危機”
隨著后真相時代的到來,真實性讓位于情感性,新聞真實性不斷在反轉新聞、虛假新聞中被解構,真相變得飄忽不定。新聞反轉是后真相時代的一個特點,它體現了真相的不確定性、事實的模糊性以及沖突的戲劇性[8]。似乎每一條新聞都能夠成為“潛在反轉”的溫床。2017年,在陜西榆林醫院孕婦墜亡事件中,信息最先呈現的是死者家屬拒絕孕婦和醫院的剖宮產要求從而導致孕婦難以忍受疼痛選擇墜樓,新聞一出使得輿論嘩然,直至當地警方和衛計委進行一系列調查,糾正了新聞事實。2018年,一輛重慶公交意外墜江,新聞一經媒體發酵后矛頭便指向了對向正常行駛的女轎車司機,直至行車記錄儀還原了事發畫面,事實出現了反轉。一些媒體為了在信息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不經確定事實的情況下就將其發出,新聞就會面臨真相“飄忽不定”的情況,甚至“逆向而行”。在這種傳播環境下,新聞業逐漸陷入一種“信任危機”,新聞生產者與新聞接收者之間的信任關系變得脆弱。
益普索(Ipsos)發布的《2018年全球假新聞報告》指出:“人們對媒體的信任正在下降,大部分人表示他們經常看到假新聞,而且人們認為媒體上的假新聞正在增長。”[9]一些新興媒體平臺不經嚴格把關將信息傳播造成虛假新聞的泛濫,容易使人們對新聞的真實性產生質疑,這種情況下也會使新聞業和主流媒體陷入“塔西佗陷阱”。當各種媒體之間相互競爭爭搶信息內容的獨發權和首發權時,一些媒體為爭搶時效性對一些信息把關不嚴會對社會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同時也顯現了一些媒體職業素養的缺失。盡管反轉新聞、戲劇新聞能在短期內提升信息內容的點擊率和瀏覽量,但這些失真現象是以消耗新聞業長期塑造的公信力為代價所換來的,以犧牲新聞業公信力和社會責任感為代價來博取公眾眼球,違背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這種新聞不實、輿情反轉亂象與媒體對社會公眾負責的初衷相悖。
(三)新聞的真實性與嚴肅性面臨挑戰
近年,新興媒體憑借其固有的優勢成為社會多元群體發表意見的平臺。網絡平臺的低門檻準入以及傳播內容碎片化,使得信息質量參差不齊,虛假新聞、反轉新聞亂象接連不斷。新聞儼然已經成為信息市場中的“快餐消費”,時刻滾動彈出的新聞使受眾應接不暇。在激烈的信息市場競爭中,部分媒體爭先搶奪公眾注意力資源,為了吸睛甚至制造爆點標題或者滿足受眾的某種情緒需求的內容,在后真相時代,情緒需求被放大,在各種各樣的信息中受眾往往傾向于選擇符合自身認知框架或激發其“情感痛點”的信息,一些虛假新聞或者戲劇新聞又恰好滿足受眾這些情緒需求,在情感裹挾的信息洪流中,新聞更迭反轉現象的泛濫使新聞與真相、事實與真實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后真相時代,新聞質量和新聞數量逐漸成反比。信息傳播環境并沒有因為新聞數量的增多而正向發展,相反,增多的是些“雞肋”信息。在信息的洪流中,人們更愿意接受符合自身認知框架的“事實”,自動屏蔽一些框架外的事實。一旦這些事實“以受眾為中心”而不是“以事實為中心”時[10],新聞的嚴肅性就會被一定程度地消解。這里新聞的“嚴肅性”指的是相對于網絡環境中新聞的“娛樂性”而言,當一些媒體平臺為了實現市場效益最大化,開始迎合受眾口味,滿屏充斥著奪目又“雞肋”的新聞,無疑會導致新聞業整體內容質量的下滑。
真實性是新聞業永葆生命力的關鍵,嚴肅性是為了更好地確保新聞的公共效益。反觀現實,后真相時代,媒介技術的革新所帶來的海量信息一方面滿足了受眾需求,另一方面也加劇了新聞亂象的風險。過去傳統媒體時代的真實性與嚴肅性在如今的信息環境中面臨著挑戰。
三、真相為何“漸行漸遠”
在技術賦權下,傳統媒體不再壟斷信息生產傳播,在權力被逐漸“分流”的媒介環境中,隨著傳播主體多元化、信息市場化、競爭激烈化以及“把關意識”的缺失,事實與真實之間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新聞的數量和新聞的質量漸成反比。一些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等新興媒體由于傳播快捷的天然優勢以及相對自由的傳播環境,在面對熱點事件時為了搶占公眾注意力,往往將一些比較粗糙、不經嚴格把關的信息內容呈現在公眾眼前,導致一些虛假新聞、反轉新聞等“翻車”現象頻發,這些新興媒體在博取公眾眼球和流量的同時無疑消耗著新聞業長期樹立的公信力,也使得公眾對新聞真實性產生質疑。在真相變得沒那么重要的后真相時代,一些新興媒體為了迎合公眾情緒而不顧新聞事實的真實性,當新聞變得“隨意”而非嚴肅,這無疑違背了新聞核心原則——真實性原則。
(一)從職業圈內到多元圈外:傳播主體泛化
正如鮑曼所言:“流動的力量已經從制度轉移到社會、從政治轉移到生活、從社會共處的宏觀層次轉移到微觀層次,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11]技術不斷發展的同時也構建著一種新的現實圖景,在人人擁有麥克風的時代,傳播權也一定程度地被分散。信息內容生產從PGC模式轉向UGC模式,信息內容生產制作的低門檻使得一些社交媒體平臺、自媒體以及草根民眾等也能參與信息內容的生產與傳播。
從前真相時代到后真相時代,信息生產傳播主體發生了變化。在前真相時代,新聞報道從內容選擇到生產制作等整個過程均由專業化和組織化的媒體機構來進行篩選把關;而在后真相時代,技術賦權下的媒介環境中一些基于新興媒體平臺的社會多元群體也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新興媒體的發展對新聞行業邊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邊界的存在就意味著邊界的這端與另一端有所不同,而新聞行業邊界兩端的區別在于職業圈內人和非職業圈外人進行的信息內容生產傳播,傳統新聞行業人員有一定的準入門檻、須有記者證以及采訪權的認定等,在發重大消息時,必須經過有新聞資質媒體的把關才可發布[12]。過去的傳統媒體與如今的新興媒體在信息生產與傳播過程中的不同在于,傳統媒體時代的專業媒體機構擁有專業的采編隊伍和成熟完善的職業運作體系。除此之外,過去“職業圈內”的人員需要遵守嚴格的規章制度以及職業倫理規范,而一些社交媒體、自媒體等新興媒體平臺擁有相對自由的傳播環境,一些依附于新興媒體之上的“多元圈外”人員在信息生產和傳播的過程中為了獲取流量,將一些信息在不經嚴格把關的情況下進行傳播,不利于新聞傳播環境的良序發展。
美國學者哈林在一次專訪中說道:“一些社交媒體、自媒體等新興媒體所產生的‘新聞’和傳統主流媒體所產生的新聞并非一碼事,新興媒體在信息市場環境下為了維持自身的運轉,也會雇一批人員來進行新聞的制作等,這些所發布的新聞中有的也是來自傳統媒體。在整體的新聞業態中,一些原有的新聞模式仍會存在,但是媒介環境中,新聞的標準和模式也多少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種現象被英國的學者安德魯·查德威克稱為是‘混合新聞’。”[13]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在技術賦權的媒介環境下“新聞”的質量參差不齊。低門檻的準入使得“多元圈外”人士能夠在一些新興媒體平臺上發表自己的所見所聞,但所發表的信息不能精準地反映事實的全貌或者事實本身,因而致使網絡空間中一些虛假新聞現象頻發,事實與真實之間的邊界逐漸消融。這些新興媒體平臺發布的信息內容往往也會被公眾認為是“新聞”的一種,因此,新聞質量的參差不齊一定程度上消解著新聞業的公信力。隨著新興媒體的發展,虛假新聞、反轉新聞現象的泛濫對新聞業中新聞的真實性與嚴肅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弱化,而這種消解在后真相時代進一步得到了強化。后真相時代,真相變得沒那么重要,一些新興媒體平臺的人員由于沒有嚴格的行業機構規范和責任意識的約束,在這種相對自由的環境中,其發布的信息內容很容易出現“翻車”現象。此外,信息內容的繁雜也意味著需要把關的內容越來越多,后真相時代中反轉新聞和戲劇新聞的泛濫逐漸消磨著新聞業與主流媒體長期塑造的公信力,新聞本該堅守的真實性面臨著挑戰。
(二)從追求真相到制造事實:商業利益邏輯驅使
互聯網在興起之初作為一種媒介技術帶給人們對于未來的想象。在看到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積極影響的同時,人們也需要看到其負面影響。人們期待技術能夠更好地幫助自己尋求真相時,現實似乎與理想背道而馳。現實與真相漸行漸遠的背后存在著商業利益動機的驅使。商業利益動機在新聞傳播領域主要體現在一些新興媒體平臺通過制造并傳播一些博人眼球、能夠引起輿論“爆點”的話題來達到其商業目的,獲得更多點擊率實現盈利。
試驗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發生率14.58%,對照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發生率為34.62%,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一些媒體的商業利益動機和受眾的情緒需求密不可分。麻省理工學院關于推特平臺假新聞的研究顯示,平臺用戶轉發虛假信息內容的可能性比轉發真實性信息高出70%。這個研究表明,虛假新聞比起真實性新聞在受眾處理信息內容過程中往往更能夠激發受眾的反饋[14]。尤其在后真相時代,真相讓位于情緒。當一些虛假新聞恰好又能夠滿足受眾的某種“情緒需求”時,虛假新聞往往比真實新聞有著更多的“曝光率”。公眾注意力等能夠為平臺創造豐厚利益,在注意力經濟時代,相比爆炸式增長的信息資源,公眾注意力資源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因此,博取公眾眼球、搶占公眾注意力、獲取信息內容的瀏覽量或點擊率等成為一些媒體平臺進行信息傳播的邏輯起點。因此,為了吸引受眾的眼球,在各大媒體平臺的商業模式中,一些虛假新聞或者能夠引起“爆點”的信息內容更能夠實現平臺想要的市場效益。后真相時代情緒勝于事實真實性,當受眾的“情緒痛點”成為一種“方向”,一些媒體為了點擊率或瀏覽量,便放低姿態迎合受眾的口味,甚至將真相拋之腦后制造一些能夠引起爆點的事實來迎合受眾需求,從而在激烈的信息市場競爭中獲得商業利益,這些媒體憑借超高瀏覽量的假新聞或者是“爆點新聞”快速實現變現,在此過程中迅速致富。
在這一過程中,比“快速致富”更值得注意的是受眾并不關注對假新聞的后續糾正,時刻滾動彈出的新聞讓受眾應接不暇,新聞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市場中的“快餐消費”,在各種各樣的信息中,受眾往往傾向于選擇符合自身認知框架和能激發其“情感痛點”的信息,反而不在乎所謂的“真相”是什么。在此過程中“興趣是第一位,真實是第二位”,個體的記憶似乎只停留在曾經的那個“爆點”。
(三)從客觀到“可觀”:新聞把關標準變化
“把關”是確保新聞真實性的關鍵環節。新聞生產傳播的過程離不開“把關”。“把關”起著決定繼續或者中止信息傳遞的作用。當把關環節出現問題,新聞可能隨時面臨著“翻車”的危險。從“前真相時代”到“后真相時代”,從傳統媒體到新興媒體,信息內容的把關的標準也發生了轉變。“把關人”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之一庫爾特·盧因在《群體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盧因認為,在群體傳播過程中,在信息的流動的渠道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者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才能進入渠道。從新聞把關的角度來講,帕梅爾·休梅克將新聞把關分為個人、媒介日常工作、媒體組織、媒體之外社會團體、社會系統等五個層次的把關,是新聞報道生產中客觀存在的[15]。
把關的過程必然離不開價值選擇。在新聞內容的把關過程中,價值選擇主要體現在對新聞內容選擇的價值標準。影響把關人的價值選擇標準往往是多種因素復雜交織的。“前真相時代”傳統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生產制作過程中對事實進行有價值的篩選,其中真實性原則是基本原則;“后真相時代”情緒勝于真相,真相變得不再那么重要,相反符合“情緒需求”的一些事實的點擊率和轉發量得到爆炸式增長。在“后真相時代”,新聞把關標準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一些新興媒體為了在信息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為了獲取一定的影響力和公眾注意力,傾向于生產能夠符合受眾喜好的內容,加之在商業邏輯驅使下,一些媒體平臺在信息內容傳播過程中,受眾的偏好興趣以及內容的“接收度”成為一種重要的價值標準。一些媒體將滿足受眾情緒需求的標準和新聞事實雜糅在一起。因此,后真相時代新聞內容的“去真相化”使得新聞真實性這一基本的把關標準被弱化。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基于數據分析的算法技術助推了這種情緒需求的擴大,把關標準更傾向于用戶的需求。在技術發展下的后真相時代,除了人的把關,還有一些技術的把關,比如算法協助人工編輯進行信息內容的把關。在技術發展的今天,算法輔助人工把關過程中,基于算法和數據分析來進行信息內容的推送并不能完全保證其準確性,信息內容傳播基于個性化精準化的推送路徑變得更加依賴用戶的偏好興趣。一些新聞事實被“添油加醋”,一些“情緒觀點”被逐漸放大,真實性的把關標準變成一種“次要選擇”。
把關意識在后真相時代弱化。前真相時代,職業圈內人更易受到規章制度與倫理規范的約束,在職業中恪守新聞真實性。而在后真相時代,多元化的傳播主體加入了信息內容的生產傳播,這些“多元圈外”的人員不像以往傳統主流媒體人員那樣有著更為嚴格的新聞職業規章與責任意識約束,因此,在這種約束較為寬松的環境下,為了獲取稀缺的注意力資源,對于新聞的把關與核實往往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導致一種“把關意識”的缺失。為了獲得受眾的情感共鳴,往往將信息內容的真實性拋之腦后。這種把關標準也使得受眾大批向新興媒體靠攏。一些新興媒體平臺“把關意識”的缺失除了信息生產主體泛化的因素,還存在著內容價值標準的碰撞。隨著社會多元文化的發展,受眾需求價值以及新聞專業價值在信息生產中產生了一定的矛盾,為了適應信息市場的發展,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和現狀一定程度改變了內容生產者的習慣,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息內容取舍的價值標準。商業邏輯驅使下為了迎合受眾獲取點擊率會造成一些媒體“把關意識”的缺失,這些因素一定程度影響著信息內容生產過程中“把關人”對于內容價值標準的抉擇。一些媒體在“專業性”與“商業性”之間徘徊,一些新興媒體甚至無法維系二者之間的平衡,有的媒體為了在市場化進程中更好地發展改變了以往的把關標準,在專業性與商業性之間選擇了后者。“商業性”的新聞注定了新聞內容的核心原則弱化于受眾的偏好需求,新聞把關的標準自然而然也會向“商業性”把關標準傾斜,當一些新聞充斥著“商業色彩”,就會面臨一個被“添油加醋”的信息環境,在滿足人們信息需求的同時,又引起人們對于新聞真實性的質疑,假新聞使受眾不敢相信新聞,也會使新聞業與主流媒體陷入“塔西佗陷阱”。
四、真相的再歸:主流媒體話語權的建構路徑
比爾·科瓦奇和湯姆·羅森斯蒂爾曾指出:“隨著社會秩序的重組,大眾傳播技術的每一次變革都會引起兩股知識流或兩種認識世界的方法——基于觀察和經驗的知識與基于信仰和信念的知識之間重新產生分歧,簡言之就是事實與信仰之間的矛盾。”[16]在后真相時代,事實與信仰便產生了矛盾。在客觀真相次于主觀報道的時代,并不意味著后真相時代“無真相”。
(一)重塑媒體公信力:主流媒體報道向“深”發展
輿情反轉是后真相時代的一個特點,新聞事實再三更迭,反轉現象對新聞的事實真實性造成影響的同時,也使得新聞業面臨著信任危機,新聞生產者與新聞接收者之間的信任關系變得薄弱。在技術賦權下,傳播權被一定程度地分散,傳統媒體不再是信息壟斷的媒體機構,新興媒體也擁有了一定的信息內容的生產傳播權,新興媒體擁有傳播快捷的天然優勢以及其相對自由的傳播環境,但由于新興媒體在面對熱點事件時沒有傳統媒體機構的采編流程完備,并且一些媒體在發布信息內容時往往為了追求時效性,搶占公眾的第一注意力,將沒有進行嚴格審核把關的事實呈現在公眾面前。一些新興媒體在信息內容生產的過程中的過“快”就注定了在傳播的過程中不能完全保證真實性,新聞隨時可能面臨著“翻車”“更迭”等現象,導致新聞失真現象頻發。這樣的媒體環境也會影響著受眾的輿論感知能力,受眾對新聞的態度也在發生著變化,甚至以一種“娛樂”“戲謔”的話語方式來理解并重建自身對于事實的認知。
傳統主流媒體擁有的獨特的天然優勢不僅在于其擁有采訪權,更在于傳統媒體擁有專業的采編隊伍和成熟完善的職業運作體系。因此,在后真相時代“真相歸位”這場挑戰中,主流媒體相比社交媒體以及自媒體等新興媒體平臺擁有著天然的內容優勢——深度報道,這是一種系統地反映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深入挖掘和闡明事件以揭示其實質以及意義等的報道方式。在新聞深度報道的生產過程中,“降速”新聞生產過程以便更穩妥保證新聞的真實性。BBC新聞編輯室曾宣布要用慢新聞來預防假新聞。“我們需要用慢新聞,需要數據、調查、分析和專業知識構成的更深入的新聞,以進一步了解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17]利用新聞生產的慢過程,報道能夠有充分完備地向“深”發展的機會,新聞隊伍在搜集全面的信息資源以及更詳盡的調查分析過程中使新聞報道的“根”向下扎得更牢靠,避免新聞事實的“翻車”。
新聞失真現象的頻現使受眾對事件真實性充滿質疑,在這樣的信息環境中,深度報道成為稀缺品,因此,將報道深耕才是主流媒體的長久出路[18]。社會問題的呈現往往是千姿百態的,解決的過程是極為復雜的。在面對熱點事件時,主流媒體和新興媒體由于傳播特性不同,二者可以優勢互補。這就需要權威主流媒體在內容問題上有一種專業化的分析和解讀,更加注重深度報道。權威主流媒體在挖掘事實方面占有優勢,因此可以加大深度報道的力度和投入,在深度報道中通過適度犧牲一點時效以確保信息來源的可靠,追求新聞的深度性和專業性;新興媒體可以利用其流量優勢獲取公眾注意力,權威主流媒體利用采編以及調查優勢后期再跟進報道,二者相輔相成。對于新聞生產領域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長期構建。在重塑新聞生產領域的過程中,主流媒體作為“老大哥”的角色依然起著帶頭的作用。主流媒體話語權的建構不僅需要“硬性建設”,還需要“軟性建設”。前者指高質量、全設備的采集硬件,后者則是報道采集和制作人員的專業能力,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論是權威主流媒體還是新興媒體,多元跟進報道比“單一戰線”更為有效。新聞生產組織建立合作模式的同時也應當健全行業自律機制,更好地堅守新聞真實性原則。
(二)新聞的“生產領域”:對事實進行核查把關
新聞事實核查制度最早始于歐美,該制度保障了新聞的真實性,也體現了媒體對于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19]。在“真相弱化于情感”的后真相時代,信息生產過程中的“主觀性”滋生了各類虛假報道快速增加,愛德華·默羅曾詼諧描述:“真相還在穿褲子的時候,謠言已經環繞世界一周了。”隨著數據分析和算法過濾技術的發展,技術所營造的“擬態環境”越來越接近人們內心的一種“真實”,這種“真實”和“現實”界限的模糊也不斷稀釋媒體的把關權力。因此,新聞的核實把關顯得尤為重要。不管是傳統媒體的人工攔截式把關還是新媒體平臺的技術篩選式把關,把關主要環節還是在于新聞生產領域的把關,因為生產領域的把關也是新聞媒體最能自控的環節,生產領域中主流媒體如何在新聞中核查事實是更好保證新聞傳播環境的重要一環。
后真相時代更凸顯了新聞事實核查的重要性。媒體要贏得公眾的信任要始終堅持新聞真實、事實真實,對事實進行精細的核查與把關。盡量還原事實真相,挖掘新聞真相,拒絕新聞爛尾。專業主流媒體機構通過增設新聞事實核查人員來對新聞事實的真實性進行核驗與檢查以確保新聞的真實性。主流媒體把關的過程中,除了對新聞事實要素真實性進行核查,還要對事實的客觀性進行審視。主流媒體要盡量將事實的全貌體現于報道,在不明晰事實要素模糊的情況下,切勿發表帶有主觀性偏向性的言論,營造一種“情緒環境”,平等對待所有涉事方,被質疑的一方也要提供回應的機會。專業型的主流媒體機構更應該深入紛繁復雜的事件,幫助人們跳出閉守的空間和越過各種復雜利益的障礙,幫助受眾看到事實真相,這也是新聞生產者的職責所在。
(三)內容的“接收領域”:與新聞保持一定距離
有學者認為,“事實核實”從某種意義上固然是后真相時代自我救贖的解藥,但未必是最有效的解藥,“后真相的生成不是在生產領域,而在接收領域”,并引出悉尼大學政治學教授科林·懷特的觀點,“后真相”不僅涉及“生產領域”,與“接收領域”也有著密切聯系,即便是新聞報道在生產領域做好了“核查把關”這一環,也未必就能夠很好地糾正公眾的認知偏差,以及引出艾米麗·索爾森提到的“信念堅持”和“信念回聲”的存在,一定程度表明,當錯誤信息在人們心中先入為主后,即便后續對信息進行了糾正也無法消除最初信息對人們的影響[20]。媒體“不能自控”的環節使得把關效果一定程度地降低。
公眾的選擇興趣制約著事實真相。李普曼認為:“多數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先理解后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21]他認為,如果報道與他們的認知框架相符,那么人們就會接受它。公眾對信息的選擇基于兩種心理機制:認知偏差與認知捷徑。前者是人們在選擇信息時會受到“先驗理念”的影響,這種影響會使得人們在進行信息選擇時虛化與自身喜好、偏見不符的信息;后者則是面對復雜情況時,人們更愿意以一種忽略整體信息、以自身現有認知框架來判斷事實[22]。在后真相時代,新聞真實已不再是衡量新聞優劣的尺度,而是新聞內容是否符合受眾原有的認知框架和價值選擇,如果新聞內容符合受眾原有的認知框架和價值選擇,人們才有可能接收信息。在這個層面上,興趣是受眾在篩選信息時的首要標準,而非準確來判斷事實。相比興趣,準確的標準在選擇過程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后真相時代到來從側面也反映了受眾“較真”意識薄弱。互聯網猶如雙刃劍,賦予公眾話語權使一些草根民眾能夠在自己的一方平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反觀現實,技術構建的現實圖景似乎也沒那么樂觀。在技術賦權下的新媒體時代,匿名性參與和低門檻的準入,平臺“表演”與情緒“宣泄”愈發凸顯。在后真相時代,人們雖然渴求真相,但并沒有以一種理性的方式尋求真相,在魚龍混雜的信息環境下,公眾像“墻頭草”搖擺不定,甚至出現群極化現象。比爾·科瓦奇與湯姆·羅森斯蒂爾曾指出,“作為信息時代的消費者,面對信息洪流的時候,我們必須具備我們曾經要求記者所應具有的懷疑精神”。因此,面對熱點事件,受眾也需要有“較真”意識,對一些越是吸引眼球的新聞內容越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如若受眾普遍具備這種“問題意識”,多一分質疑,就能更有效地減少新聞失實,促使新聞生產更加精細制作,更好地追逐真相。新聞接收者具備了一定的自身把關素養,新聞生產在追求真相的路上也會減少些許阻力。因此,新聞生產者在提高自身素質的同時也要培養公眾整體的媒介素養和“較真”思維,新聞接收者在對待新聞時要敢于質疑,與新聞保持一定的距離,以減少盲從以及群極化現象。
五、結語
新聞真實是每個新聞生產者的必修課,它要求新聞追求客觀真實,減少主觀性與情感性。后真相時代,真相漸行漸遠,新聞的真實性逐漸弱化于情感性,后真相時代的到來使情緒性越來越多地被附加在真相之上,公眾帶著情感和信念被裹挾在信息的洪流中不能夠客觀地認清真相,加劇了信息內容的主觀化失真。“情感鬧市”一定程度削弱了新聞的真實性原則,也不利于新聞傳播環境的正向發展。主流媒體是新聞業的中流砥柱,承擔著更多的公共責任,主流媒體更要在后真相時代凸顯對于真相與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因此,后真相時代,主流媒體權威話語權的建構以及引導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主流媒體通過構建權威話語權來改善新聞業面臨的“信任危機”,增強主流價值觀念的影響力。除此之外,新聞業中的媒體機構每個環節都不能放棄對真相的追求,既需要技術的跟進,也需要各類媒體對真實性原則的堅守和正確價值觀的引領。傳播環境的正向發展同樣也有賴于公眾整體媒介素養的提高,新聞內容的“生產領域”和“接收領域”都要對新聞報道“求真”“保真”“較真”,后真相時代才能更好地面朝真相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