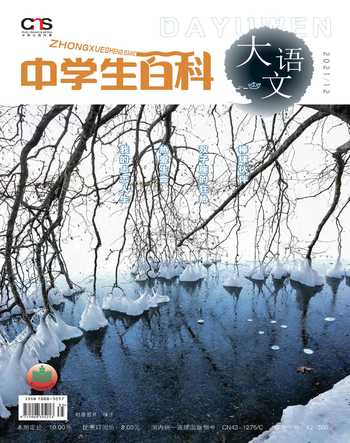我的精神家園
工作與人生
我現在已經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來比喻人的一生,現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時從朦朧中醒來,需要一些時間來克服清晨的軟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時分,他的精力最為充沛,但已隱隱感到疲憊;到了黃昏時節,就要總結一日的工作,準備沉入永恒的休息。
按我這種說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題。這個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國,農村的人把生兒育女看作一生的主題。把兒女養大,自己就死掉,給他們空出地方來——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則另有一種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會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題。站在北京八寶山的骨灰墻前,可以體會到這種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寫著:副系主任、支部副書記、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這些“副”字去掉個把,對這位大叔當然更好一些,但這些“副”字最能證明有這樣一種想法。
順便說一句,我到美國的公墓里看過,發現他們的墓碑上只寫兩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這就是說,他們以為人的一生只有這兩件事值得記述:這位上帝的子民曾經來到塵世,以及這位公民曾去為國盡忠,寫別的都是多余的,我覺得這種想法比較質樸……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寫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過傷感,還是及早回到正題上來吧。
我想要把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推薦給青年朋友們:人從工作中可以得到樂趣,這是一種巨大的好處。相比之下,從金錢、權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樂,總要受到制約。舉例來說,現在把生育作為生活的主題,首先是不合時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為不如,更不要說和黃花魚相比較,在這方面很難取得無窮無盡的成就。我對權力沒有興趣,對錢有一些興趣,但也不愿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寫小說),并且把它做好,這就是我的目標。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總不會是一個都沒有。
根據我的經驗,人在年輕時,最頭疼的一件事就是決定自己這一生要做什么。在這方面,我倒沒有什么具體的建議: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寫小說,這是和我搶飯碗。當然,假如你執意要寫,我也沒理由反對。總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個樣子來,這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人在工作時,不單要用到手、腿和腰,還要用腦子和自己的心胸。我總覺得國人對這后一方面不夠重視,這樣就會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樂最主要的源泉,對生活的態度也會因之變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體,還有頭腦和心胸——對此請勿從解剖學上理解。人腦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科學還不能說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難說清。對我自己來說,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達到的最低目標。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認為它不值得一做;某個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覺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種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會以為它不值得一過。羅素先生曾言,對人來說,不加檢點的生活,確實不值得一過。我同意他的意見:不加檢點的生活,屬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種。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樣子無所謂。從一些電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活著》《找樂》……我對這種想法是斷然地不贊成,因為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種糟糕的樣子,從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義。高尚、清潔、充滿樂趣的生活是好的,人們很容易得到共識。卑下、骯臟、貧乏的生活是不好的,這也能得到共識。但只有這兩條遠遠不夠。我以寫作為生,我知道某種文章好,也知道某種文章壞。僅知道這兩條尚不足以開始寫作。還有更加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某種樣子的文章對我來說不可取,絕不能讓它從我筆下寫出來,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以小喻大,這也是我對生活的態度。
寫給新的一年(1996年)
我們讀書、寫作——1995年就這樣過去了。這樣提到過去的一年,帶點感慨的語調,感嘆生活的平淡。過去我們的生活可不是這樣平淡。在我們年輕時,每一年的經歷都能寫成一本書,后來只能寫成小冊子,再后來變成了薄薄的幾頁紙。現在就是這樣一句話:讀書、寫作。一方面是因為我們遠離了動蕩的年代,另一方面,我們也喜歡平淡的生活。對我們來說,這樣的生活就夠了。
九十年代之初,我們的老師——一位歷史學家——這樣展望二十一世紀:理想主義的光輝已經暗淡,人類不再抱著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現實問題上去,當一切都趨于平淡,人類進入了哀樂中年。
我們都不是歷史學家,不會用這樣宏觀的態度來描述世界,但這些話也觸動了我們的內心。過去,我們也想到過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現在我們的生活也趨于平淡。這是不是說,我們也進入了哀樂中年?假設如此,倒是件值得傷心的事。
一位法國政治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在二十歲時如果不是激進派,那他一輩子都不會有出息;假如他到了三十歲還是個激進派,那他也不會有什么大出息。我們這樣理解他的話:一味地勇猛精進,不見得就有造就 ;相反,在平淡中冷靜思索,倒更能解決問題。
很多年輕人會說:平淡的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對此,我們倒有不同的意見。羅素先生曾說:真正的幸福來自建設性的工作。人能從毀滅里得到一些快樂,但這種快樂不能和建設帶來的快樂相比。只有建設的快樂才能無窮無盡,毀滅則有它的極限。夸大狂和自戀都不能帶來幸福,與此相反,它正是不幸的源泉。
我們希望能遠離偏執,從建設性和創造性的工作中獲取幸福。創造性工作的快樂只有少數人才能獲得,而我們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獲得這種快樂的機會——那就是做一個知識分子。
轉眼之間,我們從國外回來已經快八年了。對于當初回國的決定,我們從沒有后悔過。這絲毫不說明我們比別人愛國。生活在國內的人,對祖國的感情反倒不像海外學人表現得那么強烈。假如舉行愛國主義征文比賽,國內的人倒不一定能夠獲獎。
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開的書,我們更希望這本書的主題始終如一,不希望它在中途改變題目——到外文化中生活,人生的主題就會改變。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哪怕是變得平淡也罷,這就是我們回國的原因。這是我們的選擇,不見得對別人也適用。
假如別人來寫這篇文章,可能是從當前的大好形勢談起,我們卻在談內心的感受。你若以為這種談法層次很低,那也不見得。假如現在形勢不大好,我們也不會改變對這個國家的感情。既然如此,就不急著提起。順便說說,現在國家的形勢當然是好的。但從我們的角度看來,假如在社會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態度,再多一些公正和寬容,那就更好了。
隨著新年鐘聲響起,我們都又長了一歲。這正是回顧和總結的時機。對于過去的一年,還有我們在世上生活的這些年,總要有句結束語:雖然人生在世會有種種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與不幸中作選擇。
賞析
有的時候覺得,優秀又高產的作家不能節選太多次,一定要碰上合適的時機、合適的主題、合適的作品……本期的王小波節選恰好如此。王小波的生平這里不作贅述,僅給出一些本書出版的背景:《我的精神家園》是王小波自選的雜文集,出版于1997年,王小波于1984年赴美國讀書,1988年學成歸國。本書出版時,他已成為自由撰稿人多年。這本書凝結了他歷經世事之后對人生的思考,這時的他已經經歷了下放、做工、恢復高考、出國留學等一系列足以改變人生軌跡的事件。這時的王小波更顯可貴,他經歷風雨之后仍有赤誠之心,更添理解和寬容,是真正的因為了解所以慈悲。
王小波對生活的熱愛與《熱愛生命》的作者杰克·倫敦不同,僅僅是活著對他來說還不夠,他要活得有意義,不違背自己的原則。不是一句簡單的努力過了就行,努力的方式和成果同樣重要——這是王小波對生活的執念和狂熱。
本次節選的《寫給新的一年(1996年)》則能更明顯地表現出作者的成長。他對動蕩和平靜、漂泊和穩定都有了成熟的看法。此時的他做出的決定不再是聽從命運的安排,而是積極主動地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能看到社會發展的趨勢和縫隙間的不美好,他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選擇建設、改變、寬容,要自己創造出更美好的生活。
文/ Vi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