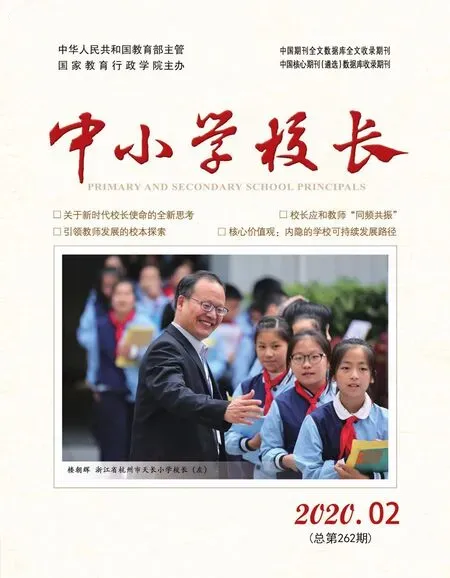人口流動背景下的中小學德育探究
□薛相鋒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發展,人們的活動受地域限制不斷縮小。根據巴格內 (D.J.Bagne)的“推拉理論”,人口流動是“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結果。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飛速推進,城鄉之間及不同區域之間的“推力”和“拉力”異常強大,使得人口流動成為常態。《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 顯 示,2015 年 至2018年間,我國每年流動人口量均保持大約2.5 億人左右。大量的人口流動,給中小學教育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特別是大量的“留守兒童”“外來少年”(這里所說的“留守兒童”“外來少年”的含義已今非昔比,已不再與“貧困”“無助”等概念有很強的關聯,他們已然是新時期人口流動的狀態下的社會樣態,本文以“留守兒童”“隨遷子女”來稱謂。)的產生,使中小學德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人口流動給中小學德育帶來的困境
道德教育的實質是人的社會化過程,會受到自身遺傳條件、家庭、學校、同齡群體等諸多方面的影響。處于流動中的兒童、青少年必然遭遇家庭、社會環境、人際關系等諸多方面的變遷,這些變遷不可避免地會作用于個體的社會化過程。而對于是非觀、價值觀都不成熟的兒童、青少年來說,只是被動地接受著流動變遷帶來的影響。他們生理、心理處于發育階段,道德認知也處于發育階段,處于可塑性強,極易受到外部變化的影響的階段。而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有時存在負面效應,學校教育卻難以企及,使中小學德育陷入困境。
(一)兒童不安全感引發德育危機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庫利的“鏡中我”理論,自我意識和人格形成,要經過觀察別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從而形成“自我”的過程,每個人的“自我”觀念其實是他人這面“鏡子”的反射。事實上,兒童、青少年處于生活、行為的“模仿”期,常常會把別人的行為和自身對照,并試圖模仿。對于父母外出的“留守兒童”來說,他們常常要面對別人“同情式”的“異樣”目光。對于隨父母外遷的“外來少年”來說,他們同樣要面對周圍的人的“疏遠式”的“異樣”對待。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隨遷子女”,這些因人口流動而產生的個體或群體,都很難平等地融入周圍的世界,這就引發了他們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在外界的指指點點中,他們對照的“鏡子”難免會發生扭曲,于是,自卑、自閉、抑郁、煩躁、暴動等情緒不斷滋生。
“留守兒童”“隨遷子女”不安全感造成的心理危機,引發了學校的德育危機。對于兒童、青少年的“鏡中我”世界,是跟他們的“流動”生活狀態和身份相關的。對于這些因人口流動而產生的特殊群體來說,要養成正常的健康的心理,樹立正常的健康的道德認識,進而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不僅需要他們內心變得強大,還需要改變周圍的人對他們的看法和態度。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僅靠學校德育的力量,難免會顯得蒼白。它需要個體、家庭、學校、社會共同努力。而學校德育如何應對,是當前的一個緊迫而重要的課題。
(二)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難以契合
人口流動造成了三種家庭生活樣態:一是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孩子留守在家;二是父母、孩子舉家遷移,戶籍、房屋等還在原地;三是舉家遷移,戶籍也遷走了,在新生活地擁有房屋定居下來,但還和原生活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第一種家庭樣態產生了“留守兒童”,第二、三種家庭造成了“隨遷子女”。第三種家庭成員已成為當地居民,但在語言、行為習慣、價值觀等方面,都還與當地環境格格不入。
中國人民大學鄭杭生教授在他主編的 《社會學概論新修 (第五版)》 中指出,兒童、青少年處于社會化進程中的“依賴生活期”,認為在這一時期個人在生活、心理上都依賴于父母或者他人,父母或撫養人對兒童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確立具有巨大的指導和制約作用。而家庭樣態的改變,勢必造成兒童“依賴生活期”的錯亂,其結果是孩子的思想、行為“游離”于家庭之外,家庭教育的影響力極具縮小。
而對于“游離”于家庭之外的學生,學校教育必然尋求家庭教育的支持。當學生接受學校德育的時候,他必然帶著他的“游離”狀態進入其中,這就會降低學校德育的有效性。而當學校教育尋求家庭教育配合時,家長與學生往往都不能從“游離”狀態回歸,要么是家長遠在他鄉鞭長莫及,要么是家長忙于事務無暇顧及,抑或是家長還沒適應當地環境,對學校教育本能地不理解。這就造成了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分離,增加了學校德育的難度。
(三)社區文化的排他影響與社會教育的反作用
曲靖師范學院梁海艷教授認為,中國流動人口的矛盾在于“空間集聚”與“生活隔離”,一方面,流入地人口多聚居在一起,另一方面,流出地人口處于“生活隔離”狀態。流入人口之所以自發地“空間集聚”,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語言、行為、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受到當地居民的排斥,或者自身認知還不能和當地融合。而處于“生活隔離”中的兒童青少年,也很容易產生一種“隔離”心理。
這也導致了另外一種現象的發生,學生在學校接受的德育認識和良好行為,回到社區卻會受到誤解或白眼。如學生在社區清掃垃圾的行為,會被指責為愛表現或別有企圖。而樣反作用的結果,會使學生道德認知發生混亂,甚至崩潰,造成學校德育越深入學生越逆反的尷尬境地。
二、破解“人口流動”德育困境的建議
在即將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當下,各地流動人口的教育問題,是擺在當下的重大問題,是脫貧攻堅戰中必須啃下的“硬骨頭”。而首當其沖的是中小學校,責無旁貸地做好流動人口兒童青少年接受平等優質的教育,需要立足立德樹人,不靠不等,對癥下藥,確保“一個不落下”。
(一)對學生個體:深度關懷,驅除兒童內心陰霾
對于內心充斥著不安全感的“留守兒童”和“隨遷子女”,許多地方的做法是開展慰問活動,給予他們一定的物質資助。許多學校和老師通過提供“小飯桌”“小課桌”或擔任“代理家長”等途徑,給予他們一定的情感關懷。這些都是值得提倡的好辦法,但效果卻不夠好,驅除孩子內心陰霾還需要深度關懷。
美國教育學家內爾·諾丁斯(NelNod.dings) 提出的關懷教育理論認為,道德教育的要素包括榜樣、對話、實踐和認可四個方面。因此,如何給予“留守兒童”或“隨遷子女”真切的、能得到孩子認同的深度關懷,不妨從這四個方面進行嘗試。一是老師要做好榜樣,帶動班級的學生及周圍的人們共同關懷這一群體;二是要與“留守兒童”或“隨遷子女”展開經常對話,營造師生、生生感情互動的對話溝通氛圍,建立相互融入感、信任感;三是要把“留守兒童”或“隨遷子女”從總是被關照的受眾中解脫出來,讓他們參與到關心他人的實踐活動中去,體驗關懷他人的快樂;四是要創造機會對學生正確的道德行為給予肯定,促進師生、生生間建立一種彼此關懷、相互信任的關系,讓每一位學生都感覺到“我”是被認同的,被尊重的。由此,這些學生心中的“鏡中我”才能回歸正常,他們才會覺得自己是安全的,內心的陰霾才會一掃而光。
(二)對家庭:深度陪伴,搭建家校共育橋梁
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學校的復雜教育過程中產生的一切困難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家庭。”因此,化解“留守兒童”“隨遷子女”的德育難題,也必然要追溯到家庭。具體來說,就是要搭建一定的橋梁,讓孩子在心理上回歸家庭,得到家人的陪伴。
不過,現實的情況是,“留守兒童”“隨遷子女”是孤立的,父母、家人往往并不能很好地陪伴他們。對此,湖北大學魏向丹教授認為“留守兒童”需要的不是一般的陪伴,而是“深度陪伴”,就是要“懂得兒童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參與到他的成長中去”。
所以,學校德育,更多是要站在“留守兒童”“隨遷子女”的立場,想他們所想,急他們所急,真正走進他們內心,與家長一道,實現“深度陪伴”。比如老師做“代理家長”,就不能想當然地認為,自己都已經盡到“家長”的職責了,學生就應該感受到關懷了,就應該“聽話”了,而忽略了學生真實的想法和心理感受。只要我們站在孩子立場,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我們會有很多辦法促進老師、家長與學生的“深度陪伴”。比如,我們可以通過家長與孩子之間每天互通電話 (或微信、QQ)、讓家長遠程參與班級活動、讓學生了解家長一天工作、師生家長視頻開放日等活動,調動家長回歸對孩子的陪伴,促進孩子對家長辛勞的理解,讓孩子真切地感受到家長、老師給予的愛。實際上,家長并不是不想陪伴孩子,只是對“陪伴”的認識不夠,通過老師、學校組織的活動和搭建的橋梁,家長參與的積極性是很高的。
(三)對社區:深度認同,強化社區角色扮演
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米德認為,人的社會化的實質是“角色扮演”。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隨遷子女”,他們固有的“角色扮演”都會被打破,“主我”與“客我”的角色都表現出害怕被“異化”或不敢被“同化”的抵觸情緒。
因此,消除“留守兒童”和“隨遷子女”與周圍環境和周邊人們的相互排斥影響,首要的是讓學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得到人們的認同。做這一點,學校可通過具體豐富的實踐活動來實現。比如,通過校園文化進社區、社區潔凈行動、送溫暖、“我來幫幫忙”等活動,讓“留守兒童”“隨遷子女”與其他學生扮演同樣的角色,同臺演出、同樣付出、合作互助,讓“留守兒童”“隨遷子女”認識到“我能行”“我很重要”“我受尊重”,從而促進他們扮好“社區的一員”這一角色,真正融入社區中去。同時,在活動中也讓周圍的人們加深對他們的認識,感受到“他也和我們一樣”“他也是我們這兒的人”“他跟我家孩子一樣”,真正接納他們。
隨著我國社會發展向“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邁進,城鎮化率還將大幅提升。未來社會人們在異地、異國工作將越來越普遍,人口流動性還將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兒童青少年的教育更加不可忽視。只要我們認真研究這一課題,傾心關注這一群體,學校德育必將不負所承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