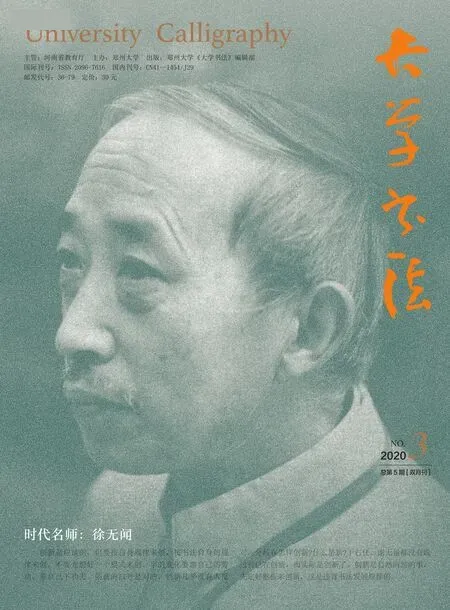論熊秉明的書法“學科”構想[1]——摭談書法博士教育和書法學學科建設的相關問題
⊙ 劉鎮
當前教育部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目錄中,“書法學”屬于藝術門類下一級學科“美術學”的下屬特設學科(代碼130405T)。既稱“學科”,顯然說明目前書法已經擁有基本獨立的知識體系、清晰的研究范圍,明確的專業本質、內涵、對象、功能以及意義。
一、由技入道
20世紀60年代,旅法華人熊秉明在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中文、中國古代哲學以及“書法課”,之后梳理編撰《中國書法理論體系》。在這之后,國內涌現出闡述書法“學科”構想的成果有《書法美學簡論》《書法美學談》《書法學綜論》《書法學》《書法學學科研究》等。自此,書法“學科”意識日益明顯,邊界逐漸清晰,體系亦趨完善。
20世紀80年代,熊秉明完成博士論文《張旭與狂草》(1984)并提出“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的重要論斷(1984,北京),后在國內出版《中國書法理論體系》(1985,20世紀80年代初于香港《書譜》連載),發表《書法領域里的探索》(1985)、《關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的分類》(1986)、《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1995)、《書法和中國文化》(1995)等系列成果。他借鑒西方理論、觀點、方法及邏輯體系,立足書法文獻及其意蘊,以“學科”意識系統闡述了書法傳統。在創造性解讀書法內涵及理論構建的同時,又先后在國內開設書技班(1985)、書藝班(1988)、書道班(1992)等,進一步將其理論成果付諸實踐,推動書法理論與技法的雙向共闡。
書技班:教材為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朱光潛《文藝心理學》(附錄部分“形體美”一節)與《談美》(第七章《情人眼底出西施》);提倡“無須臨摹”的書法學習觀念,建立“外圍點”“內接點”等概念。
書藝班:教材為S·阿瑞提《創造的秘密》,課程安排為第一日寫一幅字作自我介紹,第二日超速寫法,第三日盲目寫法,第四日模擬庸俗,第五日極限情況,第六日“對話”;其間作了題為“書法創作內省心理學探索研究”的講座。
書道班:教材為《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要求純模仿的臨寫、研究性的臨寫、意趣的臨寫以及創造性臨摹。(宗緒升《熊秉明書學思想研究》)
從內容設計來看,顯然帶有實驗性質,可以說已經預設了書法“學科”體系。這一探索,包含三個層次:“技”,強調靜態書法點畫形態的分析;“藝”,追尋的是基于點畫造型的主觀思考與重塑;“道”,是在前二者基礎上的嬗變與升華,注重一般規律的抽繹。三者之間,既有嚴密邏輯的先后順序,又與其《中國書法理論體系》思考路徑保持一致,為書法“學科”制定出一套邏輯清晰、目標明確的教學方案。這種借助西方美學理論重新厘清書法“學科”的構想,潛在地設定了書法是一種可供解剖靜態文本,又在跨文化視閾(道)中充分重視了書史背后的思想與觀念。由此,這種注重書法內核與精神的持續探索,引起了書法藝術與現代藝術甚至藝術人生(老年書法研究班2002)對話,啟發了各種書學流派與現象,推動了書法教育理念的多元化發展。
結合當下來看,熊秉明的“學科”構建與反思精神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譬如,書法學科的定位與培養方案的設置,應當基于何種語境來確定?目前,書法學專業大多游離于哲學、文學、歷史學、藝術學等門下,本、碩、博培養點名稱更是五花八門,這顯然是每所高校對其不同理解所致。實際上,從傳統中走來的書法學科理應定位在文史學科之下,其名實早已涵蓋了所謂的“文化”,某種程度說與“藝術”“造型”等存在著天然的鴻溝。由此,與其說古代寫本、刻本傳統中,任何一種學問的誕生都離不開書法,毋寧說書法自古以來就是藝術觀念史、思想史的共同載體——“書道”。
二、藝術與科學
從熊秉明的書法“學科”構想中,亦可以清晰感覺到西方美學理論與現代抽象主義的創作原理中理性思維的重要性。這種“數理”邏輯思維,根源于他承襲了父親(著名數學家熊慶來)的“優美的推導”“洗練的數學語言”,同時,也與早年研究哲學之后的“回歸”有關。如他曾在《關于羅丹——熊秉明日記擇抄》中直言,來源于生活實踐的具體技巧是形成風格的唯一來源——后來又選擇更為具象的雕塑。他的理論與實踐主題中,還從整體上展現出用西方宏觀、微觀并舉重新“觀看”東方的辯證性思維。
熊秉明曾努力探尋佛像雕塑藝術形式,稱之為“超越生死煩惱的一種終極追求”。這種追溯哲學理性與藝術感性之間的交融,何嘗不是一種“理性和信仰的沖突、傳統與革命的對立、中西文化的矛盾”呢?(熊秉明《父親之風》)與其類似,當前“書法學”專業要求同時具有“寬厚的書法學科專業知識”與“較為寬闊的文化視野”,看似錯位,實則統一。故而,我們既要強調書法傳統所根植的國學基礎,也應借鑒西方美學及相關理論觀念、方法等去透視書法傳統經典的生成與流變。尤其在具體的資料搜集、邏輯推理、體系構建過程中,注重邏輯思維在教學示范、理論推求過程中的重要性。如此,方能擁有嚴謹、縝密的思考,終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無限接近歷史真實。
熊秉明的理論原點與李格爾如出一轍,后者所構想的藝術發展程式,是立體先于平面,觸覺先于視覺,“最初的藝術沖動是出自對藝術形態事物的模仿”。由此說來,邏輯理性所標榜的“科學”不僅是書法學科建設的原點,也應是“歸宿”。因此,當前豐贍的書教資源,以及傳統中感悟性書論、題跋、筆記等看似只言片語,枝蔓叢生,但卻內在地隱含著邏輯思維嚴密的文、史、哲根基與體系。這些文本“空間”的細讀,須循依文獻考據等“笨功夫”,剔精掘微,剝繭抽絲,進而揭橥“微言”背后之大義。推開來說,學科體系等或可以借鑒無遠弗屆的哲學、文學理論來統攝與透視,以此拓寬學科視野,提升學術高度,多重維度地完成“原境”意義的追尋。這種尋繹,也是對當代學術研究中“多重證據法”的一種探索。
三、“人本論”
熊秉明認為文化的核心是哲學,從抽象思維落實到具體生活的第一境乃是書法。他在《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中,創造性地使用文評、詩話視角重新建構了書法理論系統:喻物派、純造型派、緣情派三者以自然為旨歸,以造型手段表現書者內心感情;倫理派、天然派、禪意派三者則為以上三類的綜合概括與提升,分別對應儒家(善)、道家、佛家。于此構建了一個嚴密的書法闡釋系統。
誠然,早期書論“同自然之妙有”“達其情性,形其哀樂”以及“書之為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皆尚自然。而從揚雄“心畫”、許慎“書者,如也”到劉熙載《藝概》“書也者,心學也”的推導過程,在熊秉明看來是書法重“形”但更重“神”的塑造過程,也即藝術史風格是源自“文化的與形式的”。(沃爾夫林《藝術史原理》)故他認為,書法與詩、文、畫在本質上是相通的。
此外,熊秉明不僅把書法當作中國美術的核心問題,而且始終把中國書法思想理論置于全世界各種藝術理論的背景之中,不時作東西對照、古今對話,希冀從這種開闊的視野中抽繹出中國書法的理論規律。他在異質文化融合的立場上,突破了以往僅從本土文化內部分析書法的僵局,從“人本”回歸角度為當代書法理論研究及書法“學科”建設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性的學術構架。在其構想中,還觸及中國書法認知體系、書法普世價值與審美范式的當代構建、當代中國書法海內外傳播的路徑抉擇、反理性思維與當代書風之關系等,并創造性提出“核心說”“形式論”等新的書法研究方法論,書法界至今仍在普遍采用。
熊秉明的書法“學科”意識,為我們提供了跨文化視野下古今中外對話的多重思考,雖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但在當前嘗試構建書法“一級”學科的過程中依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注釋:
[1]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華人學者中國文藝理論及思想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6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