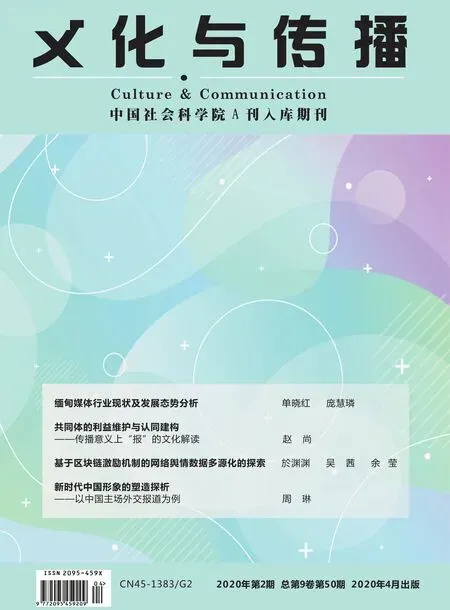“媒介理解”之理解:伊尼斯與麥克盧漢媒介研究視角的比照
在傳播學學科逐漸成型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的傳播學實證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被稱為傳播學的管理學派抑或行政學派,以傳播效果研究占據核心位置為顯著特征。而與此同時,在北方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里,卻產生了與此迥異的媒介研究范式——對媒介本身批判的、分析的研究。這也就是今天學術界常常稱道的媒介環境學派的濫觴之地,對媒介本身進行研究的傳播研究范式肇始人物是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和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他們常常被稱為媒介環境學派的雙星[1]。
雖然在媒介研究中,他們的觀點具有很多共性,例如媒介本身的出現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新的媒介會取代舊的媒介引起社會環境的改變等等。但是,他們的媒介觀點也表現出巨大的差異,伊尼斯把媒介的作用放置于整個世界文明的發展演替中分析,而麥克盧漢卻在微觀層面上談媒介與身體、媒介與人的感覺系統之間的關系。這種差異折射出二者在理解和分析媒介時的不同研究視角,而研究視角的不同反映的又是二者研究媒介的出發點,也就是在“為什么研究媒介”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答案。因此,就二者在媒介研究中的視角差異,本文將由淺入深,探索這種差異背后二者媒介研究面臨的不同現實問題,并進一步揭示他們的媒介研究方法與各自學科背景、所受學術影響間的關系。
一、伊氏與麥氏各自的“媒介理解”及其考察視角
如果說麥克盧漢是在自覺地研究媒介的話,那么伊尼斯則是在研究加拿大經濟史的過程中闖進了媒介研究領域,或者說,伊尼斯的媒介研究是其政治經濟研究衍生出的一條分支。盡管如此,伊尼斯依舊以令人驚奇的媒介與文明史研究開辟了理解媒介的新視野。伊尼斯認為,“傳播媒介的性質往往在文明中產生一種偏向,這種偏向或者有利于時間觀念,或者有利于空間觀念”[2],時間偏向的媒介往往笨重而耐久,可以長期保存,例如石頭、羊皮紙;空間偏向的媒介往往輕便易攜帶,利于運輸和擴散,例如莎草紙和中國紙。而時間偏向的媒介利于宗教的發展,容易形成非集中化的宗教性神權帝國;空間偏向的媒介利于行政組織和官僚機構的發展,容易形成集中化的世俗王權帝國。“所謂媒介或倚重時間或倚重空間,其涵義是:對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這樣或那樣的偏向”[3],伊尼斯將媒介的變遷和歷史上世界尤其是歐洲、中東、近東文明的演進聯系起來,他認為社會中主導媒介的變化必然會導致社會中占據主導和控制地位的組織力量的變化,伴隨這種變化的往往是戰爭、社會改革、政治組織改革或政權更迭,最終導致文化/文明的偏向發生轉移。在伊尼斯對古埃及、巴比倫、亞述、希臘羅馬文明等的演進分析中,他始終用一種“媒介變化-文明動蕩-新文明形成”的演化思維論述文明發展歷程。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技術的演化或許遵循著一種漸進式的路線,但是文明的演化卻未必如此。千百年間,宗教文明和世俗文明、時間偏向的文化和空間偏向的文化一直在相互交織,媒介演化出新的形式,然而文明的發展卻并未顯現出進化式的發展跡象,它們之間只有屬性之分并無優劣之別。
然而,媒介變化與文明演替之間是怎樣產生聯系的呢?伊尼斯給出的答案是知識和權力的配置與轉移。“伊氏的創造在于他把文明的生長、發展和衰落與某種傳播形式及其所依賴媒介的發軔、流布和變異聯系起來”[4]。伊尼斯認為,文明中占主導地位的媒介變化會對該文化中的社會組織力量產生影響,具體來講就是“媒介技術的革新將迫使知識領域的壟斷權力重新分配,促使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爭奪和變革”[5],這種爭奪的結果往往是“掌握新媒介的團體權力上升,而與舊媒介相維系的團體影響力衰退”[6]。一旦文明中不同集團的力量發生變化,在新興集團主導下,社會的政治組織、經貿聯系、文化教育和世俗風貌都會發生適應于該媒介的變化,并體現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集團的利益。
對麥克盧漢而言,伊尼斯扮演著啟迪式的前輩角色,但二者的媒介理論還是存在著無法彌合的鴻溝。不同于伊尼斯,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一種媒介都是人身體的某一感官的延伸:衣服是皮膚的延伸、輪子是腿腳的延伸、住宅是體溫調控機制的延伸[8]……而電子媒介是人中樞神經的延伸。在他的媒介理解中,媒介僅有對單一感官/器官的延伸和對中樞神經延伸的殊分。在以人類感知為基礎的媒介理解基礎上,他還提出冷熱媒介之分,冷媒介是信息清晰度低、對人的參與性要求高的媒介,而熱媒介反之。麥克盧漢對媒介的另一個重要論斷是“媒介即訊息”,這句話有多重涵義,一是一種媒介的形式往往是另一種媒介的內容,例如口語是文字的內容、文字是報紙的內容、報紙是廣播的內容等;二是一種媒介形式本身就能夠傳達出某種信息,比如使用電腦辦公意味著比使用算盤辦公更現代化、具有更前沿的技能;三是一種媒介形式的出現會對社會產生遠大于其內容的影響,比如火車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使不同城市之間的聯系更加便利,進而改變了社會經貿和日常生活形態。麥克盧漢的這一觀點改變了以往學者僅僅關注媒介內容而忽視媒介形式的歷史,將媒介形式本身作為研究中心。除了上述主要媒介思想外,麥氏還有一些有趣的媒介思想,例如“媒介即按摩”、媒介四定律(提升、過時、再現、逆轉)、“電子媒介將全球聯系成一個地球村”等。
麥克盧漢的媒介思想與伊尼斯從知識壟斷和權力轉移的變化來考察媒介的立足點不同,他始終強調人的身體的中心地位,并把身體的感知/感覺置于媒介研究的核心,媒介“冷”“熱”論、人體的延伸、聲覺空間、視覺空間、按摩……這些麥氏媒介理論中的核心詞語都與人的感覺系統相聯系,并突顯身體的中心地位。而在媒介研究的另一頭,麥克盧漢指出,媒介最重要的后果是他自身所創造出的新環境,對“環境”的強調暗含著人處于環境之中的前提,即“環境”并非獨立于人,而是包裹著人、與人相伴相隨。因此,作為中介的各種媒介形式實際上是人感知環境的通道、方式甚至環境本身,麥氏媒介研究的出發點在于人如何把握和認識他所處的身外世界,而媒介正是他討論這個問題的抓手。
伊尼斯和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解”具有明顯的共性,即他們都將媒介本身作為研究重點,認為技術進步帶來的新媒介形式本身就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是宏觀的。但是,從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二者的媒介理解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其一便是在“什么是媒介”這個問題上,伊氏依舊遵循著傳統的習慣,將能夠承載信息內容的,諸如石頭、莎草紙、羊皮紙、報紙等等視為媒介,而在麥氏那里,媒介的范圍拓展到了幾乎所有的人類技術產品;其二是促推其媒介研究的問題不同,伊氏希望弄清文明是如何演替和發展的,試圖從媒介研究中發現文明的動態演化機理;而麥氏則旨在從個體層面理解媒介作為中介化認識工具的作用方式。順延這一思路,自然會產生如此追問: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么?對于這一問題,可從伊氏和麥氏的學術軌跡與時代環境入手探查一二。
二、伊氏與麥氏進入媒介研究的拐點及其緣起
伊尼斯和麥克盧漢都并非一以貫之的媒介研究者,他們都是順著自己早期的研究自然進入媒介研究領域。從二者更宏大的學術脈絡來考察其媒介研究在整個學術生涯中的位置,能夠更好地理解他們媒介研究的不同角度。為此,一個較好的切入點是挖掘他們由早期研究進入媒介研究的拐點及其代表作。
伊尼斯在進入媒介研究前的切近作品是1946年出版的《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一書,在該書中,伊尼斯將19世紀歐美的新聞出版業與政治經濟生活聯系起來考察,并形成了這樣一個學術取向:“媒介所承載的知識、信息對于社會文化形態的變遷具有重大作用”[9]。伊尼斯通過此書分析了歐美自十六世紀以來的造紙業、印刷業和新聞出版業如何與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集團尤其是商業力量相互聯系從而形塑社會文化形態、爭奪社會權力并創制新的政治經濟形態的過程。他所感興趣的是傳播技術變革如何與政治、經濟、文化互動并對文明產生何種影響。然而,在此書的寫作中,他發現了一個更加重要的線索,即一個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傳播技術變革之間的互動關系并非工業革命之后才出現,而是在此前所有歷史時期的文明中都可以瞥見影子。由此,伊尼斯便打開了對古代文明與傳播媒介之間相互影響、互動演進的媒介研究的大門。《帝國與傳播》及《傳播的偏向》便在此后不久誕生于世,伊尼斯對媒介的研究始終遵循著政治經濟學分析的路線,甚至可以說是其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媒介與技術領域的延伸,他對于媒介的分析注重宏觀的社會組織、權力結構、知識階層、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的互動,探查傳播技術變革如何影響這些社會上有組織力量之間的結構性平衡,又如何塑造出新的文明形態。
然而,從《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一書前溯,可以發現更重要的線索,這種線索關乎伊尼斯展開媒介研究的根本動因。伊尼斯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政治經濟學者,他此前的專著《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史》、《加拿大皮貨貿易》和《鱈魚業:國際經濟史》都旨在對加拿大的經濟史進行研究,在大宗商品貿易中探查技術、地理、交通、文化、社會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分析加拿大、美國和歐洲之間不同文明的互動模式以及這種經貿互動如何影響加拿大的文化形態、社會生活和政治經濟結構,借以建構起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經濟史和民族國家身份,擺脫加拿大一直以來作為英美文化附庸的尷尬國際認知。伊尼斯的這種研究動因——挖掘加拿大問題的歷史成因并構建加拿大的民族國家身份,也貫穿到他的媒介研究中去。加拿大包裹在美國國土之中,曾經是歐洲強國尤其是英法的殖民勢力范圍,對于英美文化的強大擴張壓力感到既憂怖又無奈。伊尼斯的媒介研究對歐洲、中近東文明進行歷史分析,從媒介技術的偏向出發對西方現代文明發出警醒,指出西方文明的危機在于強調空間的偏向壓倒了對時間的關注,這導致現代西方文明具有擴張傾向和訴諸戰爭的危險[10]。加拿大的國家身份并非是在以擴張性媒介技術所塑造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們所想象的某一文明的附庸,而是有其自身的獨特源發邏輯。
麥克盧漢早期的研究一直在英美文學領域,他在劍橋大學的博士論文便是研究英國十六世紀作家托馬斯·納什(Thomas Nashe)的論著。從英國返回北美大陸后,由于他獨樹一幟的研究風格、天馬行空的思維方式以及加拿大高等教育匱乏的理論體系,他有感于自己在文學研究中無法尋得想象中的建樹,需要尋求其他的研究視野和突破點。而他在美國學習和任教期間,被美國商業社會的繁榮景象和高度發達的現代新聞出版和廣告業吸引,并受到伊尼斯媒介與文明研究的感召,遂以對美國廣告業的分析進入媒介研究領域。他的第一本著作《機器新娘》便是對所選取的59篇美國廣告案例進行分析,展現美國廣告業如何使用各種手段塑造人們的生活方式從而改變社會環境。麥克盧漢認為從沒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本土潛在的威脅并不是戰爭或侵略,而是在現代工業急速發展的社會中,資本、商業和傳媒集團之間的利益勾結,對大眾社會塑造一種無形的生活方式、時代風尚,即麥克盧漢《機器新娘》的副標題——“工業人的民俗”。這種工業化的現代民俗往往作用于社會大眾的集體無意識,塑造一種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社會環境,讓人潛移默化地接受在各種大眾媒介技術上充斥的廣告所傳達出的信息,并將其視為生活中的應然。面對現代工業、傳媒產業和媒介技術之間的互嵌和共謀,麥克盧漢不禁感嘆“在我們這個時代里,成千上萬訓練有素的人耗盡自己的全部時間來打入集體的公共頭腦,打進去的目的是為了操縱、利用和控制,旨在煽起狂熱而不是給人啟示”[11]。面對工業化時代,技術與商業的勾結帶來的“一種漩渦式的幻覺效應”,麥克盧漢認為我們只有將其“捕捉在手并加以思考,其意義才能把握”[12]。“工業人的民俗”作用于人的頭腦和思維,影響人們對社會環境的感知和思考,深處這種“大漩渦”中的人們相應的解決之道不是逆漩渦而行,而是深入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的漩渦中心,馴服并駕馭它們。既然大眾文化和媒介作用的是公共頭腦和集體意識,那么我們需要做的便是了解這種媒介技術如何作用于人的思維和心智,進而順勢利導以逃脫集體夢幻的困境。在具體的媒介研究中,麥克盧漢便將這一研究思維自然落地為人如何把握和認識身外世界和環境這一問題,“感覺”遂而成為其媒介研究的中心。
從《機器新娘》這一麥氏早期著作中可以發現,該書不僅透露出他媒介研究的緣起,還顯現了其后來諸多媒介觀點的端倪。在此書中,麥克盧漢將商業主義主導下的廣告業看作是塑造社會環境的主要媒介,是其后來的觀點——媒介塑造人們的生活環境的前奏;而在探討媒介如何作用于人的思維和意識的過程中,麥克盧漢自然而然地將人的感覺系統放在了中心位置,奠定了后來以感覺為基礎的媒介冷熱論、媒介延伸論;而他對以傳播技術為依托的商業主義集體夢幻采取的非批判態度——他認為這一社會圖景“不僅充滿破壞力,而且充滿了希望”,應采取積極的“認識-駕馭”的思路來應對——也預示了其對電子媒介產生的技術烏托邦思想。
上述分析表明,伊尼斯和麥克盧漢媒介研究的緣起存在巨大差異。伊氏以一個民族主義學者的姿態希望從文明演化和媒介技術變遷的歷史分析中探求架構加拿大民族國家身份的路徑;而麥氏則從美國繁榮的商業主義塑造出的集體幻覺中察查出一種工業社會的危險,并試圖給出他個人的解決思路。
三、伊氏與麥氏媒介研究方法的差異及其原因
伊尼斯的媒介研究表現出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具體表現為將文明的歷史變遷與社會制度、文化、技術、組織、權力等社會結構性因素聯合起來考察,以動態演化的、整體的思維考察政治經濟的社會變化。在他看來,傳播技術的革新并不是孤立出現的,而是存在社會制度的支持或阻礙,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思維習慣和互動方式的固化形式,它體現特定的文化風貌、組織習慣和權力結構。傳播技術對文明進程產生的影響也是通過制度體現出來的,二者在矛盾、斗爭和尋求平衡中表現出交替演進以相互適應的過程。伊尼斯對媒介形式和傳播技術的分析始終用一種系統的觀點來看待,并充分考慮社會或文明這種系統內各種結構性要素的相互作用。他所謂的媒介的偏向實際上是技術與社會制度之間相互矛盾和決定的后果,傳播技術的變革是一個文化過程,它蘊含著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階層關系和權力關系。伊尼斯在分析傳播技術演變時強調“中心-邊緣”關系,認為技術革新常常發生在一個帝國或文明的邊緣地帶,例如遠離莎草紙生產中心的歐洲大陸出現了羊皮紙、遠離法國宗教中心的德國和英國出現了印刷機和現代出版印刷業;遠離歐洲大陸的美國出現了廣播等,這體現了掌握舊媒介技術的權力集團對其他社會集團的壓制,以及邊緣社會集團爭奪權力的媒介實踐,技術嵌入社會發展和文明演進的動態歷史進程中,與其所在的包括知識壟斷階層和社會權力結構在內的制度環境發生互動并形成新的咬合關系。
伊尼斯用宏觀的視野對媒介在歷史文明中與社會其他制度性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來考察傳播技術變革的影響,而麥克盧漢的研究視角表現出個體主義的傾向,他將微觀的個人作為媒介研究的中心,將人體的感官系統抽象出來作為中介化作用下媒介的現實理據。盡管他有對社會環境的強調,但也僅僅是作為個體感覺的對象存在,環境在他這里是對象、他者、包裹人體的外衣,不具有伊尼斯媒介思想中的社會歷史屬性。另外,伊尼斯在媒介研究中十分注重從歷史演進和文明發生發展的細節中尋求聯系,以求邏輯上的連貫和自洽。但是麥克盧漢常常就社會現象做出論斷,從未顯現出從現象到洞察之間的邏輯勾連,例如他的“媒介即訊息”、“媒介即按摩”便是騰空誕生的個人體察,這也是麥克盧漢長期以來備受爭議的原因之一。
存在這種研究方法和思維的分野,與二人的學術背景存在很大聯系,從根本上說這是社會科學和文學之間研究手段的差異。伊尼斯博士就讀于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受到當時流行的制度主義經濟學尤其是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B Veblen)的思想影響,凡勃倫反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從微觀的個人和企業行動者視角將經濟學置入真空中進行數學的、物理的研究和計算,而是主張從中宏觀的層面將社會制度性因素引入對經濟學的考察,甚至將社會經濟的運行當作社會制度的一個方面來整體、系統地考察,這深刻影響了伊尼斯在媒介研究中考察傳播技術變革的整體思維和制度性視角。此外,杜威(John Dewey)及芝加哥社會學派也影響了其媒介研究的實用主義思想,強化了其聯系的、整體的研究圖底。而對麥克盧漢而言,他在劍橋大學從事文學研究的經歷尤其重要。劍橋的新批評學派一改往日文學研究中強調作者個人的才華、社會現實背景的調子,認為藝術作品本身的結構會制約作家和詩人的創作,也就是將文藝理論的研究由文學內容轉向了對文學自身形式的關注,他們認為“重要的是形式——如何組合詩歌的各種內容要素,形式就是詩歌獨特性的全部”[13]。麥克盧漢深受新批評的影響,只不過將其研究對象由文學形式轉換成媒介形式,其“媒介即訊息”便是新批評學派強調文學形式的思想在媒介領域的再現。由此,便也不難明白為何麥克盧漢不屑于從現實經驗中尋求事實材料來耙疏其思想內在聯系和邏輯了,究其根源是文學研究的方法本就是就現象談觀點,它的修辭是并置的、類比的、界面式的,而非推理的、論證的和講求因果的。
結語:元問題的再思考
伊尼斯和麥克盧漢的媒介研究作為回答各自研究問題的方法和手段,最終都構建出一個理想的彼岸。在伊尼斯這里,西方文明的危機需要通過對口語傳統的回歸從而平衡現有空間偏向的擴張和戰爭問題來獲得緩解,正如他所說,“穩定的社會需要這樣一種認識: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維持恰當的平衡”[14],因此在他那里,希臘口語傳統獲得了崇高的地位;而麥克盧漢則認為希望的曙光在未來,電子媒介的蓬勃發展將會帶來全球村,通過再部落化的過程,人們將獲得新的感官平衡從而形成一個覆蓋全球的聲覺空間。二者對各自研究緣起的問題都提供了清晰的答案,但卻表現出兩種傾向,伊氏緬懷過去那個想象中的美好時代,而麥氏則擁抱未來的媒介技術。毫無疑問的是,他們心中都抱著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只不過呈現出回望過去和展望未來兩種狀態。
然而,“作為媒介研究的邏輯起點——何謂媒介、媒介是什么,無疑是所有媒介理論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元問題”[15]。伊氏和麥氏的研究開拓出對媒介/技術本身進行關注的一種新的理論范式,引導我們關注媒介對社會環境、人的感知產生的影響。二者雖都沒有對“媒介是什么”這一問題有直接的回答,但從他們的思想中可以窺見,伊尼斯的媒介概念依舊是在傳統的可承載信息/內容的交流交往中介這一范疇內,但麥克盧漢的媒介概念卻幾乎囊括一切技術產品、信息內容和日常用品。二者對于“媒介”認識的這種差異,從根本上講是他們研究問題的差異——一個是為了研究文明演化的影響機制,一個是為了研究環境如何作用于人的思維和意識。所以,二者的媒介研究其實在他們的研究旨趣基礎上扮演了一種手段的作用,“媒介”是其破解和回答各自研究問題的切入點。反過來說,對于“媒介是什么”的問題,重要的不是去首先回答它,而是弄清研究者準備將其置入自身研究整體中的何種位置,根據其扮演的何種研究角色來決定媒介的何種社會的或技術的內涵。這意味著對媒介研究而言,“媒介是什么”的答案是流動的且會隨著社會發展程度不同、研究出發點、研究思路不同而產生巨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一味追求“媒介是什么”的標答是無意義的,也是徒勞的。在媒介研究的元問題無法獲得共識性回答的情況下,注定了此領域的邊界難以廓清,同時也蘊含著媒介研究不斷走向交叉、碰撞和革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