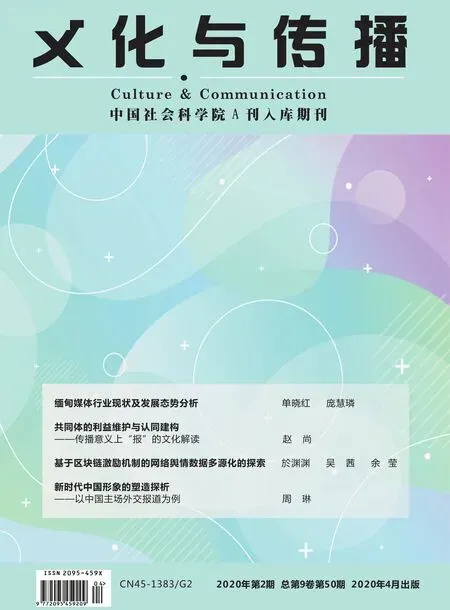從文學作品中“牛郎織女”傳說的演變看文化的傳承發展
“牛郎織女”傳說在我國流傳千年,家喻戶曉,早已成為中華民族幾千年璀璨文化大家庭里不可分割的一員。傳說之所以流傳如此之久、影響如此之大,一方面是因身處農家的苦命“牽牛郎”與來自仙界的非凡“織布女”相親相愛、難得聚首而感人至深、令人難忘,另一方面也因與故事合二為一的七夕節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節日密不可分。本文通過對文學作品中“牛郎織女”傳說發展演變的分析發現,傳說在歷史大潮中經歷了曲曲折折的發展歷程,其故事情節、內容構成、情感色彩、價值主張等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在不斷地豐富發展、演化變遷。而這背后的深層次因素則是,深厚的社會基礎、獨特的民族情感以及強烈的價值訴求。聯系我國當下文化的傳承發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入人心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全會精神的宣講等等,有可借鑒之處。需更多注意樹立正確價值導向、適應社會公眾需求、借助多樣表達形式,以此為文化傳承發展、思想宣傳教育奠定生命力,增強持久力,擴大影響力。
一、文學作品中“牛郎織女”傳說的歷史演變
(一)西周“牛郎織女”傳說的萌芽
“牛郎織女”傳說在民間已流傳兩千多年,其文字記載最早可追溯至《詩經·小雅·大東》一文:“跤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在此處,一顆星辰邊上的幾顆星星構成的形狀像織布用的菱形梭子,伴隨著星辰的移動,被聯想成不停編織的“織布女”形象;而另一顆明亮的星星與旁邊兩顆星星構成的形狀則被聯想成手牽老牛的“牽牛郎”形象。在此處可以看出,古人在夜觀星象時聯想人間事物,將天上星辰的物理特點與人間生產生活相關照,并依此為星辰命名,才有了“織女星”“牽牛星”一說。但此時“織女”“牽牛”僅僅指代天上兩顆星辰,尚未沾人間煙火氣息。隨著時間推移,《史記 天官書》:“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此處將牽牛星看成是“犧牲”,而將邊上的河鼓三星看成是將軍,“牽牛”走向人間;將織女星看成天帝后人,“織女”已經有了生命特征。盡管此時的“牽牛”“織女”已經開始擬人化,但仍未產生人間情愛,與現今“牛郎織女”傳說的形象大相徑庭。
(二)漢代“牛郎織女”傳說的形成
《古詩十九首》中寫于東漢時期的《迢迢牽牛星》一詩的出現標志著“牛郎織女”傳說基本形成。其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1]此詩在后世廣為傳頌,流傳至今。該詩奠定了“牛郎織女”傳說的主流形態,建構起傳說的基本元素、主要內涵、主流色彩、中心思想。明確了“織女星”為女子,終日以織布為務,與男子“牽牛星”分隔于銀河兩岸,相去不遠卻無法相互言語、相處一起,只能隔空相思、淚流不已。而在曹植所寫的《九詠》中則明確表明“牽牛”“織女”為夫妻關系,且在每年的七月七日相會一次,同時也點明了“七夕節”。詩中寫道:“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荊楚歲時記》記載到:“七夕,婦人結彩樓穿七孔針,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表明當時社會上對七夕節日比較重視,婦女通過穿七孔針、陳列瓜果于庭院等以示慶祝。此時,牛郎織女兩人之間的情愛故事與七夕節日的隆重慶祝已經融合,有了現今“牛郎織女”傳說的基本樣貌。
(三)魏晉以降“牛郎織女”傳說的發展
進入魏晉南北朝,七夕題材進入詩歌,到唐宋兩代,七夕詩歌迎來輝煌發展時期。[2]“牛郎織女”傳說由此迎來大豐富大發展,情節不斷豐富起來,傳說所折射的思想主張、情感立場、價值觀念走向多元。魏政權時曹丕在《燕歌行》寫道:“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表達了對牽牛、織女兩人遭遇不公待遇的深切同情。兩晉時期陸機在《擬迢迢牽牛星》寫道:“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沾露”[3],描繪出牛郎織女情深意篤難以割舍卻又不得不各自分離,緣分不夠只能引領相望痛苦流涕的傷感結局。眾多作者在詩歌中傳達出對牛郎織女分隔兩地難以團聚的萬般無奈,對隔空相思獨自淚流的深切同情,對相依相伴甜美愛情的熱烈渴望。此類詩歌所傳達的中心思想、情感色調成為“牛郎織女”傳說的主流基調。
然而,在這一大發展時期,不同于主流色調的“異文”也現于記載。齊梁時期殷蕓的《小說》中寫到:“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樣勞役,織成云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哀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妊。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該小說描繪了另類的牛郎織女形象:織女作為天帝之女,年年在天上織衣忙得連容貌都無暇顧及。天帝可憐她獨自一人,就將她許配給銀河西邊的牽牛郎。然而織女出嫁后就廢棄了織衣,導致天帝責令織女回到銀河東邊,只允許織女一年只能與牛郎相會一次。該小說傳達出織女嫁給牛郎后偷懶而荒廢織衣,最后咎由自取被天帝責罰的形象,表明作者對牛郎織女只能一年一度相會的贊同,對天帝施予懲戒的認同,以及對織女品行蛻變的譴責。異文的出現,豐富了“牛郎織女”傳說的敘事情節、情感色調、價值觀念,也讓主流的牛郎織女形象受到沖擊。
(四)現當代“牛郎織女”傳說的定型
新中國成立后,“牛郎織女”傳說被納入新中國宣傳教育事業工作之中,編入初中課本,成了中學生必讀的文章。建國后隨著戲改運動中劇本的改造及改編進教材,牛郎織女傳說中原有的男性與女性矛盾被消弭了,成為一個反封建禮教的文本。[4]書中寫道:“成天成夜織錦,一會兒也不許休息。身子老在機房里,手老在梭子上,勞累不用說,自由沒有了,等于關在監獄里,實在難受。”牛郎聽完織女的遭遇后說:“姑娘,既然天上沒什么好,你就不用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們兩個結了婚,一塊兒在人間過一輩子吧。”織女應答道:“你說得很對,咱們結婚,一塊兒過日子吧。”當王母得知織女呆在人間不回時,王母恨織女“簡直是有意敗壞她的門風,損害她的尊嚴。她發誓要把織女捉回來……給她頂厲害的懲罰。”[5]編入教科書的織女全然是一副受苦受累、飽受束縛、滿腹委屈、急盼自由的普通勞動者形象,沒有了貪圖玩樂、荒廢勞動、不守規矩、不滿人間、家庭不和、與夫相斗等不良形象。而王母則全然是一副管束嚴苛、自私自利、不講溫情、棒打鴛鴦的封建家長形象。牛郎織女的結合所反映的則不僅是婚姻打破門第、底層勞苦大眾收獲幸福、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好結局,還是普通勞動者掙脫封建枷鎖、婚姻自主、自由戀愛而結合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勞動的美好故事,與建國后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念相吻合。
時至今日,當下社會對于“七夕”節日的隆重紀念與古代社會大不相同。人們對節日的美好期盼不再是提高女紅技能,而是希望與自己的戀人、伴侶擁有一份浪漫美好的愛情;對節日的紀念方式不再是穿七巧針、做女紅、陳列瓜果等等,而是與意中人一起游玩、逛街、看電影等共同度過一年一度的浪漫“情人節”。盡管當下的“牛郎織女”傳說已與傳說的原始模樣千差萬別,但如今的牛郎織女故事卻是更加定型牢固,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家喻戶曉。
二、“牛郎織女”傳說發展演變的誘因分析
(一)社會條件是傳說產生的前提基礎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牛郎織女”神話傳說的產生并非神仙點化而來,而是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首要的就是社會條件基礎。學者趙逵夫認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男耕女織’是我國經濟基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并且,廣大農民在種種剝削下把有地可耕,有絲可織,粗得溫飽視為生活的理想。在這種情況下,隔河相望的牽牛、織女便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配偶,想到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6]就是說,因在漫長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經濟體制基礎上形成了男子普遍以牽牛耕種為務、女子普遍以穿梭織布為務的社會場景,所以人們才能發揮聯想將天上的星星與人間的牛郎織女聯系到一起,并藉此反映人間普通大眾的生活狀態以及美好希冀。除了經濟基礎、社會普遍的生存狀態,家庭結構基礎也是產生牛郎織女傳說的重要社會基礎。學者鄭慧生認為,東漢以后有了大家庭制,才產生父母干預子女婚姻的問題,所以才產生了牛郎織女的故事。而先秦社會實行的是小家庭制。[7]也就是說到了歷史發展到東漢時期,因為社會普遍存在的大家庭制才導致父母干涉子女婚姻大事才有了必要和大形勢,人們由此聯想到牽牛、織女兩顆星未緊靠在一起是因織女的父母干預婚姻,不讓她和牛郎呆在一起。此類事情在漢初以前是難有發生的,因為缺乏當時社會的家庭結構基礎。由此可見,正是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封建王朝的政治基礎、男耕女織的社會基礎等當時社會條件基礎的共同作用才使得“牛郎織女”星宿名稱的發明、人物化的萌生、愛情傳說的衍生、悲歡離合的演變有了前提基礎。
(二)社會訴求是傳說演變的關鍵誘因
在“牛郎織女”傳說的萌芽、形成、發展、定型的各個階段,我們都能看到社會的訴求在誘導著傳說的發展演變。牛郎星、織女星由普通星座到擬人化而發展成男女情愛的情節,正是小農社會中遍布存在的“牛郎”們和“織女”們對男女戀情、家庭幸福、美好生活訴求的反映。“牛郎”作為千千萬普通勞苦農民的化身,希望在窮苦的生活中得到上天的眷顧,得到幸福的婚姻。而“織女”作為封建社會束縛下普通勞碌農村婦女的化身,希望能掙脫社會、家庭桎梏,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到了漢魏六朝時期,牛郎織女的故事在詩文中塑造成表達思情、愁情、怨情、愛情等多種情感意蘊的重要表現方式。學者張亞軍認為,這是與東漢以來文人社會地位的提高與游宦風氣的影響、文人求仕無望與思婦求夫無望心理相契合等因素促成的。[8]《迢迢牽牛星》一文所寫“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曹丕在《燕歌行》中所寫“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等等,均傳達出作者對牛郎織女情深意篤但又長期兩地分居、飽受相思之苦的深切同情,表達出作者期盼長相廝守、天長地久愛情的強烈訴求。學者趙景深對此深刻指出:“牛郎織女神話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農民終年受地主壓迫,娶不到妻子,只好在幻想中求得滿足,于是就產生了《牛郎》、《董永》、《田螺姑娘》這一類的神話。”[9]可見,正是千千萬萬窮苦農民對美好婚姻的強烈渴望,千千萬萬女子對自由追求美好愛情的強烈向往,千千萬萬文人對家人對妻子的強烈思念,才誘發了“牛郎織女”傳說的種種催人淚下的情節,才有了傳說的大發展、大豐富、大演變。
(三)民族心理是傳說定型的決定因素
“牛郎織女”傳說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豐富自身的內容,敘事主題也發生了多種演變。在主流敘事的背后,種種異文也有出現。然而,盡管“牛郎織女”傳說在歷史變遷中故事情節、敘事主題、情感色調上有所不同,甚至差異甚大,但站在今日回顧過往,“牛郎織女”傳說的異文并未廣泛傳播,可以說是被封塵在歷史的短暫瞬間,唯有主流故事情節、情感色調、中心思想得以廣為知曉、流傳至今、頗受歡迎。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下,留在人們頭腦中的“牛郎織女”傳說主要是一個美妙愛情故事:“牛郎”“織女”是千千萬萬普通群眾的化身,他們在平凡乃至苦難的生活中得到上天眷顧,掙脫社會的枷鎖,找到自己的幸福,最終有情人終成了眷屬。傳說主流情節、思想的穩固,正是因漢代以后漫長封建社會“百代皆襲秦制”導致的經濟、政治、社會基礎基本穩固所使然。在這樣的歷史、社會大背景下,人們形成了穩固的民族心理,有著共同的心理訴求。學者洪樹華認為“牛郎織女”傳說中人們這樣的人類心理,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原型意象中的民族性。[10]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對家庭和睦、婚姻幸福、美好愛情、社會公平等的強烈追求,使得“牛郎織女”傳說盡管衍生出種種版本,但仍保留主流敘事情節;盡管歷經朝代興衰更迭,但仍廣泛傳播流傳至今;盡管故事原型已漸行漸遠,但仍不妨礙人們濃厚的紀念熱情。
三、“牛郎織女”傳說演變對文化傳承發展的當代啟示
(一)樹立正確價值導向奠定文化傳承發展的生命力
在“牛郎織女”傳說發展演變的文學作品中,出現過各式各樣的異文。學者屈育德通過對江蘇泅陽和蘇州一帶流傳的異文進行研究,指出文學作品中“牛郎織女”傳說確實存在“夫妻反目,關系破裂’,的故事類型。故事中織女不滿牛郎、不滿下嫁人間,一心想逃離“苦海”,在牛郎追趕織女時,牛郎更是與織女大打出手。[11]學者洪淑苓通過對“牛郎織女”文學作品的研究,以河北束鹿的一則異文為例歸納了出“夫妻反目式”異文類型。[12]學者王雅清在《論<牛郎織女>故事主題的演變》一文中,更是總結出“中原地區牛郎織女故事異文”的六大特征。其主題敘事包括“牛郎盜得仙衣,織女是迫于無奈才與牛郎結合”“牛郎用牛索擲向織女,織女也用織布梭擲牛郎,兩人大打出手”等不合主流敘事的情節。[13]然而,這些不符合傳統文化、民族心理的非主流敘事文學作品,都沒能廣為流傳,更沒能流傳至今,不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歡迎。這樣的作品也就缺乏傳承發展的生命力。因而,在傳承發展文化成果時,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即是文化本身須樹立正確價值導向,須以正確價值觀念影響人、感化人、鼓舞人。
(二)適應社會公眾需求增強文化傳承發展的持久力
“牛郎織女”傳說中各種異文之所以不能廣泛傳播、長久流傳,就在于其所反映、倡導的價值觀念不符合社會大眾的心理需求。而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正是社會需求的催化、推動,才有了“牛郎”“織女”的擬人化,有了他們的情感故事,有了他們的終成眷屬。如學者趙逵夫所言,當“牽牛”、“織女”作為星名被越來越普遍地接受,它們本來的含義,便越來越淡漠。[14]而學者劉宗迪通過對七夕故事的考究認為,“七夕原本完全是一個農時節日、無關乎愛情與婚姻、更非什么中國的情人節”,因而不必隆重紀念。[15]然而事實上,不管七夕是否為中國情人節,不管“牛郎織女”傳說的本來面目是否有關愛情,這并不影響社會大眾對“牛郎織女”傳說的歡迎與向往,也不影響人們對七夕節的重視與紀念。因為,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才是社會事物發展的源頭驅動力。因此,在文化的傳承發展中,須注意一個關鍵問題,即讓文化的價值主張、故事情節、傳播方式等適應社會大眾的心理需求,并與時俱進適應社會大眾心理需求的變化。
(三)借助多樣表達形式擴大文化傳承發展的影響力
“牛郎織女”傳說流傳至今家喻戶曉,有其深厚社會基礎、正確價值主張、適應社會需求的綜合推動作用。在此之外,還有一重要因素,即“牛郎織女”傳說豐富的表達形式。有傳說、詩歌、詞章、小說,還有說唱、戲劇,此外還有“七夕”這樣十分重要的節日。正是“牛郎織女”傳說與“七夕”節日的結合,極大地增強了傳說的生命力、持久力。使得一年一度的“七夕”紀念日成為一年一度的傳說溫習日。學者劉宗迪認為:“正是憑借著這種年復一年的乞巧儀式,牛郎織女的故事才代代相傳,流傳人間。”[16]因而,在文化的傳承發展中,需高度重視文化的傳播渠道、傳播方式,借助人們喜聞樂見、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將文化傳遍四面八方,傳進千家萬戶。
文化的傳承發展,唯有樹立正確價值導向才能奠定生命力,只有適應社會公眾需求才能增強持久力,需要借助多樣表達形式才能擴大影響力。文化的傳承發展如此,思想宣傳教育工作同樣如此。當前,我國正大力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中共十九大精神及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等等,同樣需要樹立正確價值導向、適應社會公眾需求、借助多樣表達形式,以奠定生命力,增強持久力,擴大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