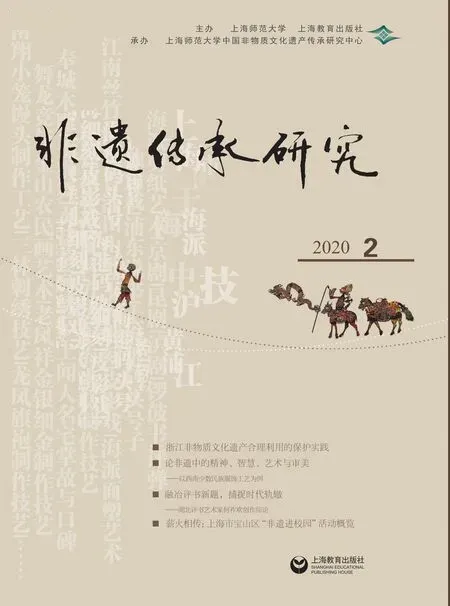我的童謠記憶
薛理勇
《辭海》于“兒歌”是這樣解釋的:
兒歌,兒童文學的一種。一般與童謠合稱為兒童歌謠。以適合兒童接受、傳唱為特點,大多數表現兒童對社會生活現象的觀點。
這應該是該詞條撰稿者對兒歌和童謠的理解,似乎認為,兒歌、童謠是一種成年人、文學家為兒童創作的適宜于兒童接受和傳唱的兒童文學作品,好像兒童傳唱兒歌、童謠,也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和應盡的義務。
“兒歌”對應的英文是“nursery rhyme”,直譯的話就是“保姆哼唱的歌謠”,比較常用的譯名就是“搖籃曲”。《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于“兒歌”的釋文是:
兒歌(nursery rhyme) 講給或唱給小孩聽的詩歌。自古就有兒歌流傳,新歌詞更不斷出 現……
西方人則以為,兒歌、童謠就是大人講給或唱給小孩聽的詩歌,而中國人以為,兒歌、童謠是大人針對兒童創作的兒童文學,使兒歌、童謠蒙上了政治色彩,給兒童增加了社會責任。我已經記不清以前老師教我們的兒歌、童謠,但是,我還記得不少自己曾經誦唱過的兒歌、童謠。兒歌是大人講給或唱給兒童聽的詩歌,童謠則是流傳于兒童之間的歌謠,可以有曲調,也可以是順口溜,不見得有人作詞譜曲,它瞬間出現、流傳,也不知道何時消失。童言無忌,一般童謠的詞面容易理解,但是,一些童謠的詞義又不易理解。
我記憶比較清晰的兒歌、童謠不多,孩提時,不會去認真理解童謠的詞義,年齡大了,才開始品味童謠的意義。以前上海兒童間傳唱一首“落雨了,打烊了,小巴辣子開會了”的兒歌。“打烊”是上海方言,一般指商店的營業時間已過,停止營業,或商店因盤賬等原因暫停營業,也可以比喻暫時放下手里的活;“小巴辣子”則是小孩、小人物的意思。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工廠、商店上班的職工天天要開所謂的班組會、班前會,閑在家里的家庭主婦也經常會被居委會召集開各種各樣的會,只有小孩無會可開,在馬路上玩,一旦落陣頭雨,上海的弄堂大多有所謂的“過街樓”,于是,小孩為避雨而集中躲進了過街樓,猶如大人們集中在一起開會。在我的記憶中,一開始此童謠往往是在小孩躲進過街樓時唱的,后來成了順口溜,不分場合和時間,隨時可以誦唱。
還有一首童謠“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有傘,我有大頭”,一般用蘇北話誦唱。從詞面上理解,傘是遮雨用的,這個小孩的頭特別大,可以用特別大的頭遮雨。
20 世紀50 年代,上海有不少“羅宋人”,“羅宋”是英語Russian 的“洋涇浜語”,就是“俄羅斯人”。居住在滬東的“羅宋人”的日子不好過,他們身著破舊的西裝,上海人稱他們為“羅宋癟三”,許多“羅宋癟三”走街串巷,以磨刀為生,不過,他們磨刀的方法與中國人不一樣,是推一輛小車,小車上安裝有磨刀使用的轉輪,用腳踏板驅動轉輪,刀擱在轉輪上磨,濺出色彩斑斕的火星,煞是好看。于是,只要有“削刀磨剪刀”(“削刀磨剪刀”是上海磨刀人的吆喝聲,于是,上海人把磨刀人叫作“削刀磨剪刀”)的“羅宋人”經過,一定會有許多圍觀的小孩。我居住的弄堂,每天會有一個“羅宋人”牽著一匹白馬,馬身上蓋著一塊樣子像被單的大白布,這是賣馬奶的,他們有固定的客戶,所以不吆喝,倒是馬的頭頸上掛一個鈴鐺,隨著馬的走動而晃動,發出“叮鈴、叮鈴”的鈴鐺聲。這時,一定會有一群小孩尾隨其后一邊走一邊唱:“叮鈴叮鈴馬來了。”大概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的“羅宋人”分批回國,賣馬奶的“羅宋人”走了,但是,“叮鈴叮鈴馬來了”成為兒歌、童謠,在小孩中一直傳唱到70 年代,但是,人們已經不知道這“叮鈴叮鈴馬來了”是什么意思了。
以前,上海人睡的床,除了木板床外,許多家庭使用棕繃床或藤繃床,時間長了,棕繃床的棕繩會松弛,藤繃的藤條會斷裂,于是,會有修棕繃人來修棕繃、藤繃。他們走街串巷,大聲吆喝:“阿有壞格棕繃藤繃修勿。”一旦接到生意,就會向居民借幾條凳子,把棕繃或藤繃擱置在凳子上,開始工作。這時,一定會有許多小孩在遠處對修棕繃的老頭喊道:“老頭浜,修棕繃,摸摸卵子硬邦邦”。“老頭浜”就是老頭,是上海人對老人不禮貌的稱呼,不知道這個“bang”該怎么寫,就寫作“浜”吧。后來才弄明白,修棕繃必須把棕繩繃得緊緊的,使棕繃顯得硬扎,童謠原來應該是:“老頭浜,修棕繃,摸摸繩子硬邦邦”,后來,“繩子”訛為“卵子”,童言無忌,這是風俗,不是下流。
幾十年前,中國的城鄉差異十分大,上海這樣的特大型城市與一般的城市和農村的差異更大,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流行這樣的一首民謠或兒歌:
鄉下姑娘要學上海樣,
學來學去學不像,
剛剛學到三分像,
上海姑娘又變樣。
由于城鄉差異嚴重,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的現象十分普遍,也十分嚴重。實際上,外國的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的現象比中國有過之無不及。記得20 世紀90 年代,我認識一位在同濟大學攻讀博士的日本人,一次,我倆在一家飯店用餐,飯店里進來一群日本老人,嘰里呱啦講個不停,這位日本博士生感覺這些日本老人的舉止行為有失日本人的風度,就不屑一顧地對我說:“這些是日本的鄉下人。”我有不少外國朋友,他們告訴我,魯尼是英國的足球明宿,但是,魯尼操一口濃郁的利物浦口音,英國人叫他“鄉下人”。我童年的時候,上海流傳這樣的童謠:
鄉下人,到上海,
上海閑話講弗來,
mi-xi mi-xi 吃夜飯(也講作“吃咸菜”)。
誰也不知道,這“mi-xi mi-xi”是什么意思,該怎么寫,只能根據讀音寫作“米西米西”,有了文字作固定,這“米西米西”反而更難理解了。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拍攝了不少如《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地雷戰》《地道戰》等以中國抗日戰爭為題材的電影,電影里的日本鬼子會學講一些中國話,最多的就是“米西米西地有”,就是“吃的東西有沒有”的意思。于是,不少人以為“米西米西”是日本話“吃”或“可以吃的東西”的意思。我也是這樣理解的,后來詢問日本朋友,他們也不知道日語詞匯中有沒有“米西米西”這個詞,或許“米西米西”根本就不是日文。那么,這個“米西米西”到底怎么來的呢?令人費解。
“mi-xi”應該是“米粞”或“麥粞”,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食品詞典》是這樣解釋的:
米粞(grist) 小于小碎米的碎米粒。多附有胚乳。于碾米過程中混雜在米糠中排出。可影響米糠提油時的出油率。將其分出后可供釀酒,制飴糖等,也作飼料用。
麥粞(wheat grist) 亦稱“小碎米”。制粉廠清理過程中分出來的碎麥。可混有小的野草種子和一定量的小麥胚乳和麩皮。是很好的精飼料,也可作生產酒精的原料。
《食品詞典》介紹的是現代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米粞和麥粞。在農耕年代,稻谷、麥子的脫粒大多是農家自己完成的,出米和出粉率低,米糠和麩皮中含的米粞、麥粞量高,富裕人家可以作為飼養牲畜、家禽的飼料,而貧苦人家往往把它作為填飽肚皮的口糧。明朝《錦箋記·爭館》:“做人切莫做余姚,到處人呼‘麥粞包’。”浙江的余姚依山傍海,土質貧瘠,人多地少,口糧嚴重短缺,所謂的“麥粞包”就是依靠麥粞充饑的窮苦人家。民國胡祖德《滬諺外編·張鳳山賣布送人情》:“無人搶口份,娘子吃點老麥粞飯已安寧。”《中國歌謠資料·日本鬼和美國鬼》:“來了矮的日本鬼,家家戶戶吃麥粞。”如此看來,所謂的“米西米西吃夜飯”或“米西米西吃咸菜”,應該是“麥粞麥粞吃夜飯”或“麥粞麥粞吃咸菜”,就是初來上海的“鄉下人”日子不好過,只能以麥粞充當口糧,成為被人看不起的“麥粞 包”。
以前,上海地區少量種植元麥和大麥,這種麥子很難磨成粉,只能粉碎成小的顆粒,單獨煮食難以下口,可以把它混入大米煮成“麥粞飯”或“麥粞粥”,這種小顆粒的麥粞也叫作“麥頭”,所以,這種飯也叫作“麥頭飯”“麥頭粥”。老友諸半農著《上海西南方言詞典》中的解釋為:“麥頭。大麥、元麥磨成的粗粒,糧食不夠吃時常加在粥、飯里燒來吃。”“麥頭飯。麥頭加米燒成的飯,如:‘飯老是不夠吃,貧寒人家辦法多,老早就懂得以粗代精,忙時吃干,閑時吃稀,常吃麥頭飯、麥頭粥’。”當年,人們為了解決口糧不夠才吃麥頭飯、麥頭粥,而如今,麥頭飯、麥頭粥成了許多人家的健康食品、保健食品。
上海是移民城市,寧波籍占了很大的比例,寧波方言對上海話有較大的影響,寧波人把“莫”講作“mao”,如“不要講了”講作“mao話了”,“不要動它”講作“mao 去動其”,“不要激動”講作“mao 激動”等。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流行一句“mao 激動,激動要進長方形的木桶”的童謠,童謠似乎沒有什么意義,大概就是告誡對方不要激動,太激動不利于健康,猶如方言所謂的“激動得要死”。我童年的時候,一些小孩還會一路奔跑一路高歌“mao激動,激動要進長方形的木桶”。后來,突然有人說,“mao 激動”的寧波話發聲與當代的偉人名字相近,“長方形的木桶”則是棺材,這童謠瞬間就變成了詛咒偉人的咒語,反革命口號,嚇得家長們魂飛魄散,立即關照自己的小孩,再也不許小孩念此童謠了。這是我的親歷親聞,記憶猶新。
20 世紀60 年代初,中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的特殊年代,物資匱乏,糧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嚴重供應不足,上海人開始體驗食不果腹的苦痛,社會秩序混亂,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當時失業青年美其名曰“社會青年”,他們等同于游蕩于社會的“不良青年”,他們中行為稍有越軌者,女青年被叫作“三三”,后來又稱為“阿三”“拉三”等;男青年被叫作“木良”,后來又被叫作“木殼子”“木殼”。“三三”“木良”經常會干一些偷雞摸狗、見不得光的糗事,于是上海出現了“三三木良,摸到天亮”之類的童謠,小孩們也懵懵懂懂地知道該謠詞的意義,也許謠詞有點下流,也有點趣味,如今五六十歲以上的人應該記憶猶新。
當時,上海人把公安局叫作“廟”,上海市公安局就是“市廟”,虹口公安分局就是“虹廟”;派出所稱之為“老派里”,公安局的警察稱之為“條子”,派出所的民警則叫作“條里”;上海市在安徽白茅嶺建有頗具規模的監獄和“勞改農場”,于是,監獄和勞改農場被叫作“山”“山浪”“山浪向”(滬語把“上”“上面”講作“浪”,如“床上”為“床浪”,“田埂上”為“田埂浪”,以前上海有許多帶“浪”字的村落名稱或其他地名,基本上就是來源于“在某某地方的上面”);所有的人犯,不分男女,進了“廟”里,一律剃光頭,于是,人犯就被叫作“和尚”。一次,一位與我同年的小朋友因不滿“條里”的蠻橫,當場與“條里”發生爭吵,于是被“條里”關進了“老派里”,并馬上被關進了“虹廟”,吃了三天“格子飯”(“格子”就是“飯格子”,是一種裝飯菜的盒子,監獄里使用飯格子裝飯菜,于是,坐牢叫做“吃格子飯”),釋放后學會了“廟”里傳唱的歌,大意是:
小呀么小和尚,頭光光。
告別父母,遠離家鄉,上山去燒香。
……
歌詞通俗易懂,曲調平和流暢,朗朗上口,很快就變成了廣為流傳的兒歌,許多人會唱會哼,當時誰也不知道此歌曲是誰作詞譜曲,訴說的是什么事情。想不到20 年后的80 年代,該歌曲被重新填詞,在電視臺的聯歡會上播出,歌詞改為:
小呀么小和尚,袈裟披身上,
小木魚敲得篤篤響,念經么當和尚。
……
此歌曲當作新創作的兒歌,流傳更廣、更遠。
兒歌是童趣,是每個人童年生活的樂趣,也是成年后美好的記憶。如今,上海的家庭多獨生子女,家庭居住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小孩除了讀書做作業,難得會有與鄰家小孩結伴游玩的機會。我真的不知道,現在的小朋友中是否還有屬于自己的兒歌童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