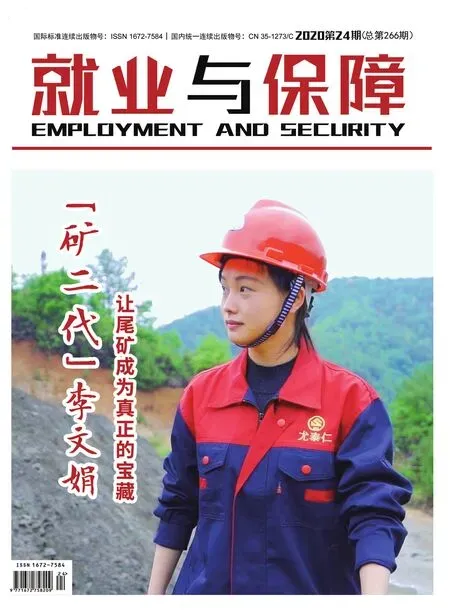海外反就業歧視舉證責任分配制度的借鑒及啟示
文/沈鵬飛 徐露 黃易
舉證是訴訟制度的核心內容,舉證責任配置與否對就業歧視訴訟成敗的意義自不待言。故而僅以一般舉證規則作為就業歧視案件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基本無法滿足實踐中案件審理的需要,也無法對于勞動者的權益進行公正的保護。為此,根據筆者研究提出海外反就業歧視舉證責任分配制度的借鑒及啟示,為我國就業歧視舉證責任分配提供參考[1]。
一、我國就業歧視法律的舉證責任分配現狀
(一)就業歧視案件適用一般舉證規則
由于我國將就業歧視案件視作民事爭議的一種,故在審理就業歧視案件中也普遍適用《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舉證規則[2]。但就業歧視案件與一般民事爭議不同,就業歧視案件是勞動者和企業之間的對抗,兩方當事人在地位上具有不平等性,在已經建立勞動關系的就業歧視糾紛中,當事人之間還具有從屬性[3]。由于以上特征導致勞動者在訴訟實踐中會遭遇各種各樣的阻礙。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勞動者難以提供充分的證據來佐證自己主張的事實,即勞動者存在舉證困難。
(二)就業歧視案件難以適用舉證責任倒置
我國現有法律法規中關于就業歧視案件可以適用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條,根據該條規定,在就業歧視案件當事人之間的舉證責任不能確定時,法官可以根據公平和誠實信用的原則,結合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能力等因素,綜合判斷以確定具體的舉證責任由誰承擔。此規定雖然給就業歧視案件提供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可能,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較難適用。這一規定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但規定內容過于寬泛,缺乏統一的執行標準,使法官有可能濫用職權、牟取私利,不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關于海外就業歧視案件的舉證規則
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賦予了法官較大的證據調查的職權,因此與之相對應的是較高的證明標準。而英美法系國家由當事人主導訴訟程序的進行,采取“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兩種法系中對于證明責任的分配都有優勢之處。歐美日等國家擁有較完善的反歧視立法系統,而有效的舉證規則保障了反歧視法在司法實踐中的順利運行,也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文章將分別介紹部分典型國家的舉證模式。
(一)美國的“三階段舉證法”
美國根據歧視對象的不同,將就業歧視分為個體差別待遇歧視(直接歧視)和差別影響歧視(間接歧視)。兩種歧視的舉證責任分配模式雖有細微差別,但總體而言均要遵循舉證責任原則——“三階段舉證法”。“三階段舉證法”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麥克唐奈案(Mcdonnell Douglas Corp .V. Green)中所確立起來的舉證模式。關于“三階段舉證法”的內容如下:
第一步,由雇員提供受到雇主歧視的初步證據,證明其符合雇主提出的招聘要求,但仍未被雇用,從而得出遭受歧視的合理推斷。如在1979年的判例中,雇員們認為,雇主排除了因吸毒而接受治療的求職者,這對西裔和非裔求職者是一種歧視。但未能證明這兩個群體中存在戒毒治療的比例特別高,因此不能證明這一規定構成種族歧視。第二步,由雇員完成初步證明后,舉證責任并轉移給雇主。雇主為了駁斥雇員提出的合理歧視推斷,其必須提供所謂的“中間階段證據”,證明自己拒絕雇傭不是基于歧視,而是基于善意職業資格。在雇主和雇員皆完成第二階段的舉證后,倘若法官依舊覺得案件有爭議,則案件將進入實質審判階段。最后,由雇員重新承擔舉證責任。雇員須證明雇主提出的理由事實上是掩蓋其歧視的借口,雇員也可直接證明雇主實際上因為歧視意圖的影響而拒絕雇傭原告。當然,這并非意味著雇員必須證明雇主拒絕雇傭原告帶有歧視性的動機。美國《民權法》第七條明確規定禁止任何雇傭中帶有歧視性動機,同時也禁止其結果,因此倘若求職者不能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工資及晉升等平等待遇是因為某些與個人能力無關的因素,那么這些與個人能力無關的因素仍然構成歧視。
(二)歐盟的“抗辯”舉證法
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歐盟發展出了自己的反歧視法。《歐盟(歐共體)條約》作為歐盟及前身歐共體的最高法律,其關于反就業歧視原則的規定對各成員國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考慮到雇員舉證難問題,歐盟的反就業歧視法在舉證的初步階段維護作為弱勢一方雇員的利益。故而法院對雙方舉證責任的分配采取以下方式:如果可以從雇主的行為中推斷出存在就業歧視,則應由被告人進行舉證,從而推翻上述推斷,證明自己的行為確實是因為其他原因。具體而言,依據歐盟的反歧視指令,只有當被告能證明其作出的規定、標準或行為是為了實現某合法目的之適當和必須方式,才可作為所謂抗辯事由。
(三)荷蘭的舉證責任倒置法
荷蘭在反就業歧視的舉證責任分配上采取的就是舉證責任倒置,且保護的對象更廣泛,包括就業歧視中的員工也包括被歧視的消費者,但結果表明荷蘭采取的該項舉證責任原則極大推動了雇主方在雇員招聘錄取方面的程序改革。
在就業歧視案件中作為原告方的雇員,相對于雇主來說天然處于劣勢地位,因此,歐盟于1997年發布了《性別歧視案例中舉證責任的指令》,其中規定舉證責任倒置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雖然或許加重了雇主的舉證責任,但基于利益和公平衡量,這種舉證責任分配方式更好地維護了相對而言處于劣勢方的雇員利益。其后在《荷蘭平等待遇法》第十條對此作出了回應,荷蘭法院及平等委員會在處理歧視案件中秉持這一原則,將保護的重心向弱勢方傾斜。其具體做法是,在歧視案件的投訴中倘若雇主無法證明其實施的行為并非歧視,或者其所采取的政策和標準不透明、不明確,則傾向認定雇主所實施的行為構成歧視。
(四)日本重點領域的舉證責任倒置法
日本1985年的《雇傭機會平等法》以及1997年修正案均未對舉證責任進行規定,在2006年修正案中也沒有進行明確規定,但是在間接歧視、禁止解雇懷孕及生育后未滿一年的女性勞動者等領域,日本實質上已經確定了舉證責任倒置。根據規定在女性勞動者懷孕和產后一年內被解雇的,雇主若無法提供證據證明解雇行為與懷孕、產假等行政法規禁止的事由無關,辭退無效。在這種情況下,只要雇員證明解雇行為發生在其懷孕和產后一年內,則接下來的舉證責任將由雇主承擔。除此之外并無其他關于特殊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
三、我國就業歧視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建議
對海外的就業歧視訴訟舉證分配責任進行研究,理論意義上在于對于我國的就業歧視訴訟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提出自己的經驗和思路。根據對以上舉證責任分配制度的探究,對我國的就業歧視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提出自己的建議。
(一)建立完善的反就業歧視法律制度
關于就業歧視我國立法上尚未有明確的定義,但是一些國際公約和理論界的一些學者早已給出了關于就業歧視的定義。如有的學者認為就業歧視是指用人單位、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基于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對勞動者進行差別對待,損害其均等就業機會或獲得平等待遇的行為。在此基礎上,應當效仿美國、日本等國家,將就業歧視分為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在直接歧視中,原告應當為其訴訟請求進行舉證證明,被告應當為其沒有實施歧視進行舉證證明;在間接歧視中,原告應當首先提供間接證據,證明被告實施了法律禁止的歧視行為。此時,如果法院認為原告的證明不成立,被告不需要提供證據,本案審理到此為止;如果原告的證據成立,被告需要證明該決定是出于合法的商業目的所作出,其后由原告證明被告的理由是為了擺脫自己實施了歧視行為的借口,若原告無法證明則需承擔不能舉證之后果。
(二)為就業歧視案件設置專門的舉證責任分配制度
招工階段的就業歧視案件畢竟沒有建立勞動關系,在很多程序方面均具有銜接上的不適應性。例如,勞動爭議糾紛適用仲裁前置,而招工階段的就業歧視由于沒有建立勞動關系,在制度上的配置無法適用勞動爭議訴訟。同時,借鑒海外對于就業歧視案件的解決思路,為就業歧視糾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分配進行專門規定。無論是借鑒荷蘭、參照某些特殊的侵權責任的完全舉證責任倒置,還是借鑒美國的“三階段舉證法”,從案件當事人地位出發,結合特殊案情,從更有利于保護受歧視勞動者的權益出發,確立結合中國國情、有可操作性的舉證責任分配制度。
(三)確立反就業歧視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標準
第一,主張權利或者法律關系的一方應當對其主張的法律要件承擔舉證責任。例如,在直接歧視案件中,勞動者主張用人單位實施了歧視行為,應當由勞動者對該行為屬于歧視行為承擔舉證責任。第二,主張權利或者法律關系變更或者消滅的一方應當對所主張的法律要件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否認變更或者消滅的另一方應當承擔證明責任。在間接歧視案件中,勞動者應當首先提供證據,證明用人單位實施了法律禁止的歧視行為,用人單位應當證明其行為符合商業目的,即被告人應當提供對該權利的發生阻礙的事實證據。
綜上,我國的一般舉證規則作為就業歧視案件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基本無法滿足實踐中案件審理的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建立新的舉證責任分配標準。可以借鑒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確定我國就業歧視舉證責任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