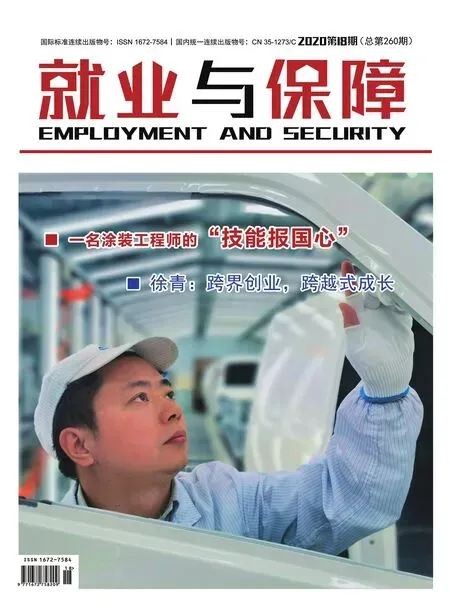對“互聯網+”時代服務業新業態中勞動關系的分析
文/魏靖華
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以及智能電子設備的不斷普及,將網絡深入融合到社會生活中,并培養出全新的生活理念和習慣。傳統服務業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依托互聯網平臺衍生出網約車、網約家政、外賣等多種服務新業態,并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所接受和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出臺之初并未涉及以互聯網平臺為基礎的新勞動關系和用工形式,隨著勞動糾紛案件的不斷涌現,服務新業態中勞動關系認定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
一、服務新業態中勞動關系的變化
基于“互聯網+”的服務新業態催生了大量非典型勞動用工形式,如送餐員、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移動APP成為商家向消費者提供各類服務產品的主要渠道之一,將有形的辦公場所轉化為無形的互聯網平臺,導致了有關互聯網平臺與從業者間勞動關系認定的爭議。從業者從網絡平臺中獲取從業信息及企業業務信息,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常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隸屬關系。例如,2017年發生的賀某與上海某文化有限公司勞動合同糾紛案,雙方于2015年12月7日簽訂《熊貓直播主播獨家合作協議》(以下簡稱“《協議》”),并做出如下約定:第一,賀某同意與平臺合作,并將該平臺作為互聯網唯一直播平臺;第二,合作期限為3年,賀某向平臺發布直播節目獲取虛擬道具,并依照平臺既定規則兌換收益;第三,合同期內,賀某直播頻次不得低于15天/月,每日連續直播時長0.5小時以上,且平均觀看人數不低于3000人,若當月累積直播時長大于或等于80小時,可獲得收益7000元人民幣。
該案一審認為,依照《協議》簽訂時的規定,賀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該行業應具備一定認識,且《協議》對雙方均有約束作用。《協議》雖對賀某直播時間做出詳細說明,但其仍具備直播時間和地點的靈活安排權,其勞動力并不受公司的約束,雙方間未達到勞動關系的要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1]。二審認為,賀某與公司間不存在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協議》雖對雙方的權利義務作出說明,但從賀某實際工作情況上看,其工作時間、地點、內容均帶有網絡直播的特殊性,二者之間關系松散。另外,二者利益分配的方式也區別于傳統的勞動關系,難以確定二者間存在法律意義上的勞動關系,維持原判。
在上述案件中可以看出,在互聯網新平臺的出現背景下,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
二、“互聯網+”時代勞動關系認定困境
法律相較于時代發展存在一定滯后性,使“互聯網+” 背景下服務新業態中勞動關系的認定面臨諸多困難,將勞動關系的認定困境總結如下。
(一)勞動者依附性判斷
服務新業態中互聯網平臺與勞務提供人員之間的合作方式非常多樣,用工方式多元化使勞務提供人員與平臺中并無典型的依附性關系。如前文案例所述,勞動者在提供服務時,有充足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依照自身意愿及需求,自主決定工作場所、時間和方式,此處的勞動者并不受企業的完全支配,二者間無明顯的依附性或從屬性關系,當出現勞動關系糾紛后,雙方勞動關系認定比較困難。
(二)經濟從屬性評估
服務新業態中勞動者的從業方式包括三種:一是分配型,如滴滴打車平臺的派單形式;二是競爭型,如餓了么、美團外賣平臺的自主搶單;三是混合型,即分配型和競爭型方式并存,勞動者可依照自身屬性及業務特點靈活選擇從業方式。而在勞動報酬的獲取上,也不同于以往企業向員工的直接工資支付,可被分為消費者——平臺——勞動者、消費者——勞動者兩種模式[2]。
從新業態中從業方式及報酬獲取方法的多樣性能夠看出,勞動者雖然能夠從互聯網平臺獲取一部分固定報酬、獎金或福利,但其報酬中仍有較大的非固定比例,即勞動者在完成業務后,依照既定標準獲取勞動報酬,或者直接從消費者處領取報酬。由此看來,新業態中互聯網平臺與勞動者之間并不存在直接、明確的經濟從屬關系。
(三)協議約定的真實合意
在傳統勞動關系中,勞動合同在雙方均認可勞動關系的基礎上簽訂。在前文案例中,賀某與公司簽訂《協議》對雙方權益義務進行劃分,忽略《協議》在形式上與勞動合同的區別,其在簽訂時,并沒有對雙方關系是否為勞動關系做出詳細說明。在其他勞動關系仲裁案件中,還出現過直接約定為非勞動關系的現象。雙方在簽訂協議之時的真實合意并不同于傳統勞動合同。因此,在勞動關系認定時,很難把協議視為勞動合同的約定作為仲裁裁決的依據。
(四)業務從屬性評估
在互聯網平臺中,勞動者共享從業信息,然而這部分信息是否對應平臺的經營業務很難判定。例如,不少平臺公司僅作為業務信息共享的中介方,單純向勞動者提供業務信息,此時業務信息則不來自平臺的經營業務。
三、“互聯網+”時代勞動關系認定建議
有關勞動關系認定問題的最終解決還需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完成。現階段,針對勞動關系認定困境,提出相應處理措施,以合理解決法律空當期所發生的勞動關系糾紛問題。為此,本文主要從勞動仲裁優化的角度出發,對勞動關系認定提出幾點建議。
(一)補充制定勞動關系認定標準
基于現有《勞動法》及有關法律法規的內容,互聯網平臺與勞動者間的勞動關系是否成立無法做出一刀切式的判斷,僅僅將平臺與勞動者間的關系認定為非典型的勞動關系,參考現有典型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對非典型勞動關系認定法律標準做補充說明。
1.人格從屬性。勞動者需充分遵守平臺業務流程、規則以及市場運行規則。互聯網平臺有權采用消費者評分的方式對勞動者的行為進行約束,且評價結果與勞動者報酬獲取相關;同一時段、同一工種,勞動者僅可通過同一互聯網平臺提供業務服務。
2.經濟從屬性。依照業務訂單完成情況進行報酬支付;消費者有權直接向勞動者支付報酬,前提要依照互聯網平臺所要求的方式和標準。平臺業務報酬必須為勞動者唯一或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平臺保留單方調整、制定業務價格的權利。
3.組織從屬性。勞動者所提供的服務構成互聯網平臺的主營業務體系;勞動者可使用平臺名義,向消費者市場提供服務業務。
(二)引入傳統勞動關系認定要素
勞動時長、數量、收入等均為認定傳統勞動關系的基本要素,在“互聯網+”所帶來的共享經濟模式中,以上要素可被用于非典型勞動關系的認定中。主要是由于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完成的業務量及其獲取的業務報酬,在較大程度上說明了勞動者與互聯網平臺之間用工關系的密切程度,并體現二者之間從屬性的深淺。
以網約車平臺為例。有數據表明,網約司機平均每月訂單完成量在400~450單;在工作時長方面,50.67%的司機日工作時長≤2小時,19.66%的司機工作時長在4~6小時,另外8.74%的司機日工作時長達到8小時;在業務報酬方面,23.54%的司機平臺業務收入≤3000元/月,39.69%的司機平臺業務收入3000~5000元/月,20.38%的司機月收入達到5000~7000元[3]。以上數據足以說明,盡管互聯網平臺中勞動者的工作時間相對靈活,但仍有較大比例的勞動者以平臺業務為全職工作,且接單量越多、工作時間越長、業務收入越高,證明勞動者與平臺間的從屬性越密切,二者間關系也更加接近勞動關系。在勞動仲裁案中,即可參考如上要素,客觀評估勞動者與平臺間的密切程度,合理保護弱勢勞動者基本權益。
(三)關注協議約定制定真實合意
平臺與勞動者間在簽訂協議時,因勞動關系界定不明確,無法將其等同于勞動合同。在勞動仲裁中,可將關注點從合同形式轉移至雙方真實合意上,從客觀事實角度判定。
真實合意的判別標準包括合同名稱、具體條款及勞動事實,三者之間存在合同名稱→具體條款→勞動事實的遞進關系。如當勞動事實與合同名稱或具體條款發生合意沖突時,依照勞動事實進行勞動仲裁。
(四)強調信息的新生產要素屬性
傳統勞動關系中生產要素包括勞動、技術、機器、管理、資金、原材料等。其中,勞動者主要提供體力、技術、管理等,而更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則由企業掌握。因此,勞動者必須依照企業給出的規定和要求工作才能獲取相應的勞動報酬,主要和次要生產要素的分配決定了企業與勞動者間的支配與被支配地位。然而,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共享經濟時代,原本生產要素結構早已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知識成為服務新業態中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即主要生產要素。在平臺與勞動者之間,平臺作為消費者信息的采集者,對該生產要素掌握絕對的支配權,甚至由勞動者自由選擇工作地點、時間、方式等,是在該主要生產要素支配下的自由,并非絕對。因此,信息的主要要素屬性是平臺與勞動者間從屬性的強化條件,能夠被勞動仲裁中勞動關系的認定所參考。
四、結語
隨著“互聯網+”服務的不斷升級,互聯網平臺信息共享中介的屬性將進一步突出,平臺與勞動者間雇傭關系也將隨之弱化。通過補充制定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引入傳統勞動關系認定要素、關注協議約定制定真實合意、強調信息的新生產要素屬性等措施,有效規避勞動關系認定困境,合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