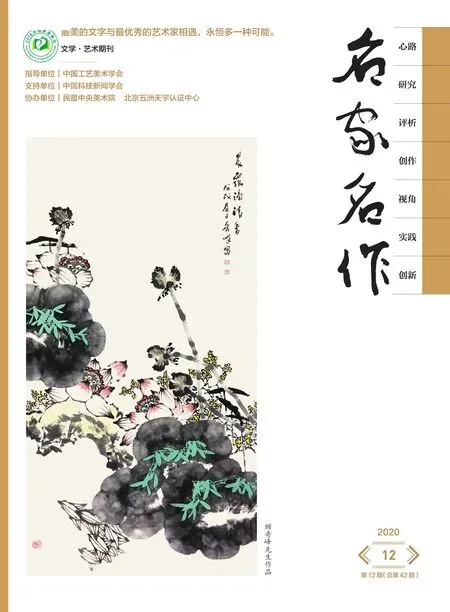糖罐子
時培京
父親會不會由糖罐想起那個貧瘠的晚上(從這以后豐裕而厚延),那糖罐和一切美好的過往將來存貯于父子間密布的空間——我們的小宇宙。父親是不會記起的。他有七個子女(大女兒早殤),每一個孩子從小到大有多少哭哭嚷嚷的事情。今年父親節,他無須想了,只有我們想他。
那是平原上的普通村莊,土墻屋里的蚊帳,我發燒了,白天毒熱的太陽闖到蚊帳睡覺,以至于那天的夏天差不多燒煳了天空,還好腦膜炎這類的病癥沒有落下來。以熱攻熱,開水灌不進去,嘴白,像魚倒沫,像坑水拱開石灰;沒味,舌苔蒙蔽心智所以不喝,開水是治療村里人最有效最省錢的方法——不停地喝下去死不了人,他們為了多補充水不去醫療室;小孩們叫父母抱去,男孩總是撐不過女孩子,同樣發燒四十度,男孩很有可能抽搐,甚至燒壞腦子,男憨子比女憨子多即是可怕的后果。
父親常說:小三孩要是女孩該多好,省事多了,錢多少找個婆家都好打發,到老了有酒喝。
父親叫他學生批了條子買奶粉,滿袋顆粒——神丹妙藥,一湯匙挖走足夠活上百十年,在我的眼里它是孫猴子賜予的。一回一湯匙,一大碗開水,營養夠了,味道有了,聞到就不鬧。糖是從濟寧批來的(不是批發),懶得動異于平常——一定不如適這時候腚幫子欠針管子攮了,母親用額頭抵住我的額頭:
“不發燒咦,扭扭耳朵,尿泡尿,俺的小三孩就好了。”
在高高的櫥柜頂上一個大白塑料罐子,搬了小椅子騎上大椅子,馬扎子騎上小椅子,這樣不敢竄蹦了,往高處伸手爭取,和父親講的童話故事里的饞嘴狐貍一樣:
“沒糖了。不喝也好,蟲子不咬牙了。”
什么事情都有貪得有厭時。一種食物,香蕉或者白面饅頭由于家里生活水平,一心工作后賺錢了吃夠吃撐。
娘的懷抱是火爐,化不開作了鐵勺子的鐵塊,我掙呀嚎呀——像是已經長大吃了二肚子干玉米粒而不是糖,結果消化不良,鼓脹難安,像是羊羔子偷吃干玉米:
“熱死了,熱死了,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娘哭,涼風陰了,要受癥的。死死裹住,她唯恐我不情愿在這個世界上陪著她停留,于是聽懂了我的心跳。
“沒糖了。”父親說。
“盡哄人玩,大白天還有的。”父親從醫院回家靜養的那天路上,在南賜宴村他要開水,我說真空了,他說:“你哄我玩的,叫你大當小狗哄的。”幾天之后,他去世了。
“你看看。”父親舉起糖罐子,洋油燈垂直向上的糖罐子是黑夜里劈山救母用的寶蓮燈,用湯匙做了挖的動作,挖不上來一絲燈火。
“倒水涮刷罐子我喝。”
多少年后父親說我方法多,變通快。看來是發燒帶來的,生病是一件不可避免的喜事。罐子內壁上有剩下的糖粒子,敲敲轉轉紛紛下來。你不哭了,不發燒了。
糖水真的能治發燒么。不騙人,也許是缺失營養,這不是鄉村魔幻。
娘記不得了。饅頭熘熘給她。“小三孩給時尚一個。她喜歡吃。”時尚是我的兒子,我是娘的兒子,她吃饅頭主要因為牙不好咬。
兒子吃著像是生吞活剝一部家族史。饅頭不是稀罕物了。驚人的相似與回環總是出現每一個精心挑選的時刻,無法自主,敢憑命運降臨。我小時候也是這樣。奶奶在時,家里八畝地,奶奶圍著父親過。三十多年前,父親幾乎隔天一斤饅頭,盡給俺奶奶。我問她要,她給我。父親說:
“不管,你奶奶老了,身體不好怎么看你了。”
奶奶總是勻出來半個一個給我,五個哥哥姐姐干瞪眼,誰叫我最小呢。
娘說:時尚和你嚼饅頭的樣子一模兩樣。吃饅頭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家人高高興興地一起吃煎餅喝芋頭糊涂簡直是一件偉大的事情。父親看夠了這種場景,他悲傷已絕;父親再也不看這種場景,我們哭不出來。20世紀60年代考上嶧縣師范,交不起生活費,奶奶賣了大青瓦罐,盛千把斤糧食的,直徑有爺爺手臂長,到父親手里是八塊錢生活費。
下班了,我總是買饅頭。糖(多甜的,蜂蜜除外)不敢買了,母親咳嗽,反反復復折磨肺部與咽喉,一整夜咳嗽睡不著,父親要來找她說上一陣子話么。父親年前1月25日死了,在墳子里盛不了糖罐子,只好在陰間給奶奶買饅頭——我們燒去冥錢。世間的悲哀是想吃糖的時候不能夠了,是子欲養而親不待,幸好把母親接來了;幸好,我的血糖高,于是常常想起父親和糖罐子,不是因為父親節,那甜甜酸酸苦澀的;于是愛惜身體,為母親,為我的兒子。
兒子再不會看到我舉起糖罐子的樣子了。這是對父親拿著糖罐子——家族引以為豪的動作最好紀念。小文獻給父親,還有我自己——做了父親的,還有所有的父親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