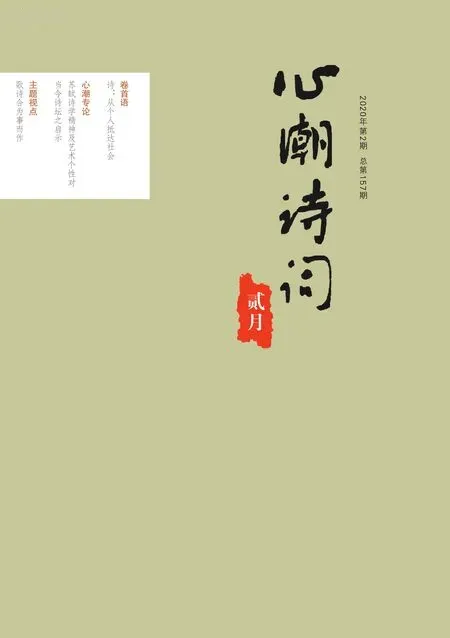蘇軾詩學精神及藝術個性對當今詩壇之啟示
楊子怡
敢于直面現實與人生,發揮詩詞的濟世功用;敢于干預生活,發揮詩詞的美學傳統;敢于堅持自己的藝術個性,寫出富有生活趣味的真詩,這是蘇軾詩學精神的基本內容。詩人應該寫什么樣的詩,詩人應該以什么立場面對生活、人生與社會,詩人如何寫出感人的有趣的真詩。這有關詩詞的發展大方向。筆者認為,當今詩壇仍然未解決好這些問題。詩壇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熱鬧、很喧囂、很繁榮,其實十分浮躁。語言粗鄙化、內容娛樂化、思想空洞化、情感虛偽化、立場麻木化、心態浮躁化似乎成為一種趨勢。詩壇可謂是亂象多多。其一,自封名家者多。人們動輒超唐邁宋,自詡少陵,秕糠太白,自詡“圣”者、“杰”者、“王”者,如過江之鯽。其二,作品多。寫作的隨意性,網絡的快捷性,造成詩作泛濫成災,毫不夸張地說,一天的數量可以超過唐詩的總量。寫詩人比讀詩人多。其三,社團多。建群的方便,造成人們拉幫結派,互相點贊吹捧,容不得批評意見。其四,賽事多。不少詩人或成為參賽專業戶,或成為評委專業戶。今天這里參賽,明天那里出評,常不乏偽劣假冒產品。其五,媚俗者多。不少創作者不惜改變自己的創作個性,用粗濫不堪的語言,美其名曰創新,其實為媚俗。詩評者也媚俗,不問作品好壞,假話空話套話連篇,評詩不是為了提升,而是為了諛人。清人李沂在《秋星閣詩話》中說:“不能自知其病,必資詩友之助。妝必待明鏡者,妍媸不能自見也。特患自滿,不屑就正于人;病不求醫,必成痼疾矣。”可見,評友人詩本是為了“資友人之助”以醫詩病,可如今之詩評大都諛友諛人,有違詩評之道。作者喜聽,評者樂諛。難見真詩人,難見真評家。一言以蔽之,當今詩壇難見到幾首關注現實、關注生命、關注民生、關注時弊、有真趣、有真情、有奇趣的作品。理論上對熱點問題、宏觀問題、方向問題的研究往往缺失,而枝節問題、技巧問題津津樂道。詩詞往何處去,人們迷失了方向。總之,當代詩詞繁而不榮,興而不旺,流而不傳,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有鑒于此,我們應該回歸傳統,少些空談創新,多些實在的繼承;少喊些口號,多關注些世俗生活;少些無病呻吟,多些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少些諛頌,多些美刺;少些套話,多些真趣。在這些方面,蘇軾為我們留下了不少的經驗,蘇軾的詩學精神與藝術追求仍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一、繼承蘇軾詩學精神,不要忘記世俗生活與民生困窘
《春秋公羊傳注疏》云:“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本身就是從生活中產生的,因此寫身邊的世俗生活,寫民生困窘,寫社會現實是詩的本質所規定的。古今中外的藝術經驗也昭示了一個真理:凡是寫世俗生活與民生的作品往往傳之彌久。詩有寫心的,有寫實的,前者著重于靈魂的拷問,后者著重歷史責任的擔當。兩者都能產生好詩。但是,一個詩人如果只停留在寫一己之心,整天只在個人的天地里哼哼唧唧,對社會、對人生、對世俗毫不關心,毫無責任感,毫無人文關懷,也成不了一個真正的詩人,至少其境界、其眼光、其胸次、其格局有問題。蘇東坡之所以成為偉大詩人,成為王國維先生心目中古代四大詩人之一,就是因為他的詩不僅在寫因困蹇飄泊帶來的一己心靈之痛苦,而是把這種痛苦與現實人生、與對世俗生活的關注,對國家民族前途之思考聯系在一起,表現出了一個詩人的文化擔當、歷史擔當,所以厚重,所以有深度。他曾以自己的藝術經驗告訴世人:詩文要“有意于濟世之用”,“詩須要有為而作”(《東坡題跋》卷二《題柳子厚詩》)。他在這方面多有論述,如其在《答虔倅俞括奉議書》中云:“酌古以馭今,有意于濟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觀美。”詩須濟世,不是滿足耳目之觀。他在《鳧繹先生詩集敘》中又說:“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顏太初(號鳧繹居士)詩關注生活,敢刺時事,以詩鳴怨,故獲得了東坡很高的評價,認為是“有為”之作。在東坡看來,即使“不適用”,難“有為”,但至少也不能忽視詩的熏陶作用,在《東坡題跋》卷三《書黃魯直詩后》一文里,他對黃山谷的詩給予了高度肯定:“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于世。”山谷詩雖有此“不適用”于世,但其詩中的熏染作用“不為無補于世”。詩須有為,是蘇軾詩學精神之一,是我們當今詩壇應該借鑒的前人遺產。我曾說過,詩之所以高雅,詩之所以成為史,在中國之所以有以詩證史的傳統,就是因詩反映時代、反映生活最快最直接,詩是一個時代的不死的靈魂,詩人就是其所處時代的社會良心。所謂“靈魂”“良心”云云,就是詩人能寫真實的時代,寫真實的社會,寫真實的人生,敢于說真話,不掩飾生活,不虛夸和文飾社會,廢止套話、假話與空話。
揆諸當今詩壇,缺的正是社會之良心,缺的正是詩人的靈魂。
明明有豐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可以供詩人們去陶煉,但人們偏偏津津樂道的是應制、應酬。比如各種節日來了,一人登高,萬人影從,賡和不斷,呼拉拉一大堆詩。不需要創作的沖動,不需要靈感的誘發,隨時就可制作一大堆,成為產詩機,口號連篇,套語累牘,令人不可卒讀。
明明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題材,寫出自己的個性,可人們硬是喜歡媚俗跟風。比如,某名人一次大壽,不管認識與否,不管喜歡與否,不管情感有無,賡者甚眾,以為和了名人自己儼然也就是名人了。甚至連某名人逝世了,沒有交情變成有交情了;沒有半毛關系,變成了有關系了。更可笑者,一次交談就可自稱門生了。一次微信聯系就可說師生情誼之深了,于是虛假、做作的悼念文字也是盈篇累牘。沒有半點悲憫之情,純是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
明明有艱窘的人生,有現世的矛盾,有弱勢的群體,需要詩人們去關注,可詩人們或是麻木,或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或是莫名其妙地視之為負能量加以抵制。人們心向往之的是所謂大題材。為了顯示大,使用語言也是套話、大話,鋪排羅列,了無詩意。比如某座橋通了,頌詩馬上會鋪天蓋地。使用頻率最高的也是“鐵龍”“金龍”“飛龍”,套語之多也是令人咋舌。我并非一味反對大家寫這類題材,但是在題材處理、構思、語言上應該進行提煉。應該確有感想了才寫。東莞鹿鳴杯詩賽獲獎的雪輕云女士的《港珠澳大橋通車有寄》所寫“飛橋隱隱水云間,我立蒼茫淚暗潸。七十年來離恨事,幾時衢道到臺灣”,境界就與眾不同,詩人意不在頌橋,而在寄慨,構思別致。三地已通,兩岸仍隔,結以問句,立意自高。詩人把自己的憂慮置于民族的統一大業中,非那些為頌橋而頌橋者可比。
以上種種現象,說明我們的詩人忘記了自己的責任與擔當,不明白詩須有用于世的道理。缺失了同情心、仁愛心,用空泛的口號代替時代的主題,不知詩是形象思維,能以少博大,不知去剪裁世俗生活之浪花。其實詩人只要有用世的理念,用心去提煉生活,是能寫出好詩來的。比如早些年湖南詩人蔣典昌先生歌頌農村改革開放后發生變化的一首小詩《農家即事》就是提煉生活很成功的例子:“春歸舊燕有新愁,不見茅檐見彩樓。三匝繞梁終辨識,鋤筐仍掛粉墻頭。”你看不見意象的羅列,看不見套語的鋪排。通過燕子找不到舊窩而發愁一個細節,反映了農村的巨大變化:農家仍舊,地點仍舊,鋤筐仍舊,只是樓已變。這首詩的妙處在于詩人在處理題材時的提煉功夫。本人也嘗試過,前年也寫了一首反映惠州百姓生活發生變化的小詩《鵝城微購》:“精選三番不忍離,羞言忘帶杖頭資。揣心老嫗殷勤語,教爾新招掃二維。”詩寫出了我當時市場購物未帶錢而不會用微信付款的尷尬場面。通過老嫗使用二維碼售貨,反映了百姓生活的變化,時代的變化,雖談不上好詩,但至少在剪載上下了功夫,知道了用生活小事反映時代大變革的道理。如前所述,生活不缺詩材,不缺乏美,關鍵是缺乏愛心,缺乏發現美的慧眼。有了愛心和慧眼,就能寫出好詩來。如浙江詩人朱小波有首《無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寫實的范例:“鄰居老者夜悲號,病痛能醫卻死熬。藥若敢和金比赤,親情又值幾分毫。”詩人用很樸實的語言把百姓看病難的事實表現了出來,明明可以醫治卻“死熬”,貴若黃金的藥,使親情盡失。詩人的錐心之痛盡在樸實的話語之中。類似這樣的民生才是詩人應該關注的。關注世俗,關注民生,蘇軾的淑世情懷,至今不過時,值得詩人們借鑒。
二、繼承蘇軾的詩學精神,不忘美刺傳統
不文飾生活,敢于對現實挑刺,是中國詩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前人把它謂之“美刺”精神,從《詩經》一直傳承下來。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美刺”,一些專擅歌功頌德的作者往往抓住“美”字作文章,而忽略了“刺”。在《詩經》時代,所謂“美刺”就偏義于“刺”,《詩經》中有專以刺為刺的,也有以美為刺的,但是這個“美”也是為了“刺”。如《詩經》中的《角弓》一詩典型地以刺為刺,而《詩經》的《斯干》篇雖是美周宣王之節儉,但其目的是反諷楚元王之奢侈,是典型的以美為刺。因此,美刺是一個偏義詞,主要義項是刺,古人又把它稱之為“譎諫”。《周禮·地官》有“司諫”之官,鄭玄注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周禮》還有“保氏”之官專門“掌諫王惡”,可見古人很重視“諫”。《詩經》因有美有刺,甚至被人們視為“諫書”。這種“譎諫”的傳統一直為后人所遵守,不難發現,中國的一部詩史就是以刺為主,優秀的詩大多是刺詩。以詩刺世,以詩諫世,到了唐之白香山,把它發揮到極致,他主張“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不懼權貴怒,亦任親朋譏”。甚至主張“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以詩為諫,發揮詩“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與元九書》)的作用。雖然他過份夸大了詩的勸世作用,但他卻把詩的美刺精神推向了高峰。他一直把這當作他創作的原則,一生寫出了不少反映現實民生,批判丑陋現象的作品。蘇軾一生對白居易十分崇拜,他也髓傳了這種精神,主張詩應有補于世,他在《鳧繹先生詩集敘》中所說的“言必中當世之過”以及在《過于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因用其韻賦一篇》所說的“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就是對傳統美刺精神的繼承。他一生關心民瘼,敢于寫實,敢于揭時弊,即使九死馀生,也不改初心,誠如其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銘》中所言,“數困于世,然終不以為恨”,表現出了古代士人的凜凜風骨。我們當前詩壇太需要這種士人風骨,太需要這種美刺精神。
無論詩家、詩評家還是管理者,都應該明白中國詩歌史這個傳統,呵護這個傳統,繼承這個傳統,不要簡單地把作品分為正能量與負能量,不要把那些優秀的揭弊的詩打入另冊,政治家應該有氣量、有胸懷、有情懷、有審美能力,應該保護詩人的風骨,應該明白一個道理:詩人雖是一個愛挑刺的群體,但不用懷疑他們的赤子之心,不用懷疑他們是其所處時代的良心,是一個時代的不死的靈魂。他們敢于揭露黑暗,是因為他們心里敞亮,充滿光明;他們敢于發牢騷,是他們太愛這個民族與國家。屈原為楚懷王挑過刺,杜甫為唐皇挑過刺,白香山為唐憲宗挑過刺,蘇軾為宋神宗和哲宗挑過刺,誰能說他們的詩不是正能量,我們今天的大學教科書不還是把他們這些作品作為精華保存下來了么!大學課堂不還在天天講他們的揭弊詩么!無論藝術家還是政治家,不要忘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古訓,不要忘記了政治上“否可相濟”的良言,須知“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的道理,政治是如此,藝術也是如此,清一色的題材,清一色的口吻,清一色的風格,清一色的諛頌與格調,藝術會走向死胡同。
只有真實反映民生,揭露問題,敢于說真話的作品才會感染讀者,作品才會長久地保存下來,那些概念化的作品很快會被淘汰。下面我舉出兩首作品,我和讀者不妨打個賭,哪首作品會保存下來。一首是網絡上的所謂正能量作品:“群英匯聚氣吞虹,喜見神州舞巨龍。巧繪宏圖云浪涌,高揚赤幟國威隆。虎添雙翼開新宇,鵬展重霄駐勁風。萬馬奔騰齊奮進,千秋偉業耀蒼穹。”一首是山東莒縣農民詩人孫守華的《村官言》:“休輕小小一村官,賣地賣河還賣山。不是清風來得緊,焉知不敢賣蒼天。”其實,無須我徒費唇舌,只要稍有點審美感的人,讀了會高下立辨。前者,按時下標準,足足的正能量,但筆者認為,無能量,因為全詩都是標語口號,足味的老干腔,不能感染讀者,哪來能量?后者可能會認為是負能量,但我認為是足足的正能量,因為它真實、含蓄,一針見血,揭露了社會問題,把那些毫無底線的“老鼠們”的行徑暴露無遺,繼承了傳統的美刺精神,像這樣的能感染讀者的詩才是真正的有能量。
三、借鑒蘇詩的藝術經驗,把詩寫得有趣味
中國古典詩詞源遠流長,古人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本人治詩四十年,對古詩詞一些重要作家及各種體式曾有過研究與比對,深知不但各個作家有不同的寫法與風格,即就體式言,不同體式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詩之正體宜莊雅,詞之正體宜媚俊,曲之正體宜俗。即使莊雅的詩也因不同體式而有種種:五絕不宜工麗,宜于古拙;七絕則宜清健蘊藉。五古宜高古雄渾,七古偏于渾重雅健、句重散化,歌行則偏于流轉奔逸。五律重豐神情韻,七律重筋骨思理。即使偏于嫵媚的詞而言,小令宜于清新嫵媚,慢詞宜于鋪敘展衍。但是,不管寫法如何不同,風格如何有異,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是講究“趣味”。筆者認為,一個真正的大家,應該能適應各種詩體而呈現出不同的趣味。像我們前面所講的蘇軾,其詩根據不同的體式表現出不同趣味:既有含蓄蘊藉的雅趣,又有不避口語化的俚趣;既有升華哲理的理趣,又有淘寫性情的情趣;既有反常合道的奇趣,又有引人發笑的諧趣。其詞也是如此,既有瀟灑清曠之風,也有豪邁雄放之格;既有婉雅嫵媚,堪比花間之作,也有逞才議論,甚或叫囂之風。總之,蘇軾對詩詞趣味之追求,值得我們借鑒。時下詩壇,派別林立,各執其風,競相自寶,不能共容。比如,江湖俚俗派譏學院雅正派為逞才使學、泥古不化;雅正派則譏江湖俚俗派為油腔滑調、粗俗不堪。筆者認為,大可不必,不同風格共存,才足顯出詩之繁榮。俗者有趣,雅者有味,都是成功者。俗而無味則庸,雅而無趣則澀。不過,筆者仍堅持,何用俗與何用雅應據詩之體式而定,比如,不分體式,一律趨俗,用寫曲之法來規范詞與詩,反之,用典雅一律規范各體式,用雅去制曲,都非正道,都泯滅了各種詩體之區隔。謂此為創新,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要使詩詞有感染力,還是在“趣”字上下功夫,力爭把詩寫得有趣味。
偏愛于典雅者,像東坡詩那樣,適當為詩增加點靈趣或奇趣。典雅是中國詩歌的傳統,雅詩傳出的味道往往深厚,令人有回味,令人咀嚼,如果再增添一點靈趣,味更濃。東坡詩很有雅趣,但他常常用語靈活,想像奇特,往往雅而見靈性。如其《次韻參寥詠雪》一詩:“朝來處處白氈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以雪喻作爛銀與白玉,進而聯想到奇貨可居成語,詩頓生靈趣。故方東樹評為:“雜以嘲戲,諷諫諧謔,莊語悟語,隨事而發,此東坡之獨有千古也。”(《昭昧詹言》)方氏之評也獨具慧眼。湖南已故著名詩人王巨農先生也善于雅中寓以靈趣與奇趣,他的《離休感懷》師承劉禹錫《阿嬌怨》中“望見葳蕤舉翠華,試開金殿掃庭花。須臾宮女來傳信,言去平陽公主家”之意,寫出自己退休感受:“輕車疑是舊僚來,忙喚妻孥備酒杯。嘀嘀一聲東去也,門前麻雀又飛回。”寫出人走茶涼、趨炎附勢之世態,讀來妙趣橫生。筆者律作也趨雅,但也能注意雅中添些靈趣,如拙作《鼓掌》詩云:“楚楚衣冠話語驚,氣場滿滿起雷鳴。大王風有諛君曲,小屁民存拍馬精。已許拂須登顯位,毋譏舔痔得殊榮。醫云手上多多穴,鼓掌何妨當養生。”整體均雅,但末尾的一聯調侃,為詩平添了趣味。
偏愛通俗者,像東坡詩那樣,為詩詞添點俚趣。我不反對通俗,但俗須有趣,無趣則難讀了。廖國華先生的一首《定風波·嘲落牙》:“時痛時鬆時發麻,半邊臉腫爛于花。應是而今緣已盡,須信,災來唇齒也分家。 基礎動搖當下崗,休想,同甘共苦過年華。后我而生先我死,從此,三餐不再嚼鍋巴。”脫牙,是衰老之象征,但詩人出以幽默之筆,且含哲理,詩人之樂觀情緒,其內心之強大全盤托出,語雖俗,而味則厚。本人的《中心醫院割疣》詩,也是注意了俗中不忘趣料的增加:“不知何日贅疣生,老臉又添新補丁。漫道芳容存舊照,花黃一貼也傾城。”把不快之事寫得松輕幽默,也獲得了詩友好評。古往今來的藝術經驗告訴我們:有趣的俗語是作者精心淘煉了的,如下一些詩句非出自大手筆的淘煉,不足傳味:“好漢最長窩里斗,老夫怕吃眼前虧”(楊憲益)、“白雪陽春齊掩鼻,蒼蠅盛夏共彎腰”(聶紺弩)、“知誰座上嗓門大,老子農民不下崗”(廖國華)。
偏于宋調好議論者,像東坡詩那樣,多點理趣。“理趣”是宋詩的特色,但這個詞最早始出于東坡。他認為:萬物有“常形”與“常理”,“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凈因院畫記》)認為窮理比盡形更難,無獨有偶,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也以為窮理難于盡形,他以形上、形下分詩詞境界之高下,與宋王柏“道者形而上者”之說有某些相通之處,認為窮理之宋詩不差于盡形之唐詩,前者他視之為“形上詩”,后者視之為“形下詩”。形上詩要把詩人自己的性情、學問、思想、道德、理念傾注于詩中,形成于哲理更難寫。因此,我們不必對好議的宋調進行貶斥。關鍵是議不能抽象地議,要融于形象之中,傳出味來。像東坡的《東坡》(其五):“雨洗東坡月色新,市人行盡野人行。晨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鏘然曳杖聲。”這是一個飽經患難的人對生活的深切感悟:人生的道路如眼前的曳杖行坡一樣,充滿了坎坷不平,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因其難而畏葸不前,相反要以十分努力與信心勇敢向前走,在艱難行走中欣賞自己,欣賞成功的喜悅。一個“愛”字寫出詩人百折不撓的樂觀。詩人之議完全融入行走東坡的敘述中,這種寄理,使詩變得有味。本人也在這方面多有嘗試,去年筆者寫過一首《詠傘》詩:“能屈能伸任自由,休言作嫁被綢繆。一朝不為人遮雨,誰舉卿卿在上頭。”也是根據傘之特點,寄寓自己對世事的一些看法,不乏理趣,雖詠傘而字面上不言傘,只暗示意象,為詩增添了含蓄之味,頗受詩友好評,有詩友還把此詩制作成一個詩謎。
偏喜于借物即興者,像東坡那樣多點情趣或真趣。詩詞景要真,狀物要真,抒情要真,真則有趣。清代史震林說:“詩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氣與靈機也。”(《華陽散稿·序》)這里所言事趣、情趣、景趣之來源,都在真,特別是借物即興的詩尤重情真。比如張學良晚年獲得自由后在友人郭冠英陪同下拜竭鄭成功祠,寫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詩:“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孽子孤臣”一語雙關,既是對鄭成功千秋功罪的評論,也是詩人自侃與自慰。詩人認為鄭于1646年反對其父降清并起兵南澳抗清,其意義并非在尊明逆,而確保了國家統一,臺灣沒有分割出去。立意高遠,情感真切,故讀來有味。2017年本人參觀內蒙滿洲里國門,看到柵欄那邊的故國之地,突然情感來潮,寫出了一首《滿洲里國門眺望》:“國門那畔綠盈嵐,故土傷心隔柵看。只有清風不邊檢,癡心無改過圍欄。”詩友認為也是一首有情趣之作,認為情感真。
為生活添點幽默,像東坡那樣,為莊重的詩添點諧趣。詩能不能做到有諧趣,是由詩人的品格、學識、氣質決定的。蘇東坡有情商又多靈氣與才氣,在他的詩中充滿了詼諧之趣,為他的艱苦困蹇的人生增添了幾分幽默之趣。因此,后人附會其幽默機智的故事也很多。據說他某次過河訪友,可船剛開,東坡要船家捎上自己,船上人認出是東坡,要他即興應景賦首一詩,且要求詩須有十個“一”字,才肯返回接他。東坡脫口吟出一首《一字詩》:“一帆一槳一漁舟,一個漁翁一釣鉤;一俯一仰一場笑,一江明月一江秋。”詩確實顯示出東坡的智慧與幽默人生。詼諧幽默之表達,形式多樣,或因物興感,或寓莊于諧。齊白石曾據泥塑不倒翁畫了一個貪官畫并題詩一首:“烏紗白扇儼然官,不倒原來泥半團。將汝忽然來打破,通身何處有心肝。”詩雖幽默,卻借題發揮,寓莊于諧,讀來有味。本人也在此方面有過嘗試,曾寫過一首《筷子兄弟》:“赴湯如杵逞風流,味海饈山倜儻游。油膩既沾仍竹韻,二人結黨未私謀。”筆者因物興感,既合筷子情事,也不乏一定趣味。其中不無莊重之意:竹子處油污而仍保“竹韻”,而時下官又如何呢,反諷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