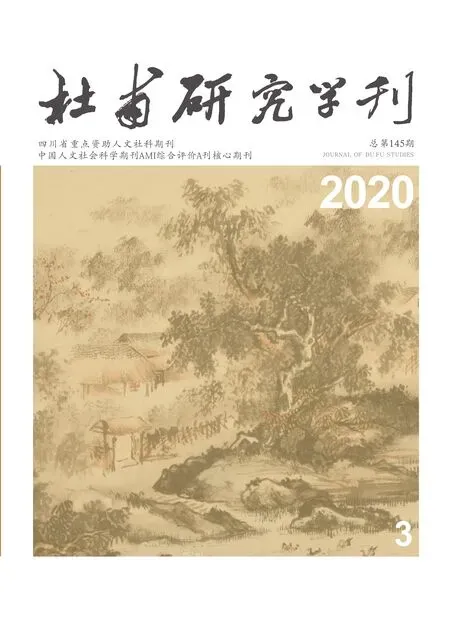隱逸與園林:關于杜甫農業詩中的幾個問題
——兼評《杜甫農業詩研究》
郝潤華
中國古代的農業詩,可上溯到《詩經》,如《豳風·七月》《小雅·大田》等都是與農事相關的典型作品,到魏晉時期出現了文人創作的田園詩,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等。田園詩與農事詩雖然并非一回事,但它們之間又不無關聯,由此影響到后來的田園詩甚至農事詩。杜甫是一個心懷天下的儒家文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①是他的政治理想;杜甫也心系下層百姓,同情廣大農民,曾作過“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秋雨嘆三首》其二)、“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歲晏行》)這樣關注同情農民的詩歌。由于特殊的時代與遭際,在避難寓居秦州、成都、夔州時期,杜甫為生計而不得不參與農事勞動,“臥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親自參加農業勞動也使杜甫創作出了不少與農業相關的詩歌,且具有十分鮮明的藝術特色。
一、杜甫農業詩與《杜甫農業詩研究》
關于杜甫創作與農業詩的情形,有學者指出:
作為當事人,杜甫與農業實踐的關系極為密切,在中國文學史上,杜甫是第一個將具體的農業實踐全部融入自己的詩歌創作中的詩人,這真是一份新鮮的驚喜。不僅如此,杜甫將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喟嘆和喜悅寫進這些詩作中,作為“詩圣”,他的才華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可以說,每一首詩都是杰作。
比起杜甫那些揭露社會矛盾、同情農民的初期作品群(這些都是被后世傳頌的名篇),筆者覺得其成都時期,特別是移居夔州后親自參與農業實踐的詩作要有趣得多。在此基礎上,筆者對杜甫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從內在覺察到了杜甫的有趣之處②。
杜甫在秦州、成都、夔州時期創作的與農業相關的詩作較豐富,如《為農》(“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大雨》(“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刈稻了詠懷》(“稻獲空云水,川平對石門”)、《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等,在敘寫日常生活細節中又多了一個有意思的題材。總之,杜甫在這一時期從事農業生產,并將自己的生活體驗與感受在詩歌中細膩地反映出來,在擴大詩歌題材的同時,對后世的詩歌創作起了積極的影響作用。因此,杜甫的農事詩值得關注,也值得專門研究。而日本學者古川末喜著、董璐譯《杜甫農業詩研究——八世紀中國農事與生活之歌》就正是這樣一部專題性研究著作。
《杜甫農業詩研究》一書,集中對杜甫秦州、成都、夔州三個時期的農業詩作了系統梳理分析。作者以細膩的觀察力與筆觸考察杜甫與農業相關的詩歌,尤其是對與農業相關的如地理環境、房屋營建與位置、蔬菜種植與飲食、樹木品種與栽種、田地之歸屬、人物之形象等專門問題的關注,以及對某些物象與意象如薤菜、柑橘等食物的具體闡述,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與把握杜甫詩歌的內涵與價值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此書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秦州期,分二章,包括“秦州期杜甫的隱逸計劃及其對農業的關注”“杜甫與薤菜——以秦州期的隱逸為中心”;第二部成都期,分二章,包括“浣花草堂的外在環境與地理景觀”“農事和生活的歌者——浣花草堂時期的杜甫”;第三部夔州期的農業生活,分三章,包括“杜甫詩歌所詠夔州時期的瀼西宅”“支撐杜甫農業生活的用人和夔州時期的生活詩”“生活底層之思緒——杜甫夔州瀼西宅”;第四部夔州期的農事,分三章,包括“杜甫的橘子詩與橘園經營”“杜甫的蔬菜種植詩”“杜甫的稻作經營詩”。此書結構安排雖然只有四部分,但總共十章,每一章下有若干節,總計97節,安排周密詳盡,每一節標題都很具體而有趣。以第二部“成都期”第一章為例,此章“浣花草堂的外在環境與地理景觀”共有十五節,題目分別是:成都城西、錦江之畔、浣花、橋、橋之感懷、“コ”字形蜿蜒流淌的錦江內側、浣花溪諸相、愛川、西嶺、知識分子階層的鄰居們、農民階層的鄰居們、村、近鄰等,如此詳細又具體的章節安排,獨具匠心,使讀者一目了然,看標題而大致知道作者將要闡釋的論題,讀起來也不至感到枯燥乏味。
此書的最大特點是分析十分細密,論述也較深入。作者對一些杜詩相關的地理空間、名物、人物的考證十分細致。地理,如西枝村與西谷、東柯谷、仇池山、赤谷、太平寺、浣花溪、愛川、西嶺、瀼西、赤甲山、白鹽山等。農業名物,如薤菜、蒼耳、橘子、萵苣等。甚至由此及彼,運用意象學說進行詳細論述。作者不放過任何一個與杜甫農業詩有關的物象,包括人物,就連杜詩中出現的傭人,如出現于夔州時期杜詩中的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人物,作者也都不厭其煩地作了考察分析,諸如身份、與杜甫的關系、杜甫對他們的態度等。作者以為杜詩不僅將傭人寫進自己的作品中,而且還有情感體驗,這種認識與杜甫一貫思想行為相一致。作者進而聯系到杜甫“示”體詩,并由此推測詩人之情。這些細節問題關系到杜詩后期創作中內容題材的變化與發展,也都是國內研究者容易忽略的地方。
尤為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作者花了大量篇幅考察杜甫賴以生存的田地問題。如成都期第二章第四節“田園的所有形式”,作者在對杜甫《大雨》(“西蜀冬不雪”)詩作出分析后指出:
成都時期的杜甫,很可能是以托管的方式擁有農田,并且這些田地還附帶了農夫。也就是說,農田并非杜甫所有,但是杜甫擁有田地的收獲和收益。所以杜甫才在詩中歌詠了自己看到黍豆茁壯成長的喜悅之情,不管是自家的田地還是其他農戶種植,兩種解讀方法似乎都行得通。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特點,因為嚴格控制字數而帶來內涵的豐富性和多種解讀的可能性。
為了論述方便,此處先提出一個假設,……也就是說,杜甫無須直接參與農園的耕作,當然也無須參與小麥、黍米等谷物以及蔬菜等商品作物的經營管理,但是農園的收獲和收益卻歸杜甫所有。自己僅需在菜園從事供家庭消費的小規模蔬菜種植。(第94頁)
此結論雖是一個預先的假設,但卻不無道理。因為,杜甫在成都至少有好友嚴武等人的幫助,能夠幫他以租賃的形式擁有一些田產,供其全家生活。在夔州也同樣,有軍閥朋友柏茂琳的資助,他在瀼西購買了果園,又主管東屯公田,手下還有一些奴仆可以使喚。
為證明論點的準確性,作者在研究中常運用比較的方法進行舉一反三地分析,而不是自說自話,這也是作者態度嚴謹、論證周密的表現。作者注意到杜甫與古代其他詩人以及作品的差異性,如第一部第一章第九節“結語”部分,在談到杜甫對農業表現出的關注角度時,作者將杜甫與陶淵明、王績、孟浩然作了比較。又如,對于薤菜的意象問題,作者將杜詩與六朝人的作品作比較,凸顯杜詩中薤菜的表現用途。第二章第八節“結語”總結:
在詩人們進行詩歌創作的時候,《文選》中的措辭和意象往往會在潛意識中發揮作用。就薤菜的意象來看,在《文選》中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薤葉之上消散的露水意象(詩);二是故鄉莊園中種植的蔬菜“白薤”,在晚秋到初冬的霜降之日,形成了所謂的“霜薤”意象(賦)。
但是,在現存杜甫詩歌之中并未使用傳統的“薤露”意象,……無論是潘岳還是謝靈運,將采薤置于歸隱和歸田之賦中,是一種被程式化的范疇。賦,原本就存在將同類事物如類書一般并列使用的敘述之法。因此,潘岳和謝靈運在賦中所寫的薤菜,只不過是各類蔬菜中的一種而已。薤菜之個性被埋沒在賦的陳列式敘述當中。但在杜甫的詩中,薤菜不是點綴在自己故鄉莊園中品目繁多的蔬菜之一,也不是相對之物。對杜甫而言,薤菜是唯一具有個性的存在。(第51頁)
在第二部成都期的論述中,作者也將杜甫草堂與謝靈運、白居易等人營建園林作了對比,得出如下結論:
筆者從外在環境和地理環境層面,對杜甫隱逸生活的舞臺——草堂進行考察確認。……筆者認為,這種創作詩歌的態度,在杜甫之前和之后的時代有明顯的區別。在杜甫之前,詩人們在描寫園林或者實際的隱逸生活時,總充斥著虛構的成分。似乎這也是一種詩歌創作的態度。多數情況下,現實生活的描寫變得暖昧起來,仿佛被面紗包裹著一般。當然,通過這種曖昧的描寫或許能夠達成優美的詩歌境界,但杜詩對園林進行描寫時,大都采取了一種寫實的態度,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明顯。(第86頁)
作者將杜甫草堂界定為園林,這一點是否合理準確,我們先不予討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過對比分析認為從杜甫開始對于園林的描寫采取寫實的態度,這一問題的發現確是作者獨具慧眼的地方。
書中時有新意,精彩疊見。作者對杜甫詩歌作了細致閱讀,發現并分析杜詩中所描寫的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一些細節與物象,而且興趣十足地對其進行討論。這些問題看似非常微小,容易被忽略,但是作者卻能以小見大,于微妙處看出端倪,并歸納提出文學史中的某些規律性的現象,時有精彩之論。
如,秦州期第二章第四節“阮隱居所贈薤菜”,作者說:
在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杜甫在詩中記敘了自己獲取生活物資的過程,并且通過詩歌的方式進行回復。杜甫的很多名篇均是得到別人物質贈予后寫下的答謝回信。這一現象在中唐以后逐漸流行起來,作為文人趣味的興起,這種現象在宋代也非常流行。杜甫起到的先驅性作用在此就不再贅述。(第43頁)
又,第五節“與菜瓜、蒼耳搭配的薤菜”:
在詩或賦中描寫食用薤菜,杜甫的這首詩乃是第一首。除此之外,他還將瑣碎的日常飲食生活特意以詩歌的方式進行敘寫。杜甫似乎是有意用詩歌這種方式宣傳和推廣自己新奇而有趣的食用方法。在另外一首(一九09 槐葉冷淘)中,杜甫還描寫了做涼面的一種新方法。這種在飲食生活上傾注大量心血和創意的態度,在杜甫之前的詩歌中很少見,這種態度從中唐開始到宋代逐漸多了起來。(第44頁)
第八節“結語”總結道:
后世詩人是如何看待杜甫創造出的薤菜意象的。……從整體來看,毫無疑問,后世詩人茫然接受了杜甫詩歌創造的薤菜意象。在實際創作過程中,他們只截取杜甫詩歌意象的一小部分用在自己的詩中,杜詩好似舞臺背景一般被引入創作當中,詩人們稍加變化,便能創造出更為豐富的意象。……不論創作出怎樣的作品,杜甫詩歌意象都成為大家的共享之物。只要以中小地主自給自足莊園經濟為基礎的士大夫世界一直延續,那么,由杜甫創造出的薤菜意象就會反復在詩中被再創作。(第51、52頁)
一個詩人,如何用語言創造一個事物意象,這一意象如何被后世詩人共享,繼而消失。作為一個具體的例子,或許通過杜甫所創造的薤菜意象,我們便能窺探一二。(第52頁)
以上三例采用的都是以小見大的研究思路,作者通過對杜詩中薤菜書寫與意象的分析,提出了三個頗有意思的論點:第一,杜甫詩歌中的一個獨特題材:得到別人物質贈予后會寫詩答謝回復,這對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以后詩歌題材的擴大有所影響。第二,對飲食生活傾注大量心血和創意的態度,在杜甫之前的詩歌中很少見,從中唐開始到宋代逐漸多了起來。第三,杜甫所創造的獨特的薤菜意象,影響到中唐以后的詩歌意象,甚至被后代詩人所共享。作者這三個結論,不僅對于我們深入研究杜詩有所借鑒,并且對于宋以后古典詩歌題材與意象的細化研究也有所啟示。
與以上薤菜同類的還有對于橘子的研究,也是作者能夠見微知著的一個范例。此書第四部“夔州期的農事”第一章“杜甫的橘子詩與橘園經營”,共設11 節,基本是對橘子與橘園的集中討論。作者對如下問題作了精心論述:成都時期的橘子詩,瀼西草堂、春天的橘子,三寸黃橘,月亮與夜露中的橘子,收獲前的橘園,東屯詩中的橘子,橘子收獲以及橘園轉讓等,最后得出三個主要結論:
杜甫詩中出現的橘子,抑或詠吟橘子的詩作,其中表現出的態度,并非自中唐以來宋代以后出現的趣味式花木鑒賞。對杜甫而言,具有更為實踐性的意味,乃是在收獲和經營橘子的立場上進行描寫的。正如迄今所探討的那樣,杜甫的橘子詩作與其自身的農業生活密切相關。(第209頁)
橘園經營帶給杜甫以希望,使他能夠保有精神上的閑暇。故此,杜甫的橘子詩作總體上多是明朗、高揚的格調。杜甫的這些橘子詩中,古體詩較少,近體詩很多,這也反映了上述格調。說到杜甫,大家腦海中都會立刻浮現出他憂國憂民、沉悶、深刻的形象。但是在橘子詩中,杜甫稍稍從那樣的形象中脫離出來。對他而言,橘子詩乃是其拓展詩風的一個側面。依靠這些橘子農業詩,杜甫的詩風呈現出多彩的一面。(第210頁)
對杜甫而言,橘子是善之存在。無論是對其人生還是詩作,橘子都是正向積極的。……對杜甫而言,能夠在夔州這個自己最后的安居之地收獲橘子和稻米,應該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橘子對杜甫的人生和詩作產生了極大影響,發掘橘子與杜甫際遇的意義,也是小論的一個目的。(第210頁)
作者通過對橘子詩與橘園的分析,認為杜甫書寫橘子,與其他詩人的花木意象審美有所不同,杜甫橘子詩與其農業生活息息相關,更為寫實;杜詩中的橘子詩,格調明朗、高揚,以近體為多,反映了杜甫拓展詩風的一個側面;橘子對杜甫的文學創作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也可見橘子對于杜甫人生的極大意義。
作者在提出論點的同時,也往往能在認真梳理文獻的基礎上兼采各家觀點,如《秦州雜詩》其十五,此詩究竟作于什么地方?作者根據詩句詩意認為是在秦州城內所作,而非作于東柯谷。因為“陳貽焮先生認為,杜甫描寫東柯谷和杜佐草堂的詩作均是其通過想象創作出來的。筆者也贊同陳氏的觀點……”(第13 頁)。但是為謹慎起見,又在腳注中對前人的代表性說法作了列舉:
究竟此詩作于東柯谷,還是作于秦州城內,有不同看法。舉其中代表性觀點,如趙次公就認為“東柯遂疏懶”乃是“言遂得東柯谷之隱”,這是前者之觀點。仇兆鰲則認為“在秦而羨東柯也”,這是后者之觀點。(第14頁)
從中可以一窺作者對于文獻的梳理與把握,亦可見作者研究之綿密。如以上這樣的細節討論在杜甫研究已十分成熟的當下對我們極具啟發意義。
二、漂泊西南:是流寓不是隱逸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農業詩研究》一書是基于隱逸而討論杜甫農業詩的創作,正如《譯后記》所總結:“古川先生這本書貫穿了兩條基本主線,即隱逸和農業。可以說,這本書是沿著杜甫隱逸的歷程來探討他與農業的關系。”(第300頁)書中的研究也基本圍繞著隱逸這一問題而展開。如,
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杜甫到達秦州之后,在多首詩中表達過想要隱逸秦州的愿望,并且非常認真地實地尋訪過幾處隱逸的備選之地。毋寧說,對于隱逸的希冀,亦是其秦州詩的一個基調。(第5頁)
又如:
第二年是上元元年(760),這年春天,在一位強有力后援的幫助下,杜甫于成都錦江上游浣花溪購置了一塊土地,營建草堂,……在這里,杜甫終于過上了自己后半生最為安定的隱逸生活。(第55頁)
作者甚至認為“從事農業作為隱逸的代名詞是常有之事”(第92 頁),由此將杜甫作于寶應元年(762)的《屏跡三首》作為隱逸詩來專門考察(見第94 頁)。這一思路在章節標題中也有表現,如第一部分第一章題目為“秦州期杜甫的隱逸計劃及其對農業的關注”,第二章題目“杜甫與薤菜——以秦州期的隱逸為中心”,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五節是“隱逸詩三首”。可見,作者立論的基點的確是杜甫的隱逸生活與農業詩創作。
何為隱逸?在中國古代,文人或隱居不仕,躬耕田園,如陶淵明;或不愿與統治者同流合污而遁匿山林,如伯夷、叔齊、商山四皓之類。主要指政治人物或文人主動遁世隱居,即身居鄉野而不出仕。如《后漢書·岑彭傳》:“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晉葛洪《抱樸子·貴賢》:“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歷數中國古代的詩人,真正稱得上隱逸者的只有陶淵明,其“不為五斗米折腰”,主動歸隱田園,并創作出了許多優秀的田園詩,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熱愛與淡泊的文人情懷。可見所謂文人隱逸,是指文人不愿與當局者合作,主動隱居山林、田園,從事一些農業勞動;若家有足夠財產,連起碼的農業生產也無需參加。文人隱逸,與其說是一種生存方式,不如說是一種姿態,一種價值觀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來說,無論長期還是短期從事農業生產,如果是主動的,那就是隱逸;只要是被動的,為了生計而從事農業勞動,似乎不能看作是隱逸。杜甫的漂泊西北、西南,究竟是不是隱逸呢?以下試作分析。
此書作者首先對秦州期杜甫涉農詩作了討論,認為杜甫西行的目的就是想隱逸于秦州,他說:“藉此可知,杜甫離開帝都的秦州之行,乃是為了尋求隱逸永駐之地。”(第7 頁)作者進一步認為:
對杜甫而言,秦州是農作物的集散地,農業亦很發達,這點相當重要。秦州時至今日依然被稱為“隴上江南”,農林業發達。對于想在此地終老一生,過上隱逸生活的杜甫而言,有適合從事農業的土地,乃是其選擇秦州的最基本條件。(第8頁)
其實,據古代有關秦州(今甘肅天水)的地理書與筆者實地調研,秦州自古農業并不發達,原因是其特殊的地理條件:秦州境內山脈縱橫,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東部和南部是山地地貌,北部是黃土丘陵地貌,中部小部區域是渭河河谷地貌。因此,秦州地形主要以山地為主,不宜耕種糧食作物,但森林覆蓋面積較廣,因此,林業較發達,可種植木本植物與藥材。對于秦州的特殊地理環境,杜甫應該比較清楚,其認識不會產生這樣的誤差。因此,即使杜甫有隱逸的愿望,但似不會選擇秦州作為終老之地。作者是否對秦州做過實地調研,不得而知。
我們再看當時的歷史背景。至德二載(757)十月,安慶緒率軍從洛陽逃往鄴城(今河南安陽),唐軍收復洛陽。乾元元年(758)九月至次年三月,肅宗令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率軍圍攻相州(今河南安陽)安慶緒部,結果與援軍史思明交鋒。戰前肅宗恐諸節度擁兵自重,不令設總帥,加之又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令其監督牽制,致使九路兵馬大敗。郭子儀退至河陽橋,李光弼返回太原,其余節度使各回本鎮,史思明重新占領洛陽。乾元二年(759),辭去華州司功參軍后的杜甫,已不可能回到再次失陷的洛陽;此時的杜甫對肅宗統治集團已十分失望,也不可能留在居大不易的長安。因此,只好選擇西行避難,試圖先尋覓一地作為暫居之所。正像莫礪鋒先生所分析:
詩人棄官西去的原因是什么?《舊唐書》本傳說是“關畿亂離,谷食踴貴”,這當然是事實。但是也還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杜甫對于朝廷政治越來越失望了。詩人就是懷著“唐堯真自圣,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二十)的滿腹牢騷,永遠離開了瘡痍滿目的關輔地區,也永遠離開了漩渦險惡的政治中心。
杜甫帶著—家人翻越了高峻的隴山,在秋風蕭瑟時來到秦州。他本以為在秦州可以得到一處避難之所,因為那一年秦州秋收較好,而且他的侄兒杜佐和他在陷賊長安時結識的和尚贊上人都在秦州居住,有希望得到他們的接濟。可是當他到達秦州后,發現那里也并不太平,日益強大的吐蕃正威脅著這座邊城,黃昏時滿城是鼓角之聲,還常常有報警的烽火自遠方傳來。而且杜佐和贊上人都沒能給他很多幫助,他想在城外建一個草堂的計劃也隨之落空。他被迫重操賣藥的舊業,以維持衣食③。
可見,杜甫是迫于安史之亂后長安米貴無法生存以及對統治者的失望而決定逃難西北,他之所以選擇秦州也是想到了親人杜佐與朋友贊上人,因此,想借助親友暫時在秦州避難,待戰爭完全結束再做打算。因此,可以說杜甫的西行,是被動的,完全是因生計所迫,恐非想去隱逸。
凡是論述與農事相關問題,作者在書中總是強調隱逸,如:“在夢想隱居住所的時候,其中必定亦有自己的家園。隱逸而居與開辟農田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對杜甫而言,在表現隱逸的眾多意象中,開辟農田是最重要的一個。”(第246 頁)筆者以為,與寓居秦州一樣,漂泊西南也是杜甫原本未預料到的,也是處于被動,無論在成都還是夔州,杜甫雖也有隱逸的意識,但其行為均屬流寓。“杜甫在成都雖然過了幾年較為安定的生活,對他辛苦經營起來的草堂也懷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內心深處是不愿終老于斯的”。④杜甫在成都作《屏跡三首》,其一云: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毋庸諱言,此詩真實表現了詩人的短暫隱居生活,乃“居士實錄”(蘇軾跋語)。其他文人是心甘情愿享受這份隱逸生活的寧靜與灑脫,而杜甫終究也不開心。此詩第二首即云: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詩人無事可做,百無聊賴,孩子們因失學而變得懶惰,妻子由于貧窮而愁眉苦臉,自己整日醉酒,渾渾噩噩,一個月連頭發都未梳。這種狀態下的詩人,他的“隱居”完全是逼不得已,因此,《屏跡三首》不能不說是杜甫的自嘲之作。無論如何,作者將其界定為隱逸詩,似不大準確。
在夔州的幾年生活也是如此,“直到大歷三年(768)正月才出峽東下。杜甫在夔州居住了將近兩年,此時他的生活還算安定。當時任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的柏茂琳待杜甫甚厚,杜甫得以在瀼西買果園四十畝,又主管東屯公田一百頃,還有一些奴仆,如獠奴阿段、隸人伯夷、辛秀、信行、女奴阿稽等。然而詩人的心情是壓抑的,心境是悲涼的”⑤。“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壯游》)正是杜甫當時生活狀態與心境的真實寫照,絕非是一種隱逸詩人的狀態。
因此,杜甫與陶淵明的區別是:前者“不為五斗米折腰”而選擇隱逸,后者是因沒有五斗米而須從事農業勞動,杜甫為此而“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詠懷古跡五首》其一),過著奔波艱辛的流寓日子。“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雷》),從事農業生產,對于杜甫來說是為了生存而迫不得已的一種辛苦選擇,如果不從事農業,他和他的全家就會遭受饑寒甚至餓死。因此,筆者以為杜甫農業詩似不能等同于古典文學中所謂的隱逸詩。
三、成都杜甫草堂并非園林
《杜甫農業詩研究》一書,通過對成都杜甫草堂外部環境如錦江、浣花溪、橋、江岸、西嶺、村以及鄰居的細致考察,認為草堂是杜甫用來隱居、用來自我拯救的一個園林⑥。如說:“杜甫在詩作中多次提到自己草堂(園林)的所在和周邊的自然環境,這絕非偶然性的描寫。”(第86頁)
我們先來看“園林”的概念。園林,傳統的解釋是:種植花木,兼有亭閣設施,以供人游賞休息的場所。如西晉張翰《雜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現代的解釋(據《漢語大詞典》)是:在一定的地域運用工程技術和藝術手段,通過改造地形(或進一步筑山、疊石、理水)、種植樹木花草、營造建筑和布置園路等途徑創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環境和游憩境域。明代計成《園冶·園說》云:
凡結林園,無分村郭,地偏為勝。開林澤,剪蓬蒿,景到隨機,在澗共修蘭芷。徑緣三益,業擬千秋。圍墻隱約于蘿間,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樓憑遠,縱目皆然,竹塢尋幽,醉心即是。軒楹高爽,窗戶虛鄰,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縵。梧陰匝地,槐蔭當庭,插柳沿堤,栽梅繞屋。結茅竹里,浚一派之長源;障錦山屏,列千尋之聳翠。雖由人作,宛自天開。⑦
很顯然,園林需要精心營構,要地偏,要建屋,要開林,要插柳,要植樹,要曲折,要藝術化,要滿足隱逸者的審美要求。而營構園林則需要大量物資投入,如假山、大石、花草、樹木、筼竹、湖水、房屋、廊橋、亭臺、樓閣等,園林是古人雅致生活的一個表現,也是自我放松的一個精神家園。
關于杜甫草堂,古代文人也有較詳細的注解,如《錢注杜詩》曰:
本傳云: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卜居》詩:“浣花流水水西頭。”《狂夫》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堂成》云:“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懷錦水居止》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然則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可考。⑧
錢謙益長于地理的考證,但在這里他也只是借助杜詩本身考清了成都草堂的具體位置,并未言說草堂是一座園林建筑。杜甫此時期寫過《江亭》詩,其中有“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句,這個江亭是否在草堂之內?筆者以為,這個“江亭”其實就是《高楠》中“楠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制茅亭”的“茅亭”,它其實是浣花溪(錦江)邊可供游人休憩的一個草亭,屬公共設施,并不屬于草堂,但因草堂沒有圍墻,它又離草堂很近⑨,杜甫可以隨時去江邊亭子中休息,因此詩人才能觀賞到“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疏簾”(《晚晴》)的景色。同樣“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的“水檻”也不在草堂之內,而是在浣花溪(錦江)邊。
綜合以上,可以說雖然草堂地偏幽靜,修筑時在周圍也栽種了一些友人贈送的樹木花草,但它充其量不過是個簡陋的農村宅院,由茅屋、樹林與一小塊土地構成,是一個可供杜甫全家暫時居住的棲身之所。杜甫《卜居》《堂成》等詩,主要描寫草堂的修筑過程以及草堂周圍的環境,也不過是“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田舍》)。從中看不出有園林的規模與樣貌。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詳細描寫草堂的情境,“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確是實寫。杜甫作于上元元年(760)夏天的《狂夫》還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江村》也說:“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杜甫一家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雖然在成都時期入嚴武幕府任過官職,但是時間并不久,他的生活也并未因此改善多少。雖然,沒有文獻材料記載當時成都草堂的細節,但可以想象杜甫一家迫于生活壓力居住的一定是一所簡陋的足以棲身的茅屋,包括后來在夔州的住所也是如此。這樣的房子怎能稱得上是園林?
作者想要塑造杜甫隱逸生活形象,不僅對杜甫流寓生活的艱辛認識不足,而且對于杜詩三個時期詩歌中展現的情感與基調缺乏總體把握,甚至美化了杜甫的生活狀態。因此,筆者以為作者似過多關注了杜甫三個時期與農業相關的詩歌,對這一時期的杜甫其他作品則有所忽略,也就是說我們研究這三個時期的杜甫農業詩,必須對這一時期的杜甫所有詩歌以及這些詩歌的整體基調與作者當時的情緒、心理有整體宏觀的關照,否則這種研究就會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之嫌。
四、結語
雖然在隱逸與園林問題上尚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杜甫農業詩研究》一書,對杜甫秦州、成都、夔州三個時期相關農業詩及其物象的關注,研究視角新穎,分析論述細膩而縝密,新意迭出,是近年來海內外杜甫研究中的優秀著作,它的面世,必將推進海內外杜甫詩歌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對于杜甫農業詩這一問題,據此書《后記》,作者似一直以來將其作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而不斷展開,所以是十分具有學術識見的一個選題,也是一項頗具價值的工作,也需引起國內學者的進一步關注。
注釋:
①(清)錢謙益:《錢注杜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本文凡引用杜詩,均出自此書,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②[日]古川末喜著,董璐譯:《杜甫農業詩研究·后記》,《海外中國研究書系·日本學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凡此書引文均不再出注。
③④⑤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8頁、第167頁、第169頁。
⑥在此之前已有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一書,將杜甫草堂納入園林范疇之中。此書作者也有介紹。
⑦(明)計成:《園冶·園說》,陶湘編:《喜詠軒叢書》,民國刻本。
⑧(清)錢謙益:《錢注杜詩》卷十一《狂夫》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71頁。
⑨杜甫《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亦可證草堂建于錦江附近,江亭即錦江之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