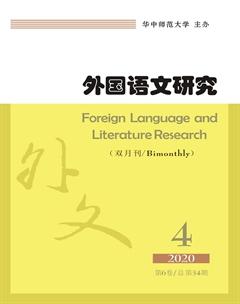《他們眼望上蒼》中現代性與原始性的背離與融合
內容摘要:本文考察并厘清《他們眼望上蒼》中原始與現代之間的關聯。小說中,非裔族群試圖丟棄白人社會加諸其身的“原始”特征,卻被現代性尋求秩序和中心的強勁力量所整改,成為了扭曲的現代主體。佐拉·尼爾·赫斯頓在批判啟蒙理性的同時,倡導復蘇人的原始性以及其與現代性的融合,以期矯正現代性霸權統治感性和直覺而造成的異化狀態。藉此,赫斯頓提出了彌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隙罅的審美救贖之路,重構了以歐美中心主義為基調的現代性話語。
關鍵詞:《他們眼望上蒼》;佐拉·尼爾·赫斯頓;現代性;原始性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美國文學地域主義與審美現代性研究”(批準號:19CWW01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健然,博士,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and clarif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imitive and the modern i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In the novel, the African minority is morphed by the enormous power of modernity that seeks order and center, and becomes distorted modern subject while attempting to get rid of “primitive” features imposed by the white society. Apart from criticizing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Zora Neale Hurston advocates mans identification with primitivity and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primitivity and modernity in a bid to redress the existential status of alienation caused by modernitys hegemonic rule over human sensibility and intuition. In doing so, Hurston provides a way to aesthetic redemption tha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nd reconstructs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featured by Eurocentrism.
Key words: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Zora Neale Hurston; modernity; primitivity
Author: Zhang Jianran, Ph. 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jr2004@163.com
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是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非裔女性作家之一。赫斯頓出生于南方小鎮諾塔薩爾加(Notasulga, Alabama),三歲時隨父母遷居伊頓維爾(Eatonville, Florida),并在這個黑人自治鎮度過童年。如果說紅云鎮(Red Cloud, Nebraska)是地域主義作家薇拉·凱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藝術創作藍本,那么,伊頓維爾則是赫斯頓寫作的素材源泉。在30多年的執筆生涯中,除了發表了大量短篇小說和兩本民俗學著述,赫斯頓也創作了四部或多或少都與伊頓維爾相關的長篇小說。《約拿的葫蘆蔓》(Jonahs Gourd Vine, 1933)的主人公約翰·皮爾遜以作者的父親為原型,他們都從家鄉輾轉至伊頓維爾安身立命。《他們眼望上蒼》(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的故事場景主要設置在伊頓維爾。《摩西,山之人》(Moses, Man of the Mountain, 1939)改寫了《圣經》,講述猶太裔領袖摩西引領以色列同胞到迦南,建立少數族裔自治理想國的故事,而這一理想國的雛形源自赫斯頓曾生活過的黑人自治鎮伊頓維爾。《蘇旺妮的六翼天使》(Seraph on the Suwanee, 1948)雖不著重反映黑人的生活境況,但描寫南方窮白人的世界和佛羅里達州的鄉土景觀,也不失為一部記錄美國現代化進程中南方區域經濟和社會文化變遷的佳作。可以說,伊頓維爾這一南方小鎮乃至整個佛羅里達州是赫斯頓的創作中揮之不去的影子,鑄就了作家立足地域的寫作姿態。因而,赫斯頓可與“馬克·吐溫、威廉姆·福克納、尤多拉·韋爾蒂這三位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土小說概念的作家”齊名比肩(Cobb-Moore 26)。
進入新世紀,赫斯頓研究呈多元化發展。其中,有學者從批評地域主義的視角考察赫斯頓的創作。科博-摩爾將赫斯頓小說的鄉土特色歸納為三類:描寫農業社區伊頓維爾、著墨佛羅里達州的人文地貌以及弘揚門廊口語(Cobb-Moore 27)。在《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文學地域主義》(American Literary Regionalism in a Global Age, 2007)一書中,約瑟夫稱赫斯頓小說為美國地域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其地域書寫關注全球化背景中與流散族裔有關的社會正義和種族正義等問題,也指出作家從“鄉民社區”中尋找到一條通往“種族完整性”的道路(Joseph 124)。這些論述梳理了赫斯頓的地域書寫反映的非洲民俗文化、種族政治和南方鄉土文明等問題,超越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學界偏向談論作家的先鋒女性意識的批評范式,也跳出了后殖民批評家為其作品反映的文化民族主義搖旗吶喊的研究窠臼,但忽視了它參與和反思現代性歷史的問題。
評論家歐文·豪指出地域文學這一文類是“地方主義與世界主義、傳統和現代性劇烈混合的產物”(Howe 25)。一方面,文學地域主義以文學話語的形式記錄鄉土歷史,頌揚地方特色,制衡同質化或男性化的國家話語,具有文化保守主義或性別政治斗爭的傾向;另一方面,它著眼地方經驗,從鄉土的視角審視懷舊與進步、地方與國家、原始與現代等二元對立范疇之間的復雜勾連,也援用實驗性的寫作技巧揭示啟蒙現代性的拙劣影響,對接著審美現代性的歷史。如果說南方鄉土經驗是赫斯頓的地域書寫的題材,那么,參與和反思美國現代性的歷史則構成它的底色。換言之,赫斯頓不僅只為非裔女性而寫作,也不只為弘揚非裔民族文化而寫作,還是為反映南方鄉土文化乃至整個美國現代文化的變遷而寫作。那么,赫斯頓的地域書寫是如何呈現原始與現代、地方與國家等二元范疇之間的關系呢?本文以《他們眼望上蒼》為例,考察小說中原始與現代之間的關聯,以期闡釋赫斯頓的地域書寫重構了以歐美中心主義為基調的現代性話語。
一、現代性的崛起
自啟蒙運動以降,沐浴啟蒙之光的現代主體信奉進步、理性等現代性價值,但壓抑甚至否認人的感性需求。對于立身啟蒙實踐構筑的“大漩渦”中的現代人來講,他們是“現代化的主體和客體”,被賦予“力量來改變正在改變著他們的世界”,也奮力“開辟出他們通過這個大漩渦的道路并將它變成他們的道路”(Berman 16)。唯有如此,現代主體才能進入啟蒙規劃為人類量身定制的文明狀態。然而,在歐美現代性的歷史中,少數族裔被排斥在啟蒙規劃之外。就非裔族群而言,他們被視為“他者”,被主流權力話語定格為“原始”和“未開化”的群體。為了改變“原始”的面貌,他們帶上“白面具”,以理性的面目示人。但這樣的改變割裂了非裔族群與非洲母體文化的天然聯系,使他們陷入了歐美現代性的歷史實踐打造的同質化社會,也使他們的存在成為桎梏自我甚至他人的異己之力。在《他們眼望上蒼》中,赫斯頓通過塑造追隨啟蒙理性的非裔形象,揭示現代性權力收編主體的現象。
小說伊始,主人公珍妮的姥姥勸誡孫女嫁給第一任丈夫洛根·吉里克斯,這一場景映照出現代性權力已逼近南方這一相對古舊的區域。姥姥認為,珍妮與吉里克斯結婚能提升她們的物質生活和社會地位,因為他是一位富有經濟頭腦的白人,坐擁60英畝土地和一棟大房子。姥姥不顧珍妮的意愿,并用自己和女兒的悲慘際遇現身說法,勸誡孫女嫁給年齡比她大十多歲的吉里克斯。珍妮和吉里克斯的結合無疑附著上了物化的色彩,前者迫于無奈,后者是用金錢物化了神圣的愛情和婚姻。這一點決定了婚后吉里克斯漠視珍妮的內心感受,視她為泄欲的對象,也只顧使喚她干活,替他節省人力和物力,累積更多的物質財富。吉里克斯有著強烈的資本主義精神,也散發出濃厚的物質主義氣息。在他和珍妮談論另購一頭騾子的對話中,沉淀于吉里克斯骨子里的資本主義算計理性無處遁形。他講道:“今年我需要兩頭騾子,秋天土豆就值錢了,能帶來大價錢”(Hurston 27)。在他眼中,金錢這一匯聚著現代性幻影的東西才是值得供奉的“新”上帝,而賺錢和獲利才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標。吉里克斯與珍妮的姥姥在認知上一拍即合,他們看重財富,善于資本算計,忽略人的感性需求。他們的思想與啟蒙話語強調的進步和理性等觀念有著家族相似性,他們的通力合作讓珍妮接受了這場“合理”的婚姻安排。本質上講,姥姥和吉里克斯自覺地將自己鍛造為現代主體,卻暴露了現代主體被工具理性所扭曲的人性。同時,他們的工具理性實踐剝奪了珍妮建構自我主體性的權利,也迫使她在刻板的日常生活中消耗自己。于是,不甘被理性主義鉗制的珍妮離開吉里克斯,與喬·斯塔克斯私奔到伊頓維爾。
然而,斯塔克斯也是現代性話語的附和者。“現代性的文化邏輯不僅見于計算和實驗活動中的理性,還在于欲望催生激情和創造性夢想之中”(Campbell 227)。斯塔克斯懷著干一番大事業的“激情”來到伊頓維爾,急于實現他的“創造性夢想”。他帶領村民修路,開設商店,創辦郵局,買地蓋房。在他看來,伊頓維爾需要一個像他一樣精明的領導。在很短的時間內,他把伊頓維爾建為黑人自治鎮,并當選市長。在他的大肆宣傳下,老百姓被招攬到伊頓維爾,“六個星期內就有十家人買下地皮搬到城里”(40)①。他把這個黑人自治社區“搞得有模有樣”,仿佛“建造了一個新世界”(40)。斯塔克斯規劃伊頓維爾的過程涉及精確的邊界繪制,“壓制和排除了一切不可能被精確界定的東西”(Bauman 7)。他認為,“什么都得有個中心,有個心臟,城市也一樣”(40)。在伊頓維爾,斯塔克斯理所當然地占據中心的位置。他對中心和秩序的追求是典型的現代性實踐,其行為的依據與現代性追求統一、絕對和確定性的邏輯如出一轍。可以說,他在伊頓維爾確立中心和權威的過程是一個自我不斷認同啟蒙話語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確證自我主體性的過程。
小說中,斯塔克斯努力掙脫主流社會冠以少數族裔的“原始”特征。他追求進步,尋求中心,據理思考。在他身上,理性主義的力量占據上風,而原初的情感意識則遭到貶斥。表面上,他和珍妮的婚姻羨煞旁人。他雖給珍妮帶來體面的物質生活,但從未讓她感受過婚姻的溫暖和幸福。物質是冷冰冰的、無情感的客體,這與珍妮對夫妻之間平等相待、相濡以沫的婚姻期待相去甚遠,因而,她在日復一日的家庭瑣事和打理商店的沉重負擔下,身心俱疲。加之,斯塔克斯在現代性的同一性思維的撩撥下,以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珍妮。他不僅將珍妮的活動空間限制在家里和商店,還禁止她在商店的門廊上與伊頓維爾鄉民聊天打趣。家庭生活之于珍妮無疑是一個壓抑自我意識的牢籠。在外人眼里,她是擁有榮華富貴的市長夫人。本質上,她是斯塔克斯的免費女傭。倆人維持多年的夫妻關系日趨冷漠,淪為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系。這種關系是現代主體克承同一性思維的效果:斯塔克斯內化了現代性追求中心和權威的邏輯思維,而這種思維外化為兩性之間男尊女卑的二元等級關系。
作為少數族裔的代表,斯塔克斯看似是進步的、現代的,但作為男性,他是倒退的,甚至野蠻的。他援用規劃伊頓維爾的理性準則維系夫妻關系,無疑忽視了妻子的情感需求,也遺忘了自身的真實內心體驗。他的主體性看似凱旋而起,實則走向主體的黃昏,而他的存在是一個異化于自我和他人的狀態。斯塔克斯不僅切斷了女性進入現代性歷史的通道,還將自己變為現代性歷史中被掏空了本能欲望和直覺感受的“空心人”。在珍妮的公開反抗下,斯塔克斯一蹶不振,臥病在床,治療無效,含憾而死。他的死亡溢出了肉體消逝的意指范疇,卻象征著現代人在工具理性的統攝下普遍經歷的主體性之蝕。很大程度上講,斯塔克斯的結局反映了現代性的歷史實踐既解放主體又奴役主體的悖論面相。
伯曼認為,現代性將人們“倒進了一個不斷奔潰與更新、斗爭與沖突、模棱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Berman 15)。在《他們眼望上蒼》中,赫斯頓塑造了被動或主動卷入“大漩渦”的非裔形象。他們都是工具理性的囚徒,力求在現代性的歷史版圖中占得一席;同時,他們都壓抑了感性需求和原初沖動,有著異化的生存體驗。至此,小說敘事映照出的現代性的非人性化力量暗示了置身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的人們,不分膚色和種族,都被裹挾進啟蒙話語構筑的現代性權力的羅網,因為“現代的環境和經驗直接橫跨了一切地理的、階級的、國籍的、宗教的和意識形態的界限……可以說,現代性把全人類都統一在一起”(Berman 15)。
二、原始性的復蘇
赫斯頓創作的時代正值歐美現代主義文學繁盛之時,許多現代主義作家用他們的生花妙筆揭示了現代性的暗啞面。葉芝發出“一切四散,中心不保”的吶喊;艾略特將現代社會表征為“荒原”;龐德稱現代美國文明是“打了補丁的文明”。同時,他們或是透過神話,或是以東方文明為鏡,反觀陷入困境的西方文明,流露出走向原始的回溯性心態,意在“從根本上或存在上重新贖回無形的、偶然的宇宙”(Bradbury, McFarlane 50)。要而言之,現代主義作家罷黜了工具理性的獨尊地位,宣揚釋放人的原初沖動,正視人的血性和感性,掀起了一股“進步或反叛”的文學思潮(Levenson 13)。同樣地,赫斯頓也倡導復蘇人的原始性,加入了批判現代性的隊伍。在《他們眼望上蒼》中,赫斯頓通過描寫珍妮充滿血性和激情的反抗男權壓迫之路,凸顯回歸原始性的裨益,以期解救困囿于現代性“鐵籠”中的主體。
縱觀小說敘事,珍妮是一個向往原始風尚的人物形象,喜好在自然中釋放和回歸自我的感性體驗。一個春日的下午,忙里偷閑的珍妮在自家后院里掛滿梨花的樹下打發時間。打從梨樹掛上第一朵小花,珍妮就在那兒凝視著它,“它呼喚她到那兒去凝視一個神秘的世界”(10)。看到光禿禿的褐色莖葉、亮晶晶的葉芽和雪白純潔的花朵,珍妮激動不已。這些大自然的造物“與引起她感官注意到但又被埋藏在肉體里的其它隱約感覺到的東西聯系在一起。這時它們涌現出來,并在她的意識中潛伏前行”(10-11)。漫步在梨樹下的珍妮向自然敞開她的身體,感應人與自然的互滲性,體悟回歸自然帶給主體的感官愉悅。同時,自然與珍妮之間的互滲感應再現了原初生命的神秘之境,而這種意境對于被啟蒙理性整改的現代人來講是無法理解的,甚至是加以排斥的。正如珍妮的姥姥那一句驚醒她的田園夢境的呼喚一樣,啟蒙理性的刺耳呼聲也驚擾了她擁抱原初生命體驗的夢想。具體而言,珍妮的前兩次婚姻都將她禁錮在現代性的同一性思維澆筑的男權牢籠之中,其感性需求受到工具理性的壓制。福柯曾言:“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Foucault 95)。毫無例外,長期處于情感壓抑的珍妮倍感窒息,愈發喪失真實的自我。在諸多因素的作用下,珍妮身體里的反抗潛流向外涌動,并將她帶上釋放原初沖動的自我救贖之路。
首先,伊頓維爾鄉民的狂歡化精神是喚起珍妮的原初生命體驗的催化劑。小說中,赫斯頓描寫鄉民狂歡的場景,意在表明原始時代那種天人合一、集體狂歡的境界益于消除現代文明帶給主體的疏離感和孤獨感。小說中第一個狂歡的場景是珍妮家商店外的門廊舌戰。作為非洲民俗文化的精髓,門廊舌戰具有鄉土性和表演性的特征,意不在攻擊他人,卻謀求釋放被工具理性所擠壓的價值理性。門廊舌戰談論較多的對象是馬特·博納喂養的一頭騾子。每當馬特路過珍妮家的商店時,鄉民會一本正經地告訴他將有大事發生。半信半疑之中,馬特被告知騾子被用作搓衣板洗衣服。一言未息,又起一言,各種打趣和玩笑撲面而來。有人嘲笑騾子的悲慘命運;有人諷刺馬特的刻薄。幾乎所有的伊頓維爾鄉民都參與這種狂歡化的唇槍舌戰。即使騾子被斯塔克斯買來放生后,關于它的笑料也未曾消失。騾子死后,鄉民們為它舉行葬禮,這構成了赫斯頓設計的第二個狂歡化場景。葬禮上,鄉民們極度浮夸地哀悼騾子的死亡,斯塔克斯也致了悼詞,而那些早已覬覦騾子的尸體的禿鷲所作的悼詞更將狂歡的氣氛推向高潮。列斐伏爾認為,狂歡是“對被現代性壓迫得越來越深重的日常生活的解脫”,它“突破常規,實現感性、審美和自由的存在,使人們體味非理性的文明和反抗工具理性”(Lefebvre 47)。鄉民狂歡的場景呈現了言說自我和打破社會規約的解放前景,傳達了直覺和感性穿透對象抵達生命本質的信息。面對這種狂歡的契機,珍妮希望參與其中,紓解苦悶的家庭婚姻生活中被壓抑的身心,但斯塔克斯“不讓她參與,不希望她與這些沒有價值的人聊天”(53-54)。斯塔克斯對鄉民的歧視和對珍妮的男權統治激怒了她,于是,她在門廊上公開駁斥丈夫,讓他顏面掃地。珍妮的公開反抗是一種擺脫工具理性束縛的行為,預示被壓抑多年的欲望帶著它的原始沖力向外迸發。
其次,斯塔克斯的死亡也是加速珍妮的原始性復蘇的重要原因。在珍妮的公開挑戰下,斯塔克斯的精神受創,久病不起。在他臨終前,珍妮講道:“與你過日子……得把我自己頭腦里的想法擠掉,好為你的想法在我的頭腦中留下位置”(86)。同時,珍妮還指責斯塔克斯:“在這個世界上,如果要得到愛和同情,你不僅要安撫自己,還要安撫別人。而你只安撫自己,從未試圖去安撫別人,凈忙著聽自己說了算的聲音”(86)。珍妮所說的“聲音”意指深遠,不僅道出丈夫在伊頓維爾實施的霸權式統治,還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千百年來西方人引以為豪的羅格斯中心主義。這一象征理性的羅格斯中心主義恰是歐美現代性急速發展的話語力量。因此,斯塔克斯的死亡之于他自身是主體走向毀滅的標志,而對于珍妮,則意味著重生,意味著禁錮她的原初沖動的理性主義之門垮塌。在斯塔克斯的葬禮上,珍妮“把自己的面孔送去參加葬禮,而她自己則隨著春天到世界各地去歡笑嬉戲”(88)。小說中,赫斯頓遴選了一個極富象征意義的場景來反映珍妮的原初沖動即將抵達自由之境。葬禮之后回家的珍妮“燒掉所有的包頭巾。……把頭發編成一根粗辮子,并甩動它,讓它直垂到腰部”(89)。珍妮的行為外化了蟄伏在她的本我中的原始力量,象征著以往強加其身的工具理性統治像包頭巾一樣被毀于一炬。
最后,茶·點心的出現使得隱伏在珍妮身體里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茶·點心是一個輾轉于佛羅里達州的季節工,他在商店買東西時結識了珍妮。作為一個極有音樂天賦的吉他手,茶·點心少了很多珍妮的前兩任丈夫對工具理性的盲從,是一位飽滿血性和愛欲的非裔青年。在與茶·點心接觸一段時間后,珍妮感到“深藏心中的感情從四面八方向她襲來”(108)。倆人的相遇進一步激發出珍妮在前兩次婚姻中被壓制的本能、欲望、肉體等生命的原初沖動,也填補了以往的婚姻生活留下的感情空白。于是,她不顧世俗的眼光,跨越十多歲的年齡差距,步入姐弟戀,并高調地在伊頓維爾鄉民的面前與茶·點心談情說愛。最終,倆人修成正果之后,一起離開伊頓維爾,去佛羅里達州的南部當季節工。從此,珍妮正式開啟了一種簡單的、原始的生活方式。
赫斯頓通過描寫珍妮的原初沖動逐漸蘇醒的過程,表達了她對現代性與原始性、理性與感性等二元范疇之間的辯證思考。實際上,“無論每個文明人的意識發展程度如何的高,在他的心理深層仍然是一個古代人”,或者說如果把人類的心理“追尋至它的起源,它便會暴露出無數古代的特征”(Jung 143)。榮格精辟地總結了現代人的存在聚集進步與倒退、理性與直覺、文明與原始等雙重因素。換言之,現代人是一個亞努斯似的雙面人,有著一個朝向進步、理性、城市、文明等現代性理念的“自我”,也有著一個面向荒野、血性、感性、本能等原始因子的“他者”。在啟蒙理性的加持下,現代性權力一路高歌猛進,將主體身上的原始因子擠出應有的合理位置,導致人們在理性主義、經驗和功利織就的大網中迷失自我,過著違背人性的生活。對此,赫斯頓痛下針砭,通過塑造珍妮這一奮力復蘇原始性的女性形象,呼吁人們關照被工具理性撕裂的感性維度。作為審美表意實踐中的藝術形象,珍妮正視了自身的原始欲望,調和了原始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分野,她的存在無疑為解救處于異化狀態的現代人提供了一個范本。正如周憲所言,審美表意實踐“在恢復被認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實踐理性的表意實踐所‘異化了的人的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潛能”(周憲 158)。毫不夸張地講,小說敘事表征的原始性復蘇是一副糾正西方現代文明中工具理性畸形發展的校正劑。
三、原始性與現代性的融合
貝爾認為,“從人類文明能自我反省之時起,人便向往和懷念原始的洪荒情景。人有一種共同特性,每當邁向復雜前進之時,難免疑懼瞻顧,懷疑整個文明的成就是否有意義。這表明人類返璞歸真的思想源遠流長,根深蒂固”(Bell 2)。自始至終,人類文明集結了無法分離的原始和現代因子。作為“一種內化于全球資本系統中的否定美學,原始性不對立于‘文明或‘西方,卻對抗著全面滲透于資本體系中的新型社會統治”(Etherington 9)。要而言之,原始性不是落后、退化或反現代的代名詞,而是強調人的直覺、感性、激情、血性等原初屬性的集合體,與現代性聯手塑形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審美視野。通常,現代主義作家將原始因素植入文明內部,繪制出原始性與現代性水乳交融的烏托邦景象,并以此發揮藝術的世俗救贖功能,因為藝術的審美維度“對規范理性的極度懷疑”,“能彌補因過度的主觀理性的失敗而造成的損失”(Wolin 73)。無獨有偶,赫斯頓也尋覓能使殘缺的西方文明健全發展的異文化養料,希冀將現代人從“不純和粗俗的現代生活中解救出來”(Berman 30)。對她而言,這種養料來自她的族裔文化,即非裔母體文化素來尊崇的人與自然的契合性和互滲性,也來自她對保存著原始風尚的南方鄉土文化的認同。因而,在《他們眼望上蒼》中,赫斯頓設置了珍妮夫婦在大沼澤體味原始生活的情節,藉此將原始性與現代性置于同等重要的平臺展開對話,想象性地解決了現代性的歷史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不斷對立的困境。
小說中佛羅里達州的大沼澤體現著赫斯頓對原始性與現代性和諧發展的烏托邦遠景的呼喚。大沼澤是珍妮夫婦做季節工的地方,布滿原始的印記。大沼澤的土地肥沃,野草遍地,“路兩旁的野甘蔗遮住了其余的世界,人也充滿野性”(129)。珍妮夫婦把家安在奧吉喬比湖旁邊,他們白天替人摘豆,謀取生計。放工后,他們有時去湖邊釣魚,有時去打獵偶爾還遇見印第安人。晚上閑下來,茶·點心或者給珍妮彈吉他,或者與工友們打撲克、喝酒、唱歌和跳舞。大沼澤的季節工們聚在珍妮家,有的是來聽茶·點心彈奏吉他,有的是來聊天講故事。狂歡之后的困意讓他們難以移步,只好圍著篝火,以天為被,以地為席,倒頭大睡。總之,“他們住在一個挖在地下的狹長的洞穴里面,平靜地以大沼澤地帶特有的、無一定之規的方式謀生”(130)。在此,沐浴原始風尚的人們與自然和諧相處,從不彼此算計,卻友善待人,熱情好客,創造了一種超脫工具理性束縛的感性生活。可以說,珍妮夫婦從伊頓維爾遷至大沼澤的地理流動象征著現代人復歸自然、回歸感性世界的精神之旅。
實際上,珍妮夫婦所在的大沼澤類似于狩獵—采集型的原始社會,體現出民胞物與、不分貴賤的理想生存之境。在此,他們“粉碎了已有社會關系建構的物化主體性,開啟了新的經驗范疇,即叛逆性主體的誕生”(Marcuse 7)。這樣的“叛逆性主體”沖出物質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重圍,回歸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原初關系。相反,在大沼澤開飯館的特納夫人難以認同黑人將情感意志傾注于自然的感性認知,也難以融入他們依靠直覺和非理性行事的生活。她對珍妮講道:“他們笑得太多,笑得太響亮。始終唱著老掉牙的黑人歌曲!總是在白人面前出洋相。要不是有這么多黑皮膚的人,就不會有種族問題”(141)。避開不談特納夫人的種族主義思想,她成為大沼澤的局外人的原因在于她不能理解身邊黑人的玩笑取樂是一種狂歡化儀式,是一種對感性生命的加冕,也是一劑消除自我異化的良藥。本質上,特納夫人屬于啟蒙理性的陣營,是歐美現代性的擁躉,而大沼澤和此地的少數族裔則認同原始性。在黑人占大多數人口的大沼澤,特納夫人孤掌難鳴,便成為眾矢之的。茶·點心和工友們故意奚落她,讓她出丑。一群工人在領工資的當晚特意到她的飯館吃飯慶祝。他們假裝搶位子,鬧紛爭,而茶·點心則假裝勸架,故意攪局,挑起打斗。打斗讓特納夫人的飯館慘遭破壞,她也被踩在地上,手指受傷,最終落魄收場。工友們的打斗看似惡作劇,實則象征處于“邊緣”的原始性向處于“中心”的現代性的強勢回歸。
在原始性與現代性這兩支話語力量的博弈中,小說敘事似乎放任原始性導致社會混亂,甚至有返祖之嫌。至此,赫斯頓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現代人到底是要回歸原始還是守望文明?赫斯頓在珍妮的最終命運中給出了回答。珍妮在大沼澤獲得的幸福是短暫易逝的。一場飆風突襲佛羅里達州的南部,大沼澤也陷入天災。避難中,茶·點心為了救珍妮,被狗咬傷,患上狂犬病。病發時,他產生幻覺,誤以為珍妮要傷害他,于是,舉槍對向珍妮。在僵持不下的廝扯中,珍妮開槍打死了他。隨后,珍妮被控故意殺人罪,而法庭調查和取證表明她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被判無罪釋放后,珍妮重返伊頓維爾。珍妮回到伊頓維爾的行為表明現代人無法倒回原始社會,而她走向原始是為了更好地回歸原有的文明,并對之進行新的文明重組和再生,以期調和人類文明中原始與現代的辯證統一關系。評論家認為,赫斯頓的“伊頓維爾是一個現代性的另類場”(Sorenson 15)。在此,“另類場”既指赫斯頓將原始話語寫入彰顯歐美中心主義的現代性歷史,也指作家將女性經驗融進凸顯男性中心主義的現代性話語,反映了作家對單質化的現代性話語的修正。
在赫斯頓筆下,單純地回歸原始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而任由現代性權力擠壓人的感性也違背人性,更與啟蒙規劃許諾人的幸福生活背道而馳。那么,現代人的出路何在?現代人在理性主義的奴役下早已不堪重負,現代文明也被充滿毀滅性的現代性力量毀損。此時,作為一個可供選擇的文化模式,回歸原始是一劑治療現代文明病癥的良藥,起著抑制現代性膨脹的作用。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言,“如果說文明等同于審查機制的建立,或者因文明疏遠和背離了‘自然秩序而變得不堪一擊,那么原始主義……就提供了一條回歸‘原初和完整自我的路徑”(Armstrong 24)。不可否認,回歸原始在不可逆的現代性大背景中是一廂情愿的烏托邦愿景,而赫斯頓在小說中想象的原始性場景亦是如此。但這種烏托邦敘事是文明的壓抑與反壓抑的產物,反映了赫斯頓尋求精神超越和救贖陷入危機的西方現代文明的理念,而正是這種理念推動著現代人自覺地尋找精神領地,加入改造異化的社會現實的文化工程,進而邁向一個理性與感性和諧共存的新世界。
結語
阿多諾指出,藝術,抑或文學藝術,只有站在社會的對立面,通過獲得自身的社會性偏離,方可表達對“特定社會的特定否定”(Adorno226)。阿多諾所言的“特定否定”無疑是指藝術作品擔綱的批判性揭示和救贖性改造的功能。同樣地,赫斯頓在《他們眼望上蒼》中秉承“否定”現代社會的批判精神,通過揭示現代主體的崛起,揭橥了凸顯歐美中心主義的現代性話語導致非裔群體經歷的異化以及帶給現代文明的負面影響。同時,赫斯頓呼吁現代人通過與原始因子的相遇和碰撞,激發被文明壓抑的原初情感,創造一種原始與現代互惠共榮的文化模式和社會形態。這些題旨增添了小說敘事的審美救贖色彩,也將文學地域主義這一文類寫入了參與并反思現代性實踐的歷史。從這一意義上講,赫斯頓的創作超越了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和激進的女性主義思想,也脫離了地域文學這一文類固守的地方主義姿態,卻從更廣闊的社會歷史層面發出了關照現代文明出路的審美現代性之聲。
注釋【Notes】
①后文只標識頁碼的地方,均出自引用文獻Zora Neale Hurston的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引用文獻【Works Cited】
Adorno, Theodore W. Aesthetic Theory.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New York &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Ltd., 1997.
Armstrong, Tim. Modernism: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5.
Bauman, Zygmund.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91.
Bell, Michael. Primitivism. London: Methuen,1972.
Berman, Marshall.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Bradbury, Malcolm and James McFarlane. “The Name and Nature of Modernism.” Modernism: 1890-1930. Ed. Bradbury Malcolm and James McFarlan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6. 19-56.
Campbell, Collin.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lackwell, 1987.
Cobb-Moore, Geneve. “Zora Neale Hurston as Local Colorist.”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2 (1994): 25-34.
Etherington, Ben. Literary Primitivism. Stanford: Stanford UP, 2017.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Trans. Robert Hurl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Howe, Irving. William Faulkn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1.
Hurston, Zora Neale.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6.
Joseph, Philip. American Literary Regionalism in a Global Age. Baton Rouge: Louisiana UP, 2007.
Jung, Carl Gustave.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1933. Trans. W. S. Delland Cary F. Bayn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Lefebvre, Henri.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I. Trans.Michel Trebitsh. London: Verso, 1991.
Levenson, Michael. Modern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P, 2011.
Marcuse, Herbert.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s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Trans. Herbert Marcuse and Erica Sherover. Boston: Beacon P, 1978.
Sorenson, Leif. “Modernity on a Global Stage: Hurstons Alternative Modernism.” MELUS 4 (2000): 3-24.
Wolin, Richard. 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 Cambridge: Columbia UP, 1992.
周憲:《 審美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Zhou, Xian.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Moderni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 2005.]
責任編輯: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