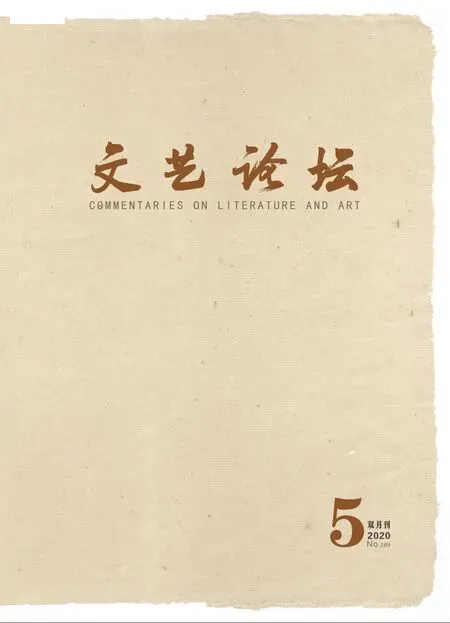創作與批評的互動:多棲文人及其四重面相
——重審文學的多重構成兼及當下批評與創作的互滲
◎ 謝尚發
如果要進行一定程度的追溯,可以看到,在文學誕生之初,因為文與論的未分,創作與評論兼具一體。古代的文學大家,無不是如此,即便不提唐宋八大家的韓愈、歐陽修等直接以散文做論文、以論文做散文,既闡發自己的文學觀念,也把這種闡發本身當做是散文寫作,單單是杜甫、元好問等人,以詩論詩探討文學理論,也足以見出這種文與論的不分狀態來。及至20 世紀,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眾多大作家,無不是文與論兼而有之:魯迅的文學成就自不必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以及論述魏晉文學的專文,也都成為此后研究者所倚重與經常征引的理論專著;茅盾一身兼具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職責,不但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在文學批評的寫作上也可謂是不輸專業文學評論者;哪怕是為文溫婉、以鄉下人身份自居的沈從文,以《沫沫集》為代表的批評文字實則是把批評寫成了散文、把散文當做了批評的典范。其他如周作人、胡風等,無不是在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上都取得了實績的文學大家。學者為文的也不在少數,最典型的莫過于錢鐘書創作《圍城》,成為1940 年代文壇重要的收獲。
情況為之一變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1980 年代以來,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兼具者越來越少。經由1990 年代“重回書齋”文化思潮的影響,此后為文者專事為文,為論者專事創論,似乎成為學界的定規,稍微越界者都要冒著被哂的風險。這種傾向到21 世紀初更為明顯,大量新潮理論繼續引進,文學批評炫技的成分越來越足,而文學創作則也埋頭苦干,試圖用作品證明自我。但這一情況也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漸松動,創作與批評之間開始模糊了界限,尤其是從2012 年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而且聲勢頗為浩大,不是手癢一試的勢頭,反而愈發成為新的專業,作家也同樣不甘于文學創作,更加上2009 年之后“創意寫作”的引入以及駐校作家成為常態,作家們紛紛開起了自己的理論鋪子,借助對作品的解讀來提倡自己的文學觀點,更有甚者,開始以學者們專著的模式為自己的文學理論搖旗吶喊。作家們從一般的創作談、隨筆開始,進入到專業的文學批評領域,學者們從文學批評跨入到文學創作的領域,且形成不小的規模,這一新狀態正在改變著當下文壇的格局,是我們不得不重視的文學現象。當然,重視之余也不必大驚小怪,畢竟,這樣的事情,“古已有之”!
一、批評家的創作:學者們的“抱負”
引起人們重視的,并不在于作家們紛紛開始以專家學者的姿態加入到文學批評的行當中,而是眾多從事文學批評的學者們開始紛紛拿起筆來從事文學創作,尤其是近幾年(2016 年往后更甚),他們不斷推出長篇小說、小說集、詩集,引發了不小的騷動。人們開始以額外的眼光來打量這些作品,重審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系——這些學者們拿起筆來寫作的動力是什么?他們的作品與專業作家的有著何種區別?在追問這些的同時,仔細觀察這些作品,似乎是當務之急,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了不小的規模。進入到這些學者們的文學作品內部,我們才能夠窺見到這種新現象背后所隱藏著的文壇的秘密訊息。為典型計,這里擬選擇李陀和吳亮、張檸作為觀察對象,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影響大,作品所呈現出的特點也比較鮮明。
學者或批評家們的寫作始終帶著一種“理論內部的沖動”,這使得他們的作品基本上都帶著堅硬的質地,主要來源于他們強大的理論能力和理論氣場。這里所謂“理論內部的沖動”,指的是批評家們對文學創作的某種不滿,理論不但未能從作家們的作品中挖掘到顯要的思想質素,反而發現創作愈發平庸起來,連闡釋的動力都幾乎消耗殆盡。這種“理論內部的沖動”自然是來自于批評家們內在的追求:對于創作的庸俗化傾向與低水平重復的不滿,也有對“理論剩余”的不滿,即面對著當下的創作,理論的闡釋顯得多余而無所用途。李陀創作《無名指》緣起于“找不到好的小說”,他說:“如果做文學批評,我覺得找不到好的小說。也許這也是我做文學批評的缺點,我一定要這篇小說感動我,我才會去評價它,如果只是還不錯,是無法引起我的激情寫批評文章的。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想了想,覺得該到寫小說的時候了。”不啻此,吳亮的長篇小說創作也有同樣的沖動,他自信“他的寫作講給當下文學界投下一縷‘曙光’,讓在昏暗中仍堅持文學閱讀的人帶來明亮的盼望”。不滿于當下文學創作,并且親自動手小試牛刀,這幾乎是批評家創作的初衷——他們并非是腦袋一熱的沖動,也非是與作家一較高下的打擂臺,而是“理論剩余”而產生的“理論內部的沖動”,驅動著他們去試圖改變文壇的狀況。在他們的文學批評閱歷中,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是理論創生的基地,且不說巴赫金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提出了“復調小說”的理論,閱讀拉伯雷等人的作品提出“狂歡化小說”以及“時空體”小說,即便是魯迅的寫作也讓一干批評家找到了用武之地。但反觀當下的創作,“理論的無用武之地”,或者說“理論強而作品弱”的局面,催生了批評家的創作。但這里卻并非是要追溯批評家的文學創作沖動的緣由,而是因為“理論過剩”在作品中有著比較鮮明的表現。
諷刺性或諷喻體小說,是批評家進軍文學創作后所帶著的較為鮮明的影響。這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只需要閱讀一下錢鐘書的《圍城》就可見一斑:入木三分的諷刺功底,隱藏在巧妙的敘事之下;處處呈現出詼諧來,卻在詼諧中不是善意的一笑而過,而是懷著沉痛的心去反思、省悟。吳亮的《朝霞》圍繞一個生活于“文革”后期的年輕人,勾連起生活于上海的一幫青年們的情感、讀書、精神乃至家庭生活,就他們的身體欲望、道德、沉思、冥想等來展現之,但其間無不透著知識分子的諷刺、揶揄,甚至是挖苦。只是諷喻體的寫作,并未讓它滑向更遠的地方,進而以不值一哂的價值判斷來終結當下生活的不可理喻,而是在小說中把整全的生活打碎,進而在這種打碎的生活界面,去探索年輕人內在的精神世界的生長。但李陀的《無名指》則反其道而行之,深諳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寫作手法三昧的李陀,故意朝著現實主義的疆土進發,開掘現實社會生活中“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病態”,他們中“最自覺的一些,都不免卷入了一場內心里發生的精神戰爭,并且在其中苦苦掙扎,尋找出路,而另外為數更多的群體,則不好察覺,樂于病態之中,混名混利,實際與魯迅先生所說的庸眾并無區別”。因為是要對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進行剖析,李陀的“反向實驗”就顯得是一種匠心獨運的“諷喻體”,使得“《無名指》以高度現實主義文學的面貌出現,最終成為典型的結構性反諷的文本”。這一“結構性反諷的文本”不僅在文本內部對知識分子進行諷刺,還以文本本身的存在構成了對當下文學創作的某種反諷。在它貌似溫順的現實主義書寫的路徑下,潛藏著對這一創作方法的解構,是典型的打著現實主義的旗號對之進行拆解的游戲。這自然是極高明的手段,但也不得不說的是,李陀的挑戰正是現實主義,即便是把自己的文學創作降低到與當下文壇流行的水平線上,他仍能游刃有余,寫出高水平的作品。若說諷刺性文本,這一點的意義甚至大于文本內部的諷刺性。張檸在其《三城記》中,針對高校知識分子的批評,可謂是入木三分。尤其是那些名教授們的行徑,包括把一個正常的博士硬是給判定為精神病患者,更顯得荒唐,令人啼笑皆非,內里卻是深深的悲涼。
知識分子式的聰明或機智,則是這一類作品的另外重要的特征。從事文學批評多年,這些學者回過頭來進行文學創作,可謂是如魚得水,諳熟于各種文學機制、文學技巧,尤其是在他們這里,很多文學創作的隱秘似乎早已經成為“文學常識”,幾乎不需要額外習得,他們就可以左右逢源,俯首皆是了。且不說李陀的“反向實驗”本身所帶有的書寫的炫技性,即便是吳亮的《朝霞》,也把他早年從事先鋒文學批評的知識全部拿過來,作為創作的基底。“大量的議論性的段落,不停地穿插其間,肆意打斷敘事。不僅如此,有時還干脆出現一些讀書筆記的段落。……議論、隨想、筆記嵌入到故事敘事當中,這也就意味著,生活并非如一般意義上的小說那樣,有著敘事上的整全。”這種拆解文本的本事,并不意味著一般的作家都會采用,恰恰相反,隨著先鋒的式微而逐漸地被遺忘。吳亮以當年先鋒小說批評家的身份重整當年的文學遺產,也就是他所謂的給“在昏暗中仍堅持文學閱讀的人”帶來的一縷“曙光”、一抹“朝霞”。言下之意,當下的文學寫作可能并不是“文學”,而應該是吳亮意義上的文學。于是,在小說創作中,他的重拾當年先鋒文學之道,還文學以文學的面貌,實際上所指乃是對“純文學”的追求。不管是李陀執意使用“反向實驗”還是吳亮采用“拆解故事”的方式,都呈現出諳熟文學技巧之后所帶來的游刃有余,帶著知識分子的機智與聰明。創作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手段,直指文學的問題本身,這顯然與作家們孜孜以求的講故事比起來,更為深刻。另外還可以提及的是張檸的《三城記》,處處都閃爍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聰明與機智,對人物所經歷的城市有著獨到的觀察,對混跡于高等學府的教授們的批評也同樣入木三分,但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怒目金剛式的,而是融入在敘事之中不動聲色的冷眼旁觀中。
還可以指出的是,敘事態度更為從容——他們的小說中都有一種游刃有余的感覺,是才華橫溢斜出的外化,也是不得不傾吐內心文學思想的結果;個性化尤為凸顯——這些作品幾乎可以看作是明顯的個人標簽的產物,不管是李陀對現實主義的“反向實驗”,還是吳亮“拆解故事”,都是印刻在他們身上理論所彰顯出的個人化質素,在1980 年代至1990 年代是被文學批評所承載;知識分子題材居多——這是他們最熟悉,也最能夠寫出東西的題材領域,因此文本中的諷喻、機智也就顯得有所依傍,也顯示出批評家的創作仍然在賡續著錢鐘書的傳統。單就某一個小說而言,還可以指出更多可以觀察的側面,但無論如何,批評家從事文學創作,其所開創的局面的確可以用耳目一新來形容。
二、作家的批評:理論功底與眼光
作家從事文學批評不是罕見的事情,尤其是近年來為了配合宣傳與雜志欄目設置而來的“印象記”,既是隨筆性質的寫人散文,也是傾向于專業的文學批評的論文,盡管他們采用的是文學的筆法,不可否認的是,在對言述對象的文學創作進行剖析的時候,已經是帶著批評家的眼光了。更由于創意寫作學科的引入與作家駐校制度的普及,許多作家因為要“開壇設法”而不得不進行大量的理論性講述,預備大顯身手,把自己的創作理論化。也因為要拿出一些有分量的大部頭,哪怕是講稿,他們紛紛開始轉向文學批評,解析、品評行內人的作品,也開始講究專業性的眼光。這其中的代表是王安憶與閻連科,以及高校任教的格非,甚至是更年輕的李浩。前兩者是創意寫作篳路藍縷的功臣,為了配合講課的需要,大量寫作文學批評的文字,對中外文學進行剖析,呈現出一種新穎的批評的品質。王安憶早在21 世紀初,便開始以專業人的身份出現在高校的講壇,陸續出版了《小說家的十三堂課》《小說課堂》等比較專業的作品。閻連科稍有不同,最開始他的批評文字主要集中在為自己的文學主張辯護、搖旗吶喊,不遺余力地宣揚“神實主義”,后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駐校作家,一手操辦了人大的創造性寫作作家班,在任課的要求下逐漸轉為較為內行的文學批評者。格非則情況更為特殊,作為華東師范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長期任教于清華大學,甚至都很難辨認得出,他到底是一位作家然后從事文學批評的人,還是一個學者轉而進行文學創作的人。理論的專業素養、學者的培養方向、理論傳授的必然要求等,都讓他的身份顯得格外迷離。這也正彰顯了當下批評與創作的融合趨勢,二者已經是難分難解的狀態了。
解讀這些作家們的文學批評文字,其特點也格外地突出。首先,他們帶著作家獨有的敏銳,進入文本的角度與深度是沒有寫作經驗的批評家們所無法企及的。王安憶在一篇分析莫言的小說世界的文章中開頭就說:“莫言有一種能力,就是非常有效地將現實生活轉化為非現實生活,沒有比他的小說里的現實生活更不現實的了。”緊接著概述《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并且將之與劉慶邦的小說進行比較,從而凸顯莫言小說世界中不可控制的力量等的元素導致了小說世界與現實生活世界的斷裂。說實話,這種問題在專業的批評家看來,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已經是自明的問題,現實主義理論早就對之進行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但在王安憶的筆下,卻并沒有給人拾人牙慧、老調重彈的感覺,反而很清晰、很輕盈。她在小說文本之間穿梭往來,用了作家獨特的眼光去觀照莫言創作的特質,指出了莫言小說世界與現實生活世界的斷裂,其實已經概括性地剖析了莫言的文學作品。這種另辟蹊徑的方式,靠的就是作家的直覺——能敏銳地把捉住文學文本中的獨特構成,從而使論述別具一格。閻連科的《自然情景:決然不是人物與情節的舞臺與幕布》,更體現了這樣一種傾向。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類似于創作談的文字,然而理論性卻十分鮮明,因此它被發表在十分專業的期刊上。如果抹去作者名稱,已經很難分辨出作家的痕跡。文章從失敗的自然情景呈現和風景描寫入手,翻而一轉,強調“在故事中,有才華的作家,高度地完成了客觀存在的自然環境與文學人物的行為及內心的聯系與統一”,接著羅列《老人與海》《白鯨》《魚王》《瓦爾登湖》《獵人筆記》等作為例證,再轉入對杰克·倫敦《熱愛生命》的分析中來,一氣呵成,圍繞著核心論點層層推進,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家作品論。它同樣以作家的創作體驗,敏銳地捕捉到作品中的獨特訊息,從而提出環境描寫這個看似陳舊卻十分有必要進行分析的話題。再以李浩分析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為例,“音樂性語言”“小人物及其平淡的社會關系”“散文化結構”等解讀的角度與路徑,已經呈現出十分專業的文學批評的理論素養,并且帶著獨具個人眼光的作家敏銳,分析得透徹、貼切,真真是貼著文本前行的典范。其實不必過多列舉例子,當作家從事文學批評的行當,他本人的創作經驗定然會以某種方式化入文章之中,且提供了不同于專業批評家們所無法體察到的文本內在的隱秘。
多關注文本的“創作性問題”,是作家所提供的批評文本呈現的另一重要特征。即便所針對的是比較專業的文本,他們進入的角度或者關心的問題,始終圍繞著“創作性問題”,即寫作的技巧、文本的技術性問題來展開,但這些似乎往往是專業的文學批評所照顧不到的——他們更傾向于探尋文本中思想性、時代性等比較宏觀的問題,對于“怎么寫”所關注的確實較少,盡管人們也完全有理由可以宣稱,剖析一個文本不管是哪方面,其實都在探討這個文本是“如何生產的”。在課堂上需要精心備課的作家們,拿出壓箱底的東西,往往是切身的創作體驗,用了別人的文本來進行呈現。閻連科在解讀了19 世紀文學之后,轉過頭來于近年又開始剖析“20世紀文學寫作”,并在專業文學批評雜志上開設了專欄,分別就“人類異經驗”“地域守根”“第三空間”“反諷”“非故事”“精神經驗”“迷宮”“心緒”“敘述與結構”“寓言”“元小說”等專題展開論述,所涉獵的作品、所鉤沉的寫作問題,實在是一般文學批評者所無法觸及的。在算是開講詞的文章中,他提出:“寫什么,終歸是人類——作家、讀者、批評家共同面對的問題,而怎么寫,卻更多是作家個人必須獨自面對的問題。”在這一主張中,不但直陳了批評與創作的差異,實際上也陳述了作家從事文學批評對“創作性問題”的格外關注,而非是文本的“思想性問題”。這里可以明顯看出作家的批評與學者的批評之間的差異。再以格非解讀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為例。在開篇介紹作者生平等的時候,乍看上去似乎他要沿著一般文學批評的路數前進了,但是接下來很快就過渡到對作品的“創作性問題”的剖析——“架構與肌質”探討的是小說“織體的圖案極為精致細密”(這里言及的“織體”就相當專業)、“平行行動”關注的是“小說的情節樞紐和敘事驅動力”……說實話,這些“創作性問題”也可以被看做是文學批評所經常關注到的,尤其是“知識與話語”“科學與道德”“關于個性”“情感問題”等,也足以表明實際上作家從事文學批評,的確在逐漸地消弭與專業學者之間的差距,也消弭了“創作談”與“文學批評”之間的裂縫。李浩分析莫言的《枯河》、王安憶解讀《包法利夫人》等也都體現著“作家的文學批評”的特質端倪。
文本細讀的方法,是作家們從事文學批評最為常用的方法。當然,這一方法也是許多專業的文學批評者所采用的,但這其中卻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作家們往往會貼著文本的故事朝前走,體察在文本各處所彰顯的創作者的功底、神采,而批評家哪怕是用了細讀文本的方式,也跟隨著文本走,卻是要挖掘文本所潛藏著的更為豐富的質素,并將之張揚出來;作家的“知人論世”是為了理解創作者所付出的那一份辛苦,揭示文本背后創作者的付出,而批評家的“知人論世”則更多是要厘清作者本人的經歷如何影響著其創作的文本,如何從作家的個人經歷中尋求破解文本秘密的鑰匙……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王安憶分析朱天心的小說,就十分具有代表性。在分析了朱天心的《威尼斯之死》《古都》等作品后,王安憶總結道:“朱天心小說就很像是一場較勁,看誰能較過誰,這場較勁終是會留下蹤跡,這大約就是朱天心的新小說。”這是貼著作家創作的心路歷程而來的對文本的解析,但整個文章的構成則是圍繞著兩個文本來組織的,尤其是對文本內容的概括,構成了比較重要的一環。幾乎是同樣的路數,閻連科在解讀瑞典作家謝爾·埃斯普馬克的《失憶》時,在小說的開頭就頗有“夫子自道”意味地感嘆說:“如果一九八七年寫就的《失憶》是在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來到中國,那么它的作者埃斯普馬克將會在中國暴得大名,如同當年的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和之后的昆德拉等一樣,因其敘述的別樣,讓中國的讀者、作家、批評家對其敬若神明,宛若文學的旱田中突然流過一道汩汩不絕的潤田甘水。”大有生不逢時的感慨與喟嘆。這與他本人的創作及遭遇也是密不可分的。在他這里,所謂的“知人論世”更有了自己切膚的體驗在其中。但整篇文章,卻又都全部圍繞著小說文本,進行一層又一層的解讀,指出其不受重視的原因的同時也挑明了其獨創性。
在同一篇文章中,閻連科還說:“《失憶》命定在中國不會有熱鬧的廣泛和群呼的讀者,但它給東方(中國) 寫作帶來的啟示性意義,將會在日后漸顯而明白,一如浩瀚的戈壁中那束遙遠的光,終會被更多的人看見和發現。”引用這一句話是想說,作家從事文學批評的工作,所攜帶著的這種種特點,實際上都是密不可分的,其緣由便在于他們是作家——他們會帶著作家獨特的感受去體貼創作者的甘苦,去理解其中的奧妙。他們的敏銳,來自于長期寫作所積累的經驗;他們關注于“創作性問題”,是因為閱讀對他們本身而言也是助力寫作的一方面;他們選擇文本細讀,是要在這讀的過程中,去發現寫作者的隱秘,從而將之公諸于世,獲得可觀的評價。如此一來,他們所攜帶著的這種種,既讓他們的批評文字區別于專業的批評家,也并未降低他們批評文本的專業性、理論性,反而具有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作家們所引導的這一波“文學批評的浪潮”,正在逐漸改寫著當下文壇的文學批評的構成面貌,且在未來將會有更大的影響,因為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投入其中,其規模不容小覷。
三、多棲文人的四重面相
當下,“斜杠青年”的稱謂正逐漸成為許多從事文學志業的青年們的標簽,這一特定稱謂背后所揭示的,正是批評與創作的逐漸融合,以及多元化的發展現象。但與其說“斜杠青年”令人眼前一亮,不如說“多棲文人”才是最恰當的稱呼,因為青年總會成長,而“多棲文人”也愈發成為不止是青年的一個獨特群體,其逐漸龐大的團體構成也彰顯了“斜杠青年”繼續擴容的必然。“多棲文人”現下已經成為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可謂是“文學新現象”之一,因此去整體把握這一現象也是勢在必行的事情。回過頭來,重新提及“創作與批評的互動”這一話題。嚴格來說,所謂的互動,實際上表征的是創作與批評之間的分裂,其間的裂縫已經巨大到難以彌合——批評家不滿于當下文壇的平庸與疲乏而奮起創作,作家則為了宣傳自己而進行批評,內里也彰顯了批評對創作的無能。它并非是良性的,甚至是惡性的開端,但卻不能就此判定這意味著一個更壞的結果在讓作家和學者們自投羅網。恰恰相反,它們重新激活了文學的傳統——不以知識、才情判定文學的時代即將開始,它呼吁重新回歸文學,既包括文學的才情、天賦,也包括文學的知識、智性,不是使之各自彰顯,而是融合為一。這可謂是“多棲文人”帶給當代文學最為豐富的資產,也是其價值和意義所彰顯的地方。
無論是批評家從事創作,還是作家們從事批評,都彰顯了文學作為“思想的事業”業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批評家們試圖從作品中去挖掘可以形塑時代的思想,而作家們也努力要保持對社會的洞穿與燭照,把握時代的脈搏。但當他們互換角色之后,盡管標志著批評與創作之間裂痕的產生,卻無意間仍舊體現出“文學乃思想的事業”這一基本的判斷。吳亮在《朝霞》中哪怕是從文本形式上進行先鋒的重回,但內里也仍舊是關注著日常生活,從而在還原日常生活的同時去觀照那些普通的人物及其命運,難怪有文章會指出:“《朝霞》中真正令我驚訝和贊嘆的,倒不是他眼花繚亂的文體、洶涌句法和敘事時間的游戲,而恰恰是他生動還原日常生活場景的素樸能力。”這一能力的贊許,實際上是對批評家從事文學創作的肯定,也因為這一能力的獲得,讓吳亮在小說中一試身手,去挖掘時代的思想性,被認為是“通過個人對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私人記憶,闡發作為時代洪流中的普通群體對歷史、政治以及生活的哲思。”而在對李陀的《無名指》進行解讀的時候,也有文章認為這“是一部深陷于時間的迷宮中難以重返現實或不能進入現實的失敗者的精神備忘錄”,在其中“歷史、現實、失敗者和精神救贖”成為解讀這部小說的關鍵詞。更有甚者,以李陀的個人經歷,串聯著先鋒文學、人文精神大討論等來解讀這部小說,認為這些精神性要素促成了小說的誕生,并讓其擁有“批評家小說”的質素。不唯此,閻連科在解讀20世紀小說之時,雖然是著眼于寫作技法、創作性問題,但其中同樣包含著對小說的思想性的關注,比如他提到“地域性和守根性”,并認為“對于求根、守根的作家言,一切‘復古’的回歸與求守,都是從他那最獨特的一片母地開始的。沒有這一片屬于他的母地的存在,也就沒有他的全部的寫作,沒有他文學的生命,沒有他的被視為偉大的作品”。文中所提到的“母地性復古”,可謂是對這一創作潮流的精準概括。在分析周瑄璞的長篇《日近長安遠》之時,李浩也是圍繞著小說的女性主義思想,以及由此而呈現出來的“女性之命運”而做文章,指出命運與選擇之間女性的困擾。不用再列舉更多例子,“文學作為思想的事業”這一命題,無論在批評家那里,還是在作家那里,都是亙古永恒的命題,不管他們的操持著理論性的批評文字,還是文學性的審美文字。這一命題在當下尤為凸顯,概因為批評與創作之間的互動,促成了這一命題的集約化。這也意味著,所謂的批評與創作的分裂,也只存在于形式上的喧鬧,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不滿,也只停留于表面的層次,內里他們仍舊從屬于文學的本質。
還必須看到的一點是,隨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文學越來越從天縱之才的獨有屬性轉向一種知識的普遍狀況,因此在批評與互動的過程中,呈現出的知識性傾向,也愈發地明顯了。理論已經不再為少數的人所獨有,尤其已經不再是批評家的專屬,它愈發呈現一種普及的狀態,越來越多的作家在創作之余對理論不但熱衷,而且深諳其中。同樣地,對于創作而言,許多寫作的訣竅或秘訣,也逐漸褪去天才的神秘外衣,被規整為一系列的文學常識,從而呈現為知識性的可以習得的理論。這首先體現在作家們的文學批評上,他們越是關注文學創作的技巧性問題,用作家的敏銳性來貼著作品走,越是把看似屬于作家所獨有的寫作秘訣公示于人,成為可以被歸納和總結的文學知識。閻連科總結20 世紀文學問題的指向,其中之一便是作家能夠從中學習到什么,以便能讓他的類似于講義的文學批評給講臺下面的學生們以啟發與教益。在對敘述與結構進行剖析時,他首先以建筑來觀看小說的結構,再來強調小說寫作從故事、人物、情節轉向敘述的趨勢,并且強調“敘述與結構,是作家創造才華的跳跳板,每一個踏上去的作家,其跳姿和高度都一定不一樣,落下時給觀眾帶來的驚艷、訝異和庸常之態也是絕然不同的”,并進而就外結構、內結構兩個方面進行論述,指出看得見的結構與看不見的結構支撐著文本的建立。李浩在分析邱華棟的小說之時,指出其作品中“大量知識性因素”等造就的“知識性和故事性相融合”,從而彰顯了一種“百科全書式寫作”的誕生。這是他分析邱華棟的創作,也同時彰顯在他本人的寫作與批評之中——作為知識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既是理論與實踐的融合,也是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的結合:批評家們的文學創作,是實踐著他們所主張的文學理念,從而讓理論走向實踐,作為證明,也是作為另一種闡釋的方式;作家們的文學批評,則是讓創作實踐逐步知識化,從而讓不可捉摸的創作變成是可以傳授的技能,從而實現理論化。李陀和吳亮的創作,都帶著獨特的理論的目的前行,在寫作中穿插的文論、議論、筆記、哲思,甚至是直接抄錄相關的理論文字,實際上已經把創作的自由度極大地進行了擴張,而閻連科、王安憶、格非、李浩等作家們也并非僅僅只是停留于對寫作的一種歸納和概括,他們也操著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元小說等為批評家們所熟知的理論來進行文本闡釋的工作。整體上來說,不管是理論從批評家向作家的讓渡,還是文學知識不但是理論的嘗試,也是文學創作的嘗試,文學的知識性特征在批評與創作的互動中顯得格外明顯。
其實,如果還在驚奇與歡呼作為一種文學現象的“批評家小說”或“作家的文學批評”,也許是當下許多人對文學的陌生與幼稚。最為根本地來講,即便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仿佛是不同的志業,在朝著不同的方向持續推進,然而批評朝著創作而去的努力從來都未停歇,只需要看看許多批評家的文章就可以看得出端倪,哪怕是李陀、吳亮等人,也都在批評文章中操著文學的腔調。與此同時,作家們的創作即使更強調詩意與靈性,但他們的觀念與理論水平也并非是止步不前,純粹地靠著天賦與才情來延續文學生涯。因此我們針對這種現象,尤其是當下越發熱烈的批評家小說與作家的文學批評,需要看到的是“審美的雙重性”問題,或者“文學的審美二重性”質地,即理論與創作都統屬于文學,它們可能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現,但卻不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始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哪怕是在文學創作中,批評家們仍然保持著他們文學文本的理論性,《朝霞》中隨處可見的筆記與哲學沉思,《無名指》 中散落著的論文的片段,就是最好的證明;哪怕是在文學批評中,作家們也仍然秉持著創作的風貌,而非是枯燥乏味的理論文字的堆砌,相反在對小說進行概述的過程中,可以看出細膩的敘述功底與超凡的寫作技能,比如王安憶對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說的描述、對莫言小說故事的概括;閻連科在敘及美國“黑色幽默”這一文學現象時,既是用“反諷”以概括之,也像是講述一個多人參加的故事一樣娓娓道來。之所以要重提“審美的雙重性”或“文學的審美二重性”,并非是要舊調重彈,而是要在批評與創作的互動中,看出它們所彰顯出的文學發展的趨勢來。這對于“多棲文人”來說,已經是他們心中默認的事實,也許還是他們對自我的期許。
最能體現“多棲文人”及其文學特色的,應該是在批評與創作的互動中所展現出的綜合性特質。借用李浩對邱華棟創作的指認,這種綜合性實際上意味著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寫作”。如果宣稱這樣的文學時代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時代”還顯得有所夸大的話,那在批評家的小說與作家的文學批評上,則完全可以如此宣稱。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個文學的綜合性開始逐漸成為嘗試的年代,如果作家僅僅只是停留于純粹天賦與才情的文學創作,雖然他們已經完成了作為作家的職責,卻也少了許多可資討論的話題。諳熟文學理論,精通文學創作,兩者兼而有之,并且融合為一,文學創作因更多理論與觀念的加入而越發顯示出銳意革新的特征(先鋒文學某種程度上在悄然流行就是一個明證),文學批評也越發顯示出更多審美的氣息來,而非是呆板的、枯燥乏味的文風(青年一代的批評家更是強調文學批評的文學審美性),都是批評與創作互動的前提下文壇所呈現出的新特質。批閱批評家的文學創作和作家的文學批評文本,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傳統對于天賦、才情的強調,在繼續發揮著影響,而對理論的熟悉、綜合素質的提升,尤其是文學的知識性與思想性的存在,也已經被逐漸地凸顯了出來。因此,閱讀,不僅是對文學作品的閱讀,也包括對理論的閱讀,成為當下默認的行規,“多棲文人”的存在,恰好典型地體現了綜合性的發展趨勢。廣涉文學領域的各個側面,并且熟稔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各門知識,已經越來越為“多棲文人”所重視,旁征博引、奇思妙想,這對于推動文學的發展,確實大有裨益。這也是“多棲文人”存在理由。
仍然需要再一次重復,當我們談及創作與批評的互動之時,實際上正在觸碰一個古老的文學問題,它是被重新恢復,而非是新時代賦予它全新面貌。“百科全書式的時代”是否已經來臨,還處于晦暗不明的狀態,但在文學的內部,逐步恢復其起始階段的融合為一狀態,已經是必然的趨勢。“多棲文人”帶著他們的四重面相,即知識性、思想性、審美的雙重性、綜合性,正在改寫著近代科學興起以來對文學造成的人為的分門別類的劃分情況,以新現象的方式恢復文學的古老傳統,正預示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來臨。有理由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批評家從事文學創作,也會有更多的作家加入到文學批評的行當中來。
注釋:
①較為典型的代表包括吳亮和李陀,他們推出了《朝霞》《無名指》這樣的長篇,更重要的是,吳亮還在繼續著他的文學書寫,最近又出版了《不存在的信札》。按照當前的架勢,這一寫作趨勢應會繼續下去。青年作家中,這一類的代表有楊慶祥、李云雷、房偉等人。我本人也在努力嘗試著在做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之余,進行文學創作。這并非是搶地盤,或者要彰顯自己的才能,而是試圖以此來讓批評與創作進行互相的印證,使得文學批評能有文學創作來進行一定程度的印證,也讓文學創作能夠文學批評的理論視角與思想深度。
②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閻連科與格非二人。閻連科為了鼓吹自己開創的“文學主義”,后被命名為“神實主義”而不斷出版專著,比如《我的現實,我的主義》《發現小說》《寫作最難是糊涂》等,包括他一系列的文學講稿類的文字,比如《閻連科的文學講堂》,包括“十九世紀卷”和“二十世紀卷”,以及最近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格非這方面的主要作品是剖析《金瓶梅》的《雪隱鷺鷥》,解讀博爾赫斯的《博爾赫斯的面孔》、解讀卡夫卡的《卡夫卡的鐘擺》,更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了《小說敘事研究》這樣的專著。
③以吳亮和李陀為例,他們的長篇小說出版之后,獲得的待遇與作家是等同的,甚至因為他們一直處身于文學批評的行當,引來的各種評論有時會比作家多,因此也顯得更加“熱鬧”,從而某種程度上也好像是搶作家的“飯碗”。只需要看看《無名指》《朝霞》出版后所獲得的各種批評資源的青睞與眷顧,就可以明白這種情況。孟繁華、徐勇、黃平、黃子平、程德培等,都撰文對這些作品進行解讀,甚至作家李洱也都開始參與其中了。
④李陀:《20 世紀文學成就不如19 世紀》,《新京報》2012 年6 月11 日。
⑤⑧張閎:《吳亮長篇小說<朝霞>及當代小說的敘事問題》,《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5 期。
⑥李陀:《我在寫作上的一次反向實驗》,“收獲”微信公眾號,2017 年7 月29 日。該“創作談”以配合小說的發表、宣傳的面貌出現,李陀也寫得很“真誠”。
⑦黃平:《如何從現代主義中拯救“先鋒文學”?——細讀李陀<無名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 第12 期。
⑨王安憶:《喧嘩與靜默》,《當代作家評論》2011 年第4期。
⑩閻連科:《自然情景:決然不是人物與清潔的舞臺與幕布》,《揚子江評論》2016 年第4 期。此文系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學所開設的寫作課《19 世紀寫作12 講》的第八講講課稿,由此也彰顯出作家從事文學批評的動機及其必然性。
?李浩:《作用于情感的“渦流”以及背景依賴——重讀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 年第4 期。
?閻連科:《20 世紀文學寫作:精神經驗——20 世紀文學的新源頭》,《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1 期。從這一篇文章也可以看出,這同樣應該是閻連科的“文學講稿”。
?上述引文參見格非:《另一個地方,另一種狀態——羅伯特·穆齊爾<沒有個性的人>(上)》,《揚子江評論》2019 年第3 期。
?這些論述,可參見格非:《另一個地方,另一種狀態——羅伯特·穆齊爾<沒有個性的人>(下)》,《揚子江評論》2019 年第4 期。
?李浩:《隱喻的叢林和現代性書寫——重讀莫言<枯河>》,《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 年第5 期。
?王安憶:《殘酷的寫實——重讀<包法利夫人>》,《讀書》1999 年第11 期。
?王安憶:《刻舟求劍人——朱天心小說印象》,《當代作家評論》2009 年第4 期。
??閻連科:《“心緒”與“事緒”的西中敘述——讀<失憶>所想》,《東吳學術》2013 年第2 期。
?張定浩:《那些來自寒冷的人——吳亮< 朝霞> 讀記》,《南方文壇》2017 年第1 期。
?張福貴、王文靜:《反閱讀邏輯的“不均衡寫作”——評吳亮的長篇小說<朝霞>》,《當代作家評論》2017 年第4 期。
?徐勇:《如何在時間的迷宮中重返現實?——關于李陀<無名指>的四個關鍵詞》,《百家評論》2019 年第3 期。
?可參見何吉賢:《批評家小說:啟示與問題——關于李陀長篇小說<無名指>的討論》,《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 年第2 期。
?閻連科:《20 世紀文學寫作:地域守根——現代寫作中的母地性復古》,《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6 期。
?相關論述可參見李浩:《向女性發問,向生存現實發問》,《小說評論》2019 年第6 期。
?閻連科:《20 世紀文學寫作:敘述與結構——寫作中的新皇帝(下)》,《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3 期。
?李浩:《“百科全書式寫作”與自我的實現——略談邱華棟的小說創作》,《寫作》2019 年第4 期。
?閻連科甚至在文章中做了批評家都不太做的工作——追溯其“元小說”概念的發展歷史,并概括其諸多特征,以及它對20 世紀文學的貢獻。參見閻連科:《20 世紀文學寫作:元小說——還原了寫作與閱讀的寫作與閱讀》,《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3 期。
?在吳亮的《朝霞》“0”節中的一段文字就特別鮮明:“不是拒絕歷史難題,而是無力談論歷史難題,甚至不相信有可能為自由談論歷史鋪平道路,反諷,戲仿,懷疑,申訴,揭露乃至不屈不撓地抗議與否定,都試過了無數次,嘩啦啦嘩啦啦,不討論,裝作看不見,拖延,模糊是非,夠好的了,他最煩那些喋喋不休的理論,一個既定目標,一套清晰的計劃,一組區分好壞善惡的標準,自上而下推動的運動,一個接一個的形式,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似乎為了獲得某種效果,使這個龐大機器運轉正常,還不僅如此。”參見吳亮:《朝霞》,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年版。
?可參見王安憶:《華麗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當代作家評論》2005 年第5 期。
?可參見閻連科:《20 世紀文學寫作:反諷——關于一種態度與立場的寫作》,《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