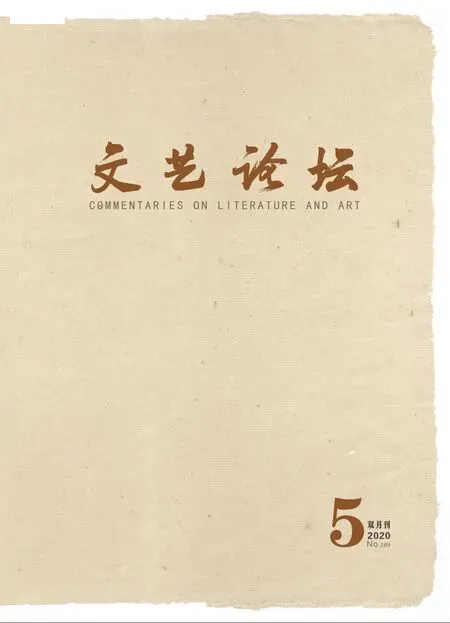批評寫作的創造性
——關于賈想
◎ 張 檸
2016 年冬天,一位高個兒男生突然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說他獲得了保研的資格,想跟我讀研。跟他隨便聊了幾句,得知是山東人,膠東半島渤海灣附近。我一琢磨:齊人。齊人近楚,似乎跟本人有些瓜葛。本人乃古九江郡梟陽人氏,祖居彭蠡大湖深處,文化上是吳頭楚尾,風格和心思更親楚。第二年秋天,男生成了我的學生,他就是賈想。
盡管是齊人,賈想并不是生活在蓬萊山或者方壺島,而是從小在農村的泥土里長大,故鄉是膠東半島西北角丘陵地帶的一個鄉村。他的身上,同時繼承了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特點,既有豐富的想象力,又有踏實的耕作精神,骨子里還有濃郁的儒家文化傳統,溫柔敦厚思無邪,但也會經常暴露他那“蓬萊夢語,瀛洲海談”的詭秘性。
賈想曾經寫過一首詩,叫《農民的兒子第一次坐飛機》,發表在《星星》詩刊上。大致的意思是說,農民的兒子要坐飛機了,興奮激動。過安檢的時候,為了能順利過關,農民的兒子打算卸下一切能夠卸下的東西,卸下現代飛行器所不能容納的一切累贅,卸下了膠東半島、丘陵麥地、晨露秋霜、蛙叫蟲鳴,甚至卸下了衣衫內褲,裸身去接受檢查。但農民的兒子依然感到局促不安,恍惚聽到安全警報器猝然響起。直到在半空云端飛行時,農民的兒子還在從里到外檢點自己,包括內臟和思想。估計碰響安全報警裝置的東西,是那個無法卸去的古老農耕靈魂。那些卸不掉的東西,接著又變成飛翔的小鳥、史前的云朵,排著隊列,跟飛機一起飛行,直奔目的地機場,去跟那些登機前卸下來的東西匯合。匆匆趕來的,還有那個半空中跳傘的“農民父親”意象。在這里,飛機安檢的“排異功能”,轉變成文化或文明傳承過程中的“排異功能”。我覺得,整首詩的思維夠“詭秘”的,帶有明顯楚(齊) 文化基因,跟魯(周) 文化有距離,但是結尾還是忍不住露出了魯(周) 文化的小尾巴。
我對賈想能將復雜的現代性問題轉化為清晰的意象這一點很感興趣。這種能力,不僅對文學創作有效,對文學批評同樣有效。我不打算繼續對賈想的文學創作多說什么。寫詩和寫小說只是他的副業。他的主業自然是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批評。
讀研究生的時候,賈想就在知名報刊發表了不少的文學與文化評論文章。其中,有些是我安排他寫的,有些是他自作主張寫的,還有一些是我們倆“結合”的產物:“領導”出思想,作者出技術。記得2018 年7 月下旬,我應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之邀,到北戴河參加一個跟“現實題材”和“青年寫作”相關的理論務虛會。我將在會上的即席發言要點,在微信上發了出來。《光明日報》文藝評論版主編王國平先生對話題感興趣,希望我能將發言要點寫成文章。但由于我一回到北京,就要去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的封閉式評獎活動,寫文章的任務就落到了賈想身上。賈想根據我微博上的百字簡短提綱,三天之內就寫出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文學期待新的現實主義》,以我們兩人的名義,發表在24 號的《光明日報》文藝評論版。文章縱橫開闔,語氣老道,儼然老同志口氣。這篇文章后來成了2019 年湘贛十四校高考模擬試題的閱讀材料和多項選擇題。我對賈想理解能力、問題意識和寫作速度表示吃驚。年紀輕輕,竟然能模仿老同志的口吻寫理論文章,完全是為了照顧我的面子。
看看他單獨寫的文章,則是另一番風景。那篇發表在《文藝報》上的《“廢柴”也有春天——男頻小說的主人公》一文,是一篇關于網絡小說人物形象的分析文章。賈想首先把“廢柴”形象納入網絡文學的人物譜系之中,認為他是“男頻主人公”的一個當下變種,讓這個新的形象一下子就清晰起來了。傳統網絡小說的“男頻主人公”是熱血男兒型,屬于古典英雄的現代翻版。而“廢柴”則是“熱血男兒”的蛻化版,或者用匈牙利理論家盧卡奇的話來說,可以稱之為熱血男兒的“衰變版”。他們“瘦削落寞、沉默寡言、與世無爭”,是佛系文化的代言者,是“轉了世、悟了空、破了執”的涼性男兒,渾身有著一種“帶發修行的素氣”風范。從熱血男兒到“廢柴”,“意味著男頻小說的主人公從怒的美學(崇高美) 向笑的美學(反諷美) 的退縮”。他們的發生學,是底層青年模仿貴族范兒,由此產生了一種“無產階級多余人”形象的產物。文章生動活潑,把一個新鮮事說明白了,還跟古老的概念系統扯在一起,老少咸宜。
我讀著比較輕松的,自然是他分析文學文本的文章,藝術感覺準確,問題意識清晰,鞭辟入里,但似乎在應酬。他更喜歡分析當下的新問題。發表在《媒介批評》輯刊上的《3D 烏托邦:論CRPG 游戲的“浸沒體驗”》一文,是一篇研究電子游戲的文章。賈想熟練運用麥克盧漢的“冷媒介”“熱媒介”理論,分析“奇幻小說”轉化為“電子游戲”的過程,以及這個過程造成的閱讀者和游戲者的不同體驗,由此分析電子游戲中“浸沒體驗”產生的社會心理根源。賈想認為,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荷蘭先知型學者赫伊哈津所研究的傳統游戲中的“隔離性”的消失。盡管賈想的這篇文章腦洞大開,但他依然注意新問題和新概念與古典知識之間的連續性,使得問題能夠在歷史層面得到梳理和理解。
賈想最引人矚目的地方,就是能夠迅速將一件新鮮的事情,一個陌生的事物,變成知識,變成人類知識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我覺得,這是文學批評最重要的才能,也是文學批評跟文學研究最重要的區別。賈想閱讀量很大,中外文論基礎好,但他并不喜歡掉書袋子,而是善于用理論解決當下的新問題,《為消費布道:解碼短視頻》《新媒體時代的文學》《作為技巧的自然》等文章都是這樣。《從人物到人設:網絡小說的人物觀》一文指出,“人設”,就是一種馬克思所批評的“席勒化”的人物觀,也就是一種“臉譜化”的人物觀,它提高了我們認識人物的速度,但降低了清晰度,這是一種資本的效率思維在文學中的反應。
我喜歡賈想的《論動作中的小說詩學》一文,視野開闊,有縱深感,且新見迭出。他從亞里士多德的“悲劇情節”理論出發,將情節和人的行動轉化為“動作”概念。首先是將“動作”分為個體的“小動作”(比如日常生活) 和群體的“大動作”(比如戰爭),進而尋找這兩類動作跟文學形式史和人類精神史之間的關聯性。其次是將“動作”分為“指向明晰單一”的古典動作和“指向含混多義”的現代動作,由此描述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分野。最后發現,人類的“動作”越來越趨向于封閉性,“動作”成為一個“能指”,并且導致了“所指”的多樣性。寫小說和讀小說,都成了猜謎語。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賈想論述了他的“新現實主義”觀念。我們來看看他的一段文字:文學作為“動作”的藝術,也進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意義之末日”。“一戰”后“迷惘的一代”出現了,“二戰”后“垮掉的一代”出現了,《等待戈多》《局外人》等荒誕派文學出現了。在眾神紛紛離去的人間荒野上,在人類集體歇息等待戈多到來的街頭,只有一個現代型的神——西西弗斯——還在推動巨石,保存著人類動作的尊嚴。以西方文學尤其是歐洲文學主導世界文學發展的局面,幾乎結束了。20 世紀后半葉,歐洲大陸與其他大陸分別出現了幾種為“動作”做心肺復蘇的文學方案:利用民族神話中的動作來拯救(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利用童話的動作來拯救(卡爾維諾);利用偵探小說的動作來拯救(博爾赫斯);干脆放棄傳統小說結構,把小說改造為一種音樂結構的藝術(昆德拉);還有海明威和巴別爾的方案——放棄心理描寫,重新強調動作描寫,從形式上復活動作。這種對于“動作”的多元化的藝術處理,整體上反映出20 世紀人類活動四肢、走出頹廢的思想傾向,同時也昭示著一個非歐洲中心的、全球化的、多中心的文學時代的來臨。
賈想已經畢業,進入一家專業機構從事文學研究。作為長者,我自然要說幾句語重心長的廢話。他的文學研究和批評還剛剛起步,今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希望他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更希望他把我的話忘掉,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不要得意忘形。但賈想是屬于那種人:所有的人得意忘形,他都不會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