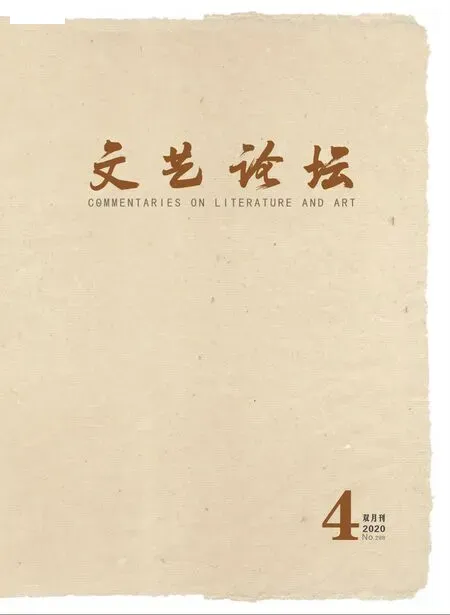失序的現代性:《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城市景觀”
田茵子
“對于我們來說,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認為我寫了一種東西,它就像是在越來越難以把城市當作城市來生活的時候,獻給城市的最后一首愛情詩。”這是卡爾維諾寫在《看不見的城市》前言中的一段話。誠然,城市不僅是人們日夜棲居的建筑之群,也是等待被書寫的美學空間,恰如巴黎之于海明威、京都之于川端康成、上海之于張愛玲、北京之于老舍,每一座城市都有屬于它的聲色與靈魂。在現代社會中,電影,亦是捕捉城市神韻的藝術能手,無數電影都通過鏡頭生產和再生產不同城市的故事和重構城市景觀,為人們認識城市提供了獨特的影像視角。當然,在我國,電影多聚焦于北京、上海、香港和臺北等城市,廣州雖然也貴為一線城市,卻很少受到當代電影的眷顧。而由婁燁所導演的《風中有朵雨做的云》(2019 年)則將攝像機的鏡頭對準了廣州,努力再現廣州那些不為人知的城市故事和城市景觀。《風中有朵雨做的云》所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千禧年前后的我國前沿城市廣州,該城的城建委主任唐奕杰莫名其妙地于繁華都會的“城中村”墜樓身亡,年輕警官楊家棟負責調查此案,并由此牽扯出一系列權色交易、官商勾結的隱秘舊事。這部拍攝于廣州的電影聚焦改革發展的廣州城市,導演婁燁以其擅長的鏡頭通過廢墟、雨霧、夜色、“游蕩者”等一系列曖昧的、邊緣的城市意象,竭力書寫繁華廣州的另一面——一個處于動蕩而感傷的“失序之地”。在這里,本文將引入鮑曼“流動的現代性”的相關理論,對《風中有朵雨做的云》所呈現的令人不安的廣州現代性城市形象展開批判性的解讀。
一、失序之地:雨霧中的廢墟城市
灰藍色的陰冷天空之下,“城中村”的破舊小樓雜亂無章地交錯著,大片的房屋已在拆遷工程中化作廢墟:斷壁殘垣上塵土飛揚,地面上滿是砂礫、磚塊與生活垃圾,圍欄上晾曬著村中居民的衣物,孩子們則在四處暴露的生銹鋼筋間肆意玩耍……此時“進行拆遷動員”的消息忽然傳來,青壯年村民們紛紛放下手頭的活計,穿過破碎的、骯臟的舊日家園,抄起棍棒跑向動員會現場,一場激烈的反抗與械斗仿佛就要拉開序幕——這是《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的開頭場景,一個處于變革的、動蕩的、失序的城市景觀通過電影鏡頭展現出來。
在書寫廣州時,婁燁沒有選取“小蠻腰”(廣州塔)、沙面、白云山等自然或者摩登都市景觀,而是選取了“城中村”這一混合了城市文明和農耕文明的獨特意象,借助“拆遷風波”這一主題,將中國當下社會的城市巨變及其所引發的動蕩視覺化、景觀化和場景化。“城中村”在這里不僅是人們居住的場所,而且變成了容易與摩登化和現代性城市產生激烈沖突的傳統世界和廢墟之地。作為廢墟而出現的廣州城市景觀是一個關乎現代性的隱喻——現代生活的到來必然伴隨著傳統的瓦解。鮑曼認為,最先被“褻瀆”的第一個神明,正是傳統的忠誠,即“束縛人們手腳、阻礙人們前進和約束人們進取心的習俗性的權利和義務”;人們通往理性計算道路的屏障被消除了,“僅僅保留構成人們相互關系和祥和責任基礎的諸多紐帶中的‘ 貨幣關系’(cash-nexus)紐帶”。作為“傳統”之象征的“村莊雜居”被拆毀,作為“現代”之象征的“房地產業”大力進駐,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得以占據支配性地位,利益博弈成了所有問題的最終答案,“現在,社會生活的‘基礎’為其他所有的生活領域創造了一個‘超級結構’(super-structure)……它的唯一功能就是為社會連續和平穩的運行服務”。過去、現在和未來就此斷裂。婁燁將廣州刻畫為一個瞬間分崩離析的“廢墟之城”,書寫了在現代性的猛烈沖擊之下,城市變革所歷經的失序與創痛。
除了對“城中村”的描摹,《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十分注重對“水”這一元素的運用。影片大量納入江水、雨天、云霧等圖景,有意識地將廣州打造為一個潮濕曖昧的“水之城”。具體而言,當女主人公犯下命案,在男主人公的陪同下到荒蕪偏僻的江岸燒毀尸體,冰冷無情的江水在暗處涌動,發熱的火光映出他們汗水淋漓的臉龐;當女主人公在惘然中登上霧氣重重的露臺,其背后的天空烏云密布、電閃雷鳴、暴雨將至。婁燁偏好在電影中使用極端天氣,在南京拍攝《推拿》和《春風沉醉的夜晚》之時,便將雨水作為修辭而引入;在廣州取景的《風中有朵雨做的云》,更是結合了嶺南地區的氣候特征,大量采用了強降雨天氣,“雨水中的詩意城市及電影內外故事所激發出來的憂傷和悲憤,都給予都市青年最好的代入感,他們的都市感傷和‘時代的情緒’在這里可以得到宣泄”。如此,“水”元素的充盈,一方面為影片增添了一絲浪漫化、詩意化的美感,一方面也讓一切具有模糊、曖昧乃至恐怖的特征。幽暗污濁的江水、暴戾乖張的大雨、神秘縹緲的云霧……《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將“水”這一元素,演繹為曖昧的、邊緣的、充滿罪惡氣息的視覺符號,不但為故事人物的茍且之行、齷齪之舉進行氛圍鋪設,亦是與傳統瓦解時期的“眾生相”桴鼓相呼應——當“可為與不可為”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恰當的社會與道德規范出現缺位,人們會陷于茫然無措的社會經驗,由此可能導致各類異端心理與行為的涌現,這正是涂爾干所稱的“失范”。如此便意味著,“所謂明顯屬于個體的‘精神狀態’ (states of mind),實際上應理解為廣泛的社會與文化狀況之產物與反應”。
正是通過“水之城”的變幻莫測、朦朧迷離,《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將現代性問題與人們心中的失范、失常、失措、失序的精神狀態聯結起來,書寫了現代社會變革時期最為普遍的“時代的情緒”——個體精神的彷徨踟躕和迷惘不安。此般苦悶,或許可以用《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段敘述加以揭示:“嗯,我就這樣沿著五馬路一直往前走,沒打算帶什么的,接著突然間,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發生了。每次我要穿過一條街,我的腳才跨下混賬的街沿石,我的心里馬上有一種感覺,好像我永遠到不了街對面。就覺得自己會永遠往下走、走、走,誰也再見不到我了。”憂心忡忡、迷惘不安,不知去往何處,不知到達何方,這就是“現代人”的現代性感受,也即吉登斯所說的“存在性焦慮”,這種“存在性焦慮感”經常就表現為對日常生活世界真實感受的喪失:“對于日常活動和話語的異常瑣細的一面,可能出現的另一方面的問題在于潛伏著無序(chaos)。這種無序不僅僅是無組織化,而且也是對事物和他人的真實感受本身的喪失。”
二、孤寂之地:個體化與城市“游蕩者”
暮色之下,警官楊家棟一人駕車穿街過巷,在幽暗的馬路上疾馳,唯有車頭燈那白慘慘的光線勾勒著他沉郁的臉龐;牽扯到命案中的年輕女孩小諾,靜靜地眺望著遠處閃爍迷離的夜景,暗自神傷;僻靜的老式居民樓之間,狹窄的舊街道之中,嫌疑人在黑暗與陰影的掩映下奔逃流竄,慌亂的腳步聲兀自回響……《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幾乎通篇使用“低影調、冷色調”的組合,大量呈現城市的夜色與陰翳;街道上亦是無甚“人煙”,行人幾乎是點綴般的存在,并沒有慣常的稠密人潮。如此,通過一系列頗為壓抑的鏡頭語言,《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廣州被打造為一個屬于暗夜的寂寥之城,人與人的間離、疏遠得以被細膩地、藝術化地表達出來。“誰此時孤獨,就永遠孤獨”,孤獨成為整座城市的底色,一個惆悵的、荒謬的“無緣社會”被刻畫出來。
把它的成員看作個體,是現代社會的標志之一,且這并非一種“一次性”的界定,而是一個每天都要上演的過程。在固有的模式和框架被打破乃至丟棄時,“人們從舊籠子里被放出來……他們還不能在新秩序里重新找到現成的屬于自己的位置”,由此,“編造模式的重擔和失敗的責任都首先落在了個體的肩上”。“個體化”即意味著每個人的身份(identity)從“承受者”(given)到“責任者”(task)的轉變,“作為承襲而來的社會歸屬的‘家庭出身’(estates),已經為虛構成員資格的‘社會階層’的目標所代替”。正如薩特所言,出生于資本家家庭并不夠,還必須像資本家那樣生活。因此,與家庭出身不同,社會階層必須是加入(joined)進去的,而且“成員必須連續地在一天一天的行為中更新、再確認并得到檢驗”,如此,“現代社會存在于它的持續不斷的‘個體化’(individualizing)的行動中”。這就意味著,現代性的演進為每個人都賦予了一份“必然的孤獨”,將“人”從“家庭出身”這一傳統的母體中剝離出來,使其成為一顆原子、一座孤島、一個獨立單位,若要擺脫這份孤獨,就必須不斷重復操練“扮演某一社會階層”的游戲,才能將孤獨轉化為“隨時都會掉隊”的焦慮。而《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所呈現的寂寥之城,既是對這一現代性所帶來的“孤獨癥候群”的寫照,又隱隱透露出對這種無休止的、無限循環的“角色扮演游戲”的厭倦與失望——導演婁燁刻意規避了繁華的、明媚和人群稠密的白日廣州,轉而描繪陰郁、黑暗和孤寂的夜幕羊城,使得一份充斥著疲憊與庸碌的“都市感傷”滲透于每一幀畫面。
從拆遷現場的滿地廢墟,到破舊民居的陰暗角落;從狹窄逼仄的街巷,到車水馬龍的公路;從靜謐的老式照相館,到粵菜館的豪華包廂,再到喧鬧的夜店……《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的故事主線隨著楊家棟的探案過程而逐漸展開,讓觀眾跟隨著這位年輕警官的目光,在廣州城內奔走、追尋,反復叩問埋藏于這座城市中的秘密,廣州城市的都會風貌得以在婁燁晃動的鏡頭中鋪陳開來。此般敘事視角的選用,自然為影片賦予了許多迂回的、神秘的懸疑效果,有力地牽引著觀眾,品味抽絲剝繭的快意,同時,也在無形中為警官楊家棟這一角色,增添了一份城市“游蕩者”的別樣色彩。“游蕩者”這一概念源起于愛倫坡的小說創作,讀者可借助“游蕩者”在都市中的行走,展開對現代生活的闡釋。受此啟發,波德萊爾指出,“游蕩者”的任務正是闡明現代性,他就是現代生活的代言人。基于此,本雅明將“游蕩者”視為一個辯證意象,“游蕩者”既身處現代性之中,又游離于現代性之外,他既是現代性的產物,又是與現代性保持距離的觀察者,甚至暗暗蘊含著打斷現代性的革命潛能。
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是猶豫遲疑的,是身處于人群之中而拒絕人群的,他有著躊躇的步伐和敏感的目光,如孤星一般對現代性加以洞察與揭示,該“游蕩者”是具有布爾喬亞性格的知識階層,喜歡現代性社會這種稠人廣眾的孤獨感。而《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楊警官則更接近愛倫坡小說中游蕩的“偵探者形象”,他的職業身份使他能夠游走于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城市景觀,但又使他不屬于這個城市的任何一處,而且他自身也陷入城市所設計的迷宮里,隨時都會遇到致命的危險。可以說,楊警官既是命案線索的追擊者,又是游走在城市的邊緣、與周遭保持著距離的觀測者;他身上所浸透的迷惑與孤苦,既是來自于案件本身的復雜兇險,又隱含著一份城市“游蕩者”的質疑——動蕩的、變幻的現代都市生活,到底為你我帶來了什么,到底是幸事還是災禍?游走在巨大的現代性城市這種迷宮或者怪獸里,城市的“游蕩者”楊警官或許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城市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人面獅身的笑容,永遠難以捉摸。”
三、流動的現代性:婁燁的“城市美學”
過去,資本如同勞動力一樣被固定在某一領域,如今,隨著金融、房地產、勞動力市場的放開,“僅僅通過一個只包括公文包、移動電話和筆記本電腦的行李箱,資本就能輕松地流動”。如果說,早期的福特主義模式的社會仍舊是“立法者、規則設計者和監督者的世界”,是一個充斥著“領袖權威”和“導師權威”的世界,當下輕靈的、流動的世界則并未破壞權威,而是使得太多權威同時存在,“以至于任何一個權威來說,都不能長久地掌權,更不用說是成為唯一的權威”。整個社會由此被拋入了一個邊界溶解的、“液化”的境地,鮑曼將此指認為“流動的現代性”(又譯“液體現代性”),舊有的結構、格局、依附和互動的模式傳統都被扔進熔爐,以得到重新的鑄造。而《風中有朵雨做的云》所呈現的影像廣州,正是“流動的現代性”的鮮明寫照——經由廢墟、雨霧、夜色、“游蕩者”等一系列曖昧的、邊緣的意象,社會變革時期的廣州城,被書寫為一個動蕩而感傷的“失序之地”“孤寂之地”,一個傳統瓦解、魚龍混雜、暗流涌動的“灰暗之城”。而這樣的一個“灰暗之城”,就是導演婁燁所追求的現代性的“城市美學”。
作為第六代導演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婁燁,他的作品大多以上海等摩登大都會為故事背景或發生空間,但是無意于贊頌和書寫這些摩登都市絢爛和繁華的外表,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的灰色地帶,書寫當代歷史記憶的側面乃至背面。在《蘇州河》中,婁燁便將鏡頭對準上海的一條著名河流——蘇州河,講述著城市邊緣人的癡纏愛情故事,鏡頭中呈現的不是外灘那些繁華的上海都市景觀,而是污濁不堪的河流、廢舊的樓群、生活窘迫的河岸居民。《蘇州河》的開篇旁白便表明婁燁對于“城市的另一面”的偏好:“我經常一個人帶著攝影機去蘇州河,順流而下,從西向東,穿過上海。這一個世紀以來的所有傳說、故事、記憶,還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積在這里,使它成為一條最臟的河。可是還有許多人在這里,他們靠這條河流生活。許多人在這里度過他們的一生。在河上,你可以看見這些人……看的時間長了,這條河可以讓你看到一切。看到勞動的人們,看到友誼,看到父親和孩子,看到孤獨。我曾看見過一個女孩跳到河里,看到一對年輕戀人的尸體被警察從河里拖起來。”婁燁看到的是城市的邊緣和灰色空間。當談及在南京拍攝的《春風沉醉的夜晚》時,婁燁也多次講述自己對于城市“模糊狀態”的關注,他說道:“我個人認為南京是一個處在中間地帶的城市,是‘灰區’的城市。我的意思是在中國,南京不如北京政治,不如上海商業,不如深圳和香港開放,但它又比重慶溫和,比西部一些城市更進步,它是歷史上的六朝古都,也是郁達夫時代的首都,它與殘酷的中國近代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江南的位置使它具有某種文人氣質。我很喜歡。”《春風沉醉的夜晚》聚焦的便是南京的灰色地帶。婁燁對于精確地、全面地復刻某座城市的社會歷史風貌并沒有十分濃厚的興趣,而是集中表現灰色地帶,并且通過對灰色地帶的書寫建構具有現代性特征的頹廢城市美學景觀。2009 年,由孫周導演的電影《秋喜》亦是以廣州為背景,該電影努力還原1949 年前后的廣州城市面貌——珠江兩岸的販夫走卒、騎樓街上的老字號店鋪、精致富貴的嶺南大宅、細膩繁復的茶樓餐點,這些場景都具有濃厚的粵地風情。然而反觀婁燁鏡頭中的廣州,除了鏡頭中一些人說粵語之外,整個電影是沒有太鮮明的粵地特色的,甚至導演在有意無意地遺漏諸多粵地的日常生活場景,而是用扁平化、模糊化的鏡頭替代立體化和生活化的城市景觀呈現。總體而言,婁燁對于城市影像的捕捉,意在探討一種變革之下、動蕩之中的現代社會生活,以及身居于其中的小人物的飄搖命運,是一種對于“混沌”狀態的書寫與揣摩。
而這種“混沌”又指向何物呢?聯系前文所言,流動的現代性的到來,正是“松開閥門”(releasing the brakes)的效力,“是解除管制、自由化、靈活化、彈性化的結果”,當舊有的、既定的秩序已潰散,系統性的、徹底的革命幻想亦會被擊碎,抵抗者失去了他們可以攻擊的對象。過量涌現的機會使人們時刻承受著選擇的焦慮,并加劇了人與群體的斷裂與疏離。“我是否做出了正確選擇”的猶疑與難以決斷的痛苦時常煩擾每個人,未知的風險和對失敗的恐懼壓在每個人的肩頭上。基于此,“隨著機會的過量,毀滅、碎化和錯位的威脅也增加了”,進行自我身份確認——這一所有人的相同任務,“必須由每一個人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來完成,那么它就把人們的處境割裂開來,并加劇了殘酷無情的競爭,而不是將人們統一起來以產生合作和團結”。
由此,現代社會的人們在心理上陷入了一個更為模糊、疏離、捉摸不定的境地,而導演婁燁在影像中搭建的“邊緣的、灰色的城市”,正是對這一精神狀態的烘托與側寫,旨在觸碰那悲與喜交加、愛與痛交織的情緒邊界;對于現代人內心中那份隱匿的曖昧與感傷的敏感捕捉,正是婁燁作品的獨特藝術魅力之所在。如此情致,或許與著名演員金士杰的體悟相近:“一個深刻的印象:幾個月前旅行到歐洲,不意來到一個小鎮,數十居民的小鎮,春雪正融、環山抱水,那絕美的景色和構圖我不曾見過,只能想象‘桃花源’。整晚開心得不能睡,坐在陽臺呆望著那山和水。到后來我發現,心中除了興奮贊嘆,竟有大量的痛涌現。這個痛與晉太原武陵人相似,與追尋二字相通。我體會到,這個痛是永恒存在的,即使站在天堂門口,身處桃花源的邊界,心中懸念的仍是缺憾的人生,自己竟如此難以自持,甚至更加的不堪了。”
注釋:
①[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著,張密譯:《看不見的城市》,譯林出版社2012 年版,第3 頁。
②③⑧⑨???[英]齊格蒙特·鮑曼著,歐陽景根譯:《流動的現代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27 頁、第28—30 頁、第69—72 頁、第69—71 頁、第111—119 頁、第28—30 頁、第158 頁。
④王小魯:《電影意義的生成——從<地久天長>到<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9 年第5 期。
⑤[美]約翰費斯克著,李彬譯:《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新華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13 頁。
⑥[美]JD 塞林格著,施咸榮譯:《麥田里的守望者》,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年版,第179 頁。
⑦[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 年版,第40 頁。
⑩?上官燕:《游蕩者,城市與現代性:理解本雅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117—118 頁、第206 頁。
?胡晴舫:《未來之城》,《大方》2011 年第2 期。
?王一川:《重建當代歷史記憶的背面——簡析影片<風中有朵雨做的云>》,《當代電影》2019 年第5 期。
?陳炯:《婁燁:不要害怕電影》,《時代周報》2009 年5 月6日。
?賴聲川:《賴聲川劇場(第一輯):暗戀桃花源&紅色的天空》,東方出版社2007 年版,第9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