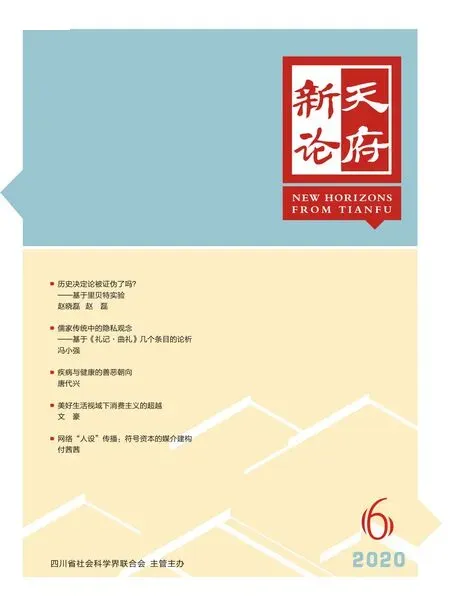疾病與健康的善惡朝向
唐代興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引發(fā)的疫病在世界范圍內(nèi)大流行,從一個(gè)側(cè)面折射出人類的身體能力在技術(shù)化存在的當(dāng)世進(jìn)程中的基本狀況。客觀審視,人的健康或疾病,實(shí)與其身體能力緊密關(guān)聯(lián)。經(jīng)濟(jì)生活水平、物質(zhì)環(huán)境以及醫(yī)療衛(wèi)生條件等方面的優(yōu)化改變?cè)骄薮螅说纳眢w能力越弱化,健康問(wèn)題越突出,疾病更猖獗。面對(duì)這種普遍的生存狀況,討論疾病與健康的善惡?jiǎn)栴},需要對(duì)人、生命、身體以及疾病和健康本身予以重新審視。
一、疾病與健康相對(duì)什么才有意義?
在人們看來(lái),疾病或健康,總是相對(duì)身體而論。這種觀念雖很片面,但卻根深蒂固。
不要忽視你的身體的健康。(畢達(dá)哥拉斯)(1)周輔成:《西方倫理學(xué)名著選輯》(上卷),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6年,第17頁(yè)。
身體之惡,若在我們能力范圍內(nèi),則予以譴責(zé),若在我們能力范圍外,則不予譴責(zé)。(2)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David Ross,revised by Lesley Broww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47.(亞里士多德)
身體獨(dú)自承擔(dān)著昨天的惡。(康德)(3)Immanuel Kant,Anthropology,History,and Education,translated by Mary Gregor, e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89.
在其深居的恐懼中,生命具有把身體主人(body-master)倒置為身體奴隸(body-slave)、把健康倒置為疾病的可能性。(列維納斯)(4)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an Essay on Exteriority,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The Hague/Boston/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79,p.154.
健康是身體在對(duì)抗必然失敗的死亡宿命的抗?fàn)帤v程中所彰顯出的生命活力和道德價(jià)值,疾病則是身體對(duì)抗死亡命運(yùn)歷程中所遭受的大大小小的失敗和道德惡。身體在直面死亡、向死而生的終極命運(yùn)中,健康、疾病的重疊交織、此消彼長(zhǎng)不僅僅是一個(gè)單向的遵循必然規(guī)律的自然過(guò)程。相反,在這一似乎必然失敗的悲壯歷程中,健康頑強(qiáng)地通過(guò)抗?fàn)幖膊◇w現(xiàn)出實(shí)踐理性的自由本質(zhì),彰顯出人類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尊嚴(yán),進(jìn)而把似乎必然失敗的命運(yùn)扭轉(zhuǎn)為浸潤(rùn)著人文關(guān)懷的倫理情結(jié)和自由航程……或許,這也正是“健康、疾病和倫理之間的關(guān)系”配享“身體倫理的基本問(wèn)題”的根據(jù)。